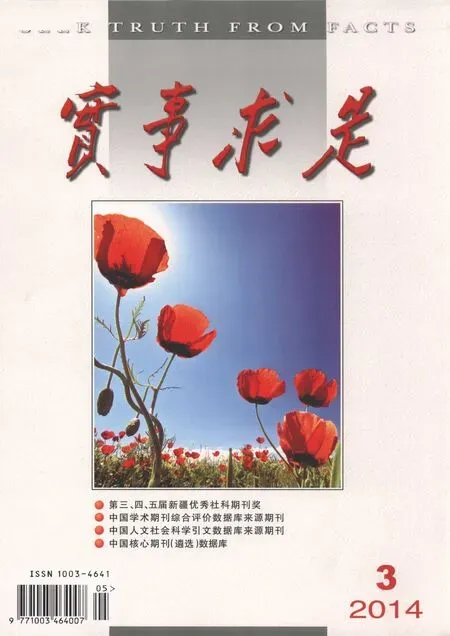论布尔迪厄的习性文化理论
王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100872)
一
一般认为,“文化”一词(Culture)可以被追溯至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灵魂的培养”(Cultur Animi)这一用法。至17世纪,“文化”(Culture)一词开始在欧洲逐渐流行起来并沿用至今。今天通行的“文化”概念,其中心意思表达的是不同历史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工具、符号、习俗和信仰等等,它也指人类思想、行为与人类活动产品的总和。[1](P222)20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关于文化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四种传统,它们各自依托现象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以及批判理论展开。[2](P7)根据伍斯诺的研究 ,[2](PP7~17)其分别以皮特·博格、玛丽·道格拉斯、福柯以及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
然而,祖森认为布尔迪厄的文化概念却不能被归类于以上的任何一种传统,按照他对“文化”概念“三个范畴”的划分标准,[3](P175)布尔迪厄的“文化”概念应属于社会学范畴上的文化。[3](P176)显然,这种划分方式并不能真正概括布尔迪厄“文化”的全部用法。事实上,布尔迪厄的文化概念在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范畴上并没有决然区分,其对“文化”一词的运用也十分模糊,文化在他那里是一个包容性的、多义而松散的指称。比如,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文化”指涉的是一种“信息”;[4](P19)在《区隔》中,“文化”又与审美以及判断力紧密相关;在论述亲属关系时,“文化”关注的则是人们无法直接归因于基因遗传的现象,这近似于人类学范畴上的文化;而当布尔迪厄用习性概念代替文化后,“文化”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哲学属性。但不管其对“文化”的用法如何改变,我们都必须抓住其中不变的核心,以此才能结束其在“文化”运用上的模糊状态,并让那些关于“文化”的各种用法显示出合理性。
二
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以习性概念为基础,而其习性概念的提出则源于他对行动者行为悖论的思考:“行为如何能够被规范却又不是服从规则的产物”。[5](P65)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界围绕着行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构主义者认为,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规则;而存在主义者则相信,人们的行为方式从根本上说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布尔迪厄指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知识模式”(Modes of Knowledge),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一种只能反映经验到的社会现实而无法脱离主观思想的考察方式,因此容易走向文化唯心主义。而客观主义则将视角局限于实践活动所依赖的社会客观条件,从而可能使文化丧失能动性。于是布尔迪厄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方式,它既能够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各自的缺憾,又能够批判性地保留二者积极的一面。
他后来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提出习性概念,使客观主义克服对行为的“机械结构主义”解读,也即将行为规则视为一种机械集合或者例行程式(Performed Programme),从而达到既能说明行为可观察的规律性,又能使主体重拾能动性的效果。他指出,习性是“持久的、可转化的倾向系统,易于使被结构之结构发挥出具有结构能力之结构的作用,即,它可作为产生和组织实践与表述的一些原理,这些实践与表述能够客观地适应它们的结果而无需预设一个有意识的目标或掌握为达目的而需精通的必要手段”。[6](P53)
习性具有一种独特的双重结构,即被结构的结构和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内化与外化的循环系统,该“循环关系的系统,它把结构与实践结合起来,客观的结构倾向于生产结构化的主观倾向,而这种生产结构化行为的主观倾向又反过来倾向于再生产客观的结构。”[7](P203)借助习性双重结构的运作,也即内化与外化,布尔迪厄试图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悄然化解,并使行为与实践融为一体,进而为其独特的文化实践理论奠基。他随后指出:“当‘文化’一词被应用到客观规律系统以及用于描述作为一个内化模型系统的行动者能力时,它会是比习性更好的术语。然而,这个过分被决定的概念带有被误解的危险,而且很难彻底解释其有效性的条件。”[8](P706)
可见,用习性取代文化不但能使文化摆脱被决定的境遇,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而这也是布尔迪厄在元理论上区别于传统文化研究方式的需要。同时,习性概念的提出也旨在摆脱理性中心主义,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实践,它所具有的“实践的实在逻辑”,这种逻辑虽具有自身的逻辑却不把“逻辑”当成自身的准则。[9](P120)而以习性为指导的文化实践理论不但能与两种知识模式下的狭隘文化观分道扬镳,而且还从源头拒斥了文化上的理性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此外,也只有从习性出发去建构文化,其有效性的条件才能在现实性的机制中被更加动态、更具关联性的发掘。
三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将习性发展成为一种作为实践的文化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其界定文化有效性的可能。换言之,文化有效性的条件意味着将习性理论化为文化的各种可能性条件。这些可能性本身又依赖于习性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各种性质。对此福克斯指出:“习性将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意义描绘成不断发展的实践,而与此类似,文化概念也总是处于形塑之中。”[10](P199)可以说,习性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其独特内在双重性的自然展开,它自身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在文化规律性、行动者能力以及文化的再生产等方面为全面考察文化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布尔迪厄看来,只有习性概念还不足以建构起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他需要更多的概念工具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工具箱。于是他求助于马克思,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灵感,最终成功发展出使其享誉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然而在祖森看来,这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相矛盾,布尔迪厄给予正统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批判,却是通过吸收、发展马克思自己的概念及方法论工具来实现的。[3](P371)布鲁贝克认为,或许布尔迪厄明显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应该让我们不再这么想了。[11](P761)而罗宾斯则明确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布尔迪厄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2](P513)
但毫无疑问的是,布尔迪厄在许多重要概念的创造上,诸如阶级、象征权力、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等,均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至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借鉴也远大于对其文化理论的批判,从这一点上说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
第一,习性在文化实践中的分类与区分能力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直接相关。布尔迪厄认为,在被表象的社会世界中,即生活风格的空间中习性承担着两种作用,具备两种能力。首先,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也即产生可分类的实践,此时可将其视为一种实践的分类系统。其次,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它又是可进行分类判断的发生性原则,或者说,它能够对其所分类的实践及其产品鉴赏与区分。而作为能力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是内在化了的客观意义上的文化,它成为解释客体以及文化行为的永久和一般的才能化性情。[13](PP108~109)
从习性承担的两种作用不难看出,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这种实践的分类能力将社会世界中活动的各种行动者相区分,将从事相同实践活动的人汇聚在一个结构化的组织空间中,同时人们也将于其中展开对该类型权力或者资本的争夺活动,而这种结构化的空间就是场域。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心理结构,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在审美偏好上的差异与区隔。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文化偏好构成了一个统一连续的实践系统、一种结构化系统,该系统使那些具有相似品味的人互相聚集,不同品味的人相互区隔。布尔迪厄认为品味既是一种经验,又是表明自己在社会层级中地位的机会。这些品味植根于习性的倾向之中,任何品味的变化实际上均来自于文化和社会阶级场域内人们对统治地位的争夺,谁拥有统治地位谁就享有界定文化和品味高低标准的资格。可见,习性不但塑造了各种不同的场域,同时又是一种区分阶级地位的方法。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阶级不能仅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界定,也应依照阶级习性来界定。[14](P372)
第二,布尔迪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的本质作用就在于使阶级的不平等合法化,或者说,象征系统的作用在于巩固阶级的不平等,并且再生产这种不平等。这种观点成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直接来源。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的一个创新概念。质言之,其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划分理念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在布尔迪厄看来,如果财产、货币能够作为一种资本(经济资本),那么文化商品同样也可以发挥资本的效用。布尔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形态:[15](PP241~258)第一,归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其主要存在于儿童的初级社会化阶段,是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态”,其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倾向。布尔迪厄认为所有的倾向都是被融入到身体图示的形式之中的。[16](P15)第二,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这是一种依附于某些物理介质而存在的文化资本,而对它的拥有可以“客观”地体现在某些专门的客体上面。第三,机构化的文化资本。这种形态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体制。名牌大学的文凭意味着高含金量的工作机会,这促使大量经济资本被投入到文化领域以获取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基础作用已日趋明显。
事实上,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涵义广泛,从学校文凭、专门技艺到学术标准、审美品位再到文化观念都可以成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三种形态的划分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要素,因此后来他又将其称为“信息资本”。[9](P6)但不管称谓如何变化,布尔迪厄都试图表明,无意识的实践因资本分配结构的侵入而变成了建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帮凶。然而问题却在于,通过这种无意识的范畴,特权与权力的不平等何以能够在代际间维系却不招致公众抵制?[17](P190)布尔迪厄指出,这是教育体制的“功劳”,事实上它主导着社会阶层之间权力关系与象征关系的结构再生产。[18](P71)而无意识是一种对历史的遗忘,通过将其自身生成的客观结构转化为习性的准自然本性,“有意识的历史”得以隐匿。华康德指出,在布尔迪厄那里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主客体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本体论契合”,是社会建构的知觉评判原则“习性”与其决定者“社会世界”之间的“相互占有”。[9](P20)布尔迪厄曾用帕斯卡尔的话“世界包容了我,而我也理解着世界”[9](P127)来解释这种状态。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其用于指导自身行为的思维范畴正是社会世界所创造的。当行动者身处其所在的场域,他会感到其充满意义,如同在家中般自在,这是因为习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表达。[9](P128)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尔迪厄把进入场域的习性喻为“历史遭遇自身”。[9](P128)而他有关习性与场域之间是一种“本体论契合”关系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元理论上的解释。
然而,对布尔迪厄而言机构层面的分析似乎更能揭示该问题的本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体制,因为就像家庭环境中获得的习性充当着塑造学校经验的基础一样,相反,被各种各样学校行为转化的习性又成为接下来所有其他经验的根基。[9](P134)布尔迪厄认为,学校教育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象征性暴力。而象征性暴力与象征性资本的拥有相关,它指涉的是合法性的表征对权力实施与维持所起到的特殊作用。[19](P5)或者说,它旨在表明被统治者何以能够将自身的被统治状态视为合法状态(正当性)而欣然接受。[9](P167)通过对教育制度具体作用的分析,他揭示了学校教育行为背后所隐藏的象征性暴力:教育的目标就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其方式、内容以及对象都旨在符合统治阶级的客观利益。表面上教育行为是通过纯教育作用的教育交流形式达成,但事实上其基础仍是阶级间的权力关系。而为了掩盖教育交流关系中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就需要建立教育权威,以使教育行为的双重专断性表现为一种合法强加的权力形式,从而赋予其合法性以掩饰其象征性暴力的本质。可以说,教育就是一种对文化专断性原则长期、持续性的灌输工作。为了保证该原则的再生产,必须将其以习性的形式内化于受教育者,这样即使教育行动终止,作为习性而存在的文化专断原则仍能在实践中长期发挥效用。可见,教育系统的作用就在于生产并再生产制度性的条件。它有两个向度上的功能。内向功能,即强加与灌输符合统治阶层的文化意识与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即将文化专断原则内化于习性,使其持续存在于实践。此后它的外向功能也将发挥作用,当该原则以实践原则的面貌指导实践,那么文化资本的原有分配方式将继续作用从而实现文化再生产,这种文化再生产又最终会导致一种社会再生产。
四
习性与马克思经典概念相结合的理论推进方式,使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获得了从行为到实践再到文化的惊人延展力。
首先,实证分析与哲学反思同时并举。布尔迪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引入由习性主导的文化实践,这必然要求其将社会实质性领域内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与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相结合,这是前人未曾企及的方式,也是布尔迪厄的一大创新。
其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融合。布尔迪厄受到马克思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他将对社会行为与社会感知的主观感受同社会结构的客观理论相融合,并以此阐释“文化实践”。换言之,布尔迪厄反对块片化的文化研究方式,传统形而上学思想导致人们将微观与宏观割裂开来分别研究,而学科内部研究视野的层级限制又加剧了这一现象。因此,他努力整合原有的文化视野,并致力于使其关系化、一元论化。这种方式最明显地体现在从习性到文化的过渡上。一个层面上,习性是以行动者个人为表征的行为方式;另一个层面,它又是布尔迪厄将文化实践化的一种方式。在此意义上说,习性昭示着一种文化实践的群体性积淀。
需要指出的是,布尔迪厄虽然批判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两种知识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倾向性。布尔迪厄曾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9](P11)这已充分表明了他对于结构主义的态度。他仍将结构主义的合理成分视为其整个理论学说的基础,同时也尽量摒除机械结构主义缺乏能动性的一面。在华康德看来,布尔迪厄的全部理论工作甚至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唯物主义人类学。[9](P14)也正是因此,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种超越两种知识模式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1]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Wuthnow,R.&Hunter,J.&Bergesen,A.&Kurzweil,E.Cultural Analysis:The Work of Peter L.Berger,Mary Douglas,Michel Foucault,and Jürgen Habermas[C].Routledge,2010.
[3]Susen,Simon&Turner,Bryan.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Critical Essays[C].Anthem Press,2013.
[4]Bourdieu,P.&Wacquant,L.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5]Bourdieu,P.In Other Words: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6]Bourdieu,P.The Logic of Practice[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7]Bourdieu,P.and Passeron,J.C.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M].London:sage,1977.
[8]Bourdieu,P.Structuralism and theory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In Social Research[J].35(4)1968.
[9]Bourdieu,P.and Wacquant,L.,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0]Fox,R.Lions of the Punjab:Culture in the Making[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11]Brubaker,R.Rethinking Classical Theory: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Theory and Society[J].14(6),1985.
[12]Robbins,Derek.On Bourdieu,Education and Society[M].Oxford:Bardwell Press.2006.
[13]Bourdieu,P.&Darbel,A.&Schnapper,D.,L'amour de l'art:les musées d'art européens et leur public[M],Paris:Editionsde Minuit,1969.
[14]Bourdieu,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5]Borudieu,P,The forms of capital.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ed.J.G.Richardon,Greenwood,1986.
[16]Bourdieu,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17]Swartz,D.Culture and Power: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18]Bourdieu,P.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in Knowledge,Education,and Cultural Change[C].ed.Brown,R.London:Tavistock,1973.
[19]Bourdieu,P.and Passeron,J.C.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M].London:sage,1977.
——现今布尔迪厄研究的焦点与反思*
——皮埃尔·布尔迪厄传媒思想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