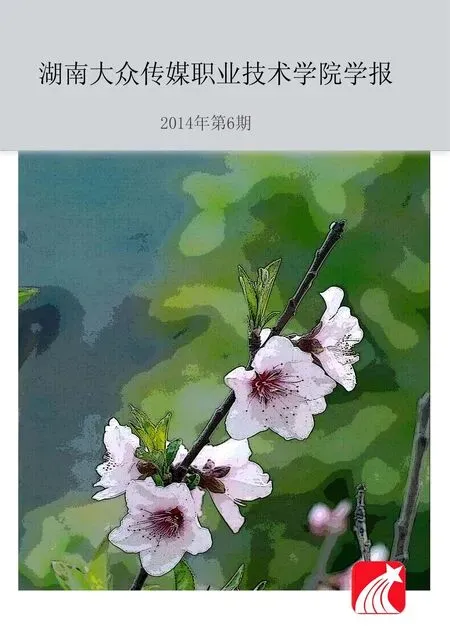电影《湘女萧萧》与小说《萧萧》的对比研究
鲍静旗岳凯华
(1,2.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电影《湘女萧萧》与小说《萧萧》的对比研究
鲍静旗1岳凯华2
(1,2.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在电影《湘女萧萧》中,导演谢飞对小说《萧萧》的改编是一次个性化解读,既解读过去又倾注着当代意识与情感。影片在呈现出小说中对原始人性赞美的同时,将文化批评和道德批判有机结合在一起,用诗化历史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道德关怀去审视人性与封建传统文化习俗,产生了与小说文本不同的语义效果。
电影《湘女萧萧》;小说《萧萧》;改编;对比研究
作为人类生活中最主要的两种叙事语言──电影与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成为众多电影人的共同愿望。影视作品的改编是对文本的再次解读和创作,弗兰西斯哥·卡塞蒂说:“改编是一个元素(情节、主题、人物)在另一个话语场域的重现。”[1]诚然,由于改编者和文本作者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所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诉求,改编的影视作品不可避免地与小说文本产生极大的差异。
在影片《湘女萧萧》中,导演凭借细腻丰富的视听语言,从主观化的叙事角度重新诠释了小说《萧萧》,通过与小说文本的互动,产生了不同的语义效果。从1979年开始,中国内地电影进入观念更新热潮与电影文化重构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以谢飞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在主体的苏醒,感性的张扬与历史的诗化中,将中国电影的道德处境,民族形象和家国梦想整合起来”。[2]导演谢飞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语境,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在主题的表达、表现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合理取舍与创作,使电影和小说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体现出不同创作者不同的价值诉求。
一、主题表达的差异
美国学者尼克·布朗曾指出:“仅仅把影片理解为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称影片为‘社会文本’,换句话说,电影不仅仅是娱乐,也并非与社会进程无关,它正是再现社会进程的变化和反复指引这种变化的一种手段。”[3]实际上一部改编影片的诞生,是文学文本、改编创作者和时代这三股力量合力的结果。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创作者不同偏好的影响下,电影《湘女萧萧》和小说《萧萧》在主题表达的侧重点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20世纪初,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改造人种和国民性”这一核心问题,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作家,侧重于对“吃人”的封建旧制度与封建传统观念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然而,沈从文却另辟蹊径,他以湘西原始性为核心,去塑造新的民族性格。正如苏雪林所说:“他就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4]因此,在小说《萧萧》中,对于湘西那种传统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沈从文不动声色地流露出对湘西人蒙昧的并带有原始状态的人性的欣赏和礼赞,对湘西世界的乡土风俗进行诗意化的审美而非鲁迅那种启蒙性的批判。
由小说《萧萧》改编而成的《湘女萧萧》讲述了20年代湖南湘西的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萧萧成为童养媳的悲剧命运故事,较之沈从文小说中对原始人性的赞美,影片侧重于展现人性的萌动—觉醒—爆发—泯灭的过程,并对蒙昧国民性和封建制度进行批判。影片所表达的主题,明显地偏离了小说的主题诉求,而这种变化与谢飞导演所处的时代意识有着深刻的关联。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第四代电影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十年文革后,谢飞等年轻导演渴望通过电影语言来重塑国民的信仰。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在继续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时,更强调对愚昧、麻木的国民性的改造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电影《湘女萧萧》放弃了小说中对童养媳这一封建制度所采取中立态度,明确地提出了对封建腐朽制度的批判,并有意识地将萧萧的个人悲剧扩展为湘西妇女的群体悲剧。同时,为了增强影片的悲剧性和批判力,影片强化了萧萧人性萌发、扭曲到被扼杀的过程,她从一个向往自我和渴望自由的女孩变成一个顺从愚昧的女人,显示出封建野蛮制度根深蒂固的存在。影片通过展现野蛮的封建民俗制度对群体及个人本性的侵蚀,说明它“吃人”的本质。
二、增补与省略
斯塔姆在《文学和电影》中说到:“文学改编电影是对原小说的一种评论或解读,加上电影自身多渠道多形式的表现手法,电影编导可以戏剧性地对原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多样化处理,并根据需要对角色和情节进行增减或者浓缩处理。”[5]为了在忠实于原著与表达诠释自我意识之间寻求到平衡,导演谢飞在保留沈从文原作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适当的省略与增补。
(一)增补
1.凸显人性的萌发与觉醒
“我造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这是沈从文创作小说《萧萧》的主题。在小说中,萧萧的原始人性被陈腐的封建思想束缚,童养媳这样的婚姻制度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即“性本能”。萧萧和花狗不顾封建礼教,释放出性欲和爱欲的行为,在沈从文看来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自然的人性表现,他欣赏这种人性之美。
导演谢飞在保留小说所营造的“人性美”的意境基础上,适当地进行一些场景的增补,更加深刻、生动地凸显人性之美。导演增补了多个“小解”的情节,如出嫁当天萧萧在花轿里小解,在油菜地小解,后来又在池塘边小解。小说中并没有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增补有其独特用意,显露出萧萧活泼自然的原始本性。小说中,花狗用唱歌的方式向萧萧表达出爱慕。而影片中,除了唱情歌,片中花狗激烈地释放着内心萌发的情欲。他发狂似的在田间嘶喊,当嘶喊还不能压制性冲动,他纵身一跃跳进河水中,他用身体宣泄着强烈的性欲。然而,最能展现人性之美的还是萧萧与花狗不顾一切的性爱。在小说中,作者没有对花狗和萧萧性事进行具体的描写,仅以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终于有一天,萧萧就这样给花狗把心窍子唱开,变成个妇人了。”沈从文往往轻性爱描写,重自然意境的营造。而在影片中,导演全力去表现萧萧和花狗的性爱场景。他们第一次的性爱发生在磨坊中,花狗一把撕开萧萧身上那代表着封建礼教束缚的裹胸布,在哗哗的雷雨声、喧闹的蛙鸣声以及隆隆的磨盘声中,两个被压抑已久的年轻人尽情发泄着内心的渴望。导演营造出与他们内心情绪相似的自然环境,达到情与景的和谐。相比第一次性爱的场景,导演将他们第二次性爱表现得更加唯美,微风吹过广袤无垠的甘蔗地,花狗与萧萧如同自然之子,在黄土之上与苍穹之下表达着对彼此的爱。导演发掘了小说中值得表现的情节,进行了适当的增补,营造出小说中的审美意境,更增强了对人性之美的表现力。
2.强化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国民性反思
任何一部影片都是创作者内在意识的表达,为了集中、紧凑地表达出导演的创作意图,在改编中有必要对文本的情节或角色进行增补或省略。在电影《湘女萧萧》中,除了凸显对人性美的表现,还强化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和国民性反思。影片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把沈从文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增补到影片中来,集中体现出蒙昧、麻木的国民性格以及对泯灭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控诉。
其中,巧秀娘被沉潭的片段是导演价值意识诉求的有力体现。“沉潭”这一古老的湘西风俗是从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巧秀和东生》中嫁接而来。影片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沉潭的场景:极富仪式感的画面,神秘而鬼魅的音乐,披头散发赤裸全身的巧秀娘,黑夜中村民打着的火把如同地狱中漂浮着的鬼火,村民麻木而呆滞的表情,巧秀的哭喊和巧秀娘绝望的哭泣。权威族长“沉潭”的一声令下,巧秀娘被抛入湖中。残忍而冷酷的沉潭带给观众强烈的内心震撼,批判了泯灭人性的封建制度。然而,讽刺的是,怀孕的萧萧却因婆家人怕闹鬼的封建迷信思想而免受沉潭的惩罚。萧萧的命运被冥冥之中的鬼神和残酷的封建制度所掌控,她的命运充满了不可控性和未知性。这些增补内容进一步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性,即人被封建制度和文化思想所奴役,失去了对自我生命的掌控力,而处在被奴役状态之下的人,却浑然不知自己的危险。
在小说的基础上,影片还增加了一些极富意味的对话,更加凸显人们的愚昧无知。当花狗说到“女学生都是喜欢谁就和谁好”时,一旁的姨婆直呼“造孽啊”,婆婆很不解地说“难道她们就不管祖宗的礼法啊”。当萧萧的胸脯日渐丰满时,婆婆一边给萧萧缠上厚厚的裹胸布,一边说:“这么大了,也不知道紧点,胸部挺出来多难看啊。”这些对话从侧面反映出萧萧的婆家人早已被封建礼教所蒙蔽,变成了麻木无知的国民。在她们眼中,追求自由的新式学生是时代的另类,如同怪物一般;而对于封建礼教中一些缠足、裹胸的陋习,她们却极力维护,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二)省略
电影是省略的艺术,为了避免叙事时间过长而引起观众厌烦,导演需要对原文本进行改编或省略。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省略可以用来维持故事的戏剧性,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破坏格调的统一,不露声色地越过同故事的总氛围不相称的事件。”[6]影片《湘女萧萧》针对电影艺术的特点,省略了小说中一些关于时间的说明。影片借用自然景物和水磨的运动空镜头来表现时空的转换。相比小说,影片这种处理方式更具现实可感性和视听吸引力。尽管电影与小说是两种相近的艺术,却有各自的优越性。在表达人物内心情绪和想法上,小说更能发挥自如,略胜一筹。在小说中,沈从文对萧萧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详细的叙事。在全家摆完关于女学生的龙门阵后,萧萧内心住进了一个“女学生”。她特别渴望自己也成为女学生,经常梦见自己也坐着女学生坐的那种“会走路的匣子”。相比小说,电影善于再现或表现事件的表象,具有直观形象性。因此,在影片中导演选择不再旁生枝节,取长补短,弱化了萧萧女学生的梦的表现,仅通过摆龙门阵的场景,直观生动地展现出人们麻木、蒙昧的内心世界。
三、表现方式的对比
(一)叙事者态度的差异
在小说《萧萧》中,沈从文采用客观化的表达方式,而影片《湘女萧萧》的创作者则改变了小说不露声色、冷静客观的情感表达,加入了更多主观化批判,极具个人风格。
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曾说:“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他的自然里露面一样。”[7]沈从文在作品中始终践行这种客观化的叙事方法。在他看来,客观化叙事意味着在叙事中不加个人议论,以冷静、平实、不动声色的态度,展示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反对热情的自炫、感情的无从节制,以及讽刺与诙谐。小说平静、从容、克制地表现着萧萧的生命历程,细腻而平实地展现出湘西世界的人性之美。小说在描叙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时,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热情似火,始终保持克制与从容。在小说结尾处,尽管牛儿的新娘将重复萧萧的悲剧命运,但沈从文也没有直接表达对封建童养媳制度和人物命运的态度,只是平淡而极富韵味地写道:“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这看似不经意的含蓄之笔饱含深意。
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二度创作的过程。影片《湘女萧萧》改变了小说客观化的叙事风格,转为主观化叙事。导演对原小说进行适当取舍,开头与结尾前后呼应,深化对封建童养媳制度的主观化批判,展现出悲剧命运的轮回。影片的开头是萧萧坐着花轿嫁人,年幼的丈夫哭喊着不肯去拜堂的场景。而片末又一次重复了这样的场景,场景一样但人变了,这次坐花轿的姑娘是另一个小女孩,哭喊着不肯拜堂的是萧萧的儿子牛儿,这个小女孩重复着萧萧的命运,热闹的唢呐声和鞭炮声寓示着她悲剧命运的开始。此外,导演还在片中寄托了希望。影片重新设置了小丈夫这个角色,他长大成为了一名新式学生,他的离开是对封建礼教制度的一种反叛。这个角色让观众看到了灰色封建制度下的一丝光亮。影片借助小丈夫的勇敢选择,打破了小说中那种看似平静的和谐局面,更具有社会批判意味。
(二)蒙太奇的运用
电影与小说作为两种相似的叙事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叙事表达方式。小说通过文字,通过读者的二度创作,去构建文本中的世界。而电影借助的是镜头语言,依靠蒙太奇进行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从而实现影片意义的表达。电影《湘女萧萧》与小说《萧萧》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也体现在蒙太奇的运用上。
对沈从文而言,象征与隐喻是进行深层客观化表达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小说中,最明显的是两处象征隐喻。一是当花狗让萧萧失身成为妇人后,刚好小丈夫的手被毛毛虫蛰了,萧萧便把小丈夫的手放进嘴里吸吮,这两个毫不相关的片段放在一起,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毛毛虫象征了一种外来物体,它通过“蛰”入侵了小丈夫,这看似不起眼的事件象征着花狗对萧萧的性入侵,而萧萧的有力吸吮其实暗示她希望将体内的“污秽”吸出来。二是当萧萧怀孕后,花狗跑了,这时她对已经结茧成碟的毛毛虫更加讨厌,于是她看到就想去踩。这样的行为也隐喻了萧萧内心那种怨恨的情绪。作者用这种含蓄内敛的细节进行间接暗示,实现了客观化的叙事目标。
在影片《湘女萧萧》中,导演更加丰富了小说中的象征化表现手段,运用大量的隐喻蒙太奇直观表达主观化的创作意图。除了小说中毛毛虫的隐喻外,影片还多处运用隐喻画面。大水车正是一个象征蒙太奇,它象征着时间的更替,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更暗示着萧萧生命阶段的变换。大量的隐喻和象征蒙太奇,表达出时间对生命的销蚀。而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磨盘,更是一个明显的象征。萧萧在磨坊被花狗性侵时,萧萧怀孕后在磨坊磨米时,都出现了磨盘转动的特写镜头,而它每次都出现在萧萧命运的转折点。磨盘象征着命运的轮回,预示着萧萧的悲剧命运无法摆脱残酷的宿命轮回。
尼尔·辛亚德(Neil Sin yard)在《电影改编:银幕改编艺术》中曾经指出:“电影改编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字转化成画面,它应该像篇最佳的评论文章,对原著的理解发表新的观点。”[8]最好的改编就是“不要绝对忠实原著”。[9]相比小说中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人性的诗意化审美,导演谢飞采用冷峻、主观的视角,深入湘西人的内心世界,将萧萧等女性的悲剧根源指向了野蛮与残酷的封建习俗,呈现出浓烈的内省和批判气质。影片通过不同的主题侧重策略和差异化的表达手段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加深了对小说文本的探索与阐释,改编电影与小说文本之间实现了有效互动,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责任编辑 陶新艳)
[1] 叶宁.紧贴时代的“重现”——从《地心游记》看科幻小说的电影改编[J].电影评介,2009(21): 47-48.
[2] 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2-431.
[3] 彭海军.历史积淀与时代超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改编透视[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 (1):42-43.
[4]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6-207.
[5] 张冲.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31-132.
[6] 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995:53-54.
[7]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5-206.
[8] 朱建新.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电影改编——论电影改编对亨利·詹姆斯小说的阐释[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8(1):326-327.
[9] 陈犀禾.电影改编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370-372.
J90-05
A
1671-5454(2014)06-0019-04
2014-10-27
鲍静旗(1990-),女,湖南怀化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戏剧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创作与批评。岳凯华(1967-),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湖南文学的电影改编研究”(编号:13YBA427)、“现代中国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编号:12YBB18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