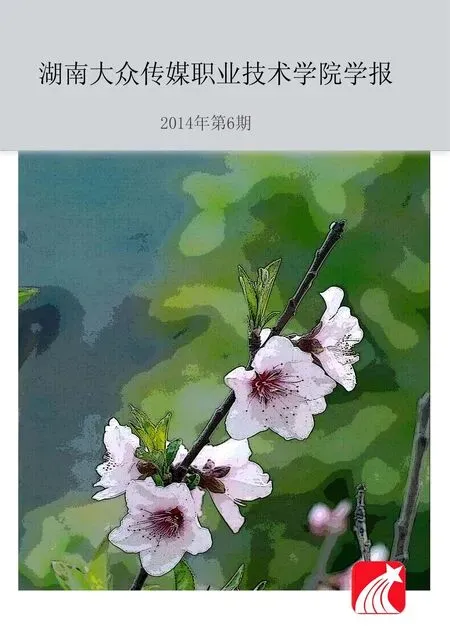从改编角度论电影的责任
徐燕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影视艺术·
从改编角度论电影的责任
徐燕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与原著相比,一些电影叙述内容单薄无力,表达暧昧,视听觉影像媚俗化,虽然暂时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对电影的长期发展毫无好处。电影制作方与观众方不是对立关系,电影的艺术审美与娱乐性也不是对立关系,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具有双向建构的特性。电影应当将特色鲜明的影像运用、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个性塑造、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挖掘展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健全的充满生命的影像语汇。
电影;改编;责任;艺术性
一
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以票房的多少来衡量电影的价值、导演的能力成为毋庸置疑的指标,再来讨论电影的责任似乎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一个具有高票房的电影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影片的市场价值,但是未必真正价有所值:导演和明星的影响力、电影的宣传造势、影院的档期安排等等,都是影响电影票房的重要因素。一些滥俗的影片一再冲刷电影的票房纪录,在“嘘”声一片中赚得盆满钵满,这种现象不断成为电影市场的热议话题却屡屡上演。票房不等于电影的自身价值是一个毋需讨论的话题。
问题是:这种现象背后昭示了什么?对电影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电影除了挣得票房之外还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要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放在一篇文章中来讨论未免过于泛泛,我们且以近些年通过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与其原著作比较,用改编前后的优劣对比来探讨前面所说的问题。
电影的商业性、娱乐性属性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被我国电影界确认,与整个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社会大潮相得益彰。作为一个导演,以票房盈利的形式回馈投资方、娱乐观众是导演能力的体现,也是导演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市场化背景的推波助澜下,这两个属性被无限放大了,另外同样重要的属性——电影的艺术性却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下来,虽然屡屡被人提起,但真正的实施者并不多。在滚滚的市场浪潮下奢谈艺术实在太过冒险,一些电影制作者的碰壁用事实论证了这个问题,而许多影响甚大的国内电影制作人更愿意用“电影产业”这个概念来对当下电影侃侃而谈,尽量避免谈论“电影艺术”。然而,假如电影抛弃了对艺术的追求,仅仅作为一个牟利性的商品而存在着,那么它特有的审美意蕴将会逐渐消弭,电影能走多远就不得而知了。
黑格尔认为,作为艺术,应当是一种自由的呈现。“只有靠它的这种自由性,美的艺术才成为真正的艺术,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1]当一门艺术在其思想表达、题材选择、内容呈现、形式运用等方面表现出百花齐放、千姿百态的伸展繁茂的状态,才能够得到良性与全面的发展,而为了某种目的对艺术进行限定,有选择地规定其方向,局部的催生将导致艺术整体的畸形成长。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电影的思想艺术价值被狭隘化、指向化,其政治工具指向被无限放大,在看电影的同时能否受到思想政治教育,是评价电影成功与否十分重要的指标。鲁迅的小说《祝福》,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人性异化关系的复杂主题,而据此改编的电影简单地将主人公的悲剧归结为阶级压迫使然,电影中祥林嫂被鲁四老爷家拒绝碰祭祀祖宗的“福礼”后,愤怒地去砍自己花了一年工钱捐献的门槛替身,表达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性,这个段落在很长时间里被当作改编的经典屡加赞扬。如今回头再看,电影人物脸谱化、类型化的改编远远逊于鲁迅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表现力高下立现。时至今日,某些主旋律影片的拍摄目标仍然与此相同,以至于观众形成一种定势,一想到看这类电影就感到是要去接受教育,未看而在心中产生抵触情绪,其后遗症明显可见。随着经济市场化的确立,电影的经济化指标被无限放大,重蹈了当年政治化指标的覆辙,单一功利性的经济性目标与单一功利性的政治目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非此即彼的电影制作倾向使得电影产业看似红火,实则底气不足、彷徨无依。
从根本上看,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并行不悖,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体,电影必须依附其受众方即观众群体的支撑才能存在,因此电影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具备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电影产业化的大目标并无问题。问题是,在此大目标下,为了实现电影经济价值的最大化,一些电影制作者失去底线意识,惟票房是图,电影叙述内容单薄无力、是非不分、表达暧昧,视听觉影像极其媚俗化,运用各种手段撮哄观众入场,只看眼前,不论以后,虽然暂时性地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对于电影的长期发展毫无好处。从早期“中国大片”惊人的高票房到后来一大批“中国大片”票房遭遇惨败,从某些烂片在不择手段的宣传造势下赚得盆满钵满而观众随后大呼上当,电影产业如若不改变惟眼前利益是图的方向,总是本着“赚一把就跑”的心态来炮制电影,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大方向上看,电影与其被改编的小说、戏剧等原著在本质是不同的两种东西,二者没有太大的关系。电影改编的目标是电影团队为观众摄制更加赏心悦目的影片而进行的活动,其根本指向在于摄制后的电影成品,不需要负载太多的对原著作品是否承继得当的责任。换而言之,电影与原著是两种相互独立的形态,电影不是原著的附属物,它没有替原著文本的文学价值忠实宣传的义务。李安说:“我觉得对一个小说喜爱,不一定要把它拍成电影,就读它好了。”[2]“把一部小说改编成一部影片时,小说只是素材,而影片是一部新的创作,是毁是誉,都与小说作者毫无干系。”[3]即便如此,一部电影之所以选择某个对象进行改编拍摄,必然由于原著中含有一定的适合电影表达的质素,原著的某个故事片段、思想理念、特定的人物诠释、故事的叙述策略等内容或形式都可能是触发电影改编的动机。然而,由于电影与原作一脉相承的关系,完全将原作搁置来解读电影是不现实的,人们必然会不由自主地将电影与其原著进行比较,判断孰优孰劣。法国导演阿伦·雷乃认为,文学小说带给了电影一种既已存在的负荷,这对于电影制作过程来说是沉重的压力。原作与改编电影具有不可分割的互文关系,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解读,才能更清楚地衡量出电影自身的真正价值。
二
当前的一些电影改编,内容单薄无力,逻辑混乱,缺乏充盈的内涵和艺术表现力,视听语言的炫目震撼与内容的苍白乏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观众的审美诉求只能停留在影像语言的表层上止步不前。蒲松龄的短篇小说《画壁》讲述了赶考的秀才朱孝廉偶与一庙宇中壁画里的少女产生情感的故事,通过人物在壁画幻境中的奇特遭遇,张扬了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同时又表达了“幻由人生”、“境由心生”的玄奥理念,故事虽短,但情节曲折有致,意蕴绵延丰厚。改编后的同名电影,将壁画里的幻境打造得唯美唯幻,然而,在这个设置得如此充满想象力的视觉空间里,讲述的故事杂乱不清,画境中一干少女被遭遇过感情挫折的极其自恋的姑姑无情压制,姑姑在疯狂地将春情萌动的少女们毁灭后,得知当年的爱人并未背叛自己,瞬间又恢复了画壁的生命力,与那位爱人双双离开。编导将人性的自由、人生终极追问的探讨降级为混乱不清的两性吸引与诱惑的弱智故事,以至于许多观众在看到电影结尾时啼笑皆非,将之概括为“一个男人拯救了女人世界的故事”。炫目张扬的动作设计、华丽的场景设置、艳丽的具有高饱和度的画面色彩等外在的观感刺激,包裹着苍白无力、乏善可陈的故事,犹如一盘精工雕琢的萝卜花,只是一场忘却主要目标的视觉盛宴,看似绚烂多姿却无滋无味。
相当一部分电影改编有意绕过原著对社会层面的演绎与挖掘,绕过对人性的拷问与表达,将严肃的人生社会问题当作一个引人耳目的噱头,以媚俗的娱乐化方式消解社会责任,刻意消弭了社会、人性的担当,将社会历史背景一概抹煞,只选择看似精彩纷呈实则不关痛痒的戏剧冲突、貌似俏皮深刻实则泛泛而谈的对白,表现出实实在在的缺乏担当的犬儒主义。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是一部刻画了当代工人典型性的生存窘境,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性的作品,据此改编的电影《幸福时光》却是一部漂浮在故事表层的无关痛痒、不伦不类的小温情影片。除开撷取了一点原作中蕴含的小人物在守望相助、患难相恤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并将之无限放大外,便是抓住以报废的公交车为想象空间营造的具有陌生化效果的故事氛围。一个可以从多层面进行横切剖析和纵深挖掘的时代小说,被刻意屏蔽了其深刻性与其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实批判性,被处理成轻飘飘的与社会现实和个人体验毫无关系的滥俗影片。难怪莫言幽默地调侃:“这部影片与我原来的作品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只剩破旧的公共汽车是原貌,结果开场五分钟后被吊车吊走了。”[4]美国科恩兄弟导演的电影《血迷宫》,叙述了由一个出轨妻子引起的连环谋杀案,在一系列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悲剧背后,探讨了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血迷宫》改编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摒弃了对人性的挖掘与探究,除了浮光掠影式地影射了当下的某些社会现象外,以夸张的小品式的戏谑调侃讲述了一个贪财与出轨的故事。由此不禁让人怀念张艺谋当年改编拍摄的《红高粱》、《活着》、《秋菊打官司》等那些具有震撼性的生命爆发力与润物细无声地折射社会文化的充满个性化的电影。
思想表达暧昧,甚至是非不分,是当下电影改编的又一问题。一些电影哗众取宠,刻意设置复杂的人物情感关系,以人血脉贲张的暴力镜头与情色化镜头来吸引观众,以电影娱乐化的名义规避艺术的责任。“戏剧的作用是集体排出脓疮”,[5]148电影编导在溃烂不堪的脓疮表面涂上“爱情”这层厚厚的粉底,看似光洁美好,实则藏污纳垢,原著中入木三分的象征意义在电影改编中杳无踪影。“爱”成了一块遮羞布,遮蔽了一切丑陋暧昧,救赎了所有的自私、伤害、残忍,仿佛所有庸俗暧昧的东西只要披上了“爱”的外衣,它就变得冰清玉洁、高雅无比,不管情节如何杂乱不清、瞎编乱凑、不知所云,只要加上所谓的“爱”进行总结性发言,一切都显得那么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每当一部文学作品的新本文、新评论或新阐释(包括电影改编本)问世时,它既是这部作品的历史的一次革新,同时也是这部作品在一个特定的当代文化瞬间以新的形式的再现。”[6]电影改编表现出来的缺乏担当的犬儒主义与单一化的经济利益追求,折射了当前社会文化发展瓶颈的一个突出现象。
三
从原著与电影改编的对比来看,当下相当一部分电影制作者有意规避反思社会现实、探索人性本质、展现人文关怀的艺术责任,撷取男女关系、不伤大雅的小奸小坏大做文章,三观暧昧不明,以隔靴搔痒式的小温情、生编硬凑的笑点和气势逼人的感官刺激场面拼命讨好娱乐观众,一副“我就是俗人我不装”的理直气壮的嘴脸。当电影市场都被如此浮华的场面覆盖,熙来熙往的热闹镜像之下掩藏着先天不足、毫无底气的电影制作人的身影。观众被这些所谓的大制作、小清新、真庸俗的影片成年累月地轰炸,潜移默化被培养形成了定式审美观,然后电影人又抱怨观众欣赏水平低下,将电影艺术水平停滞不前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观众。这是否太过矫情?电影制作方与观众方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电影的艺术审美与娱乐性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具有双向建构的特性。如同建筑师的设计,如果砖瓦一层一层地用心向上垒,那么就可能是高楼大厦;如果一点一点地向下堆砌,就可能是藏污纳垢的下水道。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作为电影工作者,首先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推脱迁就。
观众的审美能力并非如同一些电影制作者和理论批评家想当然的那样,认为观众的鉴赏能力平庸,将具有多极类型欣赏角度的观众简单化、一体化,艺术的责任被某些电影制造者以故弄玄虚、不接地气、观众欣赏不了为理由而理直气壮地抛弃,艺术的降格、深度的弱化仿佛是一个理所当然、无可奈何的趋势使然。对于电影及其观众看法的极端化,导致了电影大雅大俗绝对化。一些电影制作者将观众的欣赏水平想当然地庸俗化,以为感官刺激足够观众就买账,虽然能够凭借大导演、大明星在观众一边倒的嘘声中赚得盆满钵满,但对于电影的长足发展而言毫无益处。
成功的电影改编,“不仅要赋予人物行为轮廓以一种故事厚度,而且还要提供一种在其自身‘文学性’上完全自主的对话”。[7]丰满的故事设置、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与充满个性化的影像表达,是电影改编抗衡于原著的基础。同样改编自马识途的《盗官记》,忠实于原著的《响马县长》(1886)几乎无人知道,而《让子弹飞》将故事与理念以充满想象力的表现主义形式与观众直接交流,深刻的人性挖掘与社会批判隐藏在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中,出色的影像表现技巧与电影叙事策略,让影片具有超越小说的独特魅力。《集结号》、《天下无贼》的原著都是篇幅极短的小说,电影编导撷取了其中别具匠心的主旨理念和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将之扩展为故事丰富感人、人物性格鲜明、戏剧冲突激烈的艺术性与娱乐性兼具的电影。英国电影导演乔·怀特改编的《安娜·卡列尼娜》,电影的场景转换借鉴了舞台剧场景的转换形式,独具匠心的形式创新形成了陌生化的观影效果,具有强烈的影像视觉冲击力。无论何种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永远是其长足发展的有力支撑。
电影改编应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改编者应当对时代、社会、人性等具有明确的审美理念,在改编过程中融入富于审美个性的精神内涵。李安说,他之所以选择某个小说进行改编,不一定是因为喜欢那个小说,“它能够让我想拍成电影,是因为它在视觉上面、影像上面让我想表达什么,我可以借这个题材表达我想要的东西。”[2]《阿甘正传》对温斯顿·格鲁姆的同名黑色幽默小说的大力度改编,通过阿甘这个智障者的生平演绎,以精彩感人的故事诠释了美国梦的实现,温情励志的电影改编迥异于原著的冷酷批判性;科马克·麦卡锡的长篇小说《老无所依》探讨了人生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猎人莫斯因为瞬间的贪念拿了不该拿的钱,自己及其身边的一个个人都因此丢掉了性命,科恩兄弟却运用极其血腥残忍的影像叙述,不断发出“这个时代怎么会这样”的问询,探讨了当代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极其严肃深奥的人类终极信仰课题;库布里克对同名小说《发条橙》的改编,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视觉影像表达了一个连龌龊思想都不能产生的绝对纯净的人能否生存于现实世界的疑问。
电影产业化应当重视观众的需求,但不应当是绝对屈就其喜恶,一味地迎合、揣摩观众的口味。观众的需求与电影艺术的提高不是相悖矛盾、此消彼长的存在,从辩证角度来看,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协调产业利益驱动与艺术审美追求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为了取悦于臆想中的观众而胡编乱凑一些底气不足、苍白无力的故事,而是需要充满改编底气的生机勃勃的具有独特电影创造力的作品。电影改编应当将特色鲜明的影像运用、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个性塑造、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挖掘展现有机融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健全的充满生命的影像叙事语汇。“一次文学改编实际上是要求把制片厂的经济资本、把小说的文化资本转变成一部成功的影片的经济资本。改编过程远远超出把材料简单地转入另一种媒介,而是包括满足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要求的复杂协调过程,诸如如何既忠实于原著又适应电影艺术的实践,同时又满足观众的期待。”[5]146娱乐性与艺术责任、社会责任不是你存我亡的仇人关系,它们只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其两极是纯娱乐片与纯艺术片,而电影人完全可以在娱乐与审美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二者兼顾。
(责任编辑 陶新艳)
[1]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11.
[2] 张艺谋纽约对话李安[EB/OL].[2014-09-06].http://tv.sohu.com/20140329/n397416063.shtml.
[3] 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226.
[4] 肖扬.莫言:我肯定让张艺谋骑虎难下了[N].北京青年报,2006-07-22(C4).
[5] 杰·斯康斯.叙事的权威性与社会的叙事性——对勃朗特《简·爱》的电影改编[J].毛菊英,桑重,译.世界电影,1989(6).
[6] 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25.
[7] 莫尼克·卡尔科-马赛尔,让娜-玛丽·克莱尔.电影与文学改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26.
J90
A
1671-5454(2014)06-0015-05
2014-10-22
徐燕(1970-),女,黑龙江建三江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