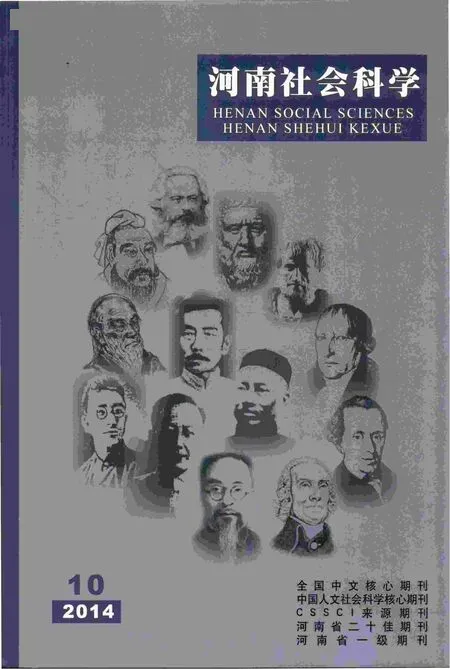从杜甫研究看现代唐诗研究的三种范式
杜学霞
(郑州师范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在唐诗研究的现代历史上,有三位学者必须提及,他们分别是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这三位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清华学人,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都推崇杜甫,都把杜甫当成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并都留下了关于杜甫研究的重要成果。将三位学者关于杜甫的研究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杜甫的关注点、评价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研究方法的差别,反映了唐诗研究在现代学术中三种不同范式的差异。
下面,我们将分析他们对杜甫的研究和论述,以期考察唐诗研究的三种现代范式。
一、陈寅恪的杜甫研究
作为历史学大师,陈寅恪是由历史研究切入文学研究领域的。陈先生有三篇关于杜甫研究的论文,它们是《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此外,他的《柳如是别传》中涉及杜诗43首,《元白诗笺证稿》中涉及杜诗5首。在《韦庄〈秦妇吟〉笺释》《论再生缘》等文中,他对杜甫的诗也有论及。在这些著作中,陈先生对杜甫诗的引用和笺释达到信手拈来、随笔而出的程度,足见先生对杜诗的熟悉程度。
陈先生推崇杜甫,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他对杜甫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对杜诗的“诗史”的论述和他采用的诗史互证范式上。所谓杜甫的“诗史”说,是认为杜甫的一些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因而具有史料的价值。杜诗“诗史”的观点,并非陈先生所独创,早在晚唐,孟棨的《本事诗》就提出了杜诗的“诗史”说。在宋代千家注杜的背景下,从“诗史”角度阐发杜诗的大有人在。到了清代,钱谦益把杜诗的“诗史”说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虽然也有人批评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事事征实,不免臆测”,但不可否认,他对杜诗的解释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实的关系之上的。陈寅恪研究杜甫,考察杜诗的“诗史”性质,明显受到了钱氏的影响,并将诗史互证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所谓的诗史互证是指:或者从诗歌中考证一段史实,或者依据一段史实来对诗歌做出相应的解释。例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他依据《旧唐书》中关于安禄山、史思明传中所谓的杂种胡以及《新唐书·回鹘传》中所言的九姓胡,指出杜甫所谓的“杂种胡”就是“九姓胡”,其根据为杜甫与安、史为同时代人,杜甫以杂种胡看安、史,实际上中亚九姓胡被称为杂种胡,证据可信。这是通过杜甫的诗歌考证出两《唐书》中的差异。又如在《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他通过杜诗中的句子“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结合唐代史料考证出,朔方健儿并不是指郭子仪、李光弼统帅的朔方军,而是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同罗部落。该部落勇健善斗,为安禄山厚禄招降,在安禄山攻下长安后,该部落与安禄山为伍,助纣为虐。再如,他通过杜甫的诗歌,考证唐代典籍、制度、宫廷结构等。如杜甫《哀江头》中有诗句“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他就根据唐代长安都城的建筑情况,指出“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殊失少陵虽欲归家,而犹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1]。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来研究杜甫的诗歌中“史”的价值,在他的眼里,杜甫的诗不仅是个人生命年谱与生活日记,而且是唐代诗体年谱与历史实录,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安史之乱、藩镇胡化,以及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了解到唐代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人事制度和财政情况等。
诗史互证也非陈寅恪的发明,而是继承了孟子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优良传统,继承了“六经皆史”的传统,还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研究方法。陈先生的最大贡献在于把这种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并成为一种学术范式。特别是陈先生对诗史互证的唐诗研究范式是有理论上的自觉意识的,因为他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明确提出“思别求一新解”,这一新解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唐诗,特别是考察杜甫诗歌对唐代历史的反映。
诗史互证的研究范式对史学是有意义的。这种研究范式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其史学意义在于,在某些史料缺乏的情况下,经过严格考证的诗歌可以补充某个阶段的历史。诗史互证范式对文学研究而言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我国历来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加之我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关注现实、借助诗歌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中国诗歌的一种优良传统。对于杜甫这样有着强烈现实精神的诗人来说,通过诗歌创作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社会发展变化,反映自己在重大社会变化时的心理感受,是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所以,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杜甫的诗歌,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
二、闻一多的杜甫研究
闻一多从事唐诗研究的时间是1928~1940年。1933年,他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中曾提及他的古典文学研究计划共八项,其中有六项是与唐诗有关的,这六项是《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外编》《全唐诗小传补订》《全唐诗人生卒年考》《杜诗新注》《杜甫传记》。由于先生的英年早逝,他的唐诗研究计划没能如愿完成,仅留下来《唐诗大系》《唐诗杂论》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在他列入的唐诗研究计划中,关于杜甫的就有两项,足见杜甫在他唐诗研究中的位置。闻一多的早逝,给唐诗研究留下了很大遗憾,如果不是这样,按照他原先的计划,他肯定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唐诗研究成果。而他当时的研究,已经具有了范式的意义和价值。从他关于杜甫的研究成果《杜甫》《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等著作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的独特的唐诗研究范式。
关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范式,已经有不少学者研究,只是这些研究成果的观点有很大出入。董乃斌把闻一多称为唐诗研究中鉴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鉴赏学派研究唐诗,主要立足于自身读诗的美感体验,着眼于对唐诗的美学分析,发掘唐诗的美学意义,并努力从中抽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认识,同时也使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领略唐诗之美”[2]。他总结出闻一多唐诗鉴赏的几个重要特点,如深入诗人内心世界、具有强烈深沉的历史感、突出美感分析、用诗化语言说诗、指向哲理的升华和规律的总结等。正如董乃斌所言,闻一多擅长文学鉴赏,我们从他未能完成的《杜甫》一文中仍可以看出他用诗意笔触为我们刻画出的一个活泼的文学天才的形象:诗人早年的经历、早慧的性格、与李白的历史性会面,都被写得栩栩如生。可惜被收入《唐诗杂论》中的《杜甫》一文没有完成,否则我们肯定能看到他关于杜甫诗风的精彩论述,正像我们看到他对孟浩然、贾岛等的论述一样。也有人认为闻一多的唐诗研究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成果。对古籍的整理和辨正是文献学的工作,也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要想做好一项研究,必须先有可靠的资料作为依据。闻一多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注重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力争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材料的准确把握上。与清代朴学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像清代朴学研究那样从事单个的证据研究,而是结合了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并将自己的研究自觉系统化、理论化。如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他不仅对杜甫的生平进行考证,还将杜甫生活时代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描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杜甫生活时代大的文化背景。但是,闻一多并不满足于文献学工作,他认为这种工作只是自己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他的着力点是在文献学基础上,对唐诗进一步研究。
从现有的闻一多的杜甫研究成果看,闻一多的研究方法远不止上面说的两种能够概括。闻一多对杜甫的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体现为一种“多元意识”。所谓多元意识,就是“面对‘一个对象’或‘一个问题’,一多先生总是避免只从一个方面进行思考,久而久之,就取得了方法论意义的结论”[3]。闻先生在杜甫研究中的“多元意识”体现为以训诂考据为基础、鉴赏与理性分析相结合、人格与诗格相结合等多个特点。如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是考据和文化阐释的结合,他的《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则显示了他对杜甫与其他唐代士人、其他诗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他的《杜甫》则是对杜甫人格和诗格的论述。在他的这种多元意识中,运用了唐诗文献学、唐诗鉴赏学、唐诗文化阐释、唐诗心理阐释等多种研究方法。
三、钱钟书的杜甫研究
钱钟书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散见于其《谈艺录》和《管锥篇》等著述中,达二百余条,足见杜诗在其诗歌研究中的地位。考虑到我们论述的对象“现代”一词的时间限制,我们把钱先生的研究限定在1948年首版的《谈艺录》中关于杜甫的论述上。
一般研究者均知道,钱钟书在宋诗研究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一部《谈艺录》有大部分是讨论宋诗问题的。钱先生对杜甫如此关注也与杜甫诗是宋诗的源头有关,与宋代诗人大多接受了杜甫诗歌的影响有关。钱先生推崇杜甫,尤其与他个人对杜甫诗歌艺术价值的欣赏有直接关系。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他明确将杜甫诗标举为中国诗的正宗。在《谈艺录》中,他更是提出“诗尊子美”,肯定了杜甫在唐代诗歌中的地位[4]。在《诗分唐宋》一文中,他论述了杜诗与宋诗的关系,指出杜甫是开宋调者;他论杜诗的境界,肯定严羽对杜诗的评价:“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5]认为“诗至李杜,此沧浪所谓‘入神’之作。”[6]他称杜甫的诗是唐诗的变体,肯定杜诗的创新精神。此外,他还研究杜诗的影响,称为“少陵七律兼备众妙,衍其一绪,绪足名家”,并列举了宋代以后诸诗家学习杜甫的得失[4]。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钱先生的杜诗研究,关注的是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在唐诗中的体裁变化、杜诗的艺术特征等诸多问题。总之,关注的是杜诗的艺术性和文学性等方面的内容。钱先生很少像陈寅恪和闻一多那样关心杜诗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很少关心知人论世、社会政治等“诗史”方面的内容。《谈艺录》中涉及杜诗的思想方面的内容,甚至是可以作为对知人论世评论方式提出的反证来读的。如针对历史上一贯讨论的杜甫诗歌中的爱国忠君思想,钱先生却说:“少陵‘许身稷契’,‘致君尧舜’;诗人例作大言,辟之榖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阙,橡饭思君,则挚厚流露,非同矫饰。然有忠爱之忱者,未必具经济之才,此不可不辩。”[6]
钱先生的《谈艺录》还采用了古代诗话的写作方式,他有意忽略诗中的本事、具体时间、地点等,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以修辞、评点、谈艺的传统诗话的继承。但他的《谈艺录》又明显融合了西方诗学的新观念,是一种唐诗研究的新范式。其中,用西方现代心理学方法阐释唐诗,就是钱先生唐诗研究的最大特色。这种阐释方法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攸同”,亦即承认在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共同的心理。如他在《谈艺录序》中开篇即宣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6]于是,揭示人类文化各层面的“同心之言”,便成为钱钟书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们从他上面对杜诗的解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他举出杜诗中《至后》一篇中“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说明文学情感捉弄人、“避愁莫非迎愁”的心理悖论。又如在杜甫《哀江头》中有诗句“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宋人对杜诗的解释,以陆游为代表,侧重于将“望”字解释为“忘”,并认为是诗人情绪惶惑,不记南北。陈寅恪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考证唐代的宫阙方位,认为“望”反映了杜甫在颠沛流离中仍然眷顾朝廷的爱国心情。而钱先生针对这一问题,肯定宋人将“望”理解为“忘”仍然是有道理的,并认为他反映了杜甫“丧精亡魂”之际“衷曲惶乱”的心理。正如有学者评论说:“陈的说法是回到历史当下,回到杜甫其人,钱的说法则可以引申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普通人性。”[7]
从钱先生对杜甫的研究看,他是以文艺学、心理学的方式在阐释杜甫的诗歌。因此,我们可以称他坚持的学术范式,是一种站在文艺学立场上,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说诗的学术范式。
四、三种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
把三位学者的研究放在一起看,也许更能看出他们的不同。
陈寅恪的研究是历史学,他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学肯定有价值。那么这种研究范式对文学研究的价值何在呢?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笔者宁愿相信胡晓明的观点:“诗歌文学不应仅仅被看作艺术、美学、理论的文本,而更应是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的辐集:社会风俗、伦理问题、宗教习尚、制度文物、妇女生活、政治军事事件、民族关系等等的文本。”[7]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就集中体现了用“诗史互证”方法研究唐诗的成就。从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政治、制度、宗教、风俗、道德、婚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他后来在实践中对专主考据的研究方法有所克服。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弊端。文学创作是一种虚构,虽然诗歌中的写实性作品能够表达某种社会现实,但并不能完全掩盖文学的虚构性质。过分坐实,把虚构的诗歌(文学)当成有信可征的历史,对号入座,容易忽略文学的虚构性质。还有,按照陈先生的观点,只要具有史学意义的诗就算好诗,那么,论诗就完全可以不管其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只要具有史料价值,即便是押韵的文件也等同好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容易造成所谓史实对“诗意”的伤害,容易模糊文学和史学的界限。对此,连陈先生自己似乎也有察觉:“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8]另外,用“诗史互证”范式研究唐诗还应该提出这样的前提条件:该研究方法只对写实性较强的诗歌才有效,对与社会内容关系不大的诗歌如王维、孟浩然等的一些抒写自然的诗歌未必适用。
其实,针对陈先生诗史互证的研究范式,早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反对最为激烈的,就是钱钟书。有学者研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范式的反对,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
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范式的不满之处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下面两则引文集中体现了钱先生对诗史互证研究范式的观点:
比见吾国一学人撰文,曰《诗的本质》,以训诂学,参以进化论,断言:古无所谓诗。诗即纪事之史。根据甲骨钟鼎之文,疏证六书,穿穴六籍,用力颇劬。然……为学士拘见而已。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古代诗与史混,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说:“古史即诗。”[6]
1958年,在《宋诗选注·序》中,钱先生又一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的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9]
从以上两则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钱先生反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诗歌(文学)与历史的学科之间的差别,意在维护诗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我们知道,文学既有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规律,我们不妨称之为“自律”,也有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相互交融之处,我们不妨称之为“他律”。这两项研究合在一起,才是文学研究的全部。作为文学的一种文体——诗歌(唐诗)有其审美的一面(这是唐诗的文学性的体现)。同时,由于诗是唐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加之以杜甫为代表的诗歌的确反映了唐代的社会内容,所以,就出现了从艺术审美角度研究诗歌和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诗歌的分野。
钱钟书反对陈寅恪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还存在着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现代文学研究笼罩在浓厚的历史学背景下,其中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学人们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诗经》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先生维护诗歌(文学)的学科性独立性就显得难能可贵。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钱钟书的著作中关于“诗史”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其《宋诗选注·序》和《管锥篇》中,他又谈到诗与史的关系,已经不是一味反对,而是承认诗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映历史的真实,并提出了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三种方式:写实、寄意、怀古。这一方面是因为钱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觉接受了唯物主义文艺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钱先生在文学评论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诗歌和历史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钱先生的转变还说明,陈先生与钱先生各自主张的研究范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互补的可能性的。文学的学科独立性是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产生的,事实上,要维护文学学科的所谓的“纯洁性”是很难做到的,比如,钱先生自己就有意识地借鉴了文化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相比而言,闻一多的研究是文献学、鉴赏学、文化诗学等多种方法的结合,其理论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但闻先生的研究范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唐诗研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献学派、鉴赏学派、历史学派等几个研究方向,其各自的研究对学术研究都有独立的存在价值。一个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中要想面面俱到,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所以,多元意识如果没有明确文学研究方法的“本体论”意识,很容易走向偏颇,从多元滑向一元。
三位先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唐诗研究中的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上,依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修养,为唐诗研究的现代化转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相对于古代的唐诗研究只重视考据或者只重视文献整理或者只重视点评等零碎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他们都在有意识地创立一种唐诗研究的新范式,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是对唐诗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五、三种范式对当代唐诗研究的启示
三位先生的唐诗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虽然有些具体观点被当代研究者提出质疑,但他们创立的范式至今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为我们当代的唐诗研究提供了经验。三位大师留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首先,唐诗研究必须坚持文学的民族性立场。在对中国诗歌民族特色的认识上,三位先生都认识到了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明显不同。西方的诗歌在表现内容上长于形而上的思维和写宗教性体验,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古典诗歌如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沉思录》以及现代的诗歌如艾略特的《荒原》等可以看出来。而中国的诗歌创作者大多是士阶层,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和责任感,这就使中国诗歌长于现实性体现,具有写实性特点,这种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最为鲜明。陈寅恪认为“支那民族素乏幽眇之思”,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的以诗史互证的方式对杜诗的“诗史”性质进行的研究也是有效的[10]。闻一多本人就是诗人,对中国诗与外国诗的不同也有清醒的认识:“西洋人不大讲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疵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11]闻一多认为中国诗歌的最大特征是诗人人格与诗风的统一,所以他在研究唐诗时,注重描述诗人人格与诗格的统一。我们从他关于杜甫的研究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诗歌民族性的认知。钱钟书也认识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异。如他在诗歌中推杜甫为第一人,在绘画方面,他认为王维的画是中国第一。很显然,他看到了同是中国艺术,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评价标准不应该是一样的,这就肯定了中国诗歌的独特性。但钱先生更强调中西方诗歌的相通之处,以此寻找出中国诗与西方诗的“文眼诗心”相通。
当今时代,坚持唐诗研究的民族性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中国民族诗歌的高峰,坚持唐诗研究的民族性,实际上就是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就是不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的诗歌,不以西方的文化标志来评价中国文化。坚持唐诗研究的民族性,也是抵制某些学人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不加转化地运用于我们带有明显民族特色的唐诗的研究行为。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思潮涌入中国,它们在给我们的唐诗研究带来新的视角的同时,也令唐诗研究出现了一些弊端。如有些人在研究中置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于不顾,对外来的尤其是西方的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名之为研究,实则造成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曲解和误读,结果是对我们唐诗研究也危害甚大。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警觉。
其次,坚持唐诗研究的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不同于感悟、联想等方法,而是重视逻辑的严密、论据、推理等方法。三位大师都深受现代西方学术思维方式和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的濡染,都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都力图把自己的学科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并将之具体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
在陈寅恪的研究中,唐诗研究的科学性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表现为借鉴了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又加上他对清代朴学的继承,使他的整个学术建立在严格而缜密的基础上。他的杜甫研究、他的《元白诗笺证稿》都可以看出他对研究材料的重视。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在科学性方面与陈寅恪有些相同,他把自己的唐诗研究建立在文献学研究上,对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均有借鉴,他对心理分析、神话学等多种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他的唐诗研究的科学性尤其体现在文学比较研究法上。如《宫体诗的自赎》,他采取纵向比较的方法,把宫体诗发展历程、转变过程清晰地勾勒出来。钱钟书的唐诗研究也同样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正如他的好友郑朝宗所说:“钱钟书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立下志愿,要把文艺批评上升到科学的地位。”[12]根据钱先生的文艺批评实践,我们说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对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自觉意识上和将文化学和心理学引入文艺批评实践中来。
科学性是中国文学研究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个标志。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规则和规范,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是文学批评的前提。而当今我们有些所谓的学术研究,不顾相应的学术规范,妄加评论。更有一些“酷评”理论,置研究的理论方法于不顾,使中国诗学脱离文本,望文生义,严重地违背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真义,更是对文学学科的伤害。对于这种研究方法,陈寅恪早就提出过批评,称之为“呼卢成卢,喝雉成雉”[10],胡晓明则称之为:“画鬼术,人天牛鬼的比较法。”[7]
再次,坚持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唐诗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是在中西方文化交会的语境中诞生的,因此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也是三位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共同特点,正是因为三位大师在学术研究上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研究方法,才体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积极主动地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对我们的唐诗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将本民族的诗歌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认识和审视,也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民族诗歌的独特之处。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现代诗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回顾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发现,历史的巨变、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唐诗的当代研究站在新的起点,也对我们的唐诗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学习和借鉴三位大师的学术范式,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将唐诗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董乃斌.唐诗研究的鉴赏学派与闻一多的贡献[J].中州学刊,2000,(2):93—94.
[3]吴艳.论闻一多诗学的“多元意识”[J].江汉论坛,2004,(6):93—95.
[4]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69—70.
[8]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郑临川.闻一多先生与唐诗研究[J].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3,(1):71—79.
[12]田慧兰.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