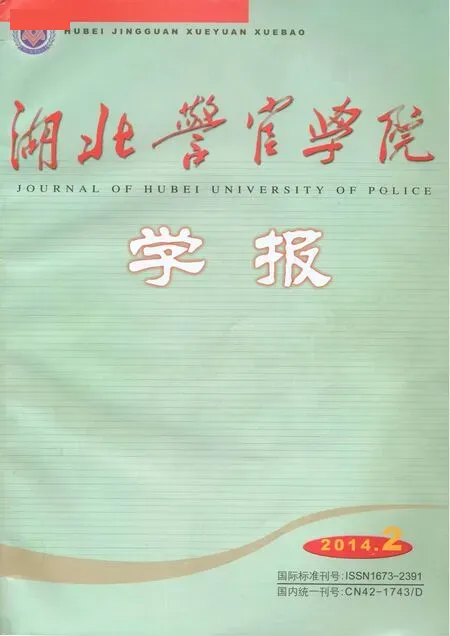社会的诉讼观对现代民事诉讼的启示
彭芳林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的诉讼观在中国学界也许是一个新事物,但它已经是一个理论上趋于成熟、实践中得以适用的指导思想。毋庸置疑,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如果引入一项新的制度或者思想要慎之又慎,并且往往会招致学界的抵触和质疑。但是,社会的诉讼观不是一套全新的观念和思想。在理论上,社会的诉讼观与国内关于诉讼模式之争论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在实践上,该理念在奥地利成功推行,后来又成为德国民事诉讼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而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司法改革。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能够看得更高、更远;同理,将社会的诉讼观同中国民事诉讼结合,也有可能会擦出强烈的火花。
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仍在继续的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传统的调解型审判模式进行了重大修正,改变了以往法官包揽诉讼的景象,强调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改革进程中也出现了若干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在事实与证据的提出层面过于强调当事人的自由,削弱法院的职权,实行所谓的“法定证据制度”。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不断缩减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便是典型。这种局面的形成虽然不乏司法机构的利己因素,即通过减缩法官职权以减轻法官责任负荷,进而缓解司法的压力,但与学界对辩论主义的误读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事诉讼法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缺乏对抗的色彩和辩论的因素。因此学者一直呼吁我国向英美学习,实行辩论主义。并且在实践中,尤其在法庭举证的环节过于注重当事人主义。其实在西方国家,辩论主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面目,其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19世纪末奥地利、德国等国家相继进行民事司法改革以来,民事诉讼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自由主义的诉讼观,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诉讼观,诉讼的社会性逐渐被强调。基于此,本文试图对社会的诉讼观进行详尽的介绍和论述,希望扭转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诉讼观的崇拜和盲目追逐,进而对我国现代民事诉讼进行改进。
二、社会的诉讼观的基本理念
国内的学者关于社会的诉讼观的论述并不多见。但是,很多学者发现了自由主义诉讼观下辩论主义的缺陷,并且隐约感觉到了民事诉讼新趋势的到来。到了19世纪末,随着“法律社会化”运动的深入和福利国家思想的兴起,先前在思想领域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逐渐衰弱,在某种程度上,先于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时期的更古老的传统理论“复活”。[1]下面,笔者将对社会的诉讼观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论述。
社会的诉讼观并不是由社会法学家将社会的观念引入民事诉讼而产生的。这种诉讼观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的出现为标志。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是最先将法律世界的关注目光转移到社会的低等阶层和贫穷阶层身上的。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关注引入民事诉讼法律当中,并且要求在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倾听社会低等阶级的声音以及保护他们的权利。安东·门格在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当时民事诉讼法律和实践的不满。他明确要求法官为每个国民,尤其是贫穷阶层作法律上的指导,而不是在审判中放任当事人完全自由地进行角逐,并且要求强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力。
接着,奥地利法学家弗朗茨·克莱因在发现自由主义诉讼观缺陷的情形下开创了社会的诉讼观,并且用该理念塑造了具有开创性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他不仅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变化已经对自由主义的诉讼观以及法治国家的民事诉讼的正当性价值提出了质疑,而且由此得出了对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社会性改造的结论。克莱因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的观点决定了诉讼的类型。专制制度在普鲁士的《一般法院法》中创造了自己的民事诉讼模式(家父主义诉讼观),自由主义时代则创造了《法国民事诉讼法》和《德国民事诉讼法》。作为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在新的时代,诉讼必须遵循新的趋势,即支持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优先地位,并将国家理解为塑造社会的工具。由此观之,克莱因是社会的诉讼观的真正奠基人,或者是社会的诉讼观的再发现者。在克莱因看来,民事诉讼绝不是供个人仅出于自身利益和为了解决个人纠纷、实现权利而使用的设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事诉讼也涉及到社会福祉的保护,被赋予了新的特征和使命。“自由主义诉讼观将诉讼看成是当事人之间的角逐,当事人自己决定在法庭上解决纠纷的方法。然而,社会的诉讼观将诉讼置于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按照社会的诉讼观,民事诉讼有两方面的构成要素:其一是纠纷的解决(就像自由主义诉讼观所表现的那样);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实现公共福祉,我们应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民事诉讼。”[2]诉讼财产和资金从经济循环中剥离出来,劳动力被浪费,社会的融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干扰,因此,诉讼的结果不仅仅涉及直接参与其中的当事人。克莱因进而得出结论:现代国家并不是与民事诉讼彼此分离地相互对立,不再允许将民事诉讼视为法律技术问题,而必须将其列入整个社会政策计划当中,诉讼的社会性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对于如何处理自由主义诉讼观与社会的诉讼观的关系的问题,克莱因指出了自由主义诉讼观的致命缺陷:民事诉讼不仅仅涉及当事人,而且也应当在个人和公共福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照顾和国家救助的思想代替了被规范了的诉讼角逐,即当事人双方在消极的法官的监督下进行战斗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要放弃民事诉讼当事人互相对立的特点,相反,应当依然保留由当事人发动诉讼的模式。是否将争议提交法院,则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在诉讼结构上,社会的诉讼观表现出与自由主义诉讼观完全不同的状态:社会的诉讼观的出现意味着告别了对诉讼过程和诉讼材料实行毫无限制的当事人主义。在克莱因看来,对于不精通法律而又没有熟知法律的朋友可供委托的穷人而言,当事人的权限及其对诉讼材料的支配实际上是很容易伤害到自身的武器。除此之外,他还反对这种观点,即认为整个司法都应当拥有法官所必须具有的消极性,即“昏昏欲睡和无精打采”。他认为,一旦“如此经常地被人们提到的对于诉讼的谨慎矜持”变成了法官的第二本性并且变成其弱点时,消极性就改变了法官的观察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长期影响法官的整个职务过程”。克莱因并没有为实现“言辞主义”和“直接审理主义”而抗争,但是他很清楚,如果当事人不亲自出庭并且诉讼中的法官被评价为是消极的,那么这些原则将毫无意义。只有当人们改变法官消极的情况,更长远的要求,如正义、迅速、言辞主义、直接审理主义等才能被实现。克莱因因此认为,诉讼就是以特定的结果为目标的多人之间的精神上的合作。
除此之外,克莱因的社会诉讼观念也赋予诉讼上的真实义务以新的生命。对于专制主义(家长主义)的诉讼法而言,这种义务是理所当然的。在社会的诉讼观中,克莱因再次将真实义务放到了诉讼的核心位置。他认为,在民事诉讼中起决定作用的仅仅是所谓的形式上的真实而非实体上的真实的观点看起来是与诉讼的社会职能相矛盾的。“诉讼是确定实体真实的手段,并且必须如此,否则诉讼就缺乏社会正当性。”[3]因此,真实义务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且更应当是法律上的。一如要求法官积极支持不精通法律的当事人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克莱因的态度同样坚决。
“公共福祉”和“社会效果”这些用语表明人们可以将克莱因列入社会主义的阵营中。克莱因在一系列的论文中阐述了改革的观念,因此被保守的奥地利政府任命到司法部并且两次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1906年和1916年),所以说他根本不是改革者,相反,在他身上当时被视为是大胆的思想同从有关社会发展和社会的相互联系的分析中得出的措施和目标的意义交织在一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所缔造的诉讼法才能持久地获得成功。克莱因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诉讼的实用性,目标是确立迅速而又经济的程序规则,判决的作出依据客观真实(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形式真实(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程序中的形式主义受到了限制,法官在诉讼中积极地主导诉讼。
三、社会的诉讼观的具象化
社会的诉讼观要求我们在程序上做到:在诉讼资料收集层面应强调当事人与法院的协作;重新思考辩论主义的三大命题,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强化法院的实体性诉讼指挥义务。[4]然而,这些要求并不是社会的诉讼观的全部。我们必须同时注重实体层面的变革:社会诉讼观背后由社会效果支撑,但社会效果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失去了具体意义的社会效果将带来恣意模糊的社会的诉讼观。
笔者认为,社会效果并不是社会作为整体的效果,而是各个社会范畴在具体冲突中各自诉求的效果。辩论主义法庭倾向于将法院和法律的价值作为中立高悬的天平,表面上看双方当事人各抒己见,自由表达各自的价值,但只要与法律的价值产生冲突,就会失去法院的支持。社会的诉讼观立足于社会价值,而法律价值从来不应是社会价值的核心,就像政府价值从来不应是社会价值的核心一样。这意味着,即使一项社会纠纷诉至法院,法院也不能简单地用法律价值衡量纠纷的对错,而忽略法律和社会在特定领域的互动。
社会范畴(social sphere)的概念来自英国法律社会学学者Galligan教授的理论。[5]他指出,社会范畴就是由特定群体所基本一致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念、知识、习惯的结合体。所有公民固然以个人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中,但同时他们几乎都免不了进入各自的社会群体,承担各自特别的职责,发挥各自特别的功能。正如他举的例子中反映的情况那样:作为一个公民,某人应当而且会认可和遵循医疗法规,尤其是精神病法规;但同时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他可能会认为议会于1983年颁布的《精神健康法案》(Mental Health Act 1983)是低效且违背行医规律的。具体而言,这种观念上的冲突源自议会立法者和精神病医学界在价值观上的不一致。1983年《精神健康法案》的价值观是:任何人均有权最大限度地享有作为公民的自由权,这种自由不能够被不正当的诊疗或精神病医师的其他临床行为剥夺。因此,病患有权在诊疗过程中寻求律师的帮助,也有权随时要求中止精神病的治疗。但对于精神病医生而言,他们一直以来信奉的价值观是:治病救人,一切以成功医好病人为根本目标。这样的信条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送进精神病院的病人被当成了客体而非主体,保护患者人权的考虑被搁置在次要的地位。这种态度背后的理论依据在于,精神病人不同于一般病人。一个腿脚甚至内脏患病的人可以自主控制自己的意识,而精神病人不可以。如果放任精神病人随时中止治疗,他们无法判断精神病人的意思表示是否属实,且这种表示的效力违反了长期以来精神病医学界的惯例。显然,当时的议会立法者并没有认真考虑精神病医学界的社会范畴和特定临床语境,这部法案受到精神病医学界的集体排斥,进而沦为一纸空文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学家卢曼的自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范畴的概念。[6]卢曼指出,一个自生系统具备以下特征:(1)它能够自我产生系统内需要的概念和知识;(2)它能够通过社会交流划清自领域的边界和再生产概念;(3)它能够和域外社会范畴保持相对明确的独立;(4)它也能够接受领域外的影响,只要这种外界影响用它所熟悉的语言、逻辑表达出来。
社会领域的多元化带来了社会范畴在种类和深度上的多元化,不同的社会范畴需要不同程度的外力影响:比如一个松散的群体很容易被法律规制,但一个成熟的系统就不容易受到法律观念的影响;有些社会领域希望接受外在观念的影响(比如学校希望吸收学生的创新思维甚至叛逆思想),有些社会领域则不希望接受外在观念的影响(比如相对封闭的宗教流派或科学流派,包括上文提及的精神病医学界)。其实,法律本身也是众多社会领域中的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分享着大同小异的价值、知识、逻辑和习惯。诉讼不仅是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也是特定社会范畴与法律范畴之间的价值冲突。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法院和法官既是法律价值的信奉者,又基于特殊的地位而是审理法律与社会冲突的裁判者。这就需要法官能够适时地抛开法律价值和法律逻辑本身。无论其目的是支持特定的社会范畴的诉求还是说服该社会范畴的成员,他都必须首先倾听、理解该方当事人的价值、习惯、知识和逻辑,并用同样的逻辑内化于法律审判中。否则,让一个长期属于特定社会范畴的成员立刻学习法律逻辑和法律术语,是对诉讼当事人的不公平,也是对法律与社会互动的不负责任。如果精神病医生在庭上阐述医学界的基本价值观和逻辑而法院草率地置之不理,也许病患可以得到一时的人权保障,但最终的效果就如同上世纪末的英国,该法案被精神病医学界所共同敌视,以至最后沦为一纸空文。毕竟,不是所有的医患纠纷都能上升至法院,成功的医疗也不能在法院完成。
综上,社会效果背后的社会价值在内容上不是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的结合体,而是具象化到各个特定社会范畴的诉求。社会的诉讼观要落到实处,仅仅在程序上进行诉讼变革是不够的,还必须用法律社会学的眼光,到实际生活和各个社会系统中寻找改革的答案。
[1]杨海,胡亚球.诉讼中家长主义的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12(3):117.
[2]C.H.VanRhee.CivilLitigationinTwentiethCenturyEurope[J].Tijdschriftvoor Rechtsgeschiedenis,2007(75):307.
[3][德]鲁道夫·瓦瑟尔曼.社会的民事诉讼——社会法治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A].[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傅郁林主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C].赵秀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92-93.
[4]熊跃敏.辩论主义:溯源与变迁[J].现代法学,2007(2):95.
[5]D.J.Galligan.Law in Modern Socie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03.
[6]N.Luhmann.Law as a social system[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