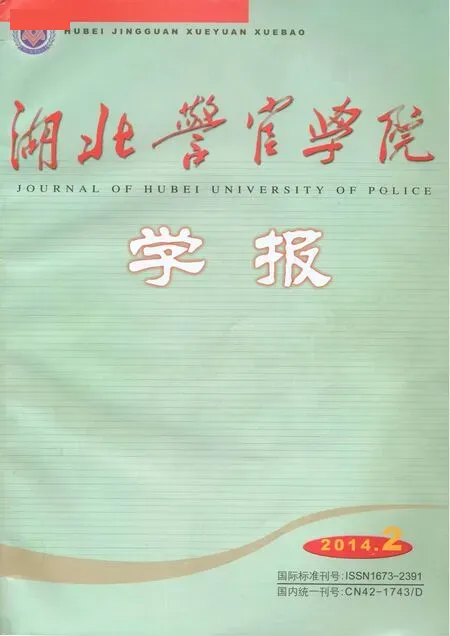“法律商谈论”在我国死刑判决中的适用
——从“盗车杀婴案”说起
陈芹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法律商谈论”在我国死刑判决中的适用
——从“盗车杀婴案”说起
陈芹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实践总能为反思法律制度提供新鲜血液,盗车杀婴的周喜军有自首情节仍在一审中被判死刑,再次为检讨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引导民意”的口号最终导致法官的独白式判决,不能实质解决问题。德国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论”用交往理性代替技术理性,将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建立在主体间理性交往之上,有利于死刑案件的判决而且能兼顾合法性与民意支持,对协调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死刑判决;法律商谈;交往理性;公众参与;盗车杀婴案
一、“盗车杀婴案”的反思——死刑判决如何兼顾“乌纱帽”与“赛先生”?
2013年5月27日,备受关注的长春市“3.04”盗车杀婴案在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周喜军一审被判死刑。2013年3月4日,周喜军将一部未熄火的RAV4丰田车(吉AMM102)盗走,并将车上仅两个月大的婴儿勒死埋于积雪中。3月5日,周喜军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事件很快引起社会的关注。一方面,作案者周喜军的残忍激起网民们的愤怒,网络上杀声一大片。另一方面,长春数千市民自发聚集在文化广场,点燃蜡烛悼念这位不幸遇难的两个月大男婴小皓博。5月27日上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周喜军故意杀人、盗窃案,并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17098.5元。法院对该判决的主要说理是:被告人周喜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汽车,价值巨大,车内的婴儿啼哭,周喜军害怕被抓获,残忍地将婴儿掐、勒颈部致死,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应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在自知无处可逃的情况下投案,虽自首成立,但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对被害人家属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依法保护丧葬费17098.5元。[1]
本案被告被判处死刑,从民意上看也许是众望所归,但在法律适用上,却值得商榷。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可以从轻或者减轻”,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亦即只有齐备“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四个条件,才能例外地不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人身危险性”指再犯罪的可能性,本案并没有提出任何表明被告再犯可能性的证据,就直接判处被告死刑,显然欠妥当,有“重民意、轻法律”之嫌。死刑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刑罚,《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死刑案件中,更应考虑自首情节,为犯罪人提供悔罪机会。因此,法院的判决明显与此规定之意旨相悖。
近几年来,网络等媒介使得公众有机会热情关注一些热点刑事案件,民意得以集中表达,并形成一股强大的话语力量。“司法民主化”、“司法判决要考虑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也成为司法人流行的口号。不可否认,司法公开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司法的公开、透明,对于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日益高涨的关注,对于保障民众对司法审判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对于树立人民法院良好形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随着公众参与司法的需求逐步增强,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司法对民意的过分倾斜导致了所谓的“民意审判”。在汹涌的媒体报导下,法院往往如履薄冰,疲于应付,有些法官仅仅关心如何应对压力,而不关心民意如何形成以及民意的真正诉求,以至于置法律于不顾,甚至以民意作为对抗法律的借口。
同样具有自首情节,同样被判处死刑,2011年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并没有让人们忘却,盗车杀婴的周喜军又一次处于风口浪尖之上。5月29日,腾讯网《今日话题》栏目发起“自首能救下杀婴犯的命吗”的话题,高达94%网友支持周喜军死刑。[2]我们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盗车杀婴的一审判决是否又是一起舆论压力下的“民意审判”?
事实上,民意与法律真的相互对抗吗?在提倡限制死刑并逐步走向废除的今天,公众对死刑案件的参与是否导致案件的重判?在我国死刑案件中,应如何建立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以下,笔者借鉴德国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论”,以另一条思路对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展开论述。
二、域外思路的借鉴:“法律商谈论”
(一)达致合法判决的途径:法律商谈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并将交往行为理论及商谈伦理学引入法学,创立了“法律商谈论”。他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霍克海默等)所开辟的技术理性批判路径,展开了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深刻批判。他提出要以自由、平等的主体间性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来取代以单一主体为面向的实践理性和以主体—客体结构为指向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物质交往”转变成以理解为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以此重构了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法律商谈论”首先揭示了民意与法律并非对立,恰恰相反,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必须建立于民意之上,是“所有人讨论的结果”。[3]哈贝马斯认为,法的合法性不在于孤独的“主体性”,而在于交往中的多视角的“主体间性”。在一个封闭领域中,一个主体单视角自足地进行,无论他怎样聪明,所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智慧,且没有经过商谈程序的筛选和辨认,正确性是没有保证的。
他强调: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4]“主体间性”必须从第一人称复数这个主体间扩大了的视角出发,“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光,而要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同的理论目标(意义诠释、概念分析和描述、经验说明),不同的角色视域(法官、政治家、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语用研究态度(诠释学的、批判的、分析的等等)。”[5]公众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要求、意见、呼声构筑了法律商谈所必须的“公共领域”。[6]
哈贝马斯指出,如果忽视主体间的交往和商谈,就不能确保法律得到普遍的认可和遵守。一方面,法律离不开强制,离开强制,法律可能会变得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如果法律仅仅诉诸制裁来强迫人们遵守,就会蜕变成一种压迫,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暴力统治。因此,一个社会要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具备推行法律的强制力,二是使法律成为值得人们遵守的规则。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作法律的事实性,将后者称作法律的有效性。[7]
(二)构建法律商谈的基础:交往理性
法律商谈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在于“理性”。何谓理性?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归诸于单个主体或国家—社会层次上的宏观主体,其特点在于其“主体性”单一,并且主体所反映的认识仅仅是对客体的认识。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代替实践理性,交往理性归诸于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这种合理性是铭刻在达成理解这个语言目的之上,形成既提供可能又施加约束的前提性条件。哈贝马斯提出:法律判决的正确性在于各平等主体之间的有效言语沟通。
哈贝马斯提到,规则的合法性的程度取决于对他们的规范有效性主张的商谈的可兑现性。[8]法律的合法性最终依赖于一种交往的安排: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法律同伴必须有可能考察一有争议的规范是否得到、或有无可能得到所有可能相关者的同意。[9]那么,如何才能确保商谈的有效性呢?
哈贝马斯认为,司法判决正确性的衡量标准,取决于判决过程对那些使公平判断成为可能的交往性论辩条件的满足程度,即在时间向度、社会向度和实质性向度中必须采取的那些理想化条件:第一,无尽的时间,它们阻止对论辩的不受合理推动的中断;第二,无限制的参与,它们通过人们对论辩过程的普遍、平等的了解和平等、对称的参与而确保在议题之选择和最好信息、最好理由之接纳这两方面的自由;第三,充分的无强制性,它们排除理解过程内外所产生的任何强制,而只承认更好的论据的强制力量,除合作地寻求真理外,其他动机都被中立化。[10]亦即,商谈的有效性、理性的交往取决于商谈主体地位的平等、信息的对等和充足的辩论时间。
三、我国死刑判决“法律商谈”之理论证成
(一)必要性:提升司法公信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限制、废除死刑成为全球刑法改革潮流。与之相适应,我国在司法上,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立法上,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这可谓我国在限制死刑路上的两大里程碑。然而,我国公众对死刑依然存在较强的依赖乃至迷信的观念,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对具体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罪犯予以严惩(即适用死刑)的强烈民愤;二是一般性地反对废止死刑,甚至非理性地主张扩大死刑的适用。正如赵秉志教授所指出的“改变普通民众对死刑的依赖与迷信,是我国现阶段死刑制度的改革当然也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11]”
近些年,媒体热衷于报导一些司法案件,死刑案件更是备受公众的关注。网民们也通过开设博客、上网讨论等方式对死刑案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司法与民意似乎有了交往对话的平台。然而,这种对话并没有形成民意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反而让两者的关系更为紧张。
表面上,法官顺应民意,做出向民意倾斜的判决。法官以民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甚至死刑判决书上也写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实际上,司法经常高高在上地藐视民意,认为民意是非理性的,民意与法律是对抗的,急于与之脱离干系。对于民意,目前学界一致的态度是:司法应当重视民意,吸纳其合理成份,但又要排除民意中的非理性成份的干扰,“司法机关不能被舆论牵着鼻子走”。
事实上,法官无法知道以何种标准来判断民意是否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会倾向于——而且也只能——根据个人好恶来取舍,被接纳的民意实际上是被法官认可的说法,被视为非理性的民意实为法官所不认同的看法,或者说,法官将自己的观点披上民意的外衣。“引导民意”最终走向了法官“独白式”的判决,这种似乎符合矛盾统一律的中庸语词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
无论是“引导民意”还是“讨好民意”都无法处理好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提倡民意与司法商谈,提出法律的合法性最终依赖于一种交往的安排,这正是中国司法判决所缺乏的。因此,在死刑案件中,借鉴“法律商谈”对协调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十分必要的。
(二)可行性:民意并非“非理性”
哈贝马斯强调:“法律商谈”是建立在理性交往的基础上。在我国死刑案件中践行“法律商谈”,首先遇到一个难题:民意是否能理性地参与司法商谈?
在我国刑事司法中,自诩“精英”的法律人为了保证自己的话语权,倾向于将民意视为理性的对立物。有学者认为:“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12]然而,民意真的是天然地“非理性”吗?
仔细推敲,我国的民意的“非理性”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民意的参与只是间接参与。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论”强调商谈主体的理性取决于商谈主体地位的平等、信息的对等和充足的辩论时间。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近年来,司法公开化、透明化程度逐步提高。在欢迎和接受舆论监督的主题下,司法与社会的距离表面上似乎正在拉近。然而,我国的公众参与最多只能称为间接参与。一方面,公众与司法机关没有平等的参与地位。对于具体案件的意见,民众主要通过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开设博客、上网讨论等方式,一般都具有自发性,公众参与过程也往往带有“符号化”色彩,流于形式,一些参与需求无法通过“制度化”方式得以表达和回应。另一方面,公众也无法得到与司法机关对等的全面的案件信息。由于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公众只能根据零碎的“爆料”、片断的报道进行事实判断。这个过程就无法排除受到不全面、不真实的新闻信息的诱导,以及部分特定身份的人(著名学者、知名人士、当事者的亲属等)在一定范围内的号召与联络。因此,基于道听途说、浏览网页的间接参与导致了对案件的非理性分析。
其二,民意倾向支持死刑跟腐败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前两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成都孙伟铭酒后驾驶肇事案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据《人民日报》报导,公众对这些判决结果的不满主要在于“公众希望被告人判得更重一些……加害人通过花钱逃避法律和惩罚在很多案件中很普遍。公众强烈抗议这种肮脏的权钱交易。”[13]
死刑中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死缓的适用。近年来,随着死刑复核权的回归,死刑控制力度的加大,死缓的扩张适用现象引起了公众的担忧。特别当死缓越来越成为与经济和政治权利相关联的选择性执法时,公众担心,死缓是否成为富贵和有权势之犯罪人的免死金牌?
综上,所谓的“民意非理性”、“民意倾向支持死刑”都根源于公众没有真正地有效参与司法,司法判决没有主体间的互动,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与服从的关系。公众没有有效地参与,其意见也没有得到重视,如此“参与”,何来理性?
因此,如能在死刑案件中,为公众提供直接参与的渠道,让公众获得与司法机关平等的商谈地位,让公众有效地参与商谈,“民意非理性”、“民意倾向支持死刑”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这也是“法律商谈”在我国死刑判决中的可行性所在。
四、我国死刑判决“法律商谈”之实践路径
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既提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必须建立于主体间的交流,又强调主体间交流的有效性,并指出商谈的理性在于商谈主体地位平等、信息对等、辩论充分。将“法律商谈”理论适用于死刑案件,具体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商谈主体之构建:公众与司法机关成为平等的商谈伙伴
对于如何建立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法机关应当保持理性,引导民意。如上所述,口号式的“引导民意”并没有任何操作规则,最终会导致法官的“独白式”判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法官,民意只是被引导的对象。
也有外国学者建议:“中国的公众仍然无法正式参与到死刑适用的决定中,陪审团虽然表面背离了司法实践,但实际是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有利补充。”[14]不可否认,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在司法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基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限制,陪审团制在我国现阶段暂时无法实现,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
在死刑案件中践行“法律商谈”,协调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首先应让公众与司法机关成为平等的商谈伙伴。以单一主体进行独白式的法律适用,其正确性没有保证,法律判决的正确性在于平等主体间的有效言语沟通。法院不必担心民意会干扰司法,而应把公众视为与自己一样具有“交往理性”的“同伴”,向民众提供参与商谈的“生活世界”,这样才能保证所有“同伴”建构的“理想类型”更接近客观真实,才能产生基于理性交往的合法判决。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普通公众才真正作为一个能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人格实体,参与判决过程。
(二)商谈程序之构建:商谈理性和有效性
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既注重民众与司法机关的商谈,又注重商谈的理性。商谈的理性建立在地位平等、信息对等、辩论充分的基础上。这种理性的商谈正是我国现在司法审判中所缺乏的。例如,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虽然人民陪审员制代表着我国司法民主,但目前我国陪审员的参审多流于形式上的”名誉陪审“。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在庭上,多表现为一言不发,犹如装饰品般辅佐审判长左右。在庭下,陪审员多代书记员之职处理送达、整理、校对等日常事务。与审判员共同组成合议庭,陪审员既不具备充分的法律知识,又担心说错话得罪法官,所以通常只是一味地附和,而不能提出实质性的见解。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员的存在价值毫无发展,陪审制度形同虚设。
因此,践行“法律商谈”,要确保商谈的理性和有效性,就必须让民众获得全面的与司法机关对等的信息。在影响重大的死刑案件中,司法公开化、透明化必须进一步提高,为公众创建一个可以直接参与的渠道,公众可以参与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了解整个案件的事实,而不是通过媒体报导或其他外来资料做出决定。公众不仅仅是道听途说、无障碍旁听、浏览网上文书、看视频直播,而是真正参与进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此外,法律的合法性来源于论证商谈。这要求民众与法官有充分的商谈时间,有完整充分的开庭、事实调查、辩论的整个庭审过程,而不是流于形式,甚至“先定后审”。
在我国的死刑案件中践行“法律商谈”,为民众提供直接参与的途径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保证死刑案件判决的合法性。死刑只适合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限制死刑并逐步走向废除的今天,对于死刑的判决更应谨慎。“法律商谈”使判决产生于所有人讨论的结果之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判决的合法性。其次,建立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可以缓解当地检察官和法官的压力。现在当他们实行严厉刑罚时往往面对公众压力的冲击,公众在真正了解案情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成为法官的商谈伙伴,使判决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得出更公平的判决结果。另一方面,在审判中有民众的直接参与有可能帮助平息对有特权的被告因赔偿被害人或关系而逃避严惩的批判,消除公众对腐败的担心。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让民众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种参与会把对司法制度的信赖感在直接参与的民众以及一般社会公众中传递”,[15]从而唤醒民众对司法的了解和信赖,增强对裁判的接受性,促进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
未来公众参与的角色仅仅是我国微妙而复杂的死刑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在死刑案件中,如何协调好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增强公众对死刑案件审判的信任,如何兼顾民众的有效参与从而使判决获得民众支持,同时又保证参与各方的理性,这是我国死刑案件审判面临的一大难题。借鉴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让公众成为与司法机关平等的商谈伙伴,将死刑判决合法性建立在公民理性参与的基础上,应当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也是未来死刑制度改革发展的一个趋势。培根说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养的过程。”[16]
[1]长春盗车杀婴案凶手周喜军一审被判死刑[EB/OL].http://news. 163.com/13/0528/07/8VUP 1L2300011229.html,2013-05-08.
[2]张德笔.自首能救下杀婴犯的命吗[EB/OL].http://view.news.qq.c om/zt2013/zxj/index.htm,2013-05-29.
[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3.
[4][5][6][7][8][9][10][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27,8-9,445-446,684,36,128,8-9.
[11]赵秉志.我国现阶段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及对策[J].中国法学, 2007(2):3-16.
[12]莫晓宇.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5):84-90.
[13]PEOPLE'S DAILY.On China's“Second-Generation Rich”[EB/ OL].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2/90872/674 1171.html,2009-08-27.
[14]Margaret K.Lewis.LENIENCY AND SEVERITY IN CHINA'S DEATH PENALTY DEBAT[J].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Spring,2011:1-33.
[15][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M].姚永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47.
[16][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前言.
D915
A
1673―2391(2014)02―0134―04
2013-08-06责任编校:陶范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刑事判决书中法理诠释之实证研究”,编号:GD12xf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