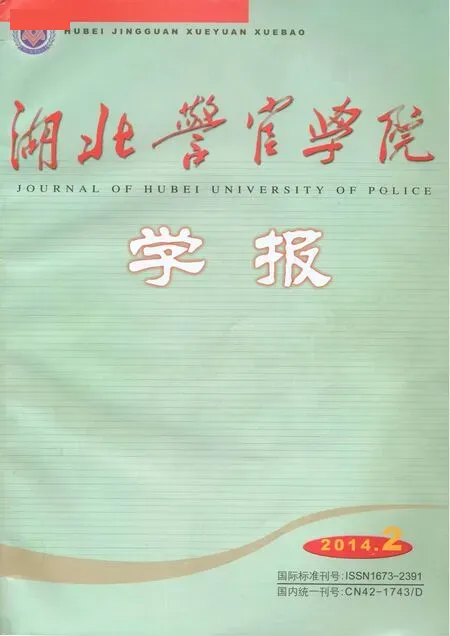习惯与惯习:在新旧分析实证法学领域的辨析
梁勇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200234)
习惯与惯习:在新旧分析实证法学领域的辨析
梁勇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200234)
对于法律的形成,存在着“习惯—习惯法—成文法”的三段式观点。历史法学派学者们的理论论述更是给这种观念提供了依据,在其著作之中一般认为司法判决、制定性法律从历史层面来说多源自大众行为的行为习惯、风俗、民族传统等等。而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角度中,笔者看到了“惯习”这一词汇,由此产生了诸多疑问。习惯与惯习分别是什么?惯习与习惯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异同?惯习在上述法律发展的三段式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对此,尝试从惯习的源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视角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起到抛砖引玉之功用。
习惯;惯习;习惯法;新旧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一、习惯与惯习提出的历史背景
最早在法律领域提出“习惯”概念的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约翰·奥斯丁,原因在于其无法认同早期自然法学派关于法律约束力来源的论证,并坚持认为法律约束力的来源在于统治者的无限命令,并且将“制裁”作为约束性手段,而人民普遍的服从习惯将为主权者的命令提供依据。此处不过多地对早期自然法与实证法的论辩进行叙述,只从习惯性观念分析奥氏的理论。而另一概念“惯习”的提出则是在分析法学大师哈特与德沃金的论战中孕育而生的。随着哈特教授《法律的概念》一书的问世,其提出的规则模式、承认规则、分离论等理论似乎使实证主义法学几近于胜利,但德沃金、富勒等新自然法学家不甘示弱,以“规则—政策—原则模式论”、“语义学之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等加以回应,开始了争论。哈特教授最终也逐步放弃了原来的理论,演变成为其所谓的“柔性实证主义”。从某方面来说,是在新自然法学与新分析法学的共同努力下,“惯习”一词才在法哲学领域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
二、习惯与惯习的概念
奥斯丁当时的说法是:“任何一个法体系都包含某些人或团体所发布之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这些命令大致上受到习惯性的服从,且被规范的群体须大体上相信:当违反这些命令时,制裁将会被执行。这些人或团体必须是对内至上,对外独立的。”这里的重点在于对于习惯性服从性质的理解,习惯本身具有如下多种含义:1.亦作“习贯”。原谓习于旧贯,后指逐渐养成而不易改变的行为。这里习惯指的是与人身、个人性格相关的特定行为。2.习俗、风尚。例如,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的“彩礼制度”。3.对新的情况逐渐适应。例如,“我非常地不习惯、需要时间来习惯”就是这种含义,即动词形态用法。那么奥斯丁指的习惯性服从是哪一种呢?由于原句中是以习惯性出现的,笔者认为此处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服从,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若不服从以制裁强制为后盾的法律,必将涉及人身,是一种对权威的敬畏。
对于惯习,主要是哈特以及包容性实证主义的学者们在运用。由于这个概念一直处于发展状态中,在此处,主要借引哈特对于惯习的描述以及科尔曼等学者的观点来进行阐释。哈特在经历了柔性实证主义的转向之后,强调法律是社会成员从内在观点接受其拘束的社会惯习事实。惯习本身也有数种含义:1.指经常性的联系、熟练。2.指习惯于、习惯。那哈特本意指的是哪一种呢?按照字面理解似乎是指第二种,但笔者在此处存有疑问:如果是第二种,那为何要特意使用惯习(convention)以取代奥斯丁的习惯(habit或者be used to)呢?故笔者进行了第二层面的分析——该词语本身在所属文字中的具体含义。habit在英语国家中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习性、气质;而convention则可以被解释为会议、国际公约、惯例、规矩等。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哈特教授运用惯习概念是以此来进一步强调对于规则中规范性层面的理解。
三、习惯与惯习的形成原因
如前所述,这里的习惯专指奥斯丁在其“法律命令说”中的习惯,并不包括诸如风俗民约或者是形容词性的用法。从惯习来说,笔者意图借助哈特教授所举事例——进屋脱帽,以一种新的视角进行论述。进屋脱帽这一惯习是缘何产生以及目的何在?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两种解答:第一,惯习的基础在于个人习惯,即群体性的规矩来源于个人的习惯。首先由一人开始,而后逐渐辐射至身边周围之人,最后形成囊括一个大范围的公众性行为方式。第二,惯习的基础与个人习惯无关,即群体性的规矩其实来源于最初某一群体之间的权衡与取舍(类似于孩童游戏时的方式,定规则、立规矩),先进入其中的参与者,有权对后参与者实行监督,唯有其确实地遵守了前者所遵循的“规矩”,方才允许其加入。但对于解答一,笔者不甚满意。认为惯习实则是来源于个人习惯的辐射,笔者在试图找寻其辐射方法时,陷入了困境。因为这牵涉到一个问题:个人的行为方式实则包含着个人的心理动态、心理意愿等诸多主观因素。如果说行为习惯可以进行辐射,其实就是在说通过某种方式,可以使他人在被动的情形下接纳自身的主观因素,但从现代法治精神来看,人人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而我们很难依据解答一来给出答案。于是只能根据解答二,即惯习概念实则来源于群体之间的权衡与取舍,类似于团体间的准入规则。但问题接踵而至,以此而论,习惯是环境、个人心理因素的产物,而惯习是人类团体组织之间的规矩。这暗示着习惯偏向于个人性,而惯习偏向于群体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轻易从身边发现存在于群体之中的行为方式(并非指风俗、民约),这又如何进行解释呢?
四、习惯与惯习适用主体的实质
根据上文的论证,我们完成了关于习惯与惯习之间不同形成原因的辨析,但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在生活实践中,我们既可以观察到某种群体性的习惯(如好友之间逐渐培养成的共同爱好,一致性行为),同样也可以观察到哈特教授所例举的“进屋脱帽”事例,两者从主体层面来说似乎都适用于群体,都存在着一致性行为的外部特征。那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主体层面将两者进行细致的区分呢?实则不然。
从外在层面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习惯虽同样作用于群体,但作用力有限,其适用的主体范围程度远不及惯习,前者至多在某一小群体内存在着,当人数上升至较多数,群体就会开始呈现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就需要在该多数集体中产生权威,进行决断。于是被群体所认可的权威为了避免事件争议的反复发生而订立规矩,因此,原先适用于小群体之间的习惯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权威建立的新秩序。
但我们不禁要问,从习惯的消退至新秩序的产生,这种秩序是否就是我们称的惯习呢?笔者认为,还不完全是。如上所说,惯习实则为规矩,并且是由多数群体成员平衡取舍之后所订立的。而由于事件的争议,群体公推权威以解决纷争,权威将以制定规矩的方式进行解决,这似乎不符合前文已经论证的惯习产生的形式。但是,这种观点也可能遭到如下反驳:当公推权威时,这种公推的行为可认为已经代表了某种明示或者默示的权衡与认同,故而权威后面的行动已不需要群体进行新一轮的重新争议。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一个具有正常的,与智力状态相符的自然人的行为总是与其自身意志不可分离。但笔者又欲对此进行反诘:当发生如下两种情形时,我们是否都应认为惯习已经形成了?第一种情形:在权威制定规矩后不久又发生事件争议时,有人对于权威的地位产生质疑,但众人将以多少人的意志选择为由驳斥这种观点?第二种情形为:当离最早的权威推选已有一段时间,同样发生了群体中的部分人对于该流传下来的惯例的抗议,众人是否会以“这是早先人们传承下来的,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你同样也应该这样行为”为由予以反驳呢?这两种情形有什么区别呢?笔者认为,对于前者,是属于从习惯转向惯习的中间状态,而后者已经属于成熟的惯习。
五、习惯与惯习本体性质的异别
当我们面对某个具备群体性质的行为时,除去惯习所应具备的多数群体性以及历史性特征外,我们还可以从违背后所产生的后果来进行辨别。
当个体违背小群体之间的习惯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是该个体遭到非议,或受劝诫,或受舆论压力,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被驱逐出该组织。但如果与成熟阶段的惯习对比来看,由于该群体内部已经认为由权威制定了规则,将不会允许肆意违反者的出现,这时若执意与惯习对抗,不仅可能受到来自群体内部的舆论非议,还可能遭遇到某种特殊形式的“自力救济”。因此,如果在习惯与惯习被违反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不同的后果,可以将其原因归咎于是否存在强制力,以此作为辨别的依据。
但当我们追问,为什么习惯与惯习各自赖以存在的群体之间会有着强制力上的差别时,这样的回答是不够充分的。笔者在这里将引入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家科尔曼对于惯习的分析作为论据。科尔曼认为,承认规则实则是以内在观点与汇聚性行为两方面所构成的,即内在观点的作用在于将汇聚行为的行为性事实转变成为了规范性事实,所以内在观点不是信仰,而是人类作为规范所采纳的某一实践或行为方式的一种基本和重要的心智能力实践。笔者对此的理解是,内在观点的本质并不单纯地是人们心中的观念,而是首先从其作用出发:1.借此以确认事实行为形成规范、规则。2.以其为基础评价自己或他人。3.伴随着评价形成信念。这三者结合即是科尔曼所论述的心智能力实践。事实上,按照其理论,习惯与惯习外在表象上表现出的存在强制力与否,实际上与其本质特性不可分离。按照科尔曼对包容性实证主义核心概念——惯习的论述,其认为承认规则是由内在观点和汇聚性行为的结合,而独特之处在于内在观点这种呈现为心智能力的实践。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科尔曼口中的惯习与奥斯丁所说的习惯的差别在于,后者本质上仅仅表现为汇聚性行为,而不存在前者所重点论述的“接受”概念。
然后,科尔曼又借用了布莱特曼的SCA行为理论,以具体说明其眼中的惯习性规则。SCA理论主要具有如下特征:1.在群体中相互行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回应”的概念,即群体中的每一个参与人都会尽力和试图去对群体其他成员的行为作出反应,同时也将以他人行为作为指导,并且所有人都知道除己以外的其他人也都如此。2.在对于由个体行为组成的群体性行为观念上,群体中的所有参与人员都对群体行为有着认同感,虽然并不要求认同的原因相同,并且个人之间的相互回应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对于群体行为的认同”。3.在处理群体中相互行为之间的关系时,不仅存在着从己方发出的“回应性”信号,还会接收到来自于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同。布莱特曼认为这是由于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试图维持群体的稳定性,他人对于群体成员竭力作出的,对于他人行为的“回应”进行认同、认可都会更有利于群体组织的牢固。这亦是笔者所要明确的问题:在本质层面,习惯与惯习究竟如何进行区分?
综上所述,笔者在本节中的思路为:首先假设在除去习惯与惯习之间已经被论证过的“多数群体性”、“历史性”特征之外,仍然存在着足以辨别两者的根本不同,并从反面——违背时可能遭遇到的不同处境证明了这一点,即两者存在着“强制力”程度的特征。但这一点仍属于表面现象,仍存在着深层次的理由,故引用科尔曼关于惯习、承认规则、内在观点的新视角作为依据,并借用其对布莱特曼SCA理论的阐释,旨在说明习惯与惯习在本质层面的辨析方法:一方面可以从该群体性行为的外在表象入手进行区分——强制力有或无、大或小、仅限于舆论压力或是已上升为自力救济模式;另一方面可以从其内在进行辨析——群体中的成员是否对于他人行为有着认同,并会基于某种原因对他人行为积极地作出回应,以期许整个群体组织的稳定性。
六、总结
笔者尝试理顺习惯与惯习,目的在于指出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将个人习惯、群体性习惯、群体性惯习错误地混合在一起。这种观念不利于我国在法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本土优势。我们真正需要保留、继承的是那些在人民群体中已相对成熟的,群体内部的个体能够自发地做到相互之间的“回应”、“认可”,并对群体行为产生某种“认同”、“归属”感的惯习,而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将之发展为习惯法,认可或重新制定为法律。
[1]陈景辉.法律的界限——实证主义命题群之展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86-199.
[2]徐爱国,王振东.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0-110.
[3][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M].徐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75-86.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35-63.
[5][美]朱尔斯·L·科尔曼.原则的实践——为法律原则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辩护[M].丁海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35-286.
[6]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88-96.
[7]Michael E.Bratman:Shared Cooperative Activity,Philosophical Re-view 101/2,April.1992:382.
[8]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 06:99-126.
D90
A
1673―2391(2014)02―0067―03
2013-08-05责任编校: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