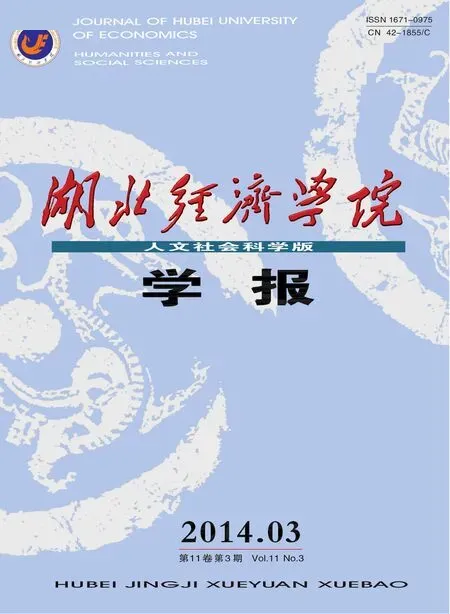藤本惠子文学中的美国人形象
韦 玮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1171)
一、问题的提出
藤本惠子1951年生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曾先后获得“作家奖”、文学界新人奖,两次获得芥川奖候补,2001年以《响彻筑地的铜锣》获得开高健奖。藤本惠子文学涉及到农村题材、团塊者题材以及边缘人物题材等方面。其农村题材小说《百合鸥》、《水芹》以日本战后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为时代背景,描写了阿雪、吉夫以及他们的孩子冬夫两代农村人的生活历程。其中《百合鸥》的时代背景正是日本从战败中恢复的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原本封闭的村落共同体的命运也受着美国的外力影响。
日本战后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就是在美国的“改造”下进行的,这也意味着对日本而言,它是被强行纳入了美国主导战后新体系当中。这样一来,现代化对村落共同体的冲击具象在农村主人公面前时始终少不了对美国人形象的审视。在美国人与日本人的对立冲突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先起”国家与“后起”国家的对立冲突。出现在日本农村主人公面前的美国人形象,既反应了农村主人公们审视美国人时的视角,同时也能看出形塑者本人审视全球化因素时所处的立场。
二、农村主人公对政治的远离倾向
农村有着天然的自我封闭的倾向。就日本农村而言,直至昭和初年仍占最大比重的农民一边耕作着世代相传的农田,一边生活在小村庄里。而那些共同体的约束一直作用着的村庄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地。即便到了近代,农民的小天地被卷进了货币经济中、受商品经济的冲击,但对农民来说,村庄仍旧是他们的社会生活关联最集中最稠密的场所。近代日本的社会,虽然称得上是亚洲唯一的工业社会,但仍然不能摆脱农业社会的性质,仍旧可以看成是农村性质的社会。换句话来说,即使不断推进近代化,但构成近代社会人口的大部分,还是那些从事零散家庭经营的农户、和数目虽有增加但与近代社会以前没多大差别的商业以及手工业性质的街道工场为主体的业主和家庭从业人员占大多数的人们。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百合鸥》中来自农村的主人公们所关心的也就是对与其生存有着密切关系的粮食、农田这样的问题,而政治、战争这样的宏大话题似乎是与他们无缘的。这突出地反应在日本战败消息传来的时候,城市、乡村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阿雪在城市听“玉音放送”的时候,可以听到“旁边的人哭了”。相比之下,宣布战败的消息在农村传开的时候,却近乎是一种黑色幽默的效果。吉夫告诉家里人日本战败这个消息的时候,吉夫母亲正是吃点心噎着的状态,又是喝水,又是捶背,最后终于好了。“好了!”是母亲恢复正常以后说的第一句话,父亲也跟着说好。这种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好了”跟战败这个原本应该令人悲伤的消息格格不入,似乎喻示着战争这样的话题原本就不属于农村,而对人的生存有着至为重要意义的食物相关的事情,才是这里人所关心的。
对来自农村的主人公们来说,政治、战争这样的语境不能主导他们的生活,对他们更有影响的还是土地这样与他们的生命原点农村联系更为紧密的事物。吉夫的哥哥英夫“最喜欢栽种完了的绿田”,甚至他在濑户内海训练的时候心里所想的还是琵琶湖,还是家乡的绿田,对他而言,“绿田就是一枚奖状”。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即便是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城市化的阿雪实际上对政治的关心固然有着染上城市人思维习惯的因素,但在这同时也有着极为个人的原因。尽管阿雪跟城里主人家关系融洽,甚至有了成为孩子母亲的错觉,但她毕竟只是一个佣人,并非真正融入城市。最终因为主人家婆婆投奔过来,使得原本就不宽裕的主人家无需再负担一个佣人,这也使得阿雪失去了这份工作,也就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而阿雪对政治的关心,也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虽说阿雪也关心“日本投降,会变得怎样呢?”这样的大问题,但实际上对她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是“自己一直做佣人的地方失去了,如何生存呢?”对阿雪这样来自农村的主人公们而言,他们所关心的永远是跟自身生存更为关系密切的问题。这也决定了当美国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审视美国人形象的时候,并没有一种政治上的敌我意识,而是完全站在自身立场上的。
三、农村主人公对美国人的审视视角
来自农村的主人公有着对政治远离的倾向,这也使得他们审视美国人时,并没有强烈的敌我意识。阿雪因为在舞场跟美国人跳舞,获得了他人的称赞,体会到了作为女人的自豪。在阿雪看来,美国人不粗暴、也不耍威风,还给孩子口香糖、巧克力,跟孩子一起放风筝,这都是日本兵不做的,这也让阿雪恍惚“这就是战败吗?”而阿雪的丈夫吉夫对美国人也有着好感,没有多少生意天赋的吉夫大赚一笔的石榴生意就是跟美国人做成的。其后吉夫、野田把美国人吃完的罐头收集起来卖给玩具厂,在洗美国人罐子的时候,吉夫、野田感叹美国人吃得真好,“战争输了,跟吃这么好的美国人打仗。”这也喻示着在藤本惠子的文学中,普通民众并不是通过所谓国家的敌我意识来看待战争,而是通过食物这个跟他们直接相关的视角来看待的。
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不能掩饰地位上的不平衡,等到美国人拿着枪来到阿雪家里检查粮食的时候,阿雪一家这才对美国人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先以跟美国人跳舞、获得他人称赞为豪的阿雪此时则感到跟美国人跳舞是一种耻辱,而吉夫这时候也感受到一种“敌方的”意识,对食物的差距感到一种“恐惧感”。但等到农田改革阿雪一家获得田地的时候,美国人的形象又变得高大起来。阿雪一家获得了田地,这被认为是美国人麦克阿瑟的功劳,吉夫母亲把筷子插在小芋上,模仿着麦克阿瑟抽烟斗的样子。此时的美国人麦克阿瑟简直就是一个救世主一样的存在,受着阿雪一家的尊崇。
从感到耻辱、恐惧到把美国人当成救世主一样的存在来尊崇,阿雪一家对美国人态度的转变正是源于土地对农村人的重要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都经历着物资短缺的问题。而农村虽说也谈不上充裕,但是跟城市相比,食物上总要好一些,这就归功于农村在供给食物上的功能。阿雪甚至还能藏着食物去送给城里主人家,体现出一种农村对城市的“救济”。有着高傲气质的城里人妙子,也曾因为缺乏食物的缘故,到阿雪家里,恳求换一些米,这些都能看出在农村特有的价值,也是农村人对农村感情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农村人对土地的感情又绝不仅源于土地在食物上的供给功能,实际上对农民来说,他们有着一种“恋地情结”,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多重混合物,即“与土地的身体接触、对土地的物质依赖以及这样的因素——土地蕴藏着记忆、承载着希望。”[1]也正因为如此,阿雪一家有了田地,吉夫母亲激动得又是感叹活着真好,又是想要早点到那个世界,告诉那个世界的亲人。在这同时,吉夫母亲也对吉夫、阿雪说可以把田地传给他们的孩子,这些都体现了农田在强化农村人代代血脉联系的功能。由此可见,吉夫母亲感叹“从此以后种田人的春天来了”,这话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并不仅仅指向农田的食物供给功能。
实际上,对农村人而言,田地还起着构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吉夫一直感受到地主家和小作人家不可磨灭的地位的差距,“从孩提时候就被无力感折磨”,在这个意义上,吉夫母亲说“种田人家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脚站立了”,这固然可以看成是经济上的自立,但还有着人际关系上的重新确立的意味。也正因为对农村人而言农田有着如此众多的重要作用,所以拥有农田的时候农村主人公们才会那么激动,而农田改革法又被认为是美国人的功劳,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吉夫一家对原本感到恐怖、耻辱的美国人变得如此热爱了。这背后所反应出来的,正是农村主人公们对政治的疏离感,他们审视“占领者”时永远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的,而所谓政治上的敌我意识,原本就不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起”国家与“后起”国家
《百合鸥》中农村主人公们与美国人的交集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日本战后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是对相对封闭的村落共同体而言,其内部成员的命运也牵涉到了其中。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而言,《百合鸥》中日本农村主人公们与美国人的矛盾、冲突正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先起”国家与“后起”国家的矛盾、对立。“所谓现代化,并不是多起源的现象,实际上,它是从“西方”这个且只从这一个起源所发生的现象。”[2]这也就使得从全球化背景来看,各国的现代化有所谓“先起”(carly starter)与“后起”(late starter)的区别,相对而言,美国正是这么一个“先起”的国家,而日本则属于“后起”国家。日本的现代化源头可追溯到明治维新,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为了巩固国防的,是为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所以,一方面在吸收所谓西洋文明的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近代产业,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搞的文明开化。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却极力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强调那种与西洋之“艺”(科学技术)相对立的东洋之“德”(道德),彻底鼓吹忠孝一元化的道德。这抑制了近代化所带来的市民们的觉醒,也死守了封建性质的家族主义,向人民灌输那些作为家族主义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性的神国思想。日本资本主义从开辟人类自由与平等的途径这一点上看,向来没有兑现过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历史性进步,人民始终没有和主权相结合,更不可能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因此,日本也只不过“形式上是近代国家”[3]而已。
从日本社会本身发展历程上来看,尽管日本的现代化由来已久,可是“在战前的日本农村,工业品市场就几乎没有侵入村落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村民并未得到多少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好处。”[4]但二战以后日本便把民主主义信封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开始实行各种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日本内部的自发性改革,而是在驻扎着占领军的情况下,不得不执行GHQ的命令实行民主主义这种新价值体系的”。[5]这也意味着阿雪、吉夫他们被卷入的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美国人影响之下进行的,这也使得阿雪他们审视现代化实际上是包含着审视美国的内涵在内的。
对阿雪他们来说,他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感知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之上的,《百合鸥》中提到人们对战败与其是一种失落感,倒不如说成是终于从轰炸中解脱开来的安逸感,亦即 “支配着日本国民的是一种怅然若失的虚脱感和从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安逸感。而且,在不明智的战争所带来的贫困中,人们首先要为糊口而疲于奔命。”[6]这种为糊口而疲于奔命正反应了对人的生存来说,食物才是最为重要的,阿雪他们对美国人的审视视角,并没有一个固化的政治上的敌我意识。而从历史因素来看,让阿雪他们把美国人奉若神明的农田改革,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在美国人主导下,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环节罢了。战后日本经济复兴需要增产以廉价大米为主的粮食时,日本政府设想出耕地改革的方案。而这一方案又是在占领军的指令下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的,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日本农业“最后还是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遗弃。”[7]但对阿雪他们而言,他们对农田改革法的审视既无政治立场上的视角,也没有经济立场上的视角,完全因为出于对农田天然的情感,这才把原本是“占领者”的美国人麦克阿瑟当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美国人在农田改革法上所起的是一个“外生因”的作用。后起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内生因”与“外生因”的区别,一个社会系统要发生结构的变迁,必须有引起变迁的动因,即行为的动机原因。这种动因自生于该社会系统内部时即为“内生因”[8]对后起国家来说,“它们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多赖于外生因”[9],日本的农田改革固然有着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没有美国人这种“外生因”的作用力,又是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所谓农田改革也经历了两次,第一次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第二次在美国人的干预下才有了较为彻底的改革。这么来看,《百合鸥》中吉夫一家对美国人充满了崇敬,这倒也正形象地反应了在日本农田改革中美国人的这种“外生因”的重要作用。
也正因为这种“外生因”的重要作用,阿雪一家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麦克阿瑟,根本就没人想起来这田原本是从何处来的,没人想到这事对地主的伤害。只有等地主自杀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才对这事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为了镇压村人的动摇,民主主义、权利等语言发布到每一家。”日本的农地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美国占领军的指令,“作为民主化的一环”而进行的改革。”[10]但对阿雪、吉夫所在的村落共同体成员来说,“民主化是农田改革的一个环节”这种说法似乎要更为合乎他们所处世界的逻辑。
五、总结
藤本惠子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所描写的是日本农村从战后恢复、进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从属于日本战后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这个大背景当中的。农村作为村落共同体有着相对的封闭性,日本农村的封闭性直到明治维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在战后被美国强行纳入全球化进程中的背景下,原先的村落共同体也受着现代化的冲击,个体命运也愈来愈与外界联系更为密切。
对村落共同体当中的成员来说,相比较政治、国家层面的因素,农田这样与他们的个人生存更为有着更为紧密联系的事物才是至为重要的,这也就使得他们审视美国人形象时,完全没有一个固化的敌我意识内涵的视角。在《百合鸥》中,就连诸如民主、权利这样属于民主化改造的词汇,也只不过是用来为农田改革服务、用来平息人心的不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形塑者本人的态度,亦即形塑者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美国人“外生因”的描述上,而是更为关注日本农村主人公对这种“外生因”的审视视角,由此可见,形塑者对全球化因素是一种专断的态度,并非着眼于美国人的形象本身,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日本人的视角之上,关注作为接受主体的日本人所采取的是怎样的一种审视视角。
(注: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子课题:“藤本惠子研究”(批准号[2010]2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tuan yi-fu topoph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97.
[2]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M].董兴华,译.云南人们出版社,1988-12.10.
[3]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M].陈曾文,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3.
[4]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M].董兴华,译.云南人们出版社,1988-12.66.
[5]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M].陈曾文,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66.
[6]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M].陈曾文,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65.
[7]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M].陈曾文,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78.
[8]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M].严立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92-03.250.
[9]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M].董兴华,译.云南人们出版社,1988-12.193.
[10]关谷俊作.日本的农地制度[M].金洪文,译.三联书店,200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