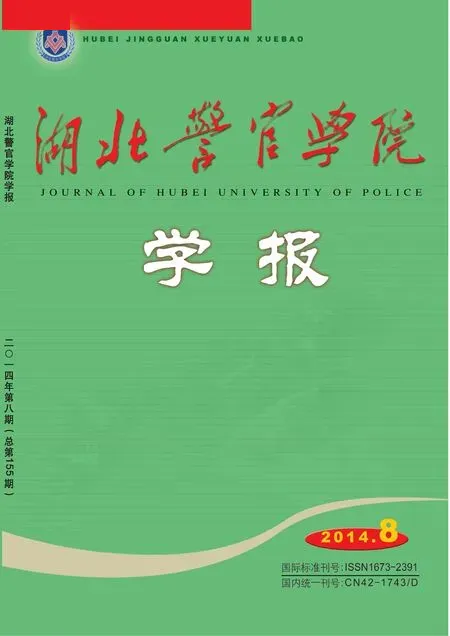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探究
——基于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冲突的反思
韩振文
(华东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中心,上海200042)
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探究
——基于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冲突的反思
韩振文
(华东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中心,上海200042)
构建法制权威的关键是认清权威确立的正当性基础。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之间发生冲突的本质为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它是通过合法律性抑或合道德性而获得的。须警惕通过合法律性建构的法制权威正当性沦落为专制统治工具的可能。为克服其正当性危机,要经过合道德性的检验矫正。人性需求奠定法制权威正当性的根基。法制不仅仅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治理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信念,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法制权威的正当性要求法律者受规则约束,但也有必要适当考量适用法律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法制权威;正当性;法的安定性;个案正义;合法律性;合道德性
法制权威的正当性是任何民主法治国家须审慎对待并建构的重大命题。权威是建立在合理性及必要性基础之上的自发接受服从的制度化。应当看到,当今中国似乎滑进了某种“零权威”的陷阱,而就法治国家建设而言,首先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1]深化改革背景之下的中国,面对疑案错案的频发、社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异军突起,对于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的探究与解答呈现诸多分歧与论争。以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冲突的反思为视角,深入考察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为此需要进行学理上的系统梳理与革新,以此增强立论的现实解释力与批判力。
一、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的范式转换
法的安定性一直是法律人孜孜追求的目标。为了确保法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法被赋予权力意志的力量而获得有效实施。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就认为法律是主权者以权力实施的命令,通过法律强制力控制社会的解释活动。功利主义改革家边沁以及“现代英国法理学之父”奥斯丁都在分享霍布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使法的主权命令说大放异彩。①边沁相信政府拥有良好的控制和改革能力,能够建立其公正而完美的理想国家状态,为此毕生实践计划着建立以革命性的设计为基础的圆形监狱,而法律作为改革的工具,通过发挥法律惩罚和制裁的特有功效,以痛苦相威胁,直达人类避免痛苦的本性,预防和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来增进社会的总体幸福。奥斯丁则站在法律和道德分离的立场上,认为准确意义上的法即实在法乃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在对实在法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法理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更是直截了当地将法律看作是社会控制的工具②庞德指出,法律就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依照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的权威性律令来实施的,具有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页。。用一句形象的话表述:只要法安定性存在,哪怕世界毁灭。诚然,法为了自身的安定性在某些特定情势下遭遇了异化,不免走得太远,乃至为专制政府所利用而变成奴役人民的手段。③在某些特定历史环境中,法被当作政治优势者进行统治的工具,体现出的是专制者的个人意志,比如在古代东方君主极权国家,法律仅是帝王牧民的器具。从人类历史的主流发展脉络中,我们发现法律作为规则治理的事业,仅从价值无涉的角度看待法律的功能,法律确实是不自觉地作为安定社会秩序和保障社会良好运行的控制工具。然而,对法律的理解停留在此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法制权威理念的形成绝不仅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之上,恰恰相反,法制权威可让强制内在化,变成自觉的行动。
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之间的冲突如何权衡?这一历史性难题在不同社会结构语境下给出了不同答案。传统的法律理论认为,这种冲突实质上是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之间的竞争。著名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可谓是应对此问题的经典之道。德国法律思想家与人本主义者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认为,“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冲突可能可以这样妥善解决:通过法令和国家权力来保障的实在法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即便其在内容上是不正义的、不合目的性的;除非当实在法与正义之矛盾达到如此不能容忍的程度,以至于法律已经成为‘非正当法’(falselaw,unrichtigesRecht)时,法律才必须向正义屈服。在法律的不法与虽内容不正当但仍属有效的法律这两种情况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不可能的,但最大限度明晰地做出另外一种划界还是有可能的: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当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2]当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之间发生冲突时,自然法被视为源于事物本质的超法律法,实定法须让步于自然法,随之丧失效力。裁决者为何舍法实证主义而取自然法,甚至赋予公民反抗权或曰善良违法的权利?取舍的要义在于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存有优先次序。法实证主义是通过合法律性而获得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而自然法是通过合道德性而具备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当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发生碰撞时,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天平趋向了合道德性。其实,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发生这样的范式转换,其蕴含的道理并非复杂神秘。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法制权威正当性的基石在于法制能够满足人之为人的需求与期待,体现对人的尊严及价值的深切关怀,使人过上应得的、可能的德性生活。由此,合道德性的法制权威总是显现出比合法律性的法制权威更强的信赖度与优位性。
二、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的工具主义批判
通过合道德性获得法制权威的正当性,植根于国民对法制的敬畏与信赖。法律体系在形式上要求规范承受者个人或集体遵行和服从,而规范承受者个人或集体自愿遵行和服从法律,必然来自自我的内心认同与接受。[3]法制从终极意义上来讲是一种信仰,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属性和良好品质,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与文化力量。国民从内心深处认同信仰法律,形成法律至上的文化,才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根基。反之,国民基于内心的信念,对不公正的法律也可拒绝服从。有良知的法律人应该超越法律文本,去探寻法律背后的规范意旨。毋庸讳言,法制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依归,旨在实现人类的最大福祉。换言之,法律制度的设计最终是为实现人权服务的,而不应成为奴役人的枷锁。法制之中包含着人情冷暖,当一个法律人有了人情味,具有人文关怀、为民之心时,才更能理解法制权威正当性的真谛。
法律作为“公意”的体现,蕴含着真理共识与人文关怀,这成为捍卫法制权威、坚守法律信念的充足理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事实与价值存在永恒的张力,法律的应然追求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自由平等保护的实然结果。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通过合法律性获得的法制权威,存在着被专制者利用来摧毁人类文明的危险。必须认识到失去道德性基础的法律很有可能沦为专断独裁者实施暴政的工具,因而,法律人有义务与漠视人类本性、践踏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恶法”而战,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审视辨别何为“法之上法”与“法之下法”。其中,在法律创制与实施过程中,扩大中立的民主参与渠道是一条重要的审查、矫治“恶法”的进路。法学作为精神科学的正义之学,有时竟被专权者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用来作为践踏良知、残害人类的借口,比如德国纳粹利用法律将犹太人变成次于人类的物,进行野蛮的种族灭绝。对法律“工具主义”标签的迷恋与崇拜,应当引起现代人的警惕与深思。为了克服合法律的正当性危机,法律人要时刻扪心自问“良知”的标准是什么,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并以客观批判理性的眼光审视世界,坚守住内心的正义法则。
面对当下司法公信力孱弱的现实,司法从业者首先应善待违法者的生命权,因为生命权是行使所有权利的基石,是不可克减的权利。倘若司法者无视人的生命,以致徇私枉法、恣意裁判,也就泯灭了最基本的良知。
另外,立法者也有可能异化为少数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打着制定致力于实现公共福祉的法律旗号,出台训诫控制国民意识的“伪法律”。此时,对“伪法律”或“恶法”进行道德性评判与指责,揭露其支配行为的违法性就成为有良知公民的义务。现实中的法律并非是完美自洽的,德沃金试图构建的整全性法律事业只是一个高贵的梦想或虚饰,但其蕴含的对法律至上权威的推崇、公平正义的价值希翼、人权的尊重保障以及对公权力的限制等因子的法制却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应该被信仰。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的工具性批判,引导我们把视野转向法治。法治下的法律是良法、善法。法律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信念,蕴含着人文的关怀,这是良法状态下的表现。因而,我们需要以法治要素为评判标准,对现实生活运行中的法律进行审视和检验,敢于对抗严重违背社会良知、突破伦理道德底线的恶法。一旦法律失去社会道德运行的基础,就应被改造或废除。“孙志刚事件”、“成都拆迁自焚事件”等悲剧的出现说明我国虽人权入宪,但次级的法律渊源的合法性需要违宪性审查,执法者的现代法律意识需要提高,国民人身财产权益得到全面的保护需要有良知的法律人及全社会长期的努力。总之,我国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仍面临严峻考验,法治中国建设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三、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的案例审思
上文对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的范式转换及工具主义批判的阐释,主要采纳的是价值评判的理路。而要想对法制权威正当性基础论题作形象本真的理解,需结合典型的案例分析,以此较直观地透视把握。
以下选取历史上发生的两个著名案例——“纽伦堡审判”与“柏林墙枪杀案”作为分析样本。“纽伦堡审判”的基本案情是:1945年11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法院正义宫开庭,二战战胜国对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审判。23名被同盟国认定为“主要战争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纳粹战犯提出辩护理由宣称:战胜国和盟军无权对他们进行审判。他们是在执行战时德国的法律和战时元首希特勒的指令,因为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他们杀害盟军军人和犹太人是在执法,所以他们没有犯罪。二战后从实证分析法学转向复兴自然法学的德国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法官们同他的这一思想达成了共识。法官们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最后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战犯的抗辩理由。①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详细法理分析,参见徐显明:《大学理念与依法治校》,载《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第8期。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判决书全面系统地揭露了纳粹首要战犯的反动历史、残暴手段和罪恶目标,历数他们惨无人道的野蛮和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判处12人绞刑,3人无期徒刑等,纽伦堡审判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柏林墙枪杀案”的基本案情是:1992年2月,德国统一后的柏林法庭审判柏林墙推倒前东德的一个守墙卫兵,因为他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柏林的青年克利斯。这个士兵的律师辩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柏林法庭最终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不难发现,以上两个案例具有相似性。两案的被告都提出了相同的抗辩理由,那就是他们的行为都是在执行法律的命令,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遵守法律的指令,因此,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行动产生的后果不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的抗辩理由是否充分合理呢?当时的法官都给予了否定回答。两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权衡、抉择法制权威的两种正当性基础——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换言之,基于道德法则的价值评判在何种程度上才能推翻实在法限度内行为的正当性?
纽伦堡审判中包含的法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如果国家发布的命令是完全应受谴责的而且其不合理性已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那么抵制执行这些命令的权利在某些情形下可以转变为一种不遵守这些命令的法律义务”。[4]这样,“恶法非法”的观念被广泛地接受,实证主义分析法学受到强烈冲击而逐渐衰微,自然法学得以复兴而再次逐渐强盛起来。在“柏林墙枪杀案”中,法官回应被告的抗辩——“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其道德性论证足以让人感到沦肌浃髓的震撼。总之,两则案例中法官作出的有力阐释扫清了焦点争议的迷雾:通过合道德性获得的法制权威高于合法律性获得的权威。不可否认,学者站在法的安定性立场上,从分析哲学视角把握实在法效力,具体剖析法律体系的要素(如概念、规则等),视受实在法支配约束为法治国的核心,①对此论点,有学者阐述道:在今天,我们受到“合制定法性原则”的支配。我们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第20条第3款明确宣称:“执行(也即行政)和司法(也即法院)受制定法和法的约束。”这是我们国家“法治国”的核心方面。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一来可把法律的技术性操作运用得更加纯粹娴熟,二来可以维护法学自身的自足自治性,保证其自组织能力的发挥。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贯彻实施,当实在法与个案正义发生冲突,法官若严格依据法律作出裁决而严重违背道德准则,甚至造成对人性的践踏时,那么他就必须保留个案正义,服从法之外更高的道德伦理准则,以此推翻实在法限度内行为的形式合法性。把遵守法律颂为美德无可厚非,如像苏格拉底那样为守法而殉道,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放弃了对法律道德性的批判与质疑。有时在特定时代,温和的不服从比屈卑的顺从要来得更迫切。在合法律性下建构的法制权威正当性,必然倾向于把法律当作社会治理工具来看待。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说,人类是有能力改良或抵抗“合法”外衣下的非正统性统治,并克服合法律性危机对权利自由的束缚剥夺的,而不是一味地陷入法的形式结构中,不去关注社会现实的伦理动态,不去审查法得以实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外在辅助性因素。要知道,“法律人如果夸大规则和概念的稳定性,机械教条地理解法律,对概念作形式化理解,有时也会背离真理、违背正义。”[5]因而,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当然要求法律人受教义学规则的约束,但绝不意味着法律者完全拘泥于逻辑规则与形式概念。面对呆板的法律与鲜活的生活,法律人也有必要适当考量适用法律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就是学界指称的“超越法律”。
结语
实现法制权威是现代法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而法制权威不强、公信力缺失是长期困扰我国法治化进程的瓶颈与顽疾。构建法制权威的关键是认清权威确立的正当性基础。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之间发生冲突的本质是法制权威正当性的获得是通过合法律性抑或合道德性。实证主义分析法学通过合法律性构建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易倾向于奉实证法支配为圭臬、视其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以至沦落为专制独裁统治的帮凶。孰不知,“在失去了高贵的德性和伟大的理念的社会里,人们非常容易形成集体堕落,而且不参加堕落都不可能,集体堕落完全可以形成某些非常恶心的普遍标准和规范。所以,仅仅考虑形式的合法性,对于社会和生活是远远不够的。”[6]通过合道德性获得法制权威的正当性,植根于国民对法制的自觉认同与敬畏。法制权威的合道德正当性高于合法律正当性,因而前者可对后者进行必要的检验与矫正。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奠基于人性的需求根基,所以说,法制不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强制性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信念,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反观我国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仍面临着严峻考验,法治中国建设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1]季卫东.论法制的权威[J].中国法学,2013(1):21.
[2]Gustav Radbruch,Statutory Lawlessness and Supra-Statutory La w,trans.By Bonnie Litschewske Palson and Stanley L.Polson, 26 O.J.L.S.,2006:7.
[3]舒国滢.法哲学沉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8-223.
[4]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67.
[5]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两元论——兼与苏力商榷[J].中外法学,2 013(6):1119.
[6]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3-1 04.
D90
A
1673―2391(2014)08―0058―04
2014-05-02责任编校:江流
受上海市地方高校大文科学术新人培育计划资助,并受华东政法大学“未来法学家·学术之星”培养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