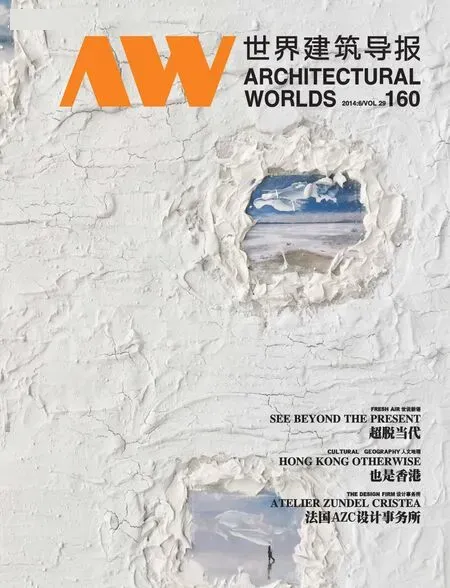城市权:重新审视革命与城市的千年
(文)刘烨
一 革命的降临
当我们撒开想象谈论千百年后的城市之前,我们不如先从反方向回顾下遥远的历史——如近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由于周厉王与民争利且辅以严刑峻法,并动用“卫巫”监视都城民众的的“反动言行”,持久的高压最终导致人们不堪愤怒,揭竿而起,围攻王宫。厉王渡河逃遁,后死在异乡。这一场可能是中国最早明确记载的城市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产,它不仅在很长时段内标志着中国历史准确纪年的开端——北京建于1999年的中华世纪坛的时间轴即以此开始;它首次诞生了“共和”一词——前841年也史称“共和元年”;它还贡献了“道路以目”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经典成语。在共产主义立国之后的史书中,这一事件又赋予了光荣的阶级斗争的色彩而更熠熠生辉。
有趣的是,正如卡斯特(Castells)所说,革命总是发生在城市。即便是在农村人口占绝大部分的古代,城市依旧扮演了人类生活的主剧场。因为,那里有文字,有祭司,有华贵的衣装、有大体量的公共建筑,有一切能将自然转化为人文的神奇魔力,那里是高高在上的被瞩目者。至少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倾向于将早期城市的出现视作一种文明的确立标志,而city一词本身和civilization密不可分。希腊的雅典,罗马帝国的罗马城,汉唐的长安,这些伟大的城市不仅成为其时代众生的灯塔,更是形同其文明的化身,带有挥之不去的神圣感。
为何革命者总是要夺取城市?当然,防御,粮草、交通,经济,通讯和其它物质设施的优越使得城市成为重要的资源,为武装力量提供了现实的支持。另有一重要的原因则是城市的中心性,这中心不仅体现在能用物理单位丈量的世界,更是体现在心理与文化认知上。城市是合法性的来源,是对于人类秩序最高层级的想象。夺取城市意味着屹立于秩序中心,掌握权力,俯瞰芸芸众生。城头的大王旗则是占城者的空间宪法。若某支势力即便占领了广袤的农村,也即便实质性地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地域和人口,也始终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难以摆脱后世史书赋予他们的游击或流寇的形象。当然,这一形象到晚近也发生了翻转。游击战作为一种战略被毛泽东确立并在第三世界多支武装力量中获得巨大的反响,并沾染上了浪漫的色彩。但是,这依旧是一种战争方法论,一个剑走偏锋的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毛和他的革命军在农村和边区摸爬滚打多年后,终于进了城。可以想象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建议中共在北平城外建一新城的方案(即“梁陈方案”),毛被冒犯的感觉可想而知,他们这群“敢叫日月换新天”先锋队好不容易进城了怎会“拱手相让”。尽管梁思成等人的提议至今看来引人入胜,但专业的城市规划及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怎能抵得过领袖在城市的政治象征与布局上的权重。
在列斐伏尔所谓的神圣空间的年代,城市自然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那些给他们施以阳光和雨露的统治者,城市按照后者描绘的圣境存在着,普通市民被安排在那个由赞美诗和王室血脉交织而成意义之网上。他们“在古老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他们又是“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象谜一样”。这一切在1789年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大转折,法国大革命,热血沸腾的巴黎市民发动起义,攻占巴士底狱。这绝不仅关乎巴黎,甚至不仅关乎法国,这是作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而成为近代史的起点。在那之前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书斋里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人民”和“公意”并为普通人的生命辩护,它们连篇累牍的信札、笔记和沙龙上的谈吐终于在那一年催生了直接的政治行动。1789年,巴黎是起义的首都,从这个城市开始,“革命”走向世界。市民起义的神话意象延续了两个世纪。在那之后的整整两百年后的那一年里——这是一个多么整齐的历史单元——学生与市民在东方古都的广场上
安营扎寨。这个广场本只是一块小空地,伟大领袖为了营造万众一心的场面而多次将其扩建。人民一次次被召唤到这里配合完成多种政治仪式。世界上也许很难找到一个如此高强度地浓缩了大量政治符号的地方,重檐歇山的城楼是国家诞生的地方,领袖的巨大肖像至今注视着广场上的一切,而他的不朽的尸身正躺在广场中心的一座殿堂里——没人知道他到底能否听到外面的响动,在城楼与纪念堂之间的是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周身以浮雕刻画着“人民”。然而在那一年,广场上的人希望将这些既有的符号重新诠释并据为己有,他们甚至还创造了新的符号:雨后春笋的帐篷,一座纯白色的石膏女神像在——她一个闪光灯疯狂闪烁的夜晚在众人簇拥下来到广场,更有用道路护栏临时搭建的路障——尽管什么都没挡住。这些大众革命的热血符号让他们做出了不顾后果的抗争,也让他们遭到了彻底而原始的殒灭。这不仅是这个古国,也似乎是全世界广场政治——两个世纪的热血与浪漫的宏达叙事——的绝唱。尽管在其后也有零星的个案上演,但已不成气候。
二 城市现状与城市权转移
中国的城市从上世纪中叶以来也许更能贴切反映出把急剧激烈的意识形态变迁。在资本的力量遭到禁绝的毛时代,国家权力以取多种力量而代之开始空前活跃在舞台上。在国家编织的宏大叙事中,城市空间被置于一个落后-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陈腐的-新生的等诸多二元对立的阶序里,成为意识形态最视觉化的载体。在共产中国的话语里,建筑必须是高大、阳刚、宏伟、质朴、对称。其它的美学形式则被视作腐朽堕落或病态可怜的。在这一阶段,吐露着浓烟的烟囱、厂房和整齐划一的集体公寓楼成为时代美学的宠儿。领路人要努力将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画卷涂抹洗白,并在白纸上描绘空前的蓝图。他们迎击未来的狂热与摆脱祖先阴魂的急迫同样的强烈不可遏制。"我们伟大领袖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遍地的烟囱",城墙的拆除,古宅的摧毁,街道的重命名,都昭示着一个新纪元的横空出世。城市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具有多重甚至是相反的意向。工业化是城市的勋章,在共产党人看来,城市应该和工厂是同构的,从建筑布局和对人员生活的安排都在模拟一个巨型的工厂。以至于那时的人们常常用“热气腾腾”、“热火朝天”来描述城市。此外,还有贯穿数十年的单位制在城市中的全面施行,所有的市民属于这个或那个单位,单位连着住宅、医院、托儿所、学校、体育馆,全都自成一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集中体现场所,也是国家实行控制、教化与动员的大本营,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能在单位里面已经很幸福了——至少说明你属于20%的城镇人口。似乎一切都有保障,从来不多,但是有。在另一方面,在毛时代的的禁欲主义中,城市又成为享乐、安逸和好日子的象征而与乡村作为朴素革命的符号区分开来。尽管重要,却始终不如乡村那么单纯而正确。当为了在经济凋敝的环境下“减轻国家负担”,也为了控制城市中混乱局势的蔓延,两千万上下的青年人“上山下乡”,胸前戴着大红花从城市到农村,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以整幅头版的位置刊出了经典的《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把下乡描绘成自愿吃苦、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光荣举动。如果我们站在当时横向参考着了解,会发现这实际上绝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与同阵营的苏联东欧诸国相比,中国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城市化水平之低也有其政治的独特因素。如果我们接受将社会主义的选择视为一种快速现代化的实际策略——高度集中统合下的各种严整的计划和实施,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带有较强的草根性和分散性。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洁癖和领袖对大众积极性的要求或期望,在红-专两极的不断撕扯摇摆中,专业化、技术化的进程一直受限,大量的技术知识分子或专家并没有因为政治服从而获得重用——像苏联那样,而是被持续地边缘化。正如用于嘲讽苏联的《马钢宪法》——强调自上而下的专家管理——而出现的《鞍钢宪法》,也如大跃进中“小土群”的崇高地位,中国的城市仅作为工业基地的地位也是一直被不断动摇的,也一直未能“坐大”。作为社会主义梦想的集中化、大规模的工业化在中国未能完全铺开。当在苏联和美国的城市化不相上下时,中国还是个农业人口占八成的国家。
要不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今日的城市会和毛时代的有如此的天壤之别。高度原子化而同质化的个体、对本国传统的离间、对富裕的渴望、缺乏道义与文化资源的心灵,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渴望资本、渴望想象的现代化、渴望赶超西方的领先者。在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开启后,城市迅速地从共产主义僵化的盆景变成了资本的生产机器。上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城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剧烈变迁,每一个城市都如此决绝地和它们的过去断裂开来,而每一座城市又如此地相互雷同。这一切都集中地指向中国改革开放后权力和资本的高度结合,它们以此强大动力推行了城市空间大规模高速度的再分配和重构。无数的旧城因其楼房低矮且容积率小而被认为没有经济价值,而其市中心地位又使其被觊觎许久,最终逃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至于那些暂时没被拆迁或改造的旧城区来说,早已惶惶不可终日地感受到资本的猎犬在他们身边嗅来嗅去,腥咸的唾沫,粗野的呼吸,暂时没有下嘴只因其它现实的考虑。对于大量的以拆迁和重建为主的城市,所谓城市更新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过程。一方面“钱生钱”的资本的积累和城市设施完善,光鲜的外表似乎映证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另一方面,关于城市的历史,文化,社群甚至与山河等都被简单的抛弃。抛弃不是被忽略,相反,他们被"高度重视",正是他们被安排好的死亡才为另一组图景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是一个资本最优的过滤机制,城市就被政商精英视作生产GDP的工具或容器。而关于城市的一切都必须在资本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个法庭只问唯一且愚蠢的问题——你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便急不可耐地敲下法槌。在这部法典里,整个世界被描述成由且只由两部分组成:资本,及其铺路石,不存在例外的命名法则。当列斐福尔在纪念《资本论》问世一百周年时发表的《城市的权利》时,他极有洞见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与空间生产的批判理论,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多年后会有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同时却又是开放资本的诡异政体。在他的时代,也许无人相信会存在这样的四不像。
三 权利还是权力?
武装夺取城市还有可能吗?游击队还有可能吗?巷战还有可能吗?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面临着诸多明显的压迫,我们今日的想象力和勇气也遭到了极大的限制。市场的流动性和扁平性,对立阶级的模糊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已不存在,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相互握手言和,国家权力的整体膨胀和保护公民自由的具体法条微妙地互相适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尽管利益对立——却在观点上从未那么接近过,似乎一切截然对立的东西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可控的差异——为装点世界的多样性及保留最后的一丝异国情调。世界上只有一套学说,甚至是一套语言。当人们讨论巴黎的拉丁区、北京的天安门时,只剩下社会科学话语里那些貌似深刻而冷静的术语,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思潮、政治机会结构和动员策略,却无心也无力体验到当时的反抗者们宏大而无疆(亦无缰)的视野与彻底的梦想。总之,一切基进的想法甚至连被批驳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被认可为一种想法。基进主义的土壤完全地退化了,它们的言辞顶多作为檄文而不能用作作战计划图。
迄今为止,我们能在公共平台看到的关于城市思想最“基进”的思想也许只能数到巴黎人列斐伏尔首次提出的the right to the city。关于the right to the city,大卫哈维在2008年的New Left Review上明确指出,这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口号。城市权指市民或城市居民有权参与进任何形塑或改变城市空间的决策过程中。居民不应被动地像棋子一样被政经精英安排,而城市不是后者的一盘生意,市民——如同公民之于国家——应有权决定自己所居住的空间。和众多的权利声张不同,首先城市权是一项集体权利,属于市民或人民;其次,城市权的重点在于空间、文化与归属,而非单纯的能用经济和法律关系清晰衡量的一种权属。
不过,我们在right to the city之外,能不能设想一种power to the city?对城市的权力?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认知上的权属,一种正当性要求;后者则直指对城市的行动力、影响力或力量。尽管power和right——尤其在中文语境下——常常以一组对立的面貌示人,但二者真的能分开吗?在福柯与乔姆斯基的“世纪辩论”中,福柯
直接引用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战争就是为了胜利,不为其它。这显然让富于人道热情的乔姆斯基十分尴尬——他不停地强调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性,认为战争不能不谈意义和价值。我所能找到的毛的原话也许是这句:“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斗争学上来说,这绝对是清醒的认识。这提醒反抗者,不仅要有理,还要有力,否则只能郁闷地将世界让于强大的对手,陷入温迪•布朗批评到的“左派忧郁症”。试想,在肉体消灭意义上的革命如果不存在,那城市革命可以怎样发生呢?
2011年11月,在占领伦敦的“主场”圣保罗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戴着红色围巾的大卫•哈维在人群的欢呼中出现在现场,他为人们的占领城市空间的行动大大地激励,认为这样的意义不亚于对经济不平等的控诉。这一点在理查德•桑奈特(Richard Sennet)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他指出空间与权力的问题才是占领运动最宝贵的遗产。也许空间是个启发,正如领土对国家的意义一般,在实体的世界,空间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就像领土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在实体的世界里,空间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对所辖空间(一个power container)进行规整化是一切当局者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会尽可能地消灭异质的、有争议的空间。而对空间的非正常通过(比如游行)甚至是长久驻留(如占领)更会让他们不安,因为对空间的失控是对其权威潜在的肢解。因此,当肉体上的消灭或被消灭不再成为一种方法,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空间争夺来进行革命。实际上,我们看到,近年来在纽约、伦敦和香港等传统的自由社会都爆发了以空间为主题大规模社会运动。在这里,社运就是以人群在实体空间的聚集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抗争,它就是要以空间为杠杆对当权者制造骚扰、破坏与不确定性,从而撬动原有权力结构并伺机重塑社会-政治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肉身和空间就是大众能拥有的武器。社会运动总是发生在实体的公共空间里,而不是在报纸上、网络世界中、教室和图书馆里。从华尔街到圣保罗大教堂,从天安门到中环,无论背后有怎样复杂的不同,运动落到实处便是一种空间展演与宣言,而受控空间的此消彼长是运动者与当权者的实质语言。
我不得不专门提到2014年9月底爆发的占领香港运动。这个绝佳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如何通过争夺城市来进行政治斗争的。占领香港是一场游击战,一场肉身-空间的战争。由于示威者和警察谁也不会再肉体上消灭谁,因此,斗争的关键在于物理性、肉体性地占据尽量多的空间,扩大势力范围,并在时间上尽可能持久。占领本身就是权力的表达与演练,占领本身就已是直接从事政治——只不过不是通过程序,而是直接动用操持权力。基于同样的理由,警方的一切做法就是要将示威者驱逐出特点空间,夺回对空间的控制,消灭市民在空间上的展演和可视性,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无形的碎片而丧失攻击力。尽管不会开枪,但是他们依然会千方百计的让抗争者一方“减员”,比如,殴打、喷辣椒水、抬走、施放催泪瓦斯(驱散同时施加身体不适)、切割、阻断、包围。这些做法一方面将空间里示威者赶出,另一方面防止更多示威者前往支援,最后实现清场即空间秩序的平复。警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在此凸显无疑。而示威者自然要发挥其游击性,他们利用人数众多,灵活机动的特点,四处“点火”,引得警方疲于奔命,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出现、扰乱、冲击秩序。这也许就是“占领香港、遍地开花”的精髓所在。在那段时间,我们能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示威者不断地呼吁“场外”加入,而又不断地呼吁市民在具体地点对警方实施“反包围”,这些战术概念充分体现了以肉身-空间作为武器的抗争运动的巨大威力,它展示了人们如何借助城市向统治者发起挑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夕岸”凭借其在场观察对金钟、旺角和铜锣湾三个最重要的示威地点的作了详细的空间分析,包括建筑与街道、人群构成、传播方式等)。人们不仅在呼吁要实现法理上的权利,更是以直接的行动实现和运用权力,这样的权力应该可以视作“对城市的权力”(power to the city),它至少昭示了一种未来“城市革命”框架。因此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挖掘的个案,无论是持“占中”还是“反占中”立场。
一种权利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权力才能实现,否则只是一纸空文。什么是权利或怎样的权利的确在不同的时空脉络下充满争议,很难等到问题获得统一的答案——事实上可能也不存在这样的答案。因此行动起来,在行动中解决问题,将政治带回公共生活。这样行使“对城市的权力”就不失为一个现实的选择。城市始终是个政治场域——除此之外的未来难以预测,无论是right to the city还是power to the city,都指向城市行动主义,它让我们在回答更多问题之前,先回答这一个问题:如何让城市继续成为行动的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