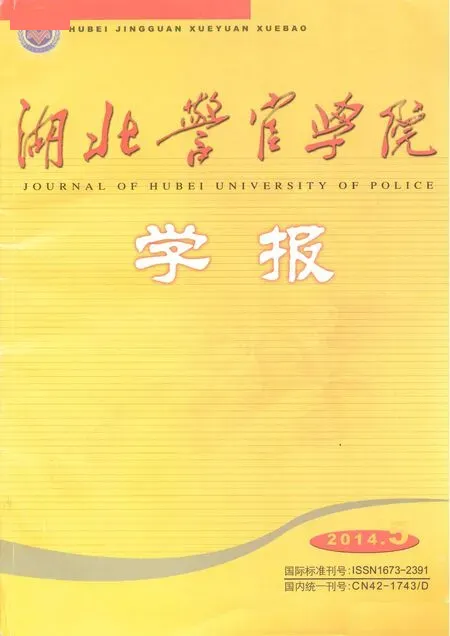《唐律》类推制度探析
程骋
(湖北欣安律师事务所,湖北 武汉430062)
《唐律》类推制度探析
程骋
(湖北欣安律师事务所,湖北 武汉430062)
唐律规定,如果“一律内,犯无罪名”,则“类举以明出入轻重”,即可以运用类举来定罪量刑。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法制史、刑法史著作,在谈及唐律的类举制度时,都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类推。但从唐律及其疏文来看,其对于性质相同但情节不同的事例所作的类举并非现代刑法的类推,而应属于一种当然的解释;其对性质、情节不同,但损害程度相近的事例的类举,是一种立法上的类推,应属于法律拟制。唐律中有关比附的规定,事实上都属于律有明文规定的,而非律条之外相似行为的比照适用,亦非扩大了罪行适用范围的类推制度。学界目前所主张的类推的观念是对唐律中相关规定的误解,其可以称之为形式意义上的类推,但绝非刑法意义上的类推。
法制史;唐律;类推制度;立法技术
学界一般认为,唐律在总结前人用法经验的基础上,使用了多种形式来扩大罪、刑的适用范围,比较典型的有类举、比附以及以礼科断等。[1]其中关于类举,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刑法史著作,凡是讲到唐律名例篇中的“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都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类推。近期有学者著文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无论是“举重明轻”还是“举轻明重”都只是对律条的涵义、用语作论证、推理,属于对法律的逻辑解释,而唐律中的比附才相当于现代的类推。进而认为,唐律比附虽未列入名例篇,但在断狱篇第18、20条中都作了规定,其适用范围比现代刑法适用类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2]钱大群教授也认为,唐律中与现代刑法中类推原则最相似的制度是“比附”,其中心也是对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作类推定罪判刑。但他同时也认为按“举轻明重”作“入罪”处置,是使无罪名的行为成为有罪,此与现代刑法中的类推相通。而按“举重明轻”作“出罪”或作罪轻处置,则与现代刑法中的类推用于有罪推定无共通之处。
一、唐律“类举以明出入轻重”解析
唐律中规定类举的律文是《名例律》(总第50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根据《唐律疏议》(以下简称疏文),“无正条”是指“一部律内,犯无罪名”,此犯罪行为,可以实用类举来定罪量刑。
(一)“类举以明出入轻重”之内容释义
1.“其出罪,举重以明轻”。即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某种犯罪行为应如何处罚,审判官若认为是可以减免惩罚的“出罪”,就可以比照律文中相近的罪行较严重的犯罪是如何惩处的,从而推断出该犯罪行为可以相应地减免的处罚。如本条的疏文举例,有人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立即把这个人打得折伤肢体。这种行为如何处理,律无明文,而适用类举可以判定其无罪。因为《唐律·贼盗律》(总第269条)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既然杀死都可以勿论,现在只是打折了肢体,性质相同情节显轻,当然可以“勿论”。故有《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夜无故入人家者,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疏文同时举例:“‘盗缌麻以上财物,节级减凡盗之罪’。若犯诈欺及坐赃之类,在律虽無减文,盗罪尚得减科,余犯明促减法。”既然比欺诈、坐赃更重的盗罪在亲属相盗时都可以比普通盗罪减等处罚,那么发生在亲属间的欺诈、坐赃之罪,就更应该可以减轻处罚了。
2.“其入罪,举轻以明重”。即如果认为这种犯罪行为是应该加重处罚的“入罪”,就可以比照律文中类似较轻微的犯罪是如何处理的,从而推论出该犯罪行为相应加重处罚的情况。如《唐律·贼盗律》(总第253条)规定:“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50条)指出:“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又如疏文指出:“‘殴告大功尊长、小功尊属,不得以荫论。’若有殴告期亲尊长,举大功是轻,期亲是重,亦不得用荫”。
(二)唐律中类举的种类
1.性质相同而情节不同事例之间的类举
此类情况的类举,是指待判的事同作比较的例在性质上相同,但在情节上轻重不同。如,谋杀期亲尊长同杀伤期亲尊长性质相同,只是前者情节轻后者情节重。对夜无故入家者登时杀死同伤其肢体,在性质上也相同,只是前者情节重后者情节轻。再如《名例律》(总第18条)规定:“即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犯奸、盗、略人若守财而枉法者,亦除名”。疏文指出,这“略人”中被略之“人”无论为良人或为奴婢,犯罪者都要处“除名”。同时疏文又提出略部曲是否要受“除名”之罚的问题,对此,疏文以类举答复说,既然不分良贱,故“略良人及奴婢并合除名”。因为,“举略奴婢是轻,计脏入除名之法,略部曲是重,明知亦合除名。”既然罪轻的略奴婢都要除名,罪重的略部曲(部曲身份高于奴婢)当然要处“除名”之罚。此处,都是略人,性质相同,略奴婢情节轻,略部曲情节重,“举轻以明重”,不属贱奴的部曲,自可通过比照奴婢类举得出判断结论。
2.性质、情节不同,但损害程度相近的事例间的类举
《唐律·诈伪律》(总第385条)规定了欺诈致人死伤罪:“诸诈陷人至死及伤者,以斗杀伤论”。但疏文提出骗人过朽坏的木桥,致人落水严重受溺,这种“不伤不死,律条无文”的情况“合得何罪”?疏文答复说应用“举轻以明重”的原则作“入罪”论处,即依《斗讼律》(总第302条)“斗殴人者,笞四十”的律文类举。理由是,这种情况“虽不伤、死,犹同‘殴人不伤’论”。骗人及殴人在性质上不同,但在造成的后果所处的处罚上,有相类似之处,因而也可作类举。
3.直接类举
直接类举是指待处置的事例与用作比照依据的法律上已有规定的事例之间,可以直接比照,不需要第三要件就可以得出结论的类举。如上述《名例律》(总第50条)疏文中所举,主人把“夜无故入人家”者打得折断肢体的待推断事例;《贼盗律》(总第269条)明文规定的主人把“夜无故入人家者登时杀死,勿论”的事例。类举时只需把这两个事例中的不同情节相比照,就可得出“出罪”的结论。再如前述“已杀伤”父祖的待推断事例和《贼盗律》(总第253条)“谋杀”父祖处斩的事例,类推时只要把谋杀和已杀伤相比,就可以依“举轻以明重”的原则作出“入罪”的结论。
4.间接类举
间接类举是指待处置的事例与用作比照根据的法律上已有规定的事例之间,还需要有第三个要件来结合,才能得出结论的类举。如《名例律》(总第6条)“十恶”中的“不孝”罪中规定了子孙诅咒父祖是“十恶”之罪。但是“厌魅”父祖是否属于“十恶”,则律无明文。这时就需要找第三要件做中介才能推断出结论。这个第三要件就是《名例律》(总第6条)规定:“厌魅”凡人属“十恶”之“不道”,而“咒诅”凡人则未入“十恶”。由此可见,咒诅罪轻而厌魅罪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则类举相明,既然已知属轻罪的“咒诅”父祖都入“十恶”,那么,对于属重罪的“厌魅”父祖,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理所当然应列入“十恶”。
再如,《斗讼律》(总第347条)规定:“父祖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夫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论”。但,对于这种亲属关系下的“告得实”怎样处理,律条却并无明文规定,疏文只是说“亦不坐”。这里只有告子孙得实的待推断实例与诬告子孙无罪的法例,还不能推出结论。于是,首先依《名例律》(总第46条)“同居相为隐”的律文,明确父祖与子孙间除谋反、大逆罪外,都可相隐。同时,从性质上认定唐律(总第346条)已规定亲属间的诬告罪比“告得实”罪重。最后判断:既然已规定情节重的诬告也“各勿论”,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情节轻的“告得实”理当“亦无坐”。
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讲,间接类举和直接类举并不能独立地成为类举制度下的一个分支。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依类举时所采用的不同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两种类举的方法。唐律中有关间接类举和直接类举的事例和情形都可以纳入前述第一、二两种类型中去考察和探讨。故下文在论述时,只对相关事例加以分析,而不再讨论直接类举和间接类举问题。①此部分论述参见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四卷·隋唐),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另见钱大群著:《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二、唐律的类举与现代刑法的类推之辩证
所谓类推,是指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比照分则中同它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它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行为的定罪判刑,必须根据事前法律明文所作的规定。而类推则是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根据法官的理解,依照与之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可能导致法官随意适用法律,侵害公民的自由权利。因此,其被现代刑法所严格禁止。需要指出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的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以及法治原则,则只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换言之,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被允许的。②因此,笔者并不赞同钱大群教授的举轻明重作“入罪”处置,是现在刑法中的类推,而举重以明轻作“出罪”处置,就不是现代刑法中类推的观点。因为即使抛开唐律的类举制度到底是不是现代刑法中的类推不谈,单从刑事法理论来看,也不能认为现代刑法中的类推只能是用于有罪推定的。事实上,只不过是因为有罪类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被严格禁止,故被现代刑法特别加以强调和突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刑法的类推制度不包含无罪类推的涵义。
下面笔者将从《唐律》规定的类举出发,来探讨其与现代类推之间的关系。
(一)性质相同而情节不同的类举剖析
《唐律》规定:夜晚无故私自闯入他人住宅者,主人立即将其杀害,不构成犯罪。而“夜无故入人家者,假有折伤”的事例,主人只是将私闯住宅者打伤,虽然律条对此并无明文规定,但刑法没有将更严重的杀害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根据“举重以明轻”原则,比杀害行为更轻微的折伤行为自然应无罪。根据形式逻辑、规范目的以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登时杀之”的律条规定适用于此事例。
对于亲属间诈欺、坐赃类犯罪,律条虽无明文规定,但律条有关于亲属相盗的明文规定。而在唐律中,盗窃罪是比诈欺罪和坐赃罪性质更为严重的犯罪,既然律条明文对亲属相盗的行为人在处罚上相对于普通人之间的盗窃作出了相对减轻处罚的宽宥的规定。那么依据“举重以明轻”原则,理所当然地,法官在处理亲属间的诈欺、坐赃罪时,也应当与普通人所犯此类犯罪有所区别,予以宽宥。
对于杀伤期亲尊长的犯罪,唐律无明文规定,但唐律对较之于杀伤为轻的谋杀作了“皆斩”之规定。在《唐律》中“谋杀”是指,预谋杀害,此时犯罪还处于谋划而未着手实施的预备阶段。既然预备阶段的行为都要处以斩刑,那么依据“举轻以明重”原则,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并造成期亲尊长伤害、死亡的行为当然更应该处以斩刑。
对于“略人”的犯罪,律条规定:“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犯奸、盗、略人若守财而枉法者,亦除名”。律条中的注释指出,“奸,谓犯良人”。既然律条在此特别强调奸淫的对象仅限于良人,哪么盗窃、略人犯罪的对象就应包括所有的人,即既包括良人,也包括奴婢等贱民。故疏文指出:“律文但称‘略人’,即不限将为良贱”。又,在唐代的等级秩序中,部曲的身份级别高于奴婢,因而“略部曲”应属已经达到“略奴婢”的标准还多,当然也应“除名”。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唐律》和疏文对于性质相同但情节不同的事例所作的类举,并非类推,而应属于一种当然的解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罪刑法定之下,适用“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理进行当然解释时,也要求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能简单地以案件事实严重为由以犯罪论处。换言之,当然解释的结论,也必须能为刑法用语所包含。[3]而根据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要求,其并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故在适用“举重以明轻”原则进行当然解释时,不必对其作此要求。
《唐律》及其疏文中所列举的性质相同而情节不同的事例类举,依“举重以明轻”原则出罪时,待判事例并未达到律条的要求,在无其他可适用的律条时,应当适用该无罪律条的规定;依“举轻以明重”原则入罪时,待判事例是在符合法条要求的前提下,还超出了该法条的要求,在无其他可适用的律条时,则依然应当适用该有罪律条。我国现行刑法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形,比如现行《刑法》第201条的规定,逃税达到犯罪数额,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由此,五年内被税务机关给予了三次行政处罚的,即使有上述情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三次”中完全包含了“两次”,两次都要追究,三次无疑更需要也更应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4]现在通行的教科书均认为《唐律》“举轻以明重”的规定属于现代刑法的类推,实属一种误读。依其理解现行各国的刑法以及法官的很多当然解释行为应都属于类推,违背罪刑法定,而这显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二)性质、情节不同,但损害程度相近的事例间的类举剖析
对于欺诈致人死伤的行为,律条规定以“斗殴杀伤论”。按理说斗殴致人伤害、死亡和欺诈致人伤害、死亡,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本不应该将其认定为斗殴杀伤罪。将二者等同视之,应属于一种类推。但其又不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因为此时的规定属于法律拟制。所谓法律拟制,是指在法律上有意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法律拟制仅适用于刑法明文规定的情形,而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此类情形,如果没有法律拟制规定,就不得比照拟制规定处理。”[5]因此,法律拟制可以算是一种立法上的特殊技术,是一种立法上的类推,这种技术性手段只有立法者才能适用,完全不同于司法上的类推适用和类推解释。同时,法律拟制规定属于刑法规定的一部分,亦不属于立法解释,故法律拟制本身并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由此律条可以认为欺诈致人死伤以斗殴杀伤论的规定本身就是罪刑法定而非类推。
关于诈陷他人,不死不伤的情形,疏文说,虽不伤、死,犹同“殴人不伤”论。对于此类情形的处罚,依据疏文亦即律条的解释①对于唐律的疏文,学界通常认为其属于唐律的司法解释。笔者以为,更为准确地说,其应属于立法解释。因为学者们对律条所作的解释本身不能自发地具有法律效力,而必须经立法者亦即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方能有效。故唐律的疏文应属于立法机关对其所作的解释,当为立法解释。的规定。作为一种对法条的解释,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以相类似的有罪法条加以类举,无疑属于一种类推解释。但需要注意的是,解释者在对此类行为进行解释时,既非基于“举轻以明重”,亦非基于“举重以明轻”,因为该规定的结论无论基于哪种当然解释原理都无法得出,只能是一种解释者新创造的法律规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认为《唐律》“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重”的规定属于类推的观点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因为在《唐律疏义》的类举中只有此种情形属于真正的类推,而其却无法用通说所主张的观点来加以解释。
三、唐律的比附与现代刑法的类推之辨析
如本文开篇所述,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并非类推,而是当然的逻辑解释,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该学者同时指出,唐律中的比附才相当于现代的类推。诚然,如著名的唐律研究专家钱大群教授指出的哪样,在唐律中比附都属于有罪的比附,是为了不使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漏脱惩罚,依据刑律中已有的类近的犯罪条文处罚,是在无正条的情况下所作的有罪比附。如此,同类举相比似乎更有理由将比附认定为类推②因为在类举中,举重明轻时,也可以是无罪。。哪么,比附到底是不是我们现代刑法所说的类推呢?下面笔者将对此展开探讨。
通说认为,比附制度在中国刑法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尚书·吕刑》中就已有“上下比罪”的记载。吕祖谦在注解“上下比罪”时说:“三千已定之法,载之刑书者也。天下无情之穷,刑书所载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穷无尽之情,要在用法者,斟酌损益之。”《周礼·秋官·大司寇》郑玄注云:“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荀子·大略》亦记载说:“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故而认为,我国古代刑法中所谓的“比附”援引,是指在遇有需要定罪判刑的犯罪而又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时,比照刑律的有关规定,或者依附于刑律的有关规定,援引这些规定作为定罪判刑的依据。[6]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权威的法制史教科书和唐律研究专著,虽然对比附作了这样的定义,但他们在论述类推制度时,却并不认为比附属于类推。笔者以为学界对比附的定义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其一,既然是法无明文规定,而比照适用刑律的有关规定,这不是类推又是什么呢?其二,既然是依附于刑律的有关规定,那又何来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呢?
一般认为,根据《唐律》有关比附的规定,比附可以分为定罪比附、量刑比附、定罪量刑比附三种,下面笔者将对此一一进行分析。
(一)定罪比附释义及辨析
定罪比附,通说认为是一种套用律中罪适用于律无规定行为的比附。这种比附侧重于罪名,被比附行为要依被比附罪名再量刑。唐律中的“与同罪”、“准x罪”、“以x罪论”、“罪亦同”、“与x罪同”等是这一比附的主要表现形式。《唐律·卫禁律》“宿卫冒名相代”条规定:“诸宿卫者,以非应宿卫人冒名自代及代之者,入宫内,流三千里;殿内绞。”如果主司“知而听行,与同罪。”在本例中,律条规定“与同罪”,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一是认为其意是指主管官员知情而放纵的,与相顶替者同罚,是一种处罚上的比附;一种如上,认为属于罪名的比附。两种观点一致之处在于,都认为对于此种行为的处罚与相顶替者相同,因为即使是罪名比附,在罪名相同的情况下,处刑也理所当然地相同。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在刑法理论和实务中,对某一犯罪行为的处理,都离不开罪名的确定,只有先定性才能进一步定量,即只有先确定罪名才能进一步依照该罪名的法定刑进行量刑。但无论如何理解该罪行比附的性质,都无法得出这是一种对律无明文规定行为的比附定罪。因为律条明文规定了此条的罪状是,主司明知下属宿卫冒名相代而不加以制止、纠正,同时对此行为也明文规定了罪名和法定刑,即和相代替者同等定罪处刑。对于律条明文规定的犯罪,何来律无规定?更何来类推适用?
《唐律·卫禁律》“向宫殿射”条规定:“宿卫人,于御在所误拔刀子者,绞;左右并立人不即执捉者,流三千里。”此条“疏议”补充规定:“余人在御在所亦不得误拔刀子。其有误拔及傍人不即执捉,一准宿卫人罪。”对于宿卫人之外的其他人于御在所误拔刀子准宿卫人罪,并非律条明文规定。疏议对此依照宿卫人罪进行了比附,那如此比附是否属于类推呢?笔者以为不然,因为在此种场合,宿卫人误拔刀子的危害程度显然要小于非宿卫人员。宿卫人员乃大将军以下、卫士以上保卫宫殿的人员,其负有保卫之职责,必要时需拔刀履职,若因对形势判断有误等情况而误拔刀子是可能的。而非宿卫人员在宫殿之内是绝对不允许拔刀的,其同职责允许可以拔刀的宿卫人员相比,误拔刀子的危险性要大得多。在律条对这种危害更重的行为未作单独规定的情形下,依据“举轻以明重”原则,当然应当准宿卫人罪。故,此种比附属于当然解释而非类推。同时,由于疏议被认为是对律条的解释,其经过立法者皇帝批准,同律条正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类似于现代刑法的立法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例中的比附也可认为是律有明文规定。①根据现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即使是立法解释也不能进行类推。
《唐律·断狱律》“死罪囚辞穷竟雇请人杀”条规定:“诸死罪囚辞究竟,而囚之亲故为囚所遣,雇请人杀之及杀之者,各依本杀罪减二等。若囚不遣雇请,及辞未穷竟而杀,各以斗杀论。”实际上,囚犯未差遣雇请以及招供审断未进行完毕而杀的行为和斗殴杀人并不相同,但律条明文规定此行为以斗殴杀人论处,应属于法律拟制。如前所述,法律拟制并非现代刑法所指的类推,而是现代刑事立法普遍采用的一种立法技术。如我国现行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第289条规定:聚众“打砸抢”,毁坏公私财物的,对首要分子,依照抢劫罪论处。对此,我们肯定不能认为刑法对携带凶器抢夺、聚众打砸抢并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没有明文规定,而是抢劫罪法条的比附适用。
(二)量刑比附释义及辨析
量刑比附,通说认为是一种引用律中对某罪使用的法定刑适用于另一些行为的比附。这种比附侧重于刑罚,被比附行为只要按被比附的法定刑或有所加减即可。“得x罪”、“减x等”、“加x等”是这一比附主要的表现形式。《唐律·斗讼律》“斗殴杀人”条规定:“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此条“疏义”作了补充规定:“用兵刃杀人者,与故杀同,亦得斩罪。”“殴兄姊等”条规定:“诸殴兄姊者,徒两年半;伤者,徒三年;折伤者,流三千里。”“过失杀伤者,各减本杀伤罪二等。”“流外官以下殴议贵等”条规定:流外官以下“殴伤九品以上,各加凡斗伤二等”。以上三例都是用比附用刑的方法,使被比附行为受到处罚。
对于量刑比附,笔者以为认为其不属于类推,应当没有大的异议。首先,对于量刑比附的立法例,其前提是某一犯罪行为的罪名已经被律条加以明确确定下来,不再存在类推制度适用的空间。在罪名被确定的前提下,无论法定刑如何确定,都不能说其属于类推,类推是针对律无明文规定行为的出入罪而言的。其次,在这些立法例中,法定刑的比附对象也都是由律条明文规定的,虽然有的疏文也对其作了规定,但都只是对律条规定的进一步明晰化。最后,律条之所以采用量刑比附,主要是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减少重复、冗长,使律文简洁、明晰,并非是为了扩大适用到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
(三)定罪量刑比附释义及辨析
定罪量刑比附,是一种移用律中罪行的完整规定适用一些行为的比附。这种比附包括罪名和法定刑两个部分,被比附行为只要照搬使用即可。“准x法”、“同x律”、“同x法”是这一比附的主要表现形式。《唐律·贼盗》“穿地得死人”条(总第267条)规定,穿地得死人不更埋的,“徒二年”。此条疏义补充说:“若穿地得死人,可识知是緦麻以上尊长,而不更埋,亦从徒二年上迭加一等,卑幼亦从徒二年上迭减一等,各准‘烧棺椁’之法”。《唐律·斗讼律》“诬告反坐”条(总第342条)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此条“疏文”进一步规定:“据令应合纠缠者,若有憎恶前人,或朋党亲戚,狭私饰诈,妄作纠缠者,并同‘诬告’之律。”《唐律·户婚律》“里正不觉脱漏增减”条(总第151条)规定:“诸里正不知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以上三例经过定罪量刑比附,使原律条中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都可受到刑律的追究。
首先来分析“穿地得死人”的立法。疏文说,掘地发现死尸而不立即掩埋者,依照“烧棺椁”之法定罪处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将“穿地得死人不更埋”的行为比照了烧棺椁的行为来处理,事实上不然。律条全文是:“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於冢墓燻狐狸而烧棺椁者,徒两年,烧尸者,徒三年。缌麻以上尊长,各迭加一等;卑幼,各依凡人迭减一等。”由此可知,律条对于穿地得死人不更埋以及对象为尊长亦或卑幼的处罚都已经作出了明文规定。疏文虽然说各准“烧棺椁”之法,但笔者以为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对于依服制加重减轻处罚的具体规则依照烧棺椁之法,烧棺椁和穿地得死人不更埋都是处徒两年的刑罚,哪么他们在加重减轻的刑罚上也应属相同。因而,结合律条原文和疏文的补充解释,笔者以为,各准“烧棺椁”之法,是指各准“烧棺椁”之服制之法,只是对律条原文的明细化,并非创设律条或扩大律条的适用范围。
再来分析“诬告反坐”的立法。律条原文为:“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疏文解释说,“即纠弹之官”,谓据令应合纠缠者,若有憎恶前人,或朋党亲戚,狭私饰诈,妄作纠缠者,并同“诬告”之律。律条已经明文规定,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同样要处反坐之律。疏文只是对怀私仇弹劾别人有罪不实的情形作了解释而已。事实上,此条立法相当于现代刑法理论上的注意规定。即使律条后半段和疏文不特别指出纠察弹劾的官员为报私仇诬陷弹劾他人依诬告的法律同样处罚,对于这种行为,依照律条前半段,凡诬告人的都作反坐的规定,对其同样应该如此处理。特别规定的用意就在于,提醒裁判者注意,以免在适用时忘记或者疏忽。
最后来看“里正不觉脱漏增减”的立法。律条规定里正对于脱户、漏口、增减年岁或者虚报疾病知情的,与家长之犯同样处罚,即“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無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此立法同样属于法律拟制,前文已多次阐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只需重申一点,法律拟制并非类推,而是法律的明文规定。
另外,《唐律·断狱律》同时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既为永格,则说明皇帝的该条敕令已经被作为一项法律规则正式确立,那么之后的相同行为就必须做相同处理,此时的法律依据则为该永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比附使用的前提是法律有明文规定。
综上可知,唐律中有关比附的规定,事实上都属于律有明文规定,而并非律条之外相似行为的比照适用,亦非扩大罪行适用范围的类推制度。更为准确地说,此乃唐律先进、成熟的立法技术的体现,注意规定、法律拟制以及引证罪状、空白罪状等在现代刑法理论中才形成的法律术语在唐律中早已被运用。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学界以所谓“举轻以明重”和“举重以明轻”得出唐律规定了类推制度的观点,是缺乏严密的逻辑证成的。唐律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以及封建时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刑事立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得益于其采取了这些被误解的所谓类推制度的规定,因此有必要为其正名。唐律本身并无类推的规定①根据现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即使是立法解释也不能进行类推。,只有疏义中有关性质、情节不同但损害程度相当的事例之间的类举才属于类推,而这和学界所主张的“举重明轻”、“举轻明重”以及比附制度属于类推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态,不可将彼此混为一谈。唐律中存在现代刑法所说的类推,但其所占范围很少而且仅存在于疏文中。学界目前所主张的有关类推的观念是对唐律中相关规定的误解,其可以称之为形式意义上的类推,但绝非刑法意义上的类推。
[1]王立民.唐律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7.
[2]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法制史学[M].北京: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3:155.
[3][4]张明楷.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8,139.
[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11:632.
[6]钱大群.唐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版,2000:214.
D929
A
1673―2391(2014)05―0143―05
2014-03-22 责任编校:谭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