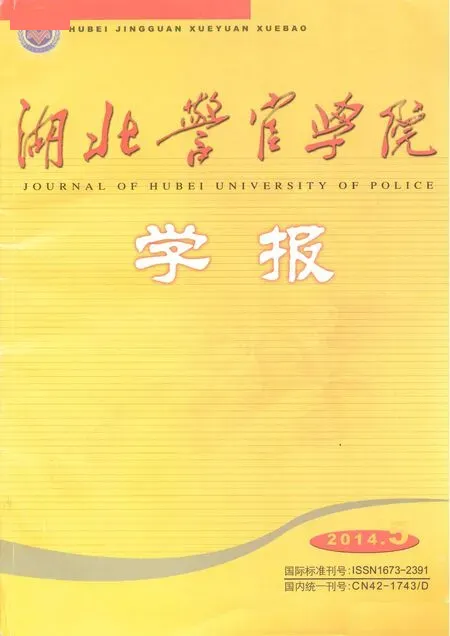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初探
曹小丽,姚慧芳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430034)
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初探
曹小丽1,姚慧芳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430034)
在研究侦查讯问法治化问题时,已有的研究使用了众多不同的概念表述,如“侦查讯问法治化”、“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侦查讯问法制化”等,但却缺乏对“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较为系统深入的阐释,也没有对其与相近概念的厘清。因此,有必要对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及相关概念作必要的阐释与分析。这既有助于明晰概念、避免混淆,同时能丰富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的理论研究。
侦查讯问;侦查讯问法治化;侦查程序法治化
一、我国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对概念的系统阐释不足
目前在涉及侦查讯问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在其文章中使用了“侦查讯问法治化”或者“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的表述,但无论是“侦查讯问法治化”还是“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对其进行明确定义与阐释的却很少。例如,研究者张国宏曾经发表《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程序》,其在文中所述“何谓讯问的法治化?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需要具备什么要素呢?”[1]这里使用了“讯问的法治化”这一表述,但是在文中并未对讯问法治化这一概念作出任何阐释。又如,研究者林喜芬在其专著《中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转型》中所述:“这些拙劣而落后的讯问技术不能得到改进,体现现代色彩的心理导向之讯问技术不能普及,标志着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尚处于初级的阶段。”[2]这里使用了“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的表述,但是同样未在专著中指明何谓侦查程序的法治化,也并未对这一概念给予明确的阐释。
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研究者张丽敏、李宝字在2010年发表了《我国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其在文中指出:“侦查讯问法治化是指为了准确实现国家法律所确定的侦查、诉讼目的,根据我国特定的宪政体制和国情基础,兼顾国际一般法治标准,在侦查讯问实施过程中的法制建设水平和运行状态的法治程度。”[3]这是少有的明确界定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的表述。这个定义中,研究者是从一种状态描述的角度来定义侦查讯问法治化的,认为侦查讯问法治化是侦查讯问的法治程度的一种综合反映和表现。具体包括“侦查讯问实施过程中的法制建设水平”,也即涉及侦查讯问的法律制度与规则的立法状态及侦查讯问的实际运行状态。除此之外,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分析研究者文中内容来了解和提炼“侦查讯问法治化”或“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概念的含义。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于讯问法治化概念的直接阐释显然不足。这种不足一方面表现为将“侦查讯问法治化”或“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视作一个独立概念对其界定与阐释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即便有所研究,也相对比较简略。
(二)对近似概念的区分与辨析不足
目前许多研究中将“侦查讯问的法治化”与“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两个概念未加区分,表述时相互混用,缺乏对近似概念的区分与辨析。
例如,上文提到的《我国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与《关于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研究》,这两篇文章在开篇下定义时,所言“侦查讯问法治化是指………”,使用的是“侦查讯问的法治化”这一表述,但文章题目中使用的是“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行文内容也都使用了“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的表述。张国宏2007年发表《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程序》一文,同样将“讯问的法治化”与“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两种表述在文中交替使用且未作区分说明。如在文中所述:“何谓讯问的法治化?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需要具备什么要素呢?笔者试就法治视野下的讯问的内涵和要素展开论述,期望对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改革与构建有所启发。”[4]
当然,也有研究者将“侦查讯问”与“侦查讯问程序”两个概念混用,但同时指出两者是存在区别的,并给予说明。例如,学者郝宏奎2004年发表《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他在文章题目、内容摘要以及文章内容中使用了“侦查讯问的改革与发展”、“侦查讯问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研究者明确作出说明,认为“侦查讯问程序”与“侦查讯问”,“两者之间意义上既是种属关系,又各有一定的侧重。种属关系体现在,‘侦查讯问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是‘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从两者各自的侧重点而言,前者侧重于表达程序性制度与规则的构建,偏重于讯问立法的问题;后者侧重于表述如何顺应侦查讯问的程序性改革,使侦查讯问活动与时俱进,保持活力,偏重于讯问实务问题。”[5]总体而言,这种将两个概念作出区分并分析两个概念之间区别的学者不多、研究较少。
二、侦查讯问法治化概念的界定
(一)从“法治”形式意义的角度来阐释侦查讯问法治化
倘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法治,我们可以理解为法治首先是以某种思想、理念(法治学说、法治研究成果)的形式存在;其次表现为法治的理想、目标诉求或政治口号;然后在这些观点或诉求被普遍认可,特别是国家的统治者认可后,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治国原则或具体化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最后,法治的制度被贯彻实施,成为一种事实状态,也即法治状态。“各种成功的‘法治’都是一个‘生命体’,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有自己的树根(价值认同)、树干(法律体系)、树叶以及花果(法治实效)。”[6]如若以此法治的较广的形式含义来分析侦查讯问法治化,那么侦查讯问法治化,就是指法治的精神贯穿于侦查讯问理念、法律制度、行为之中,在法治总构架内形成相应的侦查讯问价值理念和文化、侦查讯问法律制度、侦查讯问行为模式。即包括侦查讯问的学说、研究观点,社会公众对于侦查讯问的普遍认知,国家层面的侦查讯问法律制度,以及侦查讯问法律制度的运行是否合乎法治的精神和原则,都属于侦查讯问法治化的研究范畴。这是广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广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是“法治”的侦查讯问观念、侦查讯问原则、侦查讯问法律制度以及侦查讯问实践运行的综合体。
狭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是指制度构建层面的侦查讯问法治化,也即构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和内核的侦查讯问法律制度。狭义侦查讯问法治化的视角关注的是立法层面,侦查讯问所涉法律规范是否合乎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如果借助上述的比喻,将法治视作一个生命体,以树为喻,广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含纳树根、树干以及树叶和花果,而狭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关注的是树干部分——侦查讯问法律规范体系。
所以,从形式上来说,狭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关注的是侦查讯问的法律制度构建是否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与精神,也就是关注是否构建起侦查讯问的“法治”之“法”。广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不仅仅关注在立法层面是否构建起侦查讯问的法治之法,还关注侦查讯问的法治之观念以及侦查讯问法治之法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
(二)从“法治”实质内涵的角度来阐释侦查讯问法治化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从不同角度给“法治”的内涵作出总结和界定。
1.二层涵义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包括了两重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7]
2.三层涵义说。1885年英国法学家戴雪(A·V ·Dicey)在其所著《英宪精义》一书中,赋予法治三个方面的含义,即法治排斥行使专断权力的思想;各个阶级、阶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宪法是表述并确立权利的保障。
3.四层含义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1959年发表《德里宣言》,将法治归纳为四个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应该是创造和维护个人尊严得以保障的各种条件;规范政府行政权力不使其滥用;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取消不人道的以及过度的处罚;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
4.八层涵义说。1964年美国新自然法学代表富勒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一书中提出法治的八个原则,即法律应具有普遍性,法律应公布,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应该有明确性,应该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法律应有稳定性,官方行动应与法律保持一致。
不难看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法律至上,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力为关键,追求程序正义之价值,实现司法独立。
因此,从“法治”内涵的角度阐释,侦查讯问法治化,就是指侦查讯问的法律制度应该蕴含现代法治保障人权、限制权力、程序正义等核心精神与原则,其实践运行应实现现代法治保障人权、限制权力、程序正义等核心精神与原则。即立法层面建立侦查讯问的法治之法,且实践层面此种法治之法得到普遍的遵守,实现了法治之治。
从法律制度的属性角度分析,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内容表现出一种强制性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刑事诉讼程序之进展及其目的的达成,不可能不以干预与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手段;事实上,环顾所有法律允许的基本权干预,就属于刑事诉讼领域所允许的干预手段,最为严厉而彻底。”[8]因为侦查程序承担着抓获与查证犯罪嫌疑人的重要职能,由此决定必须赋予侦查机关有效的权力,以此保障能够逮捕并羁押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使得他们受到法律之制裁,保护公众免受侵犯。但是,刑事司法机关不能不计是非与代价地推进刑事诉讼程序。在现代社会,刑事诉讼法被称为权利之大宪章或小宪法,不仅在诉讼理念上体现出一种转变——从单一的重视惩罚犯罪到兼顾重视保障人权,而且在诉讼结构也体现出一种转变——由张扬权力到抑制权力。在刑事侦查领域,制度性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已经逐渐成为衡量各国刑事侦查法治化的基本标尺。这是由于,一方面,赋予和保障犯罪嫌疑人防御性权利是犯罪嫌疑人主体性地位的体现。在传统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仅仅作为侦查程序中侦查权力作用的对象,仅仅是诉讼推进过程的客体,不仅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而且还担负着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明责任与供述义务。另一方面,赋予和保障犯罪嫌疑人防御性权利是制衡国家刑事侦查机关侦查权力的重要向度。现代法治理念主要包括了“权利制衡权力”与“权力制约权力”两个向度。
可见,侦查讯问法治化的意涵应该包括,在侦查讯问中通过赋予并制度性地保障犯罪嫌疑人防御性权利,通过对侦查讯问权力必要的抑制,实现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呈现出重视犯罪追惩到兼顾重视保障人权转向。单一的追求实体真实、忽视程序正义,单一的重视破案的效率、讯问中口供的获取效率、忽视甚至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侦查讯问都是违背侦查讯问法治化的。
三、近似概念的辨析
(一)侦查讯问法治化与侦查讯问法制化
如前所述,狭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是指制度构建层面的侦查讯问法治化,也即构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和内核的侦查讯问法律制度。需要明确的是,狭义的侦查讯问法治化与侦查讯问法制化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法制化”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往往意味着通过立法确认合法性,并在程序上加以规范,着重强调的是“有法可依”,强调纳入法律范畴内,但不强调法之实质内核与价值取向。“法治化”有其自身鲜明的价值取向与丰富的精神内核,是一种现代化法制。这是学界对“法治化”与“法制化”的一种观点。即法制现代化与法治化是同一种内涵的两种表述方式。例如,学者杨宗辉、章昌志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安法治化》中提到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通过法律的治理实现法治。法制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实现法治。”[9]蔡道通在《国家法治先于社会法治为主导——中国法治化的道路选择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或称法治化)的启动是在市场经济几乎没有发育、全体社会民众又缺乏对法律的价值认同与信仰的基础上由政治国家推进而进行的。”[10]
在我国封建传统侦查中,拷讯从秦汉就入法,至唐宋更趋细致严格。如隋朝对拷讯总数、工具规格、行刑者等已有严格规定,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拷讯制度。一方面,对拷讯工具使用的次序、拷讯部位、刑具尺寸规定得更加具体。“用笞决勘,如又不服,然后用杖决勘。”另一方面,在拷讯总数、次数、间歇天数等方面,唐律的拷讯法律更为细化。可以说,我国封建社会的侦查讯问已经纳入国家制度规范的体系,并有着非常完备与成熟的规范,侦查讯问的“法制化”程度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但显然我们不能说这种讯问制度与践行达到了侦查讯问法治化。因为,侦查讯问“法治化”中法制的内容具有人民性、民主性,保障和实现人权,法律至上,实行权力的制约是其基本要求和本质特征。
(二)侦查讯问法治化与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
侦查讯问是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侦查过程中拥有的多项侦查措施中的一种。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设置了一系列的规定,对讯问的主体、讯问的时间、讯问的地点、讯问的内容、讯问的笔录制作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也就是说,讯问的开展必须遵循一定的流程、步骤,于是就有了“侦查讯问程序”概念的提出。“程序”在中文中最基础的含义,就是程式、步骤和顺序。在《法学导论》中,拉德布鲁赫也曾指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11]侦查讯问中的这些程式、步骤和顺序不是根据某种社会经验形成的,也不是根据某种科学公式计算得出的,而是遵循特定的原则而设计的,意图将侦查讯问导向某种特定的形态,实现特定的目的。而且,这些程式、步骤和顺序不是临时的而是稳定的,不是建议性的而是强制性的。这些程式、步骤和顺序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必须借由一定的法律制度与规则来呈现,必然会反映为一定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于是,从“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这个角度切入来研究侦查讯问时,基本上是立足法律制度层面,探讨怎样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才能实现讯问的法治化。例如,学者刘方权发表的《论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一个权利的视角》,研究者在其文章中表述道:“基于国家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侦查讯问权的存在有其目的正当性,基于程序的正义要求,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应当符合法治精神。”[12]他认为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来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与自由性。纵观研究者全文,这种制度设计包括:第一,需要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二,需要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情权;其三,律师帮助权;其四,讯问的适当限度——自由的保障。
侦查讯问法治化是一个比侦查程序法治化范畴更大的概念。同时,作为一个研究侦查讯问的切入视角,是一个比侦查程序法治化更宏观的研究视角。侦查讯问法治化对于讯问法治化的实现不仅仅从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分析,还关注侦查讯问中的理念层面以及侦查讯问的实践运行层面;不仅仅需要考虑到微观的侦查讯问规则的设立,中观的司法制度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还需要考虑到宏观的某些社会基础与客观条件。因为侦查讯问法律制度与规则的法治化固然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前提,但是仅仅侦查讯问法律制度与规则达到较高程度的法治化,缺乏理念的跟进,或者侦查讯问法律制度与规则的实际践行与法条相脱离都不是真正的侦查讯问法治化。现实也表明,没有法治化的理念以及某些客观社会条件的成熟,不可能在立法层面形成法治化程度高的侦查讯问法律制度。
[1][4]张国宏.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程序[J].犯罪研究,2007(5).
[2]林喜芬.中国刑事程序的法治化转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15.
[3]张丽敏,李宝字.我国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J].河北公安警察学报,2010(4).
[5]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J].法学,2004(10).
[6]张生.从幽微到辉煌:中国新民主主义法治成功之经验[A].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法治的哲学之维(第一辑)[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29.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65:199.
[8]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8.
[9]杨宗辉,章昌志.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安法治化[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10]蔡道通.国家法治先于社会法治为主导——中国法治化的道路选择分析[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3).
[11][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20.
[12]刘方权.论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一个权力的视角[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2).
D631.2
A
1673―2391(2014)05―0025―04
2014-03-18 责任编校:边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