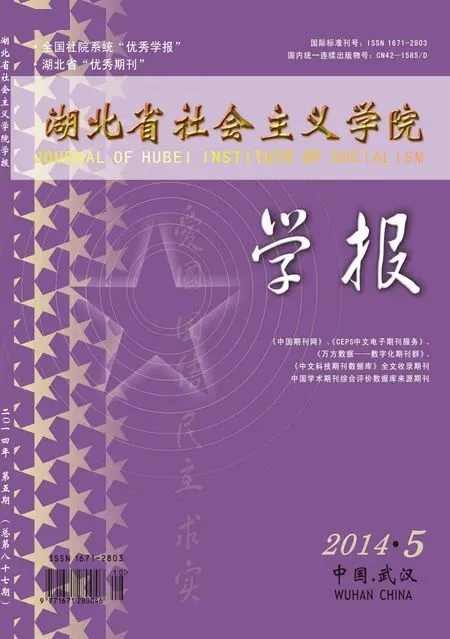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规律
——以湖北省为例
王相红 肖建平
(1.2.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从价值观念取向、成员整体结构、新成员发展情况、新社会阶层增幅情况、领导人年龄结构、基层政治参与情况等六个指标来看,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呈现出新的趋势。本文试图分析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客观规律。
一、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影响因素
新中国60多年来,就湖北省来看,民主党派的发展实现了三次代际变迁。鉴于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秩序中的定位及自身特点,其代际变化受制于诸多内外因素。时代主题、执政党执政方针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大转型和大变迁,是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民主党派的组成结构、文化更替、参政意识、参政行为等无不受到相应的冲击和影响。
1、时代主题的转换。从湖北省民主党派的代际变化来考察,其第一代独立性特征显著,第二、三代角色较为模糊,第四代自主性特征、制度需要性特征显著。民主党派成员的代际变化,都随着执政党及执政党执政思路主导下的时代主题(建国初期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期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日高)的变化而变化。如:改革开放前,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相对较慢;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成员发展相对较快,代际更替加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主题的转换需要调动最大方面的积极因素投身到经济发展之中,需要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关切。由此,民主党派成员从思想文化到成员结构等方面呈现出来的代际变化的趋势则大为加速。同时,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政党”、“服务型政党”转变,这需要民主党派从“友党”向参政党转变,以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对民主党派提升参政能力的要求,也影响着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思路调整,从而影响其成员的更替及代际变化。
2、治理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调整政治发展模式,突破政治发展过程中关于制度化建设的误区,按照“民主化和制度化紧密结合的要求”,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由组织化国家到制度化国家”的转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制度化建设,实现了治理由政治动员到制度化建设方式的转变,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使政治转型走向了民主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治理方式的转变,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推动了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参政行为的模式转换,也进而推动了民主党派政党意识的自觉和强化,这一特点在最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中表现鲜明。
3、经济条件的调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展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尊重多样化的利益选择,实现冲突与一致的平衡。决定在公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推动所有制的多样化调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所有制多样化调整的实现,一方面,为民主党派成员结构的改变提供了可能的社会基础,也使其进而成为必需;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变革必然影响着社会成员乃至民主党派成员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构成了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经济基础。
4、社会基础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初的30年,城市的单位制度、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制度建立起的组织网络压抑了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在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的时代背景下,民主党派代际变化客观上难以进行。而改革开放则积极推动着社会建设。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制度建设以及地方分权化的改革,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社会建设也促进了权力由国家向社会回归,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意识到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区别,逐步厘清着各自边界,促进了社会的成长和成熟,从而推动了社会基础的转型,这为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5、政治文化的转型。文化世俗化是民主政治成长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下,中国政治从打倒传统、拒斥西方文明向尊重传统、借鉴外来文明发展,执政党自觉从传统中寻找有效资源,祛除个人崇拜,促进政治回归常态,推进法理化和程序化建设。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推动着民主党派活动的正常化,领袖特质走向传统化进而向法理化过渡。政治文化世俗化的推进,是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政治文化基础。
6、中共政策的调整。民主党派代际变化也因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调整而引发。在反“右倾”和“文革”中,相当高比例的民主党派人士受到冲击,民主党派的成员构成几乎出现断层。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入宪,给予民主党派以制度定位、宪法保障,其同时也对民主党派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宪法责任要求。统战政策的调整引发了对民主党派成员身份要求的调整,对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相关条件的把关更加严格。正是中共统战政策的这一调整,要求民主党派新一代提高参政能力,也使民主党派参政能力提高成为现实。正是因为定位为参政党,民主党派新一代在“参政党如何参政”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才成为可能。
二、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基本规律
四代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逐渐推进的过程。考察民主党派代际变化,其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政治文化世俗化趋势充分呈现。发展的政治就是权利的政治和参与的政治。随着中国政治世俗化的推进,民主党派代际变化从组织结构到政党文化、参政行为、领袖特质等各个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新中国以来的政治文化世俗化有两种作用机制,一是传统条件下精英与大众关系的根本变化,文化精英从臣民文化走向参与文化,自觉承担了社会启蒙的任务,为社会大众导入世俗的政治观念;二是知识与权力的联盟在改革中适度分离,政治权力既失去了对知识的解释、生产和评价的控制能力,也失去了对知识承载者的控制能力。政治文化世俗化造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结果:政治合法性基础变化,“人民”的地位得以确定并深入人心;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大规模扩展的过程。民主党派由“友党”向“参政党”的转型,民主党派人士由传统的知识精英向现代公民的过渡,标志着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的世俗化趋势,也推动着中国新型政党关系的确立。
2、制度化和组织化趋势明显强化。制度化和组织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期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探索的挫折和失误,虽然组织化建设得到了加强,但制度化建设却严重欠缺。改革开放后制度化建设成了政治发展的主题。在民主党派建设方面,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同样的彰显。随着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12年《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发布和执行,民主党派建设的制度化力度非常大,从民主党派重新定位、政治交接、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实现了民主党派权利法定、程序法定等方面的充实和完善,这也是民主党派代际变化的重要表征。
3、政治参与由动员到主动。从动员参与到主动参与,是民主党派代际变化的显著进步,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建国初期,由于革命政治的影响和延续、民主党派人士和执政党的私人关系、制度化建设的缺失等因素作用的结果,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参与虽然较为积极主动,但缺乏制度化和法理化的保障机制。1956年-1978年这一时段,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停滞阶段,由于执政党政策的失误,民主党派成员受到打压,政治参与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阶层结构分化和利益格局分化以及中国政治走上制度化之路,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参与有了权利的保障、利益的冲动和机会的可能,政党意识逐步清晰明确,政治参与更加自觉主动,参与主题更加丰富多样。这一参与模式的转变,是民主党派代际变化的显著外在特征。
4、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化。在建国初期,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是政治发展的首务。在政治一体化和国家能力建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民主党派政治参与逐步扩大化的依赖条件。改革开放之初,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关注视野狭小,主题层次较低,问题较为单一,多集中在社会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其政治参与主题层次趋向深入宏观,结合国家政策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参与话题逐步进入改革深水区,对顶层问题的参与更加活跃。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化,是民主党派代际变化的必要基础。
5、民主党派成员发展的开放化。1996年,《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组织发展的重点分工和组织发展的地区、范围,继续坚持“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的原则。但是,从湖北省的发展来看,八个民主党派的特色越来越不明显了,尤其是民盟、民进、九三与民建,出现了各个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交叉融合趋向;从发展地区和范围来看,中小城市和县城的民主党派成员的绝对数量保持了相当的增长,基层化和社会化趋势明显,这些都表明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呈现开放化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