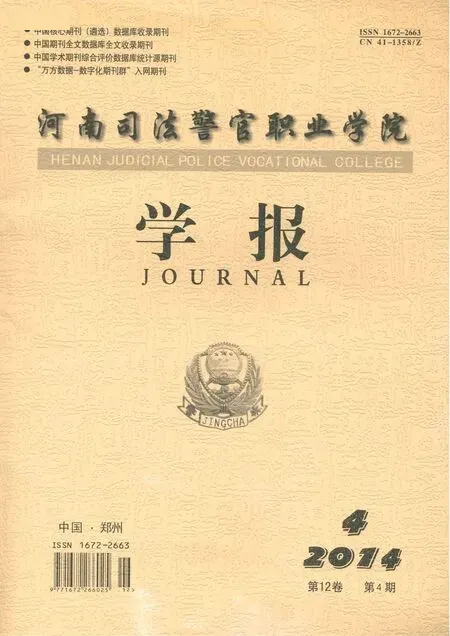问题与走向——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析
罗 雪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四川 成都 610200)
问题与走向——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析
罗 雪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四川 成都 610200)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贯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教育、感化、挽救”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现了法制化。实施以来,这一工作取得了一定实效,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重回社会提供了方便,同时充分体现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实践工作同时反映出该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导致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立法目的难以全面实现,因此,进一步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置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点,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程序作出了规定。从“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原则;从设立特别程序的立法结构,到11条的条文数量;从比较丰富的条文内容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都充分说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无疑是我国刑事诉讼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升华,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伟大进步与发展。
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贯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教育、感化、挽救”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现代国家之所以确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犯罪记录的存在必然会对被记录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产生很多有形的(如法律明确规定的从业禁止)或无形的(如在生活中遭遇歧视)的不利影响,并且很容易形成“一朝为贼,终身为贼”的“标签效应”,进而阻碍被记录人的改善更生,甚至会使这些人因回归社会无望而再次实施犯罪,并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因此,为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允许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封存甚至消灭犯罪人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而消除由于犯罪记录的存在而对该人产生的不良影响,使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回归社会。该项制度旨在通过调适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犯罪人员的正当利益,在确保国家有效管控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并实现社会自我防御功能的同时,敦促犯罪人员自省并保障其能够顺利回归社会,开始正常的生活。〔1〕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和销毁,有利于对未成年人实施特殊保护。我国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免除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这一规定包含了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内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嫌疑人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0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3条、第504条、第505条、第506条、第50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法律、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封存,尽可能缩小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不良影响,为未成年人升学、就业,成功地回归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开庭审理时已满十八周岁的案件难以保证案件信息不流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时候未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是实践中有这样的情况: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开庭审理时已满十八周岁,对于这种案件,在公开审理的情况下,案情信息泄露不可避免,由此导致封存工作效果甚微。
(二)单纯一个环节实施犯罪记录封存难以达到封存效果
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一件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案件至少都会经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三个环节,有些还会涉及司法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如果只是某一个环节或者某几个环节封存,那么也难以保障封存效果,因为涉及环节较多,办案人员较为复杂,在那些没有实施封存工作的环节,很难保证信息不会流出。
(三)一案多人多种刑期的案件封存工作难以产生实效
一案多人的案件中,部分被告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部分被告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如此就会出现一案中部分被告的犯罪记录符合封存条件,部分被告的犯罪记录不符合封存条件的情况,此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犯罪记录封存存在操作难题。比如:如果对全案犯罪信息进行封存,一旦有人要求查询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犯罪人的犯罪信息,很难保证同案其他信息不被泄露。
(四)《刑事诉讼法》关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过于笼统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从1月1日起办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记录应当封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0条第2款规定,2012年12月31日以前审结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除刑事处罚的犯罪记录,应当封存。《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规定,公安机关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依据是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两者都没有对诸如不予起诉、行政处罚等是否应当列入封存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很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案件没有得到封存,或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的案件缺乏明确的封存依据。而这是不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否应当包括免除刑事处罚、不起诉等,建议立法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
(五)关于数罪的封存问题
当行为人在年满18周岁前后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构成一罪或者数罪的,其犯罪记录是否应当封存?如果应当,如何封存?(1)如果连续实施数个行为构成一罪,定罪量刑的依据是综合衡量数个行为后的结果,其不满18周岁时实施的行为不能单独评价,自然也难以实现单独封存。(2)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数罪,由于数罪一并审理,一并判决,定罪量刑在同一份判决书中,封存其18周岁之前的犯罪记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六)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等环节容易导致案件信息扩散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案件公开宣判、不起诉决定的公开宣布、社区的监督及其矫正,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信息客观上产生扩散效果,犯罪记录封存难以产生实效。以社会调查制度为例:虽然社会调查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但开展社会调查却无意中扩大了案件的影响范围,本来只是在很小范围内知晓的案件,由于开展社会调查程序被更多人了解,这不仅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犯罪记录封存的立法原意相矛盾。因为犯罪记录封存目的在于保障未成年人的隐私,减小犯罪的影响面,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再次融入社会创造有利条件,而社会调查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犯罪的影响面,二者同时适用必将削减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效果。
(七) 网络化办案如何实现犯罪记录封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各自系统内案件管理上大力推行计算机联网,纸质卷宗封存容易由具体的承办案件部门操作,但网络化如何实现犯罪记录封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网络化办公的特殊性,网络病毒、黑客等都很容易导致信息的泄露,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案件信息就会迅速传播。所以,在网络化办案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犯罪记录封存需作进一步的思考。
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言
(一)加强立法,进一步明确封存工作的主体、对象、程序
1.明确封存工作的实施主体。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同时,并没有明确规定该项制度的实施主体,实践中,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做出决定者居多。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主体应当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案件危害程度的不同,上述机关都有可能获取到相应的未成年人犯罪、违法信息,都应当将相应的犯罪、违法信息进行封存。比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期满后,社区矫正期间的有关犯罪记录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封存。此外,应当注意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主体和遵守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义务主体加以区分,前者是法的适用主体,后者是法的遵守主体。
2.立法明确封存对象。(1)18周岁的年龄限制:此处需要区分多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种情况,18周岁前后分别实施多个犯罪行为,触犯一个或数个罪名,一罪处罚或数罪并罚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法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第二种情况,因不满18周岁实施的犯罪行为被附条件不起诉、判处缓刑、宣告假释,其在相应的考验期限内犯新罪(犯新罪时已成年)或者发现判决之前还有成年后实施的犯罪没有被处罚,如果撤销缓刑、假释,实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为5年有期徒刑以下,且成年后所实施的犯罪比较轻微的,一般也应当对相应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第三种情况是行为人因不满18周岁的犯罪之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此时,不管所发现的漏罪与其之前被判处的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同一案件,如果数罪并罚的结果是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对于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完整,有新的证据证明遗漏了犯罪行为的,究竟是应当对新发现的事实部分做出判决后与原判决判处的刑罚数罪并罚还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综合前后两次行为做一个有罪判决,实践中存在争议。,一般也应当将相关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2〕将上述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的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司法政策。(2)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限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第1款从刑罚轻重的角度对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进行了限制,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相关犯罪记录应当被封存。笔者认为,此处应当从立法目的角度出发对该法条作扩大解释,对于只是被法院定罪而没有被实际判处刑罚或者没有被检察机关起诉(包含存疑不诉、酌定不诉、法定不诉)或者仅被处以行政处罚的相关犯罪、违法记录也应当予以封存。理由有三:其一,从鼓励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本着“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规则,既然对于犯罪危害程度较重的(被判刑、被起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都应当予以封存,那么对于没有被起诉或者虽被起诉但被法院免除刑罚的未成年人来说,对其相关的犯罪、违法记录予以封存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二,立法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作为犯罪记录封存的限制条件,目的是将那些犯罪危害程度较重的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分子排除在封存对象之外,但是立法并没有明确定罪免刑、不予起诉、行政处罚等不在犯罪记录封存对象之外,相反,定罪免刑、不予起诉、行政处罚等行为在符合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基础上在罪轻的“量”上还更进一步。〔3〕其三,如果将被定罪免刑、不予起诉、行政处罚的未成年人排除在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之外,那么一旦未成年人因此而在入学、就业、入伍方面被歧视或遭到冷遇,由此将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因为那些主观恶性更重、社会危险性程度更重的被判处刑罚的人的犯罪记录得到了封存,他们在入学、就业、入伍时反而没有遇到阻碍,这必然会给那些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新的创伤,影响他们回归社会,影响教育、感化、挽救的效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凡是让他人知悉后可能引起他人确定、推测、怀疑行为人曾经在未成年时实施过犯罪的材料,均应属于“犯罪记录”的内容,应当予以封存。例如:未成年人参与讯问、刑事审判的通知材料、未成年罪犯在监狱内会见亲属、监护人等的登记材料、监控材料等,以上材料一经对外公开,很有可能会泄露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因此,都应当纳入“犯罪记录”的范畴予以封存。
3.明确封存的程序。有学者主张,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应当采用多元化的启动模式,即法院职权启动模式、检察院职权启动模式、当事人申请和法院决定模式。〔4〕笔者认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第1款规定对相关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封存,“应当”一词表明这种法律规范属于命令式规范,对于负有封存职责的司法机关来说,封存犯罪记录既是职权,也是职责。只要符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5第1款,相关司法机关就应当主动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即使没有未成年犯罪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申请也应当主动予以封存,因为法律没有赋予他们不予封存的职权,相反,如果相关当事人发现司法机关或其他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对符合封存条件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有权提起申诉、控告,因此,犯罪记录封存应当是一种依职权的行为。
4.完善封存的法律后果。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第2款的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对于上述法条的理解,笔者认为需要厘清三个问题:封存主体和查询主体的保密义务、查询依据、违法后果。(1)封存主体和查询主体的保密义务。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注意:第一是封存主体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执行封存工作和封存案件查阅制度,对办案机关或其他单位的查询、调查申请进行认真审查,依法按照相关档案管理办法做出处理。应当书面告知相关查询单位履行保密义务,保障未成年人的涉案信息只用于“国家规定”的范围而不被泄露,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对于查询单位或个人非法泄露未成年人涉案信息的行为有权进行通告、制止、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的行政、刑事责任。(2)查询依据。对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对“国家规定”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6条关于“国家规定”的解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基于以上法律规范,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依据上述“国家规定”进行查询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在缺乏国家规定的依据时依据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对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查询。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立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因为依附于法律,也应当属于“国家规定”的范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有关单位在依据“国家规定”对未成年人涉案信息进行查询时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人在入伍、就业时的前科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如果冲突则不得作为查询的依据,相关犯罪记录封存单位也不得同意其查询犯罪记录的申请。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第3款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这就要求,对于因未成年时犯罪被判处监禁刑刑满释放或被刑事处罚的罪犯,相关单位在其复学、升学、就业时不得查询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如向犯罪记录封存单位申请查询的也不应被批准,否则,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单位的查询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行为。(3)违法后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封存机关和查询单位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负有保密义务,但是没有具体规定违反这种保密义务的违法后果,导致违法成本不明。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具体设计该项制度时,可以根据违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犯罪主体以及行为性质和行为轻重等确定违法后果,如详细罗列封存主体的封存义务、保密义务,查询主体的保密义务,以及违反以上义务所产生的违法后果。
(二)强化保密意识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法制宣传、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等环节容易导致案件信息泄露,因此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保密意识至关重要。举一简单事例:据大河网报道,某省高级法院院长以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犯罪案件开场,给同学们上了春季开学第一堂法制课。司法人员给在校学生们进行法制课宣讲,为了增添真实感,常常将未成年人的相关资料、犯罪过程绘声绘色加以描述。从执法过程来看,犯罪记录封存实际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再比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期满后,社区矫正期间的有关记录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封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教育、共青团、妇联、工会等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等社区基层组织、未成年罪犯所在学校或单位、未成年罪犯的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辩护人及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等,都有义务对封存的犯罪记录情况保密,依照国家规定查询这些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当对这些犯罪记录情况保密。
(三)尝试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犯罪记录消灭”也称为“前科消灭”,是指曾被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由相应国家机关抹消其犯罪记录,使其不利状态消失,恢复其正常法律地位,行为人自此在法律上被视为没有犯过罪的人的一种刑事制度。〔5〕关于犯罪记录消灭的方式,从各国的做法来看,主要有自然消灭和裁定消灭两种。〔6〕自然消灭是指:有犯罪记录的人,经过法定的期间,符合消灭犯罪记录的条件时,其犯罪记录自动归于消灭。与犯罪记录有关的一切法律后果不复存在。裁定消灭则是指:经申请人(可以是有犯罪记录的人、检察官等)的申请,审判机关根据行为人的表现,依法作出撤销犯罪记录的裁决。对于裁定消灭而言,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也就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例如判处缓刑、不起诉、劳动教养等可以由法院在裁判时做出,也可以由相关人经过法定期限后向未成年人住所地法院提起。对于裁定消灭,限于严重犯罪以及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对此,可以设置较为严格的考察条件,谨慎适用,应该围绕犯罪的原因、再犯的可能性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综合评估;另外还要规定,当事人不服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申请复议。〔7〕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新问题,因此在建立该项制度的过程中,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宜盲目地照搬国外的现成做法,而应当在全面、客观、深入地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同时,应当高度关注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实效性,研究犯罪记录得到封存是否真正对未成年人在复学、入学、就业时产生积极影响。
〔1〕〔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731-733.
〔2〕〔3〕肖中华.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J〕.法治研究,2014(1).
〔4〕田宏杰,温长军.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的构建〔J〕.法学,2012(11).
〔5〕彭新林.论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根据〔J〕.北方法学,2008(5):71.
〔6〕于志刚.刑罚消灭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714.
〔7〕马长生,彭新林.关于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一点构想——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下的前科消灭制度〔J〕.法学,2007(2).
(责任编辑 连春亮)
ProblemsandTrend—— Analysis of Minors Criminal Record Storage System
LUO Xue
(Longquanyi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engdu, Chengdu, Sichuan 610200)
Minors criminal record storage system is implement of the important criminal policy of “education, persuasion and saver” on the underage criminal suspect. The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turns the criminal record storage system to legalization. Since then, the work has obtained certain effect,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the juvenile criminal suspects to return to society. But the practice work reflects some problems of the system, lead to that the goal of criminal record storage work is hard to achieve, therefor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of criminal record storag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minors; criminal record storage system
2014-09-28
罗雪(1986-),女,四川成都人,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DF73
A
1672-2663(2014)04-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