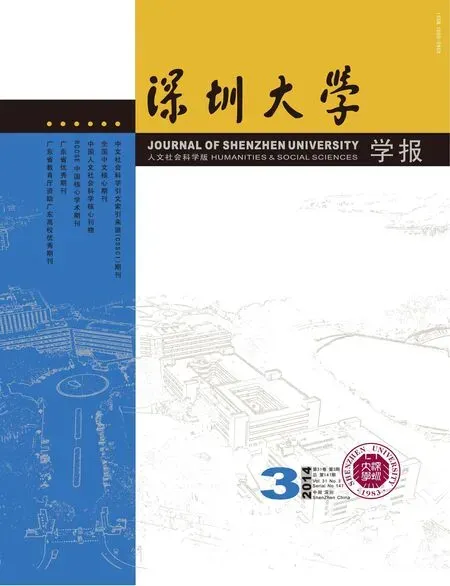差别待遇与刑事诉讼性别平等的思考
——女权主义差异与平等理论带来的启示
莫英耐,狄小华(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差别待遇与刑事诉讼性别平等的思考
——女权主义差异与平等理论带来的启示
莫英耐,狄小华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由于立法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对于尚处在弱势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中国女性,法律为实现刑事诉讼中之性别平等竭力创制的两种模式——无性别差异待遇与有性别差异待遇都隐藏着难以接受的实质性不平等。为走出差别待遇与刑事诉讼性别平等的困境,需要重塑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差异与平等观,将性别差异纳入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考量,以全面实现刑事诉讼领域的性别平等。
刑事诉讼;差别待遇;性别平等
一、基于刑事诉讼性别平等现状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成为国家的基本政治方略和法律原则,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性别平等”被理解为赋予女性与男性完全相同的权利义务,以及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基于女性特殊性给予其“额外”特别保护。对“性别平等”的这种理解相应地体现为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两种模式:其一,无性别差异待遇,将女性视为与男性完全相同,规定男女在刑事诉讼中相同的权利义务,即法律上给予女性与男性完全相同的待遇;其二,有性别差异待遇,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单独赋予女性通过刑事诉讼获取“额外”特别保护的权利。中国刑事诉讼性别平等保护的此两种立法模式,看似具备了一定的性别视角,然而却难以实现法律平等保护的初衷。考察中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性别平等保护现状,即可清晰地发现其在性别平等保护上陷入了困境。
(一)无性别差异待遇下的性别不平等
刑事诉讼中无性别差异待遇下的性别不平等主要由中性立法模式和隐性歧视立法所致。刑事诉讼中性立法模式是指刑事诉讼立法无视人的性别角色,对男女一视同仁,赋予男女刑事诉讼法律上相同的权利义务。中性立法模式看似客观中立,维护了男女平等,事实上由于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对不同情形下的男女等同对待,对女性常常引发实质性不平等。譬如,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被害人(无论男女)都无从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从形式看上,这种制度规定似乎是性别中立的,因为它对男女都适用,规定了男女相同的权利义务。但是,这项制度规定在应对性犯罪案件时,法律的平等保护受到了挑战。实践中,由于生理上的特殊性,性犯罪的侵害对象多为女性,且因为犯罪目的的特殊性(满足男性变态性欲等),犯罪分子强占的是女性的身体,而非财物,故除反抗过程中因身体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少量物质损失外,被害女性因性犯罪行为没有或少有直接的物质损失,但却由于社会与文化强加于女性的贞操与贞洁压力,而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事项被挡在诉讼大门之外,对大多数被害女性而言,罪犯被绳之以法是其获得的唯一心理慰藉,刑事诉讼并未在损害赔偿事项上给予其实质性的救济。现行刑事立案标准、证明标准等看似中立的制度在应对家庭暴力、性侵害刑事案件时也存在类似性别不平等问题。
隐性歧视立法是指由于刑事诉讼立法设置了某些条件,客观上阻碍女性在刑事诉讼中权利的行使。譬如,《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刑法》将未达“被害人重伤、死亡”程度的涉及家庭暴力的虐待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自诉案件,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如此规定,表面上看并无性别偏见,但由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男女组合的家庭中,女性往往成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而隐含着性别歧视。其表现如下:一方面,《刑法》将受害人主动要求处理作为公力救济的前置条件(即告诉才处理),客观上为受害女性寻求法律保护设置障碍,因为在家庭暴力的特殊场境下,受害女性常常因为惧怕施暴人刑满释放后实施报复,而被迫放弃追诉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自诉人负举证责任,受害女性即便鼓起勇气拿起法律武器以求保护,作为自诉人,她需要负担举证责任,家庭暴力之隐蔽性、私密性等特殊性使得其对家庭暴
力的举证超乎寻常的困难,加之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属于被控制的一方,其对家庭暴力的举证更是难上加难,常常因为举证不力而无法成功自诉。刑事诉讼相关立法关涉家庭暴力的规定客观上对女性行使权利设置了多重障碍,女性的人身安全权并未得到刑事法律的平等保护。又如根据《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采取的制止行为才属于正当防卫,如此规定,表面上也未见显性性别歧视,事实上,“当对抗的双方是家庭暴力关系中强男弱女时,就显失公平了。”[1]
(二)有性别差异待遇下的性别不平等
刑事法律性别平等保护的另一种立法模式——有性别差异待遇,基于女性特殊性,单独为女性提供额外的“特别保护”,譬如,刑法设置了以女性为保护对象的特殊罪名——强奸罪、侮辱妇女罪、强制猥亵妇女罪等等。立法初衷是对弱势性别群体(女性)的特别保护,实现刑事立法的实质性别平等。然而,这种立法模式却导致对女性更为不利的后果。以“强奸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性别平等保护的这种立法模式,认识到了男女间的性别差异,并为保护女性权利采取了积极措施。然而,这种出于“善意”的特殊保护,事实上将女性推向了更为不利的境地。将犯罪对象特定为“妇女”,是一种单一性别立法,貌似向保护女性权益倾斜,给予女性“额外”的特别保护,因为男性被强奸的情况不被视为法律事实,不受强奸法的保护。但这种立法同时固化了女性被损害、被保护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进而强化了女性的屈从地位;同时,这种单一性别立法也将性暴力犯罪议题“女性化”、“边缘化”,使得消除强奸等正义行动难以获得全社会的共同关注[2]。在强奸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被害女性在与传统性规范配套的司法审判仪式中再次被男性强权话语所“强奸”[3]。司法实践中,对强奸既遂、未遂的认定标准,无论持“接触说”或“插入说”,都是对性器官重要性的过分强调,无疑是借由法律之名固化女性的贞操节烈观,造成对被性侵女性的污名化社会评价,进而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继发性伤害。这正是无数强奸案发生后,被害人选择沉默的原因所在,而事实正如福柯所言“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性器官比其他身体器官更为重要或更不重要。”[4]刑事诉讼性别平等的特别保护模式因而遭受质疑。
我国法律为实现刑事诉讼中之性别平等竭力创制的两种模式,并未实现刑事诉讼领域的性别平等,对于尚处在脆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女性,无性别差异待遇与有性别差异待遇都隐藏着难以接受的实质性不平等,我们缘何在性别差异与刑事诉讼性别平等议题上陷入了困境? 我们究竟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差异与平等观,才能调和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中男女平等的理想与性别差异之间的矛盾,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实质性别平等?
二、刑事诉讼性别平等困境之原因探究——借助女权主义差异与平等理论的分析
关于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的理论研究最早由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推动,经由女权主义多个流派的理论辩驳,至今已形成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多视角的理论体系,所以考察西方女权主义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理论分析,必定对我们寻找问题的症结有所启发。
众所周知,平等是个有着多种理解标准的有争议的议题。西方女权主义阵营尽管有着争取女性权益、实现男女平等的共同目标,但由于在女性何以遭受性别压迫问题上的认识不同,西方女权主义不同流派形成了关于差异与平等的不同理论。“同一平等”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追求的性别平等观,它视“相同”为“平等”之基础,尽量淡化,甚至完全抹杀两性差异,认为“男女相同即是男女平等”,因此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将“性别平等”阐释为“两性机会均等”和“无差别待遇”。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将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遭遇不平等的现实归咎于女性没有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为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各项基本权利而战。起初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选举权、就业权,极力为女性走出家庭走入社会铲除一切有形障碍。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开始向法律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挑战,要求赋予男女相同的法律权利,即要求法律制度无视性别差异,不做性别区分,认为唯有法律体制的这种改良,方能实现普遍的性别平等。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推动下,西方社会取消法律中对女性的歧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至少排挤、压制、歧视女性的显性字眼得以从法律文本上移除。由于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被完全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同一平等”的思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是极具诱惑力的,得到了一切平权斗士的积极拥护。然而,当“男女平等”在官方法律文本上得以实现,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最后有形障碍已被清除,女性在主流社会依然遭遇不平等。这让西方女权主义者意识到“起码从当前来说,法律面前的绝对平等并非总是对妇女有利。”[5]
当以无视性别差异的方法来实现男女平等所牵涉的不利变得明显时,引发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同一平等”模式的深刻反思。文化女权主义提出的“差异平等论”就是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同一平等”模式的反思而形成的另一种性别平等观。文化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陷入不利境地的主要原因在于生理上的特殊性,性别中立事实上对女性是不利的,只有给予女性差别对待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因此与“同一平等论”无视、淡化男女差异相反,“差异平等论”承认两性差异,并弘扬女性特质,主张针对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殊经历与需求,给予法律上的特殊保护。于是文化女权主义对“平等”概念作出修正,提出对男女“完全相同的对待”并不是平等的全部含义 ,平等还意味着在女性有别于男性之处就应当有不同对待,法律应反映女性特有的价值和需求[6]。显然,文化女权主义的性别平等观已超越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要求男女“同一对待”之形式平等观念。然而,随着“差异平等”模式得以制度化,其所固有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从体制上承认性别差异以实现性别平等,对女性而言,这种承认带来好处却总是有代价的。这些代价包括:为特别保护女性而设计的措施结果却变成主要是防止她们去获得男人所享受的待遇;男女区别对待还会强化对女性不利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在法律上将女性看成一个需要特殊保护的类别可能鼓励同质同类的看法或 “本质先于存在论”[5],即将所有女性作为一个同类的群体来对待是对一些特殊的女性个体的不公,认为性别差异是先于社会的或生理性的已知物实际上强化了女性弱势地位的自然属性。
当重视性别差异的平等保护模式在女性权益保障上的不足也变得明显时,西方女权主义关于差异与平等的讨论陷入了理论僵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无视性别差异从平权立场捍卫性别平等;文化女性主义重视性别差异,并倡导对女性的特殊保护以实现性别平等。对于长期处于弱势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女性来说,此两种性别平等保障模式都包含着难以接受的不利和危险。无视性别差异与重视性别差异的平等模式不会在一切情形中都是最佳出路。至此,我们发现,西方传统女权主义关于性别平等的两种实现模式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前述我国刑事诉讼性别平等保护的两种立法模式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如出一辙,我们无法从传统女权主义平等理论中找寻解决我国刑事诉讼性别平等问题的一剂良药。
时间上稍晚出现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性别平等观为我们认识差异与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跳出关注男女之间差异的传统性别平等视界,兼而关注女性间的差异。对于女权主义两种传统性别平等保护模式在女性权益保护上的不足,后现代女权主义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对性别平等的两种传统阐释——无视性别差异的“同一平等”观与重视性别差异的“差异平等”观都建立在一个对性别差异的不适宜的理解上。无视性别差异的平等观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没有多少社会意义,亦即它无视性与社会性别对男女生活方面的影响之大;重视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观自然对影响男女生活的性别差异十分敏感,但其对平等的阐释总是依赖于这样一个性别差异观念——女人在某些方面比男人低劣,并且将女性亚群体与男人之间的性别差异理解为全体女性的共同本质,而忽略了女性不同群体及个体间存在的影响平等实现的种族、民族、阶级、宗教、婚姻状况等等方面的差异[5]。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更为完整的性别平等思想——恰当的性别平等应当是对女性间的差异和男女间的差异都很敏感,亦即性别平等的观念必须包容男女间的差异以及女性间的差异。同时提出女性间的差异及男女差异都不是先于社会而存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受到了社会力量的强烈影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传统两种性别平等保护模式忽略或强化性别差异都不必然带来男女平等,这是一种“差异困境”[6],不管是无视性别差异的中立策略,抑或是明确承认性别差异的特别对待策略,“差异困境”都缘于两种模式所带来的平等的相反结果,甚至强化或再生女性的屈从地位。走出“差异困境”的方法是摒弃把“差异”视为一定群体固有的、客观的、本质的特性的传统观念[6],而以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性别差异,亦即在思考性别平等问题时,必须认识到妇女从属的历史,尤其是它与其他从属群体的历史的交叉,是如何形成了并继续形成两性的差别以及我们看待和评价这些差别的方式的[5]。
后现代女权主义对性别平等的理解对我们思考性别平等问题带来了有益启示——它承认男女差异以及女性之间差异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性别平等的制度建构及实践中必须正视当前我们无法逾越的性别鸿沟。但它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先于社会的或生理性的已知物,而认识到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因素,从而避免性别差异与平等的议题陷入本质主义的执泥,启发我们以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看待性别问题。以动态的方式理解性别差异有助于我们消解对女性不利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为我们阐释了改变女性“他者”形象的理论可能性。
综括上论,如果说西方传统女权主义关于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两种模式的策略失当同时也是我国两种刑事诉讼性别平等保护模式无法实现事实上的性别平等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后现代女权主义性别平等的思想则击中了我国刑事诉讼性别平等问题的要害。我国刑事诉讼无性别差异待遇的立法模式,完全抹杀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性别鸿沟,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两性间的性别差异是显著的、无法忽略的,当刑事诉讼相关立法在形式平等的名义下忽略这些差异时,两性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便被掩盖,甚至被合理合法化,至少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在有些情况下并不能保证结果上的男女平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实现男女平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女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信。然而,中国女性在权力享有、社会资源利用上尚不及男性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诉讼正是一个利用权力(主要是司法权)与社会资源(主要是司法资源)以维护自身权益的的过程,权力与社会资源享有上的不平等,使得女性在形式平等的刑事诉讼立法面前遭遇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上的实质不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有性别差异待遇的立法模式,认识到了男女间的差异,但缺乏对社会性别差异的深层洞见。男女之间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外,社会与文化还在男女外显的生物性标志的基础上,以社会性方式建构出两性的社会性关系以及社会性差异,即社会性别。中国女性的生活更多地受到社会性别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在现阶段难以消除,导致中国女性在“特别”保护的同时遭受社会性别层面的更大伤害。一言以蔽之,我国刑事诉讼性别平等问题的症结在于刑事诉讼性别平等观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无论是无性别差异待遇的“同等保护”模式,抑或是有性别差异待遇的“特别保护”模式,均未在立法与司法中进行充分的社会性别差异考量,导致女性在刑事诉讼中遭遇事实上的不平等。
三、走出刑事诉讼性别平等困境之对策
西方女权主义构思平等概念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深入反思中国刑事诉讼性别平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鉴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因缺乏社会性别视角而导致女性在刑事诉讼中遭遇实质性不平等的现状,我们需要从宏观思想层面、中观立法层面以及微观司法层面对性别差异作出全方位回应,以全面实现刑事诉讼中的性别平等。
首先,在宏观思想层面,重塑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差异与刑事诉讼平等观。相较于男性,女性既具有人的一般性,又独有使其之所以成为“女人”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上的先天性差异,这些差异乃自然造化之结果,都有其当然存在的价值,人类生命因此得以繁衍生息,因此应受到承认和尊重,而不应被忽略,基于女性的生理特殊性给予特别保护是必要的;其二,社会与文化后天造就的社会性别差异,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决定其性别倾向的因素中,除了生物性差异外,更多的因素在于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别差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性别差异与性别鸿沟,大多与先天性生物差异无关,而是在社会与文化的逐步建构下形成的两套关于男性或女性行为方式和活动准则的不同性别规范体系。这些社会性别差异无不表现为男性优势、女性弱势,现实生活中男女地位之不平等正是源自社会与文化的这种后天建构作用。社会性别差异与生物性别差异一样,是任何性别平等议题不可忽略的两大重要因素。重塑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差异与刑事诉讼平等观,要求我们在思考刑事诉讼性别平等保护议题时,必须承认和尊重两性的生物性差异和社会性差异,尤其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差异。其“硬核”并非单纯要求女性在刑事诉讼中能够享有与男性完全相同的权利,它更要求在界定和分配各项诉讼权利的过程中,纳入女性的视角及生存体验,要求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的社会性别意识[7]。要求刑事诉讼相关立法既要确认和保障女性与男性平等地享有刑事诉讼中的一般权利,又要赋予并保障女性基于其生理性别及社会性别之特殊性单独享有的特别权利。此外,我们还应当对不同女性群体及个体间的差异时刻保持敏感,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对于个案中的女性,我们需要针对其特定需要,采取临时性的“特别措施”。但是,在给予女性特殊待遇的同时,我们需要遵循“合理原则”,防止不合理的区别对待实际上造成对女性权利的剥夺或限制。
其次,在中观层面,对刑事诉讼立法进行性别检审。将性别视角作为刑事诉讼立法方法论,一是对我们现行刑事诉讼相关法律、政策,重新以社会性别的视角进行检审,清除其中隐含的性别偏见,使刑事诉讼相关法律、政策成为维护社会性别平等的工具;二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政策付诸实施前,进行全面的性别影响评估,主要包括这项法律、政策的施行会给女性带来何种事实上和实质上的影响?如果会给女性带来实质性的、严重的不公或损害,则该项法律或政策不应实施,如果仅是些许损害,我们则应有相关的补救方案[7]。
最后,在微观层面,对刑事诉讼实践进行性别考量[8]。将性别视角作为刑事司法实践的方法论,在刑事诉讼个案中进行性别考量。刑事司法人员必须现实而客观地面对性别差异,正确认识两性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经历方面的差异,以通过手中掌握的司法裁判权在具体个案中对正义进行最有效的衡平,力求实现最大化的性别公正。而欲达此目的,需要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培养刑事司法人员社会性别分析思维以及能动保护的女性关怀意识。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关涉女性的案件,司法人员应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其发生、发展之原因,寻求个案公正之应对方法,确保司法公正的真正实现。第二,优化刑事司法人员的性别结构。虽然现代司法之“程序公正”理念要求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诉讼参与者,法官应只服从法律,而不受其他任何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刑事诉讼活动也不应存在基于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的歧视和偏见,但诉讼活动的作业者是社会化了的“人”而非机器,故而性别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实践中也常见不同性别的法官面对不同性别的当事人态度迥异,或引发同情,或引起反感,进而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导致定罪、量刑差异。而司法活动中的这种性别差异现象是无法根除的,很难避免其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因此,为提高刑事审判的正义质量,我们需要对刑事司法作制度上和技术上的改进[8],使其迈向性别正义之目标。对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人员性别结构进行优化,主要是对刑事审判组织的人员进行合理性别搭配[8]。当然,并非所有案件的审理都需要进行审判组织人员的性别搭配,否则会徒增司法人力资源运作成本,我们只需对性别敏感度较强的两类案件——涉性刑事案件、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实行此要求[9],对这两类案件的审理必须由女性法官和男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由此可以衡平性别差异,减少由于单一性别的同情或仇恨心理而产生的“畸形”判决,形成更为公正的判决[10]。
[1]陈敏.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我国立法中的性别不平等[J].法学杂志,2004,(5).
[2]张祺.对有关妇女性侵害法律和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以强奸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06,(12).
[3]马姝.论强奸罪应当废除——基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种观点[J].河北法学,2011,(12).
[4][法]福柯著.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6、75—77.
[5][美]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A].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8.191—212.
[6]刘小楠.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平等与差异观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
[7]王丽萍.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及其启示[J].法学论坛,2004,(1).
[8]潘怀平.性别差异宜纳入司法考量[N].检察日报,2010-10-27.
[9]贺寿南.论司法裁判中法律规则与潜规则的博弈选择[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3):49-53.
[10]彭志刚,邢晓玲.论品格证据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4):113-117.
【责任编辑:张西山】
Thoughts on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riminal Litigation:inspirations from feminist theories about difference and equality
MO Ying-nai,DI Xiao-hua
(Nanjing University Faculty of Law,Nanjing,Jiangsu 210093)
As a result of non-gender-differentiated legislation,women,who still constitute a second class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in China,are not afforded substantive equality with gender-differentiated and nongender-differentiated procedures in criminal litigation practiced today.In order to move out of the dilemma of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riminal litigation,we need to revamp our views regarding sexual differences and equality.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sexu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tru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spher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may be attained.
criminal litigation;differentiated treatment;gender equality
D 925.2
A
1000-260X(2014)03-0086-06
2014-04-20
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2012CW03);江苏省普通高校博士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2_0015)
莫英耐,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刑法学研究;狄小华,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