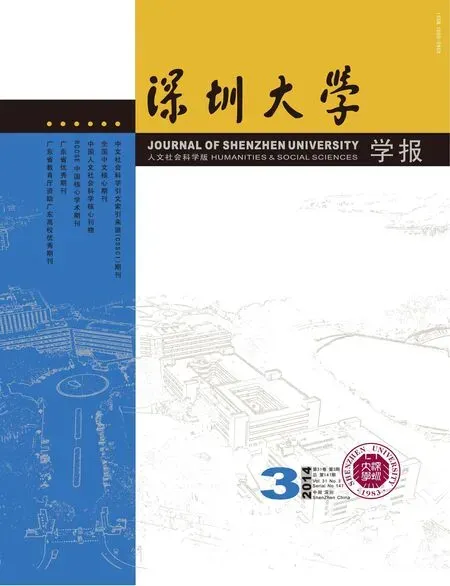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比较研究
郑湘萍,田启波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比较研究
郑湘萍,田启波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均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重要生态思潮,都孕育于当时西方社会蓬勃发展的环境运动。两者都反对主客二分的机械自然观,都重视环境实践并关注环境正义,并主张未来理想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考察生态危机根源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科学技术、经济理性、价值观念等维度出发,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度挖掘;生态女性主义则主要从文化视角透视生态危机,认为其根源于西方父权制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遵循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相结合的思路,主张建立全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则采取一种思想文化进路,强调只有恢复女性原则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上,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深受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主张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生态女性主义则强调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尤其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在社会实践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了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组成部分;生态女性主义发出了女性在生态问题上的声音,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表现出行动主义取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应互为借鉴,以促进各自发展和环境哲学的深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环境正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活跃的生长点,它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深入分析全球化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内在关系,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努力寻求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变革途径。生态女性主义则以女性性别视角深入探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试图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贬低自然与贬低女性之间的特殊关联,强烈反对西方社会父权制世界观及其二元式思维方式对自然和女性的共同压迫,主张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和谐关系,最终实现自然解放和妇女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异同点,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影响。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共同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自然观、环境正义以及未来理想社会建构上有着诸多共同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机械自然观将自然视为二元化、分裂和碎片化的,外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被严格区分,自然与文化、自然与历史处于对立面。自然不断受到人类这个绝对权威的残酷拷问和严厉质询,不得不讲出自身秘密,最终失去其原有本性。自17世纪以来,将自然视为一种机械式结构体的新科学主义自然观取代了原来那种有机整体自然观,这标志着非人类或外在自然界的各种因素已从理论上被割裂出去[1](P34)。人们基于操纵自然的目的来理论探索自然内部,以工具主义思路将其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人们坚信,科学技术在巫术般光环笼罩下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产品,人类对物质欲望的渴求以及对所谓幸福的追求会得到有效满足。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事实证明,偏离价值理性的科学技术并未按照人们预先设计的路线发展,在自然异化加深的同时,人的异化状况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的确是一个物理实在,但同时具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应被视为一个整体放到历史长河中为人类考察和研究。技术联系只是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一部分,二者在文化和价值等方面存在重要联系。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加深的异化现状提醒人类合理控制自身行为,全面反思控制自然的非法化。
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自然”概念和“女性”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与女性有着密切联系的自然是有活力的,而非僵硬的,它并非只供人类剥削的对象,而是与人有机共存。自然与人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前者为后者提供生存所需之物,后者则应养育与看护前者,将其视为家庭和社区不可缺少的成员。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父权制以及二元论思维方式共同压迫自然与女性。在《自然之死》一书中,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C.麦西特(Carolyn Merchant)从历史视角出发,详细论证了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观逐步被以男性为主导的机械宇宙观摧毁的过程,并精辟分析了人类企图统治自然这一妄想的父权制根源。总的说来,生态女性主义认为,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形成的父权制主张男性中心论,以权力、控制、等级制和竞争为主要特征,并借助二元论思维模式和简化论科学观来实现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征服。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用整体主义的自然和谐观取代西方父权制下的价值等级和价值二分的世界观。
如上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都反对把自然看成是机械的僵化的机器,认为自然界有着人类不能超越的自身界限,并作为有机的整体与人类共存。人类应该抛弃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转而运用整体的联系的思维方式来探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第二,二者都重视环境实践并关注环境正义。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紧密相关,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社会正义包括环境正义,解决环境难题的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正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J.奥康纳(James O’Conner)认为,正义应该是事物的平等生产,而非事物的平等分配。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或环境正义包括:“一方面是环境利益(如风景、有河流灌溉的农场土地)的平等分配,另一方面则是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如靠近有毒废弃物的倾倒场所,受到侵蚀的土壤)的平等分配。”[1](P535)人们越是奉行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环境分配性正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越会遭受更严重的破坏,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计算无法彻底解决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环境正义应该是环境关注和社会公正的有机结合。D.佩珀(David Pepper)则强调,由于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缺乏社会正义维度,社会正义在环境问题中越来越紧迫和必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自然界被人类以非公正方式加以对待。自然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尊重,反而被人类操纵和主宰。两者的关系异化成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与那种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本真关系相去甚远。其次,代际之间环境非正义现象普遍存在。资本主义内含经济成本外在化趋势,不得不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未来以维持其顺利运行,这必然导致后代被迫为前辈的环境破坏行为付出代价。再次,特定国家内部存在诸多环境非正义现象,每个阶级不平等地分担环境利益以及环境风险。诸如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大量废弃物、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难题不平等地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其阶级性非常明显。穷人比富人更容易遭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各种危险,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最后,生态殖民主义是当今世界国际环境非正义的典型表现。福斯特指出,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新殖民主义倾向内置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进程之中,其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不可能成为其生产目的,高生产、高消费的运行方式是其必然选择。这种有失环境正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高速扩展到地球各个角落。奥康纳强调,发达的北部国家对不发达的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少数民族造成巨大的生态伤害,前者的兴旺发达以后者的生态付出为前提。然而,这种生态伤害并非后者理所当然应承担的。更加可怕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公正国际秩序的支持下,生态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愈演愈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行径直接导致国际环境非正义,这构成社会正义的最大威胁,严重损害社会正义和平等,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施生态掠夺的生态霸权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
贯彻落实开孔施工的时候,应规避冲击振动所引发的邻孔塌陷问题[2]。通常情况下,要在完成邻孔混凝土浇筑工作一天以后进行钻进作业。若孔口要采用人工填土的方式,应当在开钻之前,将适量黏土与粒径不超过15cm的片石填入到孔内,将顶部抛平,保证泥浆比重控制在1.6以内。当钻进的深度达到1m以后就要回填黏土。综合考虑具体的状况,选择使用低冲程冲砸的方式反复操作以上流程。当冲砸在钻头顶部护筒之下1m的情况下,即可选择高冲程钻进的方式,最终完成开孔作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而从制度根源上挖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非正义现象出现的深刻原因。它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持续地削弱生态系统,不断制造社会不公,这归根结底在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遵循利润最大化逻辑。环境正义严重缺失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利润动机和剥削本质造成的。建构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全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摧毁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不公平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这是人类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维护环境正义、寻求持续发展的真正出路。“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而且交换价值服从使用价值。 ”[1](P439-44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无法在社会化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 ”[1](P538)
将女性问题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的做法是生态女性主义一贯主题,其在重视环境实践的基础上积极维护环境正义。早在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生态女性主义者聚集在美国华盛顿,发动并领导了两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即 “妇女的五角大楼行动”。她们呼吁 “维护妇女的社会、经济和生育的正当权利”,强烈谴责军备竞赛和“出于私利无节制剥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2]生态女性主义从种族、性别与环境关怀之间相互依存的角度出发,积极提倡公正伦理原则,希望给地球和女性带来更多关爱和正义。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生态危机给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不论是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在各个国家之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儿童、有色人种、社会低收入者、少数族群等人群无力抵抗各种生态灾害,他们总是承受更大生态伤害,承担较大环境风险,并较少分享环境权益。环境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男性与女性在生态权益和生态责任等方面坚持平等和公正原则,而且要求自然受到人类社会的公平对待。作为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印度学者V.席瓦(Vandana Shiva)非常关注国际环境正义,尤其是跨国公司给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带来的恶性发展和生物剽窃等问题,并严厉批判跨国公司对被殖民国家的妇女和自然所犯的双重罪恶。总的来说,生态女性主义者是典型的行动主义者,她们“组织游行示威以展示压迫妇女与压迫动物之间的联系;封锁那些为砍伐和毁坏森林而修建的道路;为遭受暴力侵犯的妇女和动物提供保护;领导妇女精神运动团体和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团体;抗议并阻止生物技术的扩散”[3]。在维护环境正义、妇女健康、各种形式的原住民权利以及推进绿色运动进一步发展等方面,这些行动作出了极大贡献。
第三,二者都主张未来理想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目标上都主张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构一种新型和谐关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正义是其所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首要价值目标,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则是其生产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发展模式,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奉行的高度繁荣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倡导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以保护环境[4]。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经济“零增长”(zero grow th)观点,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放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立场,主张建立一种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适度发展经济模式,在理智地使用自然的基础上保护自然,同时维护后代人的利益。他们始终坚信,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将成功建构人与自然的全新关系。人类能够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人类物质有限却又丰富多样的需求将会得到满足。自然界成为人类的家园,人则居于中心地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尽情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如建设“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建设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建构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等。他们坚持把“非暴力”革命作为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提出了多种社会变革的道路设计,如三步走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文化传统进行嫁接,劳工战略以及生态革命道路。在寻求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时,他们主张汇合马克思主义运动(“红色”)和生态运动(“绿色”)政治力量,并尝试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5]。
在建构未来理想社会时,生态女性主义者将女性主义原则和生态学原则融合在一起,特别强调多样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崇尚简朴的生活模式,坚持产品主要是为了自用而非市场生产,倡导人类扮演生态社区和人类社区“耕种者和守望者”角色。H.皮特勒(H ilkka Pietil)主张建立“耕作经济”(cultivation economy)模式,在允许经济活动存在的同时,特别强调那些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决策要以目前需要为基础,也要考虑到对环境和后代的影响。这一模式主张通过为人们提供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等需要来成就其他方面的才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使当地社会可持续地生存。
席瓦和M.米斯(Maria M ies)则提出以生存必需视角来建设未来理想社会,按照所谓女性原则来组织社会生产。在她们看来,西方父权制社会遵循着主张侵略、扩张、压迫妇女以及掠夺地球的男性原则。与此相反,她们主张的女性原则是一个用非暴力方式感知世界,通过维持自然界互联性以及多样性以保存生命进行活动的范畴,是一个与现代简化论科学相对抗的范畴[6](P14)。她们在《生态女性主义》一书中勾画了一个全新的愿景:人们及其后代以及地球上所有作为人类伙伴的生物要过上一种新生活,所有男人和妇女就应积极参与生存斗争,彻底抵制流行于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发展模式,以生存观点建构一个“好社会”(good society),即一个女性主义的、非殖民的、非剥削的社会。然而,席瓦等生态女性主义者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构建新社会的途径。她们主张为了环境保护而减少消费、甚至拒绝发展的生活方式。这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不会为了保护环境而拒绝发展;发达国家也不会断然抛弃之前殖民式发展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社会大众虽然关注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但是如果需要改变自身生活方式以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则未必乐于接受。众所周知,大多数人既不是素食者,也不是和平主义者,更不是抱树主义者,他们并不希望急着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正如李银河所指出的,席瓦拒绝无限制发展、追求生存必需的发展方案,仍然需要继续深化,这样才能避免流于空谈[7]。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畅想的未来生态型理想社会蓝图确实美好,但由于二者提出的构建策略和实施途径均不太切合当前社会实际,其理想社会建构蒙上了一层乌托邦色彩。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差异
生态学马克思和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二者考察生态危机根源的视角不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科学技术、经济理性、价值观念等多个维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上深度挖掘其生态危机的根源。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技术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遵循的工具主义技术理性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类对科学技术的错误认识和使用。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这种片面看法,主张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本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当性,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及其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和资源能源危机。
其次,A.高兹(Andre Gorz)着重从经济理性层面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高兹指出,经济理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最大化、消费最大化和需求最大化的理性。在发端于计算和核算的经济理性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开始突破“够了就行”的原则,转而崇尚“越多越好”原则。经济理性产生了巨大危害,不仅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且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蜕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并逐步使生活世界“殖民化”。这三种危害是经济理性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时期的普遍危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奴隶主义的出现则是经济理性新危害的具体表现。高兹主张建立一种新理性即生态理性来超越经济理性。生态理性是指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人意识到人的活动具有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理性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但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其动机是保护生态、追求生态利益最大化。在高兹看来,“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以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能源的花费来生产这些东西。”[8]生态理性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即“更少但更好”。
再次,W.莱斯(William Leiss)从哲学价值观视角来剖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考察了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 “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生态效应,认为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控制自然”观念,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作为一种既有进步性又有退步性的悖论,“控制自然”的征兆是人对人的控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观念彻底沦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消极作用已经掩盖并大大超越其积极作用。人们应将“控制自然”重新解释为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而不再理解成对自然的控制。
生态女性主义主要从文化视角透视生态危机,认为其根源于西方父权制文化。K.J.沃伦 (Karen J Warren)认为,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统治自然与统治妇女存在某种概念上的联系。她指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均源于西方父权制世界观及其意识形态,这种压迫性概念框架包括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以及统治逻辑。西方父权制认为,不同个体有道德等级高低之分,高级特征的物种合理统治低级特征的物种,这证明了奴役女性和奴役自然的合理性。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的男性主导原则扼杀了女性原则。
第二,二者依据不同的思想进路来解决环境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采取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相结合的思路来分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根源,认为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激烈斗争才是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必须否定其拼命追逐利润最大化这一固有逻辑,建立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高兹提出,现代工业社会应使生态合理化标准有效制约其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成功进行生态重建。佩珀则认为,只有植根于生态理性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才能克服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在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能重新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终结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采取一种思想文化进路探讨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当前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在于父权制的滥觞和女性原则的毁灭,恢复女性原则才是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席瓦强调,西方父权式发展与现代简化论科学结盟,二者相互支持、相互辩护。在一个本性上相连和多样的世界里,现代科学简化论内含暴力和破坏。而女性原则允许实行生态转换,从暴力转换为非暴力,从破坏转换为创造,从反对生命转换为给予生命,从统一性转换为多样性,从分裂以及简化论转换为整体论和复杂性。席瓦提出,“女性原则的恢复以包容性为基础。”[6](P50)女性原则的恢复是一种在自然界、妇女以及男性的存在与感知中进行创造性的恢复。自然界被视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女性被视为生产性的、活跃的;在男性身上,女性原则的恢复意味着重置行为来创造一个增加生命而非减少或威胁生命的社会。
第三,二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不一致。
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不同时期有变化。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较为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B.阿格尔(Ben Agger)、莱斯等人虽没有明确提倡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但其设想的关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明显深受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R.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和佩珀率先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为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存在走向反工业化的生态浪漫主义危险,应该清除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他们强调,人类在检讨自身对自然界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建立一种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自然观。人与自然都是生物性存在,都具有自然本质。自然没有独立于人的存在价值,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社会性。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类中心论新价值观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这种价值观以全人类利益作为衡量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尺度,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社会生产目的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满足社会需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权利;尊重个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反对官僚主义组织形式,支持实行直接民主;反对资本剥削劳动,要求劳动真正成为人们自身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把劳动仅仅作为生存手段[9]。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拒绝生态中心主义对增长和人口过剩的简单限制,认为生态运动应该集中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度增长。在他们看来,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一种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主义基础上,坚定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总之,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辩证法的指导下,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在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同时,断然拒绝技术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资本主义积累逻辑。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尤其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并非宽泛的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或父权制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概念包含的“人类”实际上只是男人,特别是白人男子。妇女(以及其他弱小民族)只是征服自然这一“伟大事业”的受害者[10]。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以更广泛的生物中心观取代人类中心观,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以及那些依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第四,二者在实践中产生不同影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动向。正如奥康纳所强调的,整个世界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发生了诸多变化,“导致了一些有关社会及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生态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1](前言P5)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区分自身理论和实践,着重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和概括,以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命名其实践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沿袭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理论观点的同时,有力应对了现代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诸多挑战,大为提高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导的社会运动是广义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部分,高举马克思主义红色旗帜,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现代西方生态哲学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的派别之一。生态学女性主义虽然没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但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经济分析理论等,发出了女性在生态问题上不可或缺的声音,为人类生态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了必要的反思,为马克思主义应对现代生态学的挑战提供了借鉴。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者重视纯理论研究不同,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表现出可贵的行动主义取向。她曾亲身参与印度20世纪70年代的抱树运动,创立九种种子基金会,发起“为多样化的多种女性”运动等等。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实践不仅对保护印度种子和食物主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已见成效。印度的“抱树运动”、肯尼亚的“绿色带运动”、中国的“保护黄河母亲”运动等成为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活动的典范。但是,生态女性主义目前还难以真正让社会大众接受并践行,主要是因为面临参与人群和保护人群狭隘化的现实困境,在实践中缺乏多样化手段以及与政府间的深度沟通合作,加上思想激进和具有乌托邦色彩。
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生态运动中产生了相应影响,为解决当前生态难题提出了必要的生态智慧。二者应互为借鉴、取长补短,以促进各自发展和环境哲学的深化。生态女性主义一直被质疑有 “女性中心主义”(female centralism)之嫌,其主张通过恢复女性原则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难以获得高度认同。实际上,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重新定义和审视人类中心概念及其作用,在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平等和自由[1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尤其值得生态女性主义反思。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生态中心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合理性和非现实性,辨析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温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异同,这有利于人类正确认识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更好地承担维护生态平衡、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他们没有陷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观层面的抽象争论,主张把生态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制度层面加以解决。这不仅增强了正面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力度,而且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正确方向。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可参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三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方法,不能将所有生态问题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罪恶,而应将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与价值批判紧密结合起来,以进一步增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吸收生态女性主义的精华,善于从资本主义父权制世界观批判和二元论思维方式的解构等视角,探讨自然和女性的同时解放,尤其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生态实践来夯实其理论基础,其行动主义取向值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借鉴。
[1][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Stephanie Lahar.Ecofem inist Theory and Grassroots Politic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M].Mc-Graw-Hill inc,1999.445.
[3]王云霞、李建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异同之辨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7,(6).
[4]韩欲立,温晓春.生态文明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基础[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11.
[5]郑湘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32-156.
[6]Vandana Shiva.Staying alive:Women,Ecology and Survival in India[M].London:Zed Books Ltd,1988.
[7]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87.
[8]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32.
[9]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修订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34.
[10]杨通进.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J].广东社会科学,2003,(4).
[11]彭慧洁.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困境[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3.
A Com parative Study of Eco-Marxism and Eco-Feminism
ZHENG Xiang-ping,TIAN Qi-bo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518060)
As two different forms ofWestern ecological thinking,Eco-Marxism and Eco-Feminism grew out of the same period.Both reject the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which is grounded in the subject-object dichotomy;both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and both stand for the opinion that human being will get along well with nature in the future ideal society.Yet,with regards the cause of ecological crisis,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anthropocentrism an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they have different ideas.Eco-Marxism and Eco-Feminism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This will help promote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deepen their environmental thinking.
Eco-Marxism;Eco-Feminism;view of nature;environmental justice
B 03
A
1000-260X(2014)03-0071-07
2013-11-25
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课题“社会思潮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2JD71011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项目“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启示”(GD13CZX02);深圳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的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2QNCG16)
郑湘萍,法学博士,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田启波,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从事生态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董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