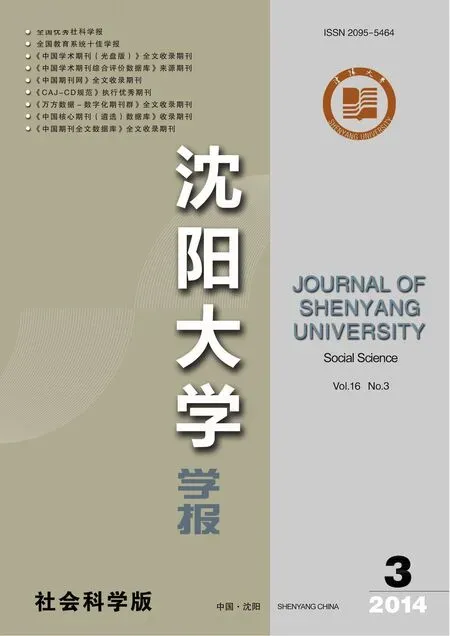现代化镜像中的农村社会
——孙惠芬农村题材小说创作
郑 晓 明
(1.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2.沈阳大学 新民师范学院,辽宁 沈阳 110300)
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以血亲关系为中心的宗法礼俗社会,大陆式的农业生产模式以其稳定性、规律性和结构性生成了这种社会结构。中国从封建社会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经济都欠发达,重农抑商的文化思维范式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生成了闭塞的农村社会。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当下的农村社会也在主动或被动的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在不断解构和重构,农村文化表层结构解构表象下依然是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重构过程。对孙惠芬“歇马山庄系列”小说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乡土社会在新时代追随改革开放步伐悄然完成的解构与重构过程。
一、现代化冲击下的乡村文化重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现代化强国之梦开始建构起来,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推进,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工业的标志,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力量渐趋强大。现代化国家的建立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重心,农村的城镇化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农民的心理阵痛。孙津在《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中说“我把农民文化看成一种社会功能特征。这种功能特征是在自然结构、社会结构、人的观念这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历史地形成的,它包括资源、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组织、习俗、族亲、心态、制度等多方面因素,或者说体现为这些因素某种转为固定的功能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文化的裂变,其实就是农民这个社会主体自身的一种变化。”[1]因而现代化建设给农村文化带来的冲击纠结在广大农民的身上,孙惠芬用文学的方式展开着对农村现代化的文化思辨。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农村社会的表层结构在逐渐走向瓦解,但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又在以传统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为核心不断地重构。孙惠芬在其“歇马山庄”系列小说中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辽南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一切,现代化的气息无法阻遏地进入了“歇马山庄”这个封闭静谧的小山村,许多家用电器、通讯工具、交通工具被引入,乡民在惊奇错愕中慢慢适应,他们的日常生活表象确实发生着巨大变化,但深层文化心理的变化却非常缓慢。《上塘书》中上塘村的婚姻形式、贸易方式、交通工具、建筑风格都在发生着变化,但上塘依然是上塘,村长爹的死曾经使上塘脱轨了一个冬天,成为村民谈论的焦点,当春天到来时,上塘的一切又重新回到旧有的轨道上,缓慢地随着时代的步伐渐变着。电话、电视给上塘传来了外面的消息,但大多时候电视只是家庭的装饰品,只有闲暇的时光才用电视来打发。聚在一起时也纵谈国家大事,但上塘人大多时间都在忙碌、劳作着,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有闲心去想别的;上塘人带着手表,但在劳作时依然看太阳来确定时间,用影子的变化来表述时间,人们心中的日子依然是老皇历;处在辽东半岛的上塘离大连很近,很多上塘人也出门打工,但大都是候鸟式的民工,年首出门打工岁末回家,农闲时打工农忙时务农,他们的家人除了多一份思念牵挂,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些打工者把青春和激情甚至健康献给了城市,同时也受到过城市文明的洗礼,但当他们无法再出门打工时,便又重新回归单调、寂寞的乡村生活。《民工》中的鞠广大、鞠福生长期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漂泊流浪的身体之根却在农村,当鞠广大的女人死去后,这对父子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感觉失去了维系自己心灵家园的精神支柱。《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曾经在城里做过小姐,风光无限,最终还是回到歇马山庄做了一个普通的女人,被传统的道德观念淹没,过上了与她姑婆婆相同的生活。《亲戚》中的吕十四因为要给表哥孔兴洋准备丰盛的晚餐在炸鱼的过程中被炸伤,但他却没有丝毫怪罪表哥的意思,因为是亲戚。小说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人的心理变化,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的变化有时把人们的心理距离拉远了,似乎很难回到当初那种真淳的情感中,但作为传统乡俗社会的农村依然把亲戚的感情放在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纯朴之情。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中国北方的大陆旱地农业种植方式又具有极强的季节性,这对农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人作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而生活,记忆和期望的纽带把他束缚在这环境中。人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生存着,而是作为家庭中的成员,团体的同人,具有众所周知历史渊源的各种‘人群’中的组成部分而生存着。借助于传统,他成为他自身。”[2]广大农民在农闲时节创造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这些习俗形成他们的身份标示。孙惠芬在《上塘书》中全景式地展现了这里的年节习俗、结婚仪式、丧葬仪式、邻里关系、家庭观念,以及农民思想中的迷信观念。在历史的演进已然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而广大的农村依然在许多方面固守着老传统,这种社会生活模式的背后,虽然已经渗入了现代气息,但生活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比如,在丧葬仪式燃烧的扎纸中出现了电话、电视、轿车、冰箱等现代新事物,但烧扎纸的本意仍是用来满足死人的宿愿或者建构冥间的生活。在邻里出现矛盾时出面解决的并非农村的行政长官——村长刘立功,而是受人敬重的鞠方采,民间的权力认同并非政治权威而是民俗人气。现代文明渗入了上塘,但传统文化依然在方方面面把这里构建成固若金汤的堡垒,它可以吸纳新鲜的事物和观念,并将其同化、融入到农村原有的文化体系中,进行自身文化结构的微调,在表层结构的解构中完成以传统文化内核为基础的自身重构。
稳定、静寂是农村乡土社会的生活特点,在这个世界里自然的天籁和稳固的结构是主体,缺少新鲜的文化气息涌入,乡民在静寂和稳定的生活中同样渴望惊奇的变化和瞬间的喧哗,所以人们把各种能够吸引注意力的时间都视为节日,如正月的扭秧歌、结婚时的“坐床”、丧葬的扎纸、张五忱的猴戏,甚至是邻里间的争吵都被看作是打破静寂的欢乐时刻。乡土世界作为封闭的文化单元,在周而复始的不断重复中向前行进,同时许多乡俗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下不断地走向凋敝。农村中的许多青年和精英被城市所吸纳,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无奈地守望着农村。如《歇马山庄》中的李平、玉柱、于成子,《民工》中的鞠福生,《吉宽的马车》中的申吉宽、许妹娜、林榕真、黑牡丹等都曾经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争取进入城市的机会,他们中有的无奈地重回故里,有的依然在漂泊,但也有成功进入城市者。农村的传统社会生活模式最终会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下走向解体,但也许那时的农村可能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所占比重很小了,而农民将走出固守的田园生活。
在当下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过程中,传统宗法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已然出现了裂痕,乡土文化秩序出现混乱,“只要存在分为秩序和混乱,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了现代性。”[3]现代的价值理念正悄然地通过这裂隙进入到乡土传统文化的结构中,《还乡》中“叔叔”在家乡前后不同的遭遇让人们窥探到人情的冷暖,利益取代了人情的评判标准,当“叔叔”能够给乡民带来利益的时候,他受到人们的拥戴,而在他失势的时候即便是至亲的人也会在他受伤的心灵上增加痛苦。《亲戚》中吕十四的儿子偷了亲戚负责放映的录像机,《吉宽的马车》中的许妹娜虽然喜欢吉宽却嫁给了李国平,就因为李国平是城市打工的小包工头,可以带她离开农村。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渐渐冲淡了人与人之间的纯朴情感。“社会只有重建精神崇拜,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4]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乡土中国正在重新完成自我的“精神崇拜”。
二、现代化镜像中浪漫的乡情追寻
鲍德里亚尔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特殊的文明样式,它不同于传统,也即不同于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传统文化在地理上和符号上是异质的;而现代性发韧于西方,然后传遍全世界,世界由此成为同质的世界。”[5]全球化从表象上看是从西方社会发起的,从初衷看是渴望用西方的模式来整合世界,这必将消弥异种文化,但在其展开中可以看到全球化实际也为世界提供了机会,各种异质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属于乡土文化,农村的城镇化必然引发传统文化的裂变,这种裂变的危机在当下文化氛围中是一种不可解脱的必然。恰恰是在这种乡土文化的解构与重构中孙惠芬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一程一程失去家园之后,我发现,只有虚构,才是我真正的家园。”(《舞者》)生活在大城市的孙惠芬只有借助虚构的小说世界来重回自己精神的家园。
孙惠芬的《舞者》是一篇自叙传奇式的小说,作家借助女性的“倾诉”展现了自我的裂变过程。七岁的“我”在母亲的“过膝袜子”事件中品味到母亲作为乡下女人与在镇上长大的二娘、四婶的差别,在内心里渴望自己成为“青堆子镇上的女人,”于是“我”开始了自我的追寻过程,也是对乡村的逃离过程:12岁开始离家疯跑,是渴望逃离的“表征”,16岁辍学回乡可谓是灾难性的打击。到镇上的制镜厂上班,重新燃起逃离的欲望,后来和大庆恋爱则开始自我迷失。小说《静坐喜床》的发表是她命运的转折点,从此她实现了对乡村的逃离,开始接近城市,到省城读书,小说获省政府奖,直至在小城过着平静的生活,“我”实现了第一次逃离;但是随着“我”的办事能力在亲人面前的显露,于是陷入了帮助亲戚进城的纷扰中,面对亲情与爱情的冲突,“我”又开始第二次逃离,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逃离,使“我”割断了与那片乡村的联系。但在短暂的幸福过后,又陷入无根的痛苦。“我”开始领悟到“我的一程一程告别着的昨天前天原来就是今天”“在我一程一程失去家园之后。我发现,只有虚构是我真正的家园。我又开始静心于写作”“一个大俗的目的让位给了一个大雅的过程”。其实这种“逃离”的心理是许多人共有的内心渴望,特别是生在农村的孩子,对于乡村生活的逃离可能是一种永恒的信念。他们拼尽全力,借助各种途经实现这种逃离,只有无奈之下才会选择留守,继承父业。对陌生世界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不断奋斗的动力,但有许多时候,在走过之后才明白,“只有虚构”才是“真正的家园”。小说还叙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裂变过程,那就是母亲的精神裂变:由“过膝袜子”事件中的失落到分家时被奶奶选中后的得意,勤俭持家时的意气风发到分家的无可奈何,从渐失劳作能力的心中凄惶到因“我”而受到别人的尊宠,母亲的心在波峰与波谷之间颠沛,但是她用自己的“宽容、隐忍”默守着这无处遁逃的生活,走向暮年。这是两代女人的命运,是时代的折射,而这现代化的进程给“我”提供了逃离的契机。
现代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对于价值的判断标准已然发生了变化,安分守己的乡村生活已然无法吸引人们的兴趣,城市作为一种“幸福”的镜像吸引着农村的年轻人。正如《吉宽的马车》中许妹娜对吉宽所说“我许妹娜就是臭在家里,也不会嫁一个赶马车的!”有时恰如吉宽所感觉到的“从来都不是人,只是一些冲进城市的困兽,一些爬到城市这棵树上的昆虫”,但是“我们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光亮吸收,情愿被困在城市这个森林里,我们无家可归,在没有一寸属于我们的地盘上游动”。城市生活已然成为农民梦开始的地方。
这种价值观念的改变在乡下无处不在。《天窗》中大娘们儿到村里找人干活时的气势和语态让乡人羡慕,《亲戚》中孔兴洋因为当了乡里的文教助理而疏远了亲戚。性爱的观念在发生变化,《一树槐花》中二妹子在丈夫的疼爱中感受到“那种五月槐树被摇晃起来的动,随着自下而上的动,她觉得槐花一样的香气就水似的流遍了她的全身。”乡村婚姻的体验中有了更多的爱情追寻,如《天窗》中鞠老二愿意到孔家帮工很大的原因是喜欢听大娘们儿破锣样的嗓音,而大娘们儿最展耀的恰恰是鞠老二放光的眼神,抖动的身子,男人不愿意听她破锣样的嗓音,鞠老二愿意听。大娘们儿的内心感受到“原来的她粗劣、讨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原来的她是一个孤单的佣人,讨厌的附带品,跟不上形势的拖累,现在不同了,现在,她是一个被人挂念的人,是一个让人死了都不肯放手的人,这多么稀奇啊!在她多年来追着男人的尾巴,一层层离开土地和乡村,越来越不清楚自个儿是谁,不清楚自个儿到底要什么的时候,有人知道她是谁,有人要她,她是多么的值啊!”这种看似与人物身份不相附的抒情化议论却具有其合理性,它一层层地剥开了一个曾经依附在乡村世界的灵魂在离开了土地和乡村后,精神世界无所归依的痛楚和郁闷。那种被抛弃的、无法言传的忧伤压得她难以呼吸。这种孤独无助找不到自我的感觉是中国当代社会走向商品时代过程中人们心灵所遭遇的共同感受。巴塔耶指出“没有肉体的拥抱,我们就无法想象个体的爱。肉体的拥抱是爱的终点,在热情的拥抱中爱人的选择获得了圆满的意义。”[6]大娘儿们在地窖里完成了和死去的鞠老二的拥抱,发生在地下室的“人尸偷情”的离奇情节折射出人性压抑中的异变。
但在这种不断的嬗变中孙惠芬用细腻的浪漫化抒情表达着广袤的土地给予农民的精神文化内核,即便他们如候鸟般飞向城市,根却深深地植入了乡土中。在《吉宽的马车》中作者对黑牡丹房间里茧的描写是充满诗意的,特别是她的那些话语,“你不知道,这每一个茧里,装着的都是歇马山庄的风景,要是你贴进它听,你能听到只有乡下才有风声、雨声,秋天打场的梿枷声,还有各种虫子的叫声”,而吉宽所感觉到的是“在一个乡村走出来的人那里,不用贴近任何地方,只要静下来,满脑子都会是乡村的声音。”正是在这种情感的痛苦裂变中人们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广大农民经历的精神痛苦。
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着解构与重构的嬗变,这正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样是未竟的过程,孙惠芬用她的小说世界映射出现代化镜像中的农村社会,建构着乡土社会变化的文学观照。
[1] 孙津.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5.
[2] 卡尔·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M].周晓亮,宋祖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7.
[3]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
[4]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
[5] 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03.
[6] 乔治·巴塔耶.色情史[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