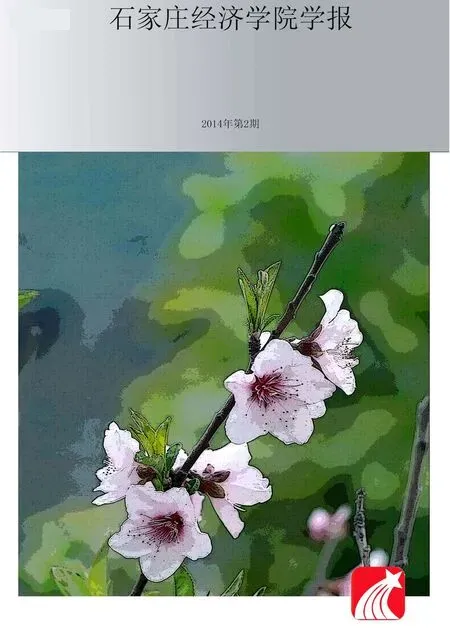转型期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
——一个经济分析的视角
邱成梁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转型期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
——一个经济分析的视角
邱成梁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中国法律体系的内涵应涵盖着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以实体规范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本质上是正式的信息体系。法律体系的结构,强调的是分立与融合,最基本的一个方向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立与融合。在中国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后,通过立法的完善仍然具有宏观性,而通过司法的完善则更具有针对性、微观性。相对完善的开放性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社会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利于社会主体之间形成均衡的博弈状态,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
法律体系;体系结构;体系建构;法治主义
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学界对法律体系及相关理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集中探讨,例如《法学》2011 年第 8 期推出“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司法的责任和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法律体系的集中探讨还有三次,分别是1982年关于法律体系与政治分离的争论、1993年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探讨、1999年关于用十年左右时间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争论。
一、法律体系的内涵
在中国法理学语境之下,法律体系这一学术术语被赋予了诸多涵义。在宏观的角度下,应注意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关注法律体系的内涵,以此来剖析当下的法律体系。“实际上,百年中国存在两种法律体系:即六法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看到两种法律体系之间的断裂同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继替关系。”[1]在国内主流法理学教材中,关于法律体系往往将其界定为部门法体系。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当然部门法这一视角,主要从法律规范的内容属性角度切入,对于法律体系的研究亦可在深层次上从法律规范的等级属性切入。当代中国有各种不同层次或范畴的制定法,已基本形成了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构成的体系。在形式上,当下中国法律体系的内涵应涵盖着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当然文章的研究主要从横向方面切入,但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纵向方面。
“法律分类以归纳逻辑为基础,体现了法律规范在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和可以加以不同组合的复杂性要求的基本特征;法律体系强调对体系化对象的整体上的逻辑相关性的要求,体系化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法律规范所赖以创制的演绎形式。”[2]我们要注重法律体系理论与法律分类理论的区别,但不应割裂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事实上,在实体规范视角下,法律体系即是以具有逻辑关联的分类元有机构成的。法律体系内涵的界定,在本质上是以法律分类为研究导向的。当前主流法律部门划分理论遭到各方面的批判。划分标准的非逻辑性,即以法律的调整对象为主要标准与调整方法为辅助标准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法律体系的主权问题,强调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建构法律体系已日益受到法律全球化与区域化运动的冲击。面对这种批判与冲击,有学者意重新整合部门法体系。例如,以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大法域为划分标准、以私法、公法、社会法、国际法为基本元素来重构我国当代的部门法体系。根据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原则,提出以利益为标准将我国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统领之下的国家法、社会法、家庭法和自治法四大部类的新观点。从法哲学角度,把中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四个部分。
整合目前部门法分类,作出相应的变通,而无须对主流部门法作出根本性的建构。传统法律体系在整体架构上,宪法类属于中心地位,由刑事法类、民事法类、行政法类与诉讼法类以及相关的补充法构成的。当然,目前这种分类的缺陷是无法纳入新兴的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与军事法等法律部门。同时,不应忽视的是传统法律部门与新兴法律部门划分模式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所以,对于目前法律部门体系,最合理的模式,宪法类居于核心地位,法律部门划分为主部门体系与从部门体系。“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归属和法律规范的性质两个向度作为研究法律体系的框架。前者的目的在于描述中国立法的现状,后者旨在分析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在各个法律部门的分布。”[3]从经济学的角度,以实体规范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根本上是正式的信息体系,信息所具有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信息分类与组合的必然性。从法律体系意义的角度切入,更主要的是使社会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尽可能处于完全信息对等的地位,从而整体上降低信息成本。
二、法律体系的结构
法律体系的结构,并非是基于传统意义上法律部门的范畴,而是以法律部门为基础的研究新范畴。法律体系的结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分类,强调的是分立与融合。法律体系的结构,最基本的一个方向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立与融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立是现代法律不断演化的结果,这一演化过程具有历史使然性,其动力在于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和社会形式的不断分化。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立,归根结底源于法益保护效率性的要求。法益应为法律保护的利益,即某些利益成为一定法的目的。“法益目标结构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依保护形态区分,法益应由积极法益和消极法益构成;二是以法律的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加以区分,法益由直接法益和间接法益组成。”[4]“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程序法对实体法的实施起着保障作用,这是程序法对于实体法的工具性价值;另一方面,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也具有某种独立性,程序法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价值。”[5]当前在法制实践中,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同程度上融合的趋势,这在根本上也源于法益保护效率性的要求。
关于法律体系的结构,公私法的划分历来是探讨的重点,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实体法范畴内的公私结构。公、私法分立与融合都涉及公私法的划分标准,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尤以利益与方法为代表。“公私法的划分是法的内在结构问题,划分公私法的直接根据是法律调整的不同方法,而法律调整的方法,基本上或主要地决定于法律调整的对象。”[6]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次明确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并阐述了以不同利益为根据划分公法、私法,即后来的“利益说”。“利益说”实际上是根据法的目的去区别公法和私法的思想,以公益为目的的法是公法,以私益为目的的法是私法。实际上,利益标准与方法标准是相互关联的,法益保护最终需要通过法律保护方法予以实现。法的制定与实施必须配置相应的资源,才能够有力地保护法益,而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限的,亦即是稀缺的。这便决定了不同法益的保护具有不同的顺位性,每一类法在立法设计时势必会选择某一法益作为优先保护的目标,并尽量在实施过程中分别配置相应的资源,以保证法益保护的有效性。
在国家利益、个体利益二元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存在两种本位与法益的选择,同时也以此为根据对法域二元划分。法的首要法益目标为国家利益时,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体的关系,为公法;法的首要法益目标为个体利益时,法主要调整的是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为私法。由于早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截然分立,公法、私法的分立与不同法益的保护均是比较明显的。当然在一定时期内,公益与私益保护的资源配置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倾斜性。这种倾斜分别代表了两种本位:公法优位与私法优位,这也具体体现在立法规模上。总之,公法、私法的分立实质上源于资源配置的稀缺性,以致于在法益保护上须作出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有宏观性的也有微观性的。公法、私法的分立,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法益保护的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的分立实质上反应了法益保护效率性的要求。公力救济的国家成本明显高于私力救济,因此公力救济保护的法益往往是涉及整体性、重要的,毕竟国家资源是有限的。而私立救济所需要的国家资源相对较少,从立法上主要将个体性的经济利益纳入私立救济。如此,既对法益有重点的保护又能够有效兼顾整体的法益保护。
公法、私法的融合主要体现为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这融合的背后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效率性的要求。尽管法益保护的截然分立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解决了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效率性。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势必对法益保护资源配置的效率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公私法融合的进程中,在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中间地带势必会存在一些模糊地利益形态需要保护。这些模糊利益形态的出现对公私法的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期待有效保护。在这种大背景下,便是一些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法益目标的部门法出现。公私法的融合是资源配置效率性的要求,但不应忽视公私法融合及其背后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效率性前提,坚持法益的顺位性与首要法益目标的保护。当初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的相对截然分立,对于法益的有效保护不具有效率性。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作为法益保护的方法也日趋融合,公益的保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更加需要私力救济,而私益的保护整体上更加需要公力救济,以期待更有力的保护。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法益保护的效率性更加依赖于保护方法的运用,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作为法益保护的方法的融合也成为必然趋势。
三、法律体系的建构
关于法律体系的建构,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首先涉及的是建构的理念与标准问题,从结果主义的视角便是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其整体上内涵着逻辑与伦理两条主线。鉴于传统法律体系构建的认知缺陷,以多主体认知理论反思传统法律体系的缺陷,构建以共识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转型期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应当更加强调共识性,包含着逻辑性共识与伦理性共识。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共识应该涵盖“以宪法为基准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调适机制的确立,以宪法为基础的常态法律体系与非常态法律体系的衔接”[7]。共识无疑有助于降低相互交流的成本,以及提高了在一定时期内维护现状的可能性从而保证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法律体系的建构主要涉及价值要素与实体要素,其中实体要素主要涵盖法律体系的概念与法律体系的构件。从法律体系建构立法主义的视角拷量,系统论的指导能够有效避免法律体系构件在横向上的断裂和纵向上的跳跃。当然,中国特色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具有一些源于中国本土特色的技术特征,“即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配合的运作模式,以及简约主义的风格,这些特征在集合意义上铸就了当下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上的某种封闭性质。”[8]实际上,对此的反思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关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构建的开放性思考,并针对性地作出相关的制度安排。在不涉及国家根本性质的法律中,去意识形态因素则是法律体系科学化的重要因素。应注意的是,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并不意味着立法在法律体系进一步建构中的完全缺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很大的创新性。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之后,地方立法成为转型期中国法律体系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其中实施性立法、自主性立法等创新方式应予以重视。此外,配套立法是在法的实施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配套立法存在问题应予以重视解决从而确保法律体系得以有效运行。
从法律制度发展史视角切入,法律体系的建构存在着两种大致的方向:演绎建构主义的法律体系(立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与归纳进化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司法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要,意味着通过司法来完善、改进法律体系既是效率性的选择也是科学性的选择。整体上,司法通过作用于法律体系微观向度的固有缺陷来完善法律体系。在新形势下,人民法院与法官在提升法律体系的品质、维护法制权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作用。关于完善法律体系的司法路径,可通过司法裁判的能动性来增强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例如,最高院通过颁布指导性案例来不断强化判例的作用。当然,对于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具体方式应包括包括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司法审查、司法建议等。在这种背景下,法律体系的融贯性便具有了重要意义,也是法律体系品质提升的重要方向。法律体系的融贯性意味着法律体系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证立,并应借助于诠释方法予以建构,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应该是法律体系品质整体提升的关键所在。
从我国法律体系建构的本土经验分析,通过快速的法律移植式的立法来建构法律体系,较强的信息能力是优质法律体系形成的不可或缺要素。特别是通过法律移植途径的立法,其实施所遭遇的困境,更加凸显了信息能力在法律移植和立法设计中的重要性。尽管官方宣布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通过立法、法律移植来完善法律体系,仍然是重要的途径。法律体系建构者的信息能力,如何得到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必然会强调评估机制的重要性。鉴于通过立法、法律移植来完善法律体系所具有的宏观性,因此在评估机制构建中,应特别注重法律体系建构者宏观性信息甄别与信息选择能力的提升并通过制度予以激励。与此相对应,通过司法途径来完善法律体系,则具有微观性,而应注重微观性的信息甄别与选择以及进一步的信息对应。在我国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后,通过立法的完善仍然具有宏观性,而通过司法的完善则更具有针对性、微观性。“国际的制度较量或体系比赛不外乎一场全面而具体的法律技术格斗,日复一日用具体案件处理的结果和效果来检验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9]
四、 法律体系的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宣布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形成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不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结构整合,而内含着法律价值理念的转别,深刻反映了法律理念由工具主义向法治主义转变的质的飞跃。特别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程序法深化发展有效地改变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另外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法治的法律基础,把各项事业纳入到法治的轨道,激起了民众对法律秩序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治的可能性,以及面对法律体系遭到的冲击应当强调形式法治的重要性。”[10]此外,我国宣布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分殊的固化,利益与权力的结构化,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社会管理中的司法维度应当成为理论与实践上研究与推行的重点。法律体系的形成,能够有效改变我国法治进程中过于依靠立法的局面,提高司法的地位,迈向法治的立法—司法双轨制。对于法律体系的法治意义,一个简单的总结是,法律体系的形成对法治的观念、法治的基础、法治的模式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我国法律体系发展进程中,其体系结构存在全面化、严密化、科学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尤其体现法律、法规数量上急剧膨胀与增长,截至2011年2月底,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39 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8 600多件。此外,针对大量法律、法规的修改与完善也在同时进行。已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律保障权利,并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法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整合。但实际上,在市民社会相对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移植的先行立法的社会根基是相当薄弱的。尽管这种快速立法、完善立法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但也会加剧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渐从强国家模式过渡到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尽管会有相应的限权措施,法律体系的深化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家干预的深化,强国家模式应会有回归的趋势,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合理有效利用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来协调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将成为法律体系完善中面临的政治难题。当然国家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应对这一难题,例如大力实施的普法宣传。其实,有诸多问题并非仅仅是法律体系自身机制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借助于其它机制,这便需要法律体系与其它机制的有效链接。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法律体系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完整的国家法律体系,是一个理想型的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法律体系的法治意义还是与法律体系关联的国家政治问题,均内涵着经济逻辑地进路。之所以存在法律理念的工具主义,根源在于法律主体的法律信息不对称,特别是拥有优势信息的主体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获得自身甚至多余利益的工具。显然,在假定获得信息成本相同的前提下,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无疑会改变不对称的状态,将法律理念从工具主义导向法治主义。特别是诉讼法、程序法的日益完善,无疑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进而推之,法治的基础是在这种破与立的情况下建立的,法治的模式也是在此基础上实现多元化的。总而言之,相对完善的开放性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社会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有效降低信息成本,使社会主体在利益博弈中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在更广阔的视角上,利于社会主体之间形成均衡的博弈状态,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也正以此来形成适应法治秩序的稳定市民社会,从而缓解国家与社会的矛盾。
〔1〕 喻中.百年中国的两种法律体系[N].法制日报,2012-06-27(10).
〔2〕 莫纪宏.论法律体系构建的非法治化倾向[J].社会科学,2000(8):34.
〔3〕 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11(3):20.
〔4〕 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62.
〔5〕 万毅.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考辨——兼论程序优先理论[J].政法论坛,2003(6):101.
〔6〕 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4):100.
〔7〕 刘茂林,王从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J].法商研究,2010(6):90.
〔8〕 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J].中国法学,2009(2):147.
〔9〕 季卫东.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技术重构[J].法制资讯,2011(2):5.
〔10〕 陈金钊.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3):72.
(责任编辑 吴 星)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A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alysis
QIU Cheng-liang
(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Weihai,Shandong 264209)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can be analyzed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This paper defines it as a formal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entity n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alysis.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within this scope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other kinds of classifications,and its basis is the separ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The improvement of this system is featured by the microcosmic approaches in legislation as well as microcosmic and specific actions in judiciary.An open and relatively well-developed legal system contributes to the reduc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game equilibrium of social subjects,so as to reduce the transaction and management cost.
legal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rule of law
2014-02-16
陈金钊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法律方法理论研究”(10JJDB820008)。
邱成梁(1990—),男,山东沂水人,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法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经济学、法律方法论。
DF0
A
1007-6875(2014)02-01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