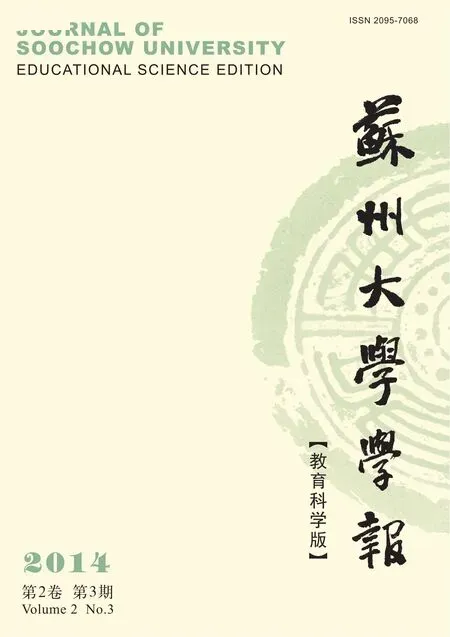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几点思考
赵 俊 芳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几点思考
赵 俊 芳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变动,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两个发展阶段。1985年政府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高等教育应国家、社会及高校之需实施了后勤社会化、高考、成本分担收费制度、就业制度改革以及高校合并重组等举措,取得了巨大成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高等教育发展中众多关键性、迫切性的问题,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这些改革缺少协调性、整体性,具有软弱性,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分兵作战、修修补补的特点;遇到问题,绕道而行,没有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尚未解决变革中的棘手问题。为此,2012年中央即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7月,刘延东副总理出席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4次会议,强调高校要切实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深化综合改革,要增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使命感、责任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之路,要把立德树人、提高质量贯穿综合改革全过程,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要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努力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涉及的内容林林总总,高校定位、特色发展、专业结构、学生就业创业、考试招生、公平公正、人事制度、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班子建设、内部治理结构、简政放权等,但关键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质量,二是制度建设。两者互为因果,制度是提高质量的前提与保障。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先后推出“211”“985”等旨在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卓越工程,工程实施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大幅提升,高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高校一直在国际一流的边缘徘徊,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顶级学者,无法满足知识创新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难与国际接轨,其根本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尽如人意。基于此,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高度关注体制制度建设问题。报告由十六个部分构成,从经济制度、政府职能到思想文化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具体环节无不以制度为主线,在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同时,突出强调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高校内部制度体系建设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建设目标是确立适合高校发展、有利于人才培养及知识生产的高校顶层权力结构,破解高校改革发展中的制度瓶颈,合理配置资源,建设与社会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人才培养机构。
近年来,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高校内部治理的先进经验,我国在高校内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如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校长职业化、学生通过制度途径参与高校管理等。但也应该看到,在权力、组织、制度及其运行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使得转型期中国高校的内部治理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挑战。在高校顶层治理的设计中仍存在权力本位、权力越位、权力错位、权力缺位、权力无位等令人费解的怪相,有名无实的董事会、软弱无力的学术委员会说明中国高校尚未完全摆脱制度变革中的组织尴尬。高校学术权力具有维护学术秩序、保障学术自由、配置学术资源、制衡行政权力等功能,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高校学术权力空泛,缺少决策职能,学术委员会多为学术咨询机构,导致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错位,行政部门持有重权成为高校管理重心,官风盛行。
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树立公平、民主、平等、分权、参与、制衡及回应性等理念,消解线性思维与平面思维方式,克服僵化的行为准则,破解官僚本位、制度异化、部门壁垒等改革瓶颈;加强高校顶层设计,在保证党委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由政府、社会、大学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大学管理,发挥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功能,通过协调高校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边关系,建立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的公共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民评民选的高校校长选拔制度,改变被评与被选者的责任取向,以制度保证权力对下负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责任体系”及合法性支持,以制度构建责任型、服务型“治理结构”,注重权力主体的职业信念、责任感及使命感,并将其内化为高校管理者的行为准则与品格;明确组织目标,借鉴外来经验,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提高高校教育质量与管理效能,推进高校进一步发展。
而就,更不存在改革的万灵药方或绝佳方案。更何况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问题错综复杂,利益纠葛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改革本身的超级复杂,当前至关重要的不是推出更多的改革方案或加大改革宣传,而是要坚定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终极目标。只要方向正确了,假以时日高等教育的改革就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方向错误了,依赖政府的超强支持,世界一流大学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或许可以取得暂时的成功,但由于缺乏可持续性的创新能力和高质量的制度架构作为支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奇迹”终将被“危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