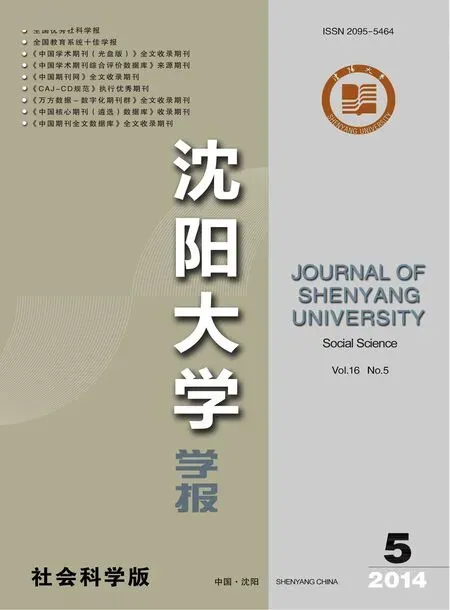浅析朱熹训诂著作的指导思想
贾 璐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浅析朱熹训诂著作的指导思想
贾 璐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分析了朱熹著述《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和《周易本义》的指导思想,认为这些训诂著作表现了朱熹独到的诗学思想、史学思想、易学思想,以及理学思想,作为宋代训诂学的代表作,奠定了朱熹在汉语训诂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朱熹; 训诂著作; 创新思想
一、 关于《诗集传》
宋代的《诗经》学研究兴盛,仅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宋代的《诗经》诠释学著作就达46种之多。其中,朱熹的《诗集传》“是在宋学批判汉学和宋代考据学兴起的基础上,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是《毛诗传笺》、《毛诗正义》之后,《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1]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欧阳修的《诗本义》、王安石的《诗经新义》、郑樵的《诗传辨妄》、王质的《诗总闻》等对传统诗说基本上持排斥的态度,朱熹虽然在《诗集传》中亦颇多创新,但是他首先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
“因说学者解《诗》,曰:‘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么道理?公且说,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么用?所贵乎读书者,是要理会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2]191
可见,朱熹并不赞成没有读懂先儒对《诗经》的注解便妄下己意的做法,认为“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那种“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结果只会落得“于己无益,于经有害”。
朱熹对类似做法的批评又如:“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2]191
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朱熹的诗学思想是在对以往《诗经》研究成果继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扬弃,是通过批评毛传、郑笺以来诗学传统的不足而提出的,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3]朱熹的《诗集传》以其鲜明的特色把中国的《诗经》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与朱熹写作此书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 关于《四书章句集注》
宋孝宗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把“四书”合为一集刊刻于婺州。据束景南先生考证,“这个在婺州的刻本(宝婺本),是朱熹第一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标志着儒家十三经经学体系中四书学在经学文化史上的出现与确立。”[4]在儒家诸经中,朱熹对“四书”倾注的精力最多,仅关于“四书”的著作就有《论语集解》《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评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孟子要略》《论孟精义》(后改名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中庸集解记辨》《中庸辑略》《新定中庸》《大学集解》《新定大学》《四书音训》《四书集义》《四书或问》等多部。《四书章句集注》是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订而撰成的,刊刻之后又反复修改、完善,集中体现了朱熹的“四书”学思想。
对于治“四书”的先后次第,朱熹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和要求: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2]249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2]250
朱熹写作《四书章句集注》的基本思想是以阐发义理为主的,而不是以训诂注疏为主。但是朱熹也不忽视训诂,他主张在以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对宋学学者过分强调义理而轻视训诂治经方法的扬弃,亦是对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而不及义理治经路数的辩证的发展。既体现了当时以阐发义理为主的宋代经学的时代精神,又对宋学流弊有所修正。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体现了朱熹经学的兼容包含精神。”[5]264
在阐发《大学》的义理时,朱熹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三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八条目,对《礼记·大学》篇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总述三纲领八条目的第一章为“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经”以下为“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中庸章句》亦是朱熹重点阐发义理的著作,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首次将“道”“统”二字连用:“《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6]并且在注解《中庸》的过程中,朱熹也论述了包括道统思想在内的多种理学思想,对《中庸》进行了全面的义理阐发。
在《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中,朱熹阐发义理的地方更多,但他同时不废章句训诂:“某解《语》、《孟》,训诂皆存。学者观书,不可只看紧要处,闲慢处要都周匝。”[2]184朱熹在注解古籍时,正如他自己所说:“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2]2626例如《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朱熹集注:“许氏《说文》:‘侃侃,刚直也。’‘訚訚,和悦而诤也。’”关于“侃侃”和“訚訚”的解释,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云:“侃侃,和乐之貌。訚訚,中正之貌。”朱熹未从孔注而改依《说文》,他的弟子问:“先生解‘侃侃、訚訚’四字,不与古注同。古注以侃侃为和乐,訚訚为中正。”朱熹答曰:“‘衎’字乃训和乐,与此‘侃’字不同。《说文》以‘侃’为刚直。《后汉书》中亦云‘侃然正色’。訚訚是‘和说而诤’,此意思甚好。”[2]998可见,朱熹对于一字一词的训释,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程树德对朱熹《论语集注》的评价云:“《论语》一书,言训诂者则攻宋儒,言义理者则攻汉学。平心论之,汉儒学有师承,言皆有本,自非宋儒师心自用者所及。《集注》为朱子一生精力所注,其精细亦断非汉儒所及。盖义理不本于训诂,则谬说流传,贻误后学;训诂而不求之义理,则书自书,我自我,与不读同。二者各有所长,不宜偏废。”[7]这是非常中肯的。
三、 关于《楚辞集注》
朱熹在《楚辞集注》的序言中说:“然自原著此词,至汉未久,而说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而刘安、班固、贾逵之书,世不复传。及隋、唐间,为训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骞者,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而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櫽括,定为《集注》八卷。”[8]
朱熹指出历来注释《楚辞》的书,或者“已失其趣”,或者“漫不复存”,唯独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并行于世。朱熹认为二人对名物的考证是很详尽的,但对于王书的可议之处,洪兴祖却“皆不能有所是正”。此外,王逸作《章句》和洪兴祖作《补注》都是逐句作注的,且忽略了对作品大意的阐释。朱熹依照《诗集传》的体例,以章为单位进行注释,通常以四句、六句或八句(句数不等)为一章,先释字词,然后通释章内大意,这是针对王逸的《楚辞章句》偏于字句名物训诂,“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从宋儒的立场出发,对汉儒的说经习气所做的纠偏。例如:
《楚辞·离骚》:“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王逸在注解时是逐句为训的,洪兴祖一依王逸的体例,二人注解如下:“瞻前而顾后兮”,王逸注:“瞻,观也。顾,视也。前谓禹、汤,后谓桀、纣。”《补》曰:“《说文》:‘瞻,临视也。顾,还视也。’”“相观民之计极”,王逸注:“相,视也。计,谋也。极,穷也。言前观汤、武之所以兴,顾视桀、纣之所以亡,足以观察万民忠佞之谋,穷其真伪也。民,一作人。”《补》曰:“相,息亮切。言观民之策,此为至矣。计,策也。极,至也。相观,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览相观于四极’,与《左传》‘尚犹有臭’、《书》‘弗遑暇食’语同。”“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王逸注:“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谁有不行仁义而可任用,谁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义则德不立,非善则行不成也。”[9]
朱熹在注释时虽然继承了部分前人的故训,例如:“相,息亮反。……瞻,临视也。顾,还视也。相观,重言之也。计,谋也。极,穷也。……服,事也。”但朱熹还是能根据自己对句意的理解给出不同于前人的看法的,如对“前”、“后”的训释:“前,谓往昔之是非。后,谓将来之成败。”更重要的是,朱熹对他按照自己的标准所划分的章节的大意予以了概括和总结:“言瞻前顾后,则人事之变尽矣,故见民之计谋,于是为极,而知唯义为可用,唯善为可行也。”[10]这是王逸和洪兴祖逐句为训所不及的。
四、 关于《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自成一家,集中体现在他的《周易本义》中,这里不展开论述,只通过朱熹对《易经》的一些认识,来分析朱熹的创新精神。
朱熹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通过追本溯源,纠正了治《易》的两种偏向。“《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序例》也,安能晓!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2]1622故应从《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出发来探求经文的本义。
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还主张将《易》的经传部分分开排列,即分为上下经和《十翼》的经传两个部分。朱熹反对把经传合一而混同其差别的做法,指出“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2]1622因为经和传分别讲的是卜筮和义理,如果把经文和传文混杂在一起,则会以阐发义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但这并不表示朱熹反对卜筮和义理的结合,相反,朱熹还很赞成以卜筮、象数来求义理的方法。
根据《汉书·艺文志》中“《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11]的观点,朱熹把易学的发展概括为两大阶段:以卜筮为教的阶段和以义理为教的阶段。朱熹指出:“《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是岂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异,故其所以为教为法者不得不异,而道则未尝不同也。然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术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适乎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则惟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12]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朱熹又把易学的发展分为四个具体的阶段,即伏羲阶段、文王阶段、孔子阶段和程颐阶段。朱熹说:“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2]1648
此外,朱熹还采用了以图解《易》的方法。在《周易本义》卷首的《图目》下,朱熹就征引了《河图图》《洛书图》《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卦变图》等多种图,又证之以《系辞》《尚书》和《论语》等经典,还结合《太极图》来解释《周易》,促进了宋代易学的发展。
对于朱熹的易学思想,蔡方鹿先生曾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朱熹以义理思想为指导,重本义,重象数,将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把宋易之义理派与象数派包括图书学统一起来的易学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易学史上先前思想资料的吸取、借鉴、继承、扬弃和发展,亦是对宋代易学的总结和发展,而集其大成。”[5]290可谓得其肯綮。
以上分析了朱熹著述《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和《周易本义》的指导思想。这些训诂著作作为宋代训诂学的代表之作,奠定了朱熹在汉语训诂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同时,朱熹不墨守成说,敢于自创新解的精神,也值得后世不断继承和发扬。
[ 1 ] 夏传才. 诗经研究史概要[M]. 郑州:中州书画社, 1982:141.
[ 2 ]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3 ] 朱熹. 诗集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序言2.
[ 4 ] 束景南. 朱熹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96-197.
[ 5 ] 蔡方鹿. 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 6 ]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14.
[ 7 ]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凡例6.
[ 8 ] 朱熹. 楚辞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序言2-3.
[ 9 ]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24.
[10] 朱熹. 楚辞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4.
[1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1704.
[12] 朱熹. 书伊川先生易传板本后[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朱子全书:第24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3842.
【责任编辑王立坤】
GuidingIdeologyofZhuXi’sExegeticalWorks
JiaL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Zhu Xi’s exegetical works,ShiJizhuan,SishuZhangjuJizhu,ChuciJizhuandZhouyiBenyi, is analyz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se exegetical works reflected Zhu Xi’s unique poetic thought, historians thought, Yi-ology ideas and though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laid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onnecting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xegesi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egesis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Xi; exegetical works; innovative ideas
2013-11-30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066)。
贾 璐(1983-),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内蒙古师范大学讲师,博士。
2095-5464(2014)05-0628-04
H 109.2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