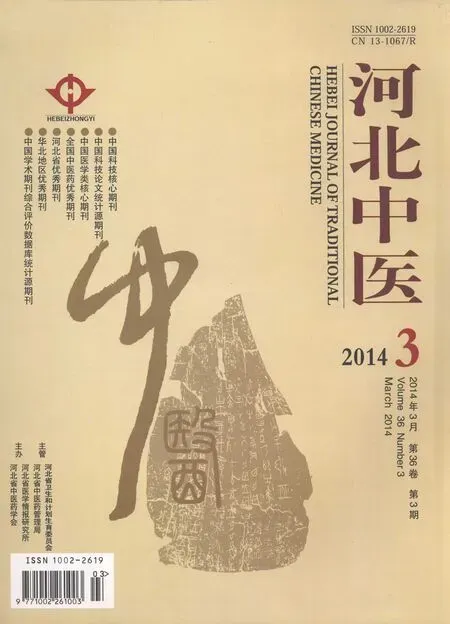活血化瘀方药联合腹腔灌注化疗防治大肠癌肝转移的理论探讨
王文静 齐元富
(山东中医药大学2012级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014)
活血化瘀方药联合腹腔灌注化疗防治大肠癌肝转移的理论探讨
王文静 齐元富△
(山东中医药大学2012级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014)
肝肿瘤;肝肿瘤,继发性;结直肠肿瘤;中药疗法;注射,腹腔内
大肠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消化道肿瘤,据统计,约有超过50%的大肠癌患者死于腹腔内复发转移[1],在手术根除术后3年内可发生肝转移的患者占25%~50%[2],可见肝转移已成为大肠癌常见的死亡原因。门静脉系统的存在为大肠癌肝转移提供了捷径,使大肠癌原发灶易经门静脉系统转移至肝脏。结合大肠癌肝转移的治疗进展,考虑门静脉是早期3 mm以下的肝内微小转移灶的重要供血源[3],应用活血化瘀方药联合腹腔灌注化疗防治大肠癌肝转移具有针对性强、局部浓度高、持续时间长、改善血液高凝状态及毒副作用小等优势,可能成为临床治疗大肠癌肝转移的一种新策略,其前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1 大肠癌肝内微小转移灶的发生机制
从解剖特征上分析,大肠癌患者出现高发肝转移率具有理论支持。大肠与肝脏之间存在门静脉系统,肝门静脉始末均为毛细血管,一端始于胃、肠、胰、脾的毛细血管网,另一端终于肝小叶内的血窦,特殊的结构使之成为大肠癌发生肝转移的主要途径。大肠癌原发灶在生长过程中侵蚀肠壁黏膜下的静脉丛,部分肿瘤细胞由此进入小静脉,进一步汇入门静脉系统,最终抵达肝脏。其中大多数肿瘤细胞被宿主的防御系统吞噬,幸存下来的肿瘤细胞可穿过通透性较大的肝血窦壁,在肝血窦周围的间隙落户,形成小的细胞集落,即肝内微小转移灶(微转移癌)。微转移癌经恶性增殖与微血管化后,成为临床意义上的转移癌。再者,大肠癌细胞的组织学特点也是造成大肠癌肝转移高发的因素之一。大肠癌的组织学改变80%以上为高分化腺癌或乳头状腺癌[4],发生此种改变的细胞多以癌细胞块的形式脱落,脱落细胞数量较多,不易被肝脏的枯否细胞
全部吞噬,肿瘤细胞在肝脏内残存的可能性较大,更容易形成肝内微小转移灶。
2 腹腔灌注化疗的选择及作用优势
目前,针对不同类型的肝转移灶,临床多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单发或多发局限于肝脏一叶的肝转移灶,可行手术切除;多发或无法切除的直径较大的肝转移灶则首选肝动脉灌注化疗[5]。然而在临床上,还有很多肝转移灶是肉眼不可见的微小转移灶,如行肝转移灶切除术后1年内患者可发生再次肝转移,且几率较高,此种转移灶体积微小,却可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此种微转移灶肉眼不可见,无法进行手术切除,且有自己的供血特点,不适合肝动脉灌注化疗。有关研究表明,在肝转移灶逐渐增大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瘤灶的供血不尽相同。当肝转移灶直径>5 cm时,肝动脉为其主要供血源[6],在此之前转移灶由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供血,而早期3 mm以下的肝内微转移灶则主要由门静脉供血,因此针对此类早期微转移灶,采用肝动脉灌注化疗显然不合适,故在临床上防治大肠癌肝内微转移灶发生,采用腹腔灌注化疗或门静脉插管治疗更具有理论支持。姚少霖等[3]对34例大肠癌肝转移患者予根治性切除加门静脉插管灌注化疗,并与同期32例行单纯根治性切除的患者对照观察,经4年随访,2组再次肝转移率、3年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经门静脉插管治疗属于创伤性疗法,对患者的身体条件要求较高,且临床操作存在一定难度和风险。相对而言,腹腔灌注化疗更有临床优势。
有关研究表明,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反应率与其接触药物的浓度和时间有密切关系。经腹腔灌注的化疗药物由于腹膜-血浆屏障的存在,其扩散率会相对减缓,药物的清除率也随之降低,其在腹腔内能维持较长时间的高浓度状态。邹多武等[7]实验发现,用腹腔注射和静脉注射2种不同的方式给予卡铂注射液,24 h时腹腔给药的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值比静脉给药的AUC值高17倍。卿三华等[8]应用高剂量、大容积的5-氟尿嘧啶行腹腔灌注化疗后,药物的腹腔液峰值浓度及平均浓度分别为股静脉的288倍和145.1倍。可见腹腔灌注化疗可保持腹腔内的化疗药物高浓度,延长肝表面与药物的接触时间,且保证有足够大的接触面积,有利于药物的渗透和吸收,提高肿瘤细胞对药物的反应率。同时,通过腹腔灌注进入体内的化疗药物,可以被脏层腹膜下大量的毛细血管床所吸收,随血液汇入肝门静脉,到达肝小叶内的血窦,弥散到肝血窦周围间隙,抵达由门静脉提供主要血供的肝内微小转移灶,直接与肿瘤细胞接触。此时,被吸收的化疗药物,亦由于腹膜-血浆屏障的存在,其运输及代谢较为缓慢,可经门静脉以相对恒定的浓度较为持久地输送至肝内转移灶,形成“泵效应”,以此取得较好疗效。再者,化疗药物进入肝门静脉后,可以杀灭正由门静脉转移向肝脏的部分肿瘤细胞,在其未形成微小转移灶之前将其消灭,起到预防新的肝转移灶形成的作用。除此之外,由于肝脏对药物的“首过清除效应”,化疗药物经肝代谢后毒性降低,可提高患者对药物的耐受性,使腹腔灌注化疗较全身化疗更为安全。且大多数化疗药物在用于腹腔灌注时,具有高选择性区域化疗药代动力学特点,即在腹腔液、门静脉血和肝内保持恒定持久的高浓度,仅极少量药物进入体循环,使以上3处部位的药物浓度与体循环血中保持较高的梯度差,相对于传统静脉化疗,降低了对患者全身的毒副作用[9]。
因此可见,腹腔灌注化疗能使腹腔液、门静脉血和肝脏3个关键部位中的药物保持恒定、持久、高浓度,既能将腹腔中常见的大肠癌转移部位,如肝脏,浸泡在抗癌液中,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反应率,又能有效攻击门静脉内处于转移状态的游离细胞团和肝脏内已形成的微小转移灶,可从根本上防止大肠癌肝转移的发生且在临床操作上相对安全、简便,对机体毒副作用较小,有着给药方式上的独特优势。
3 活血化瘀方药的应用特色
由于凝血系统激活、血小板的激活及聚集、抗凝活性降低等多种作用机制,肿瘤患者的机体多处于一种血液高凝状态,血液流速慢,药物代谢缓,加之瘤灶及其周围出现大量蛋白原沉积,阻碍化疗药物的渗透,使化疗药物在瘤灶处呈低浓度状态,影响药效发挥。从中医学角度来看,血液高凝状态是血瘀证的表现之一。已有临床研究表明,许多肿瘤患者存在血瘀证,其表现可为舌质紫瘀、皮肤黧黑、腹部结块、脉象滞涩等。针对血瘀证,中医多采用活血化瘀之法,所以在改善肿瘤患者的血液高凝状态时,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中药或复方常被广泛应用。有报道称,芎龙汤(药物组成:川芎30 g,地龙15 g,葛根30 g,延胡索30 g,川牛膝30 g)能降低肿瘤患者的红细胞比容、全血黏度、纤维蛋白原等血流变指标,改善患者的血液高凝状态[10]。桃红四物汤加味能迅速有效改善乳腺癌术后血液流变学的异常,降低血液黏度,改善微循环[11]。鸡血藤甲醇提取物可通过阻断肿瘤细胞诱导血小板凝聚反应,降低血黏度[12]。芪连扶正胶囊(我院制剂室制剂)作为治疗大肠癌的辅助用药,在晚期大肠癌的治疗中可取得较好疗效,其成分中含有的莪术、全蝎、蜈蚣、壁虎等药物,具有活血化瘀散结之功效,可改善患者的高凝状态[13]。由此可见,诸多活血化瘀方药具有抗血小板黏附聚集、降低纤维蛋白原含量、促进纤维蛋白溶解等功效,可以破除微循环障碍,改善肿瘤患者的血液高凝状态。在配合腹腔灌注化疗时,活血化瘀方药可提高肝脏微小转移灶处的化疗药物的流量和浓度,增加血液灌注率和药物渗透率,力求使肿瘤细胞处于化疗药物的控制之下,从而达到增强药效的作用。
然而,对于活血化瘀方药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医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有学者研究发现,以丹参、赤芍药灌胃后的大鼠,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血清浓度明显升高,说明活血化瘀药物可能促进肿瘤的侵袭与转移[14]。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川芎嗪、水蛭素对肺癌细胞的黏附有促进作用,而丹参酮ⅡA则有抑制作用[15]。因此可见,活血化瘀药物可能对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有促进作用,但其复方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尚无定论,故活血化瘀方药对肿瘤细胞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仍需谨慎。
4 小 结
活血化瘀方药联合腹腔灌注化疗治疗大肠癌肝转移具有自身的特色,一是经腹腔灌注的化疗药物可在腹腔液、门静脉及肝内微小转移灶处保持高浓度、长时间,既模拟了“泵效应”,又具有针对性、预防性,可使化疗药物产生最大限度的抗肿瘤功效;二是化疗药物经门静脉系统吸收入肝,与体循环血保持较高浓度的梯度差,且经过肝脏的“首过效应”大大减少了体循环毒性,可产生最大限度的药物耐受性;三是活血化瘀方药可改善肿瘤患者的微循环,增加肝转移灶处的血液灌注量和药物渗透性,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反应率,与腹腔灌注化疗相辅相成。
总之,活血化瘀方药联合腹腔灌注化疗防治大肠癌肝转移具有理论依据,此种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可能为大肠癌肝转移提供新的临床治疗策略,值得我们在科研和临床上开展大量实验,进行深入研究。
[1] 李玲玲,徐海帆.腹腔热灌注化疗在大肠癌治疗中的应用进展[J].现代医药卫生,2013,29(6):884-887.
[2] 左朝晖,邱晓昕,许若才,等.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综合治疗研究的进展[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3,7(1):261-263.
[3] 姚少霖,马怀宏,魏淑君.手术后早期门静脉预防大肠癌肝转移[J].当代医学,2012,18(13):34-35.
[4] 孙国哲,王铮,刘芬.大肠癌肝转移的诊断与治疗新进展[J].中国实用医药,2009,4(23):236-237.
[5] 王炜,黄世锋,陈德伦,等.结肠癌肝转移术后经脐静脉置管门静脉灌注化疗的效果[J].江苏医药,2012,38(23):2837-2839. [6] 王志军,徐鸿兵.肝动脉栓塞化疗联合无水酒精治疗结肠癌肝转移[J].现代肿瘤医学,2012,20(3):559-561.
[7] 邹多武,许国铭,苏暾,等.复方阿嗪米特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胆囊炎、胆结石、肝硬化腹胀的疗效观察 [J].中华消化杂志,2005,25(7):421-424.
[8] 卿三华,周锡庚,周正端,等.高剂量大容积5-FU腹腔化疗药代动力学和疗效实验观察[J].中国肿瘤临床,1996,23(1):2-5.
[9] 陈清卫.大肠癌术后早期5-Fu+CF腹腔低渗温热化疗的临床观察[J].河北医药,2010,32(10):1259-1260.
[10] 张国荣.活血化瘀法治疗恶性肿瘤作用机制探讨[J].山西中医,2010,26(5):61-62.
[11] 万晓燕,任东峰.桃红四物汤加味配合功能锻炼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肿胀21例[J].吉林中医药,2007,27(11):30.
[12] 姜林.活血化瘀药抗肿瘤作用的实验研究概况[J].湖北中医杂志,2008,30(8):63-64.
[13] 李慧杰,孟双荣.芪连扶正胶囊对化疗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河南中医,2009,29(6):561-562.
[14] 钱丽燕,郭勇.恶性肿瘤高凝状态—血瘀证—活血化瘀的思考[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3,31(4):856-858.
[15] 包文龙.活血化瘀中药在肿瘤治疗中应用浅析[J].浙江中医杂志,2013,48(5):388-389.
(本文编辑:习 沙)
△ 通讯作者: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山东 济南 250011
王文静(1985—),女,博士研究生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研究。
R735.350.22;R735.705
A
1002-2619(2014)03-0371-03
2013-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