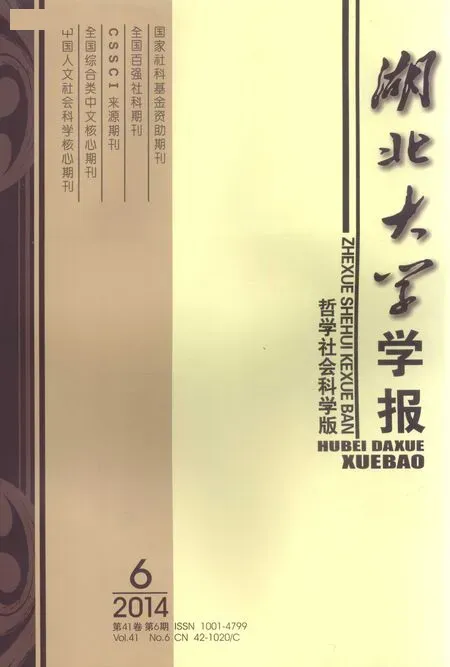铜钱危机视野下的明代币制变革
张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铜钱危机视野下的明代币制变革
张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宋金以降,钱、钞、银的竞争是币制演变的主题。明代中叶,大明宝钞废弃,银钱并用币制确立。但铜钱的流通一直处于危机状态,近半地区为“不行钱之地”,流通铜钱的地区受到官铸钱不足和私铸泛滥的困扰。明政府推广制钱的努力屡告失败,明末滥铸又加剧了危机。由于铜钱危机的存在,加之明中后期赋役折银和海外白银内流的推动,落后的称量货币——银两过度流通,在民间金融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明代;货币制度;铜钱;白银
明代中叶,经济领域发生一大变动。北宋以来政府发行纸币的历史走到尽头,货币制度进入银钱并用(或称银钱平行本位、钱钱两本位、银铜复本位)时期。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一币制的基本特点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货币化及其影响是研究的焦点①对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虽多,大都从白银供应、用银与赋税改革、物价、白银流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真正着眼于货币流通的探讨反而很少,如傅衣凌的《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黄阿明的《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当时货币流通的配角——铜钱,则备受冷落②就笔者所见,涉及明代铜钱问题的研究很少,如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第七章《明代的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滨口福寿的《隆庆万历期钱法新展开》(《东洋史研究》1972年第31卷第3期)、屠燕治的《谈洪武年间的钱币窖藏》(《中国钱币》1988年第1期)、王裕巽的《试论明中、后期的私铸与物价》(《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王玉详的《明代私钱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张瑞威的《足国与富民?——江陵柄政下的直省铸钱》(《明代研究》2005年第8期)、张瑞威的《劣币与良币——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论文集》第2册,东吴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版,第395~407页)、张诗波的《明代铜钱铸造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黄阿明的《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在此次币制变革中,白银是赢家和主角,但抛开银、钱两种货币的竞争,难以理解货币流通演变的实际状态。彭信威[1]453、黄仁宇[2]421都指出明代铸钱少且私劣钱泛滥是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重要原因,但一直缺少专门研究。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刘光临强调“盗铸钱对规范铜钱的排挤才是白银‘取代’铜钱的真正原因”[3],黄阿明注意到明人关于某些地区不用钱的议论[4]。然而,主要的疑点并未解决,大量明代史料揭示的“不行钱之地”和小数用银的情况,与“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成说大相径庭。从铜钱危机入手,剖析货币流通演变的地域差异和银两的实际流通方式,避免简单化的认识和笼统的讨论,是解开上述疑点,全面了解明代币制变革的关键。
一、宋金以来铜钱危机的形成和沿续
明代的币制变革,是宋金以来货币制度内在矛盾的演化结果。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古代币制的突出特点是贱金属货币铜钱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政府发行的唯一铸币。作为贱金属货币,其缺点非常明显:一是大量使用不方便,长途搬运成本高昂,有“斗米运斗钱”之说;二是币材受到铜矿产量制约,又与日益增加的生活用铜竞争,周期性发生钱荒;三是手工铸钱的技术条件下,币值低微导致铸造费用畸高,如不能持续获得大量低于市场价格的铸材,或高溢价发行铜钱,铸钱必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北宋时期,铜钱铸造量达到历史高峰,危机也隐隐浮现。一方面,相继确立四川、陕西、河东等发行铁钱的特殊
货币区。另一方面,铜钱有了新的竞争对手,纸币(交子)始发于铁钱区,徽宗时一度在包括京师在内的淮河以北广大地区行用。白银的货币性也在增强,开始取代绢帛的地位。到南宋与金的对峙时期,纸币和白银的势力大为扩张。在南宋,铁钱区沿长江以北连成一片,并禁用铜钱,以防流入金国境内,后又向南延伸到京湖区(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币制变化重点在纸币,突破了铁钱区(四川交子,淮南交子)限制,先后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关子等多种区域性纸币[5]。此外,白银在财政收支和私人支付上的使用又有长足进步[6]。在金国,前期用铜钱,但渐趋短缺,私铸泛滥,在币材不足的情况下铸造铜钱又造成官民交困;后期主推纸币(交钞、宝券),铜钱被限禁流通,大量销熔为铜器或运往国外。随着纸币滥发和战乱加剧,白银经常用作大额交易支付的媒介和价值尺度,政府曾铸发“承安宝货”银锭。宋金时期,铜钱虽然遇到其它货币的挑战,只是出现局部危机。但铜钱铸造量从北宋的高峰迅速跌落,孕育着更深远的危机。由于铜器需求猛增,外贸导致的巨额流出,到南宋末期,杭州等大城市铜钱短缺,小额交易中不得不以鑞牌、铅牌等替代。多种货币较量的结果,是元代确立专用纸币(中统钞),禁止铜钱、白银流通的货币政策。禁令在长江以南的南宋旧地未能完全贯彻,铜钱仍有流通。至大、至正年间,两度解禁,铸发至大、至正通宝,意在与纸币“子母相权”,维持钞价,对白银也曾解禁,但维持不久,又恢复禁令[7]。
宋金元以来的钞、钱、银三种货币的矛盾,正是明初货币政策面对的首要问题。朱元璋的第一个选择是铜钱,包括(称帝前的)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洪武八年(1375)才发行宝钞,与铜钱兼行,禁止民间以“金银物货”交易。与前代相比,大明宝钞更快地陷入滥发贬值的恶性循环。为维持这一财政工具,洪武二十七年(1394),“诏禁用铜钱……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从各地发掘的“洪武窖藏”看,此次禁钱压力之大,来势之猛,前所未见①近几十年间,各地相继发现数十处洪武年间的铜钱窖藏(埋藏铜钱数量大,包括汉唐宋各代铜钱,但全都截止于洪武通宝,往往匆忙埋入,应是洪武禁钱之际埋藏)。遍及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地。半数以上在浙江,2013年杭州蒋村一次发掘(上迄西汉,下至洪武)37万余枚铜钱。。在洪武、永乐朝的高压政策下,贬值的宝钞(从十文到一贯共六等)尚能在小额交易支付中替代铜钱,不见复申钱禁。但大额交易中仍有白银流通,故洪武三十三年(1400)、永乐元年(1403)、永乐十七年(1419)、洪熙元年(1425)多次重申金银或白银禁令。至宣德年间,虽屡经整顿挽救,宝钞大有难以为继之势,政府继续严禁金银,但“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8]。铜钱的流通应已复苏,因为宣德八至九年(1433-1434)曾铸造宣德通宝。
四百多年来政府推行纸币的历史在明正统年间落幕。明英宗即位,“驰用钱之禁”,欲使宝钞铜钱兼行②解禁的具体时间为宣德十年(1435)十二月,当时明英宗已继位。《明史·食货志》“食货五”误作“驰用银之禁”,从上下文看,再参酌《英宗实录》,应为“驰用钱之禁”,故清人修《续文献通考》时予以改正(《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五,考2868)。。亦不再厉行银禁,正统时各地多有赋税折银的规定。禁令既然放松,民间自然不肯用钞。对徽州土地交易契约中使用通货的统计表明,除正统元年(1436)一例注明钞数而以谷物成交外,其余以银为主,辅以绢布谷物[9]。在京城,民间交易“纷竞铜钱,不复以钞为事”。景泰元年(1450),宝钞局停止造钞。此后,大明宝钞变成货币幽灵,仅用于某些政府支付项目和个别税种。
宝钞退出货币流通后,除了某些落后地区和农村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实物媒介外,白银和铜钱成为货币流通的主力,确立了银钱并用币制。由于铜矿衰竭,币材匮乏,政府对铸钱畏为难事。从前铸造洪武通宝时,“有司责民出铜,民间皆毁器物以输官鼓铸,甚劳”(《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宣德铸钱也多有扰民,英宗即位伊始,即作为一项弊政予以革除。此后,直到嘉靖六年(1527)的近一个世纪里,政府只在弘治末年铸造过少量弘治通宝③弘治十六年(1503),明孝宗命两京及各省开铸,照洪武旧额量为增减。但两年多时间里,“各处所铸才十之一二”。直到正德二年(1507),弘治通宝仍未铸完。两年后彻底停铸。。铜钱危机愈演愈烈,货币竞争的天平完全倾向银两。
二、铜钱危机与白银货币优势的确立
银钱并用币制没有主辅币之分,两种货币皆可无限制使用。两者的流通范围亦无清晰绝对的界限,“大数”与“小数”之间,存在一个弹性较大的可相互替代的区域。与贱金属铸币铜钱相比,白银以落后的称量货币形式(银两)流通,“虽然适用于高额、跨地区结算,但本质上不适合在日常性低额交易中使用”[7]112。使用银两时,需称重量(各地、各行业的重量标准分歧)、鉴定成色,往往还要将不同重量、不同成色的银块折算成某一标准成色。如果优质铜钱供应充足(如清代中期的情形),普通民众宁愿用铜钱而不用银
两。然而,在铜钱危机的环境中,白银过度流通,侵入小额交易领域,也即小数用银①本文所谓“小数用银”,指金额在一钱以下(即分厘用银)。隆庆元年(1567),因京城内外钱法不通,曾下令“(京城)各铺行人等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只许用钱”(《万历会计录》卷41,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8页)。一两银子重37克多,若金额低于一钱,剪凿称量,极不方便。至于鉴定成色,“实生涯之本领,过眼须要留心”,《三台万用正宗》之类商书载有鉴定方法,相当复杂。从外国人的角度,更能看出使用小额银两的费事。1712年,在崇明岛传教的耶稣会士彭加德有一封信提及当地的货币流通,银钱并用,“银锭是用以支付大笔款项的。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二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从明英宗“驰用钱之禁”到嘉靖初,铜钱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国近半地区为“不行钱之地”。如上文所述,早在宋金时期,不铸(铜)钱、不行钱的地区相继出现且不断扩大,在元代的钱禁中得到强化。明初,大部分布政司设局铸钱,但时铸时罢,以停铸禁钱告终。因此,铜钱解禁无法改变众多地区不行钱的状态,由官方文献可见一斑。成化十七年(1481)颁布京城铜钱使用规则时,“仍行南北直隶及河南山东等布政司府行钱地方通为禁约”[10]17。专用“行钱地方”一语,说明“不行钱地方”的存在。弘治通宝开铸前,户部要求“旧未行钱地方务要设法奉行”。工科给事中张文上疏反对,历数不行钱之地:“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骤欲变之,难矣。”(《明孝宗实录》卷197,弘治十六年三月戊子)
在“钱法不通”之地,民间交易媒介是白银与实物②云南是一个特殊货币区,主要以海贝交易,乃至以贝币纳税上供。。白银用于零细交易,方法是降低通用银两的成色。生长于西安府的康海比较“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的用银习惯:“两直隶、山东、河南、江淮等处俱行用细丝银(按:足色银),盖此数处钱法通行,不得不行用细丝”,而“诸边之民,习于布帛银谷之交”[11]18。因无钱可用,故使用银两时,除缴税用足色外,“其余用使,常五六成耳”,此为不得已之事。“行钱之地,每分得钱六七文,可干六七事;行银之地,每分不过干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银常常通于不行钱之地者,其势使然也”[11]50~51。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张文奏疏称“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茴香花银或称“茴银”,也流行于西北,据弘治四年(1491)大同右佥都御史称:“(大同)街市买卖行使银两,多系茴香花银,止有六七成色,……因循已久,……,非但大同一城如此,外卫城市皆然。”[12]708~709不行钱之地长期流通低银③万历十八年(1590),四川巡抚饶景晖奏称“蜀之茴香花银相沿已久,低假混杂,不可识别”(张晋生:《四川通志》卷15下,“钱法”)。康海所云西安用低银的习俗难变,直到明末清初,“市易并低银”(谈迁:《北游录》,“西安低银”,中华书局1980年版)。,万历年间的日用类书《三台万用正宗》强调:“不行钱处,用银决低;用钱之方,使银不便。”[13]16
二是行钱之地的铜钱质量开始恶化,民众被迫更多使用银两。据前引成化十七年谕令及康海言论可知,北直隶、河南以东的黄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下游为流通铜钱的地区。此外,两广与福建也是用钱之地④福建的许多地方习用宋钱。16世纪初,漳州地区出现私铸宋钱的产业,不但内销,而且通过走私贸易港口月港向日本大量出口(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第118页)。广东、广西长期流通旧钱,宣德十年(1435),梧州知府李本奏称“今两广交易用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请求解禁,终于推动中央政府解除钱禁(《续文献通考》卷11,考2868)。。当时流通的铜钱主要是唐宋旧钱,历经几个世纪的销镕、磨损、出口和窖藏损耗,所存有限。刘光临估算,16世纪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约为3600-5400万贯,仅有北宋铸造铜钱总量的12%-21%[14]。铜钱是铸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存在差异。优质铜钱供不应求,必然推动名义价值上涨,加之铸钱技术简单,导致质量低劣的私铸钱大量投入市场。铜钱解禁仅二十年,苏松等地私铸的永乐通宝已扰乱了京城货币流通。又过了四年,因私钱太多,京城民众拒用明制钱⑤明代称本朝官铸钱为“制钱”,是前代旧钱的对称。,旧钱根据质量好坏巧立名色,“挑拣使用”。天顺四年(1460),政府首次颁布挑拣铜钱禁令。由于钱分等级,铜钱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职能遭到破坏,民众转而增加用银,京城“大凡买卖并柴米行使,诸色铺面兑换,俱要白银交易”[12]720。成化三年(1467),政府为增加税收,决定钞关商税等原来纳钞的税项改为钱钞各半缴纳,这是提升铜钱地位的举措,但适得其反。由于政府不铸钱,对铜钱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私铸[15]。
15世纪下半叶,重要的私钱流通区多是大运河流域的商业城市及附近地方⑥当时政府官员报告及破获的私铸案件显示,私铸的渊薮多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临清等地,在河南许州等地也有发现。这些地方的私钱通过大运河运至北京,掺杂行用,因此引起中央政府的密切关注。。进入16世纪,私钱向更多地区蔓延,银进钱退的局面随之加剧。以下两例颇能说明这一变化:在杭州湾北岸的海盐县澉浦镇,
“自国初至弘治以来皆行好钱”,正德十二年(1517),类似于京城流行的“板儿”之类低恶之钱迅速取代了好钱[16]338822。在闽中莆田,宝钞废弃后一直习用宋钱,“府县征收此物,民间零碎使用极为便益。乡村之民,有垂老不识厘秤者(按:厘秤即称银两的戥子)”。正德初,闽南漳州“私铸新钱盛出”,流入莆田,替代好钱。官府严行限禁,莆田民间遂不再用铜钱[17]217~218。
三、货币改革失败与银两地位的巩固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货币政策出现新动向。一方面,一条鞭法推广,赋役征银逐渐通行全国。作为财政收支工具,银两流通的广度和深度几近无远弗届。该政策顺利推进,实有赖于白银供应的戏剧性变化。西属美洲和日本在16世纪下半叶发现大银矿,巨量海外白银从此通过外贸流入中国①海外白银流入中国是学术热点,论著颇多,参见梁方仲的《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全汉升的《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书院1972年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庄国土的《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李隆生的《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宋元以来白银货币地位扩张的进程达到顶峰。另一方面,政府恢复铸钱,铜钱流通地域有所增加,但张居正在全国推广制钱的改革失败,未能改变铜钱危机的现状②黄仁宇根据北宋的经验估算,“要保证货币供应充足,国家必须保证每年要铸造20亿到30亿文铜钱”,但整个明代制钱的总产量只有约80亿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总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第421页)。。
从嘉靖六年(1527)起,政府局部恢复鼓铸。所谓局部,基本是两京铸钱,南北两个工部宝源局岁铸嘉靖通宝的规定数额仅有四万余贯(4149.12万文),仍不能足数完成。至于外地,曾命工部差官在直隶河南闽广铸钱,解运京城司钥库备皇帝赏赐之用,执行情况不得而知。嘉靖二十年(1541),两京宝源局因“得不偿失”而停铸。十二年后,嘉靖帝突发奇想,要求补铸洪武至正德九朝通宝4500万贯,嘉庆通宝5000万贯,按当时成本核算,需工料银32,820,770两,而户、工两部贮银合计才2,236,000两(《明世宗实录》卷405,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亥)。补铸政策未实施,嘉靖通宝恢复铸造,亏损多,产量很低③北京宝源局到嘉庆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停铸。每年约用工料银15200两,可铸钱6840贯,为规定铸额(每年18830贯)的36%(《万历会计录》卷41,第1037-1038页)。此外,嘉靖三十四年(1555),命云南每年铸钱31000余贯,解送京城太仓库,十年后停止(《续文献通考》卷11,考2871)。。
尽管铸钱“利不酬本”,通过铸钱开拓“理财之道”的呼声渐起。赋税改革迅速拉升了对白银的需求,海外白银尚未大规模流入,白银日益短缺。与此同时,财政愈趋困难。隆庆年间,先后有蓟辽总督谭纶、山西巡抚靳学颜、直隶巡按御史李家相等上理财疏,建议重钱轻银,广开鼓铸,以增加货币供应,充实财政(《明穆宗实录》卷35,隆庆三年七月辛卯;卷42,四年二月;卷43,四年三月戊子)。这一想法在当时颇有市场,滨口福寿认为张居正的货币政策实源于谭纶[18]。受此推动,隆庆四年(1570)开铸隆庆通宝,仅限于两京。到张居正主政时期,铸钱足国便民之论付诸实践。
万历四年(1576),改革的锋芒指向货币政策。是年,诏令两京及各省一体开铸万历通宝。为解决币材与流通的痼疾,规定废铜官收,增加制钱在俸禄工食发放及赋税收纳中的比例。张居正冀望官民双赢,“世间银少铜多,公私之费,皆取足于银,故常患不足。今化铜为宝,则民用益饶;民用益饶,则上供易办,故足民亦所以足国也”[19]22~23。但各省奉行不力,时过两年,无一省上报铸钱数量。原因仍在成本、币材与流通之难。当时沿嘉靖旧例,铸金背、火漆、镟边三种万历通宝,要求秉持高质量原则,“费多利少,私铸自息”。京城主要发行品质最优的金背,掺杂少量火漆,各省铸镟边钱,金背定价800文一两,镟边、火漆定价千文一两。据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巡抚在开铸之初的乐观估算,也仅能保本或微利。因工价已定,必须控制币材价格。产铜大省惟有云南四川,当地民间不用钱。在其他省份,“吏责民输铜,销器毁成,不尽给其值。责铜急而铜价腾跃,非产铜之地尤甚。则是未得钱之利而已被铜之害也”。赋税是疏通钱法的重要渠道,中央政府允许“存留钱粮春夏纸赎各不拘银钱兼纳”,但在不行钱之地,官府以官价推广制钱,收税时往往不收钱,民众当然不愿接受[20]2873~2874。万历十年(1582),浙江当局将积存难用的制钱强行用为(驻杭州、宁波军队的)兵饷,“饷既减,又杂钱,而市中钱不行”,激起杭州兵变[21]4805。
货币改革进退失据。万历八年(1580),因钱不能行,云南首先获准停铸。两年后,张居正去世,万历帝借皇子出生的机会宣布“恩例”,其中一部分是对张居正政策的纠偏,包括货币政策,“铸钱本以利民。近
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如地方钱法通行,官民相安,愿仍前鼓铸者,听从其便”(《明神宗实录》卷128,万历十年九月辛酉)。此后,大体回归两京铸钱的旧制,地方钱局仅湖广在维持①湖广从前只有郧阳府和襄阳府为“行钱地方”(用旧钱)。因邻近西南产铜区,币材易得(荆州是南方重要的铜交易市场),万历年间开荆州、武昌、衡阳三局,持续铸钱,制钱得以流通。崇祯十年(1637),徐霞客游历湖南,从衡阳、道县至祁阳,皆银钱兼用(《楚游日记》,见《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浙江兵变是货币改革急刹车的直接诱因,但叫停的做法失之仓猝。由于币材供应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大规模地发行制钱难以持续。但只要坚持高质量铸钱,收税时增加制钱比例,就能适当提高制钱的名义价值来填补成本缺口,被市场认可,又不会引发大规模私铸②以万历金背为例,因其用料足(四火黄铜),铸造精工,在京城的流通价值不断升高。万历十三年(1585)达到500文一两的市价,26年后还维持在660文一两,远高于实际价值。。这样,完全可以维持一个较小的全国性铸钱的体制,逐渐推广制钱流通。
货币改革期间,从前的“不行钱之地”开始有制钱流通。改革半途而废,制钱的扩张也告终止。在四川,“市民习用茴银,(制钱流通)渐复废格”,只有川东还能用钱[22]4。在江西,“惟宁都,石城、广昌二三山邑行之。其省会及诸郡邑,行之数年,辄复告罢”[23]197。在浙江,大部分地区不行钱的状况延续到17世纪末③据生于康熙晚期的浙江人朱叔权回忆:“臣生长浙江,如宁波、温州、台州等府无论大小交易,往皆但知用银而不知用钱,即厘数之间,亦皆用银。”(《广东粮驿道朱叔权奏陈平抑钱价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乾隆六年二月十五日)。在山西,明代碑刻显示的民间货币流通常见小数用银,几乎不见铜钱④现存11件正德至崇祯年间的碑刻(晋中太谷,晋南洪洞,晋东北代县,晋西南万荣,晋东南高平、平顺、泽州),有庙宇、戏台的修建捐资、典礼费用详细记录,至分厘之细亦用银两,仅崇祯十六年(1643)高平有一例用钱(“酒钱三百文”),可能受到相邻的河南影响(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
在从前的“行钱之地”,制钱的行用区域有所扩大。在北方,京城所铸制钱流通于“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圆两千余里,河南兼用制钱和旧钱,山东仍以宋钱为主[24]248。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钱的辐射力扩大,万历通宝取代了江南江北流通的开元通宝,“于地方甚便”[25]35。南京工部宝源局乘势大举扩张,三十余年里,铸炉从60座增加至600多座。
总体而言,到17世纪早期,始于正统年间的金融变革基本完成,白银成为财政收支的货币工具和民间货币流通的主导力量。两京之间的运河流域、河南、两广⑤广东用唐宋钱,尤以粤西南用钱最广。据屈大均记述,明末清初,雷州府、高州府用唐宋钱,廉州府专用开元钱(《广东新语》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7~408页)。流通的铜钱质量较好,晚明时高州府吴川县民众还以钱纳税,“石米岁输千钱”(陈舜系:《乱离见闻录》,载《明史资料从刊》第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广西铜钱流通状况,由徐霞客游记可见。崇祯十年(1637),他从桂林、柳州向南,行至与交趾接壤的胡润寨(今靖西县境内),皆为行钱之地,每到城市辄以银换钱,以备旅途之用。在向武州(今天等县境内)获赠一笔旅资,皆为宋钱,与交趾流通宋钱的风气相通(参见《粤西游日记》)。、福建部分地区⑥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六》所引《漳州府志》(已佚)记载,嘉靖至万历时,在福建八府一州中,福州府、兴化府、汀州府、邵武府和福宁州“皆不用钱”,铜钱只在漳州府、泉州府、延平府和建宁府流通,但漳州的龙岩、漳平也不用钱,各地所用宋代年号钱多为民间盗铸,用钱习惯各自不同。和湖广等地银钱并用;其它地区大小数皆用银⑦日常交易一次用1克或不到1克银两,在今天看来,实在难以想像。在当时的“不行钱之地”为平常事,如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载一事例:万历十五年(1587),江西新建县“一民乡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货之,得银三分。……乃以二分银买米,一分银买信(石)”(《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2页)。,偏远之地掺用实物货币。值得注意的是,流通中的铜钱质量又有恶化趋势。南京宝源局追求铸利,钱质下降,万历三十年(1602)后,官钱壅滞,私铸大兴[26]。尚存的地方钱局也不乐观,湖广的荆州、武昌、衡阳三局“所铸各限一式”,不能互通[10]21。在旧钱流通地区,海外白银内流,铜价上涨,私铸钱品质每况愈下,“钱分等级,不是适当的价值尺度,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1]453。以福建私钱生产和出口中心——漳州为例,本地漳浦县一向行用私铸的宋代年号钱(只在万历五年时用过万历通宝),“乡村自少至老有不识银,一村之中求一银秤无有也”。16世纪晚期,从马尼位进口的“佛朗银钱”(手工铸造的西班牙银币)涌入闽南,以日本为重要市场的私钱制造业衰落,漳浦遂废钱,专用银⑧《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引《漳州府志》中漳浦废钱专用银的记载,发生时间应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黑田明伸从东亚地区海上贸易与货币流动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25页)。。
四、明末滥铸与“钱法”的崩溃
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军兴之际,政府多铸钱牟利。从王莽到清咸丰,主流做法是铸各种大钱,从当五当十到当百当千,名义价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是以少抵多的金融掠夺。为防私铸,大钱多以钱质精工著称。大钱的流通,对民间原有的小铜钱破坏有限。明末,当局首先采用这一古法。天启初,两京开铸当十大钱,外地如宣府、密云亦有铸造。因两京民众怨声载道,天启五年(1625)停铸。此后,货币政策走上另一条更危险也更具破坏性的道路,政府大规模铸造质量低劣的制钱,铜钱危机急剧恶化。
当时,论理财者多以“籍钱息济军兴”为药方。天启元年(1621),“以辽饷匮乏”,命各省开铸,规定每年上交铸息共82万两。从此,鼓励各省铸钱为既定方针。除两京外,陕西、山西、宣府、密云、河南、山东、苏州、浙江、福建、湖广、云南①天启六年(1626),云南当局在省城设局铸钱,“滇之有钱,自今始矣”(《条答钱法疏》,载《滇志》卷23,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94~796页)。制钱在云南的推广比较顺利,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游历云南,在寻甸、大理、保山以及偏远的腾冲都有用钱的记录(参见《滇游日记》)。、四川等地相继开铸,可谓“开局遍省直”[20]2877~2879。但或乏铜材,或难于流通,相继报罢,地方铸局仅剩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密云、宣府等处。至崇祯年间,内外交困,罗掘无计,“各镇有兵马处皆开铸以资军饷”[27]667~668。搜刮废铜、旧钱,大肆铸造劣钱,以旧定的银钱比价折成军饷发放或强制向民间采购物资,等于是公然的抢掠。官钱滥恶,私钱浑水摸鱼,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顾炎武指出明末滥铸对货币流通的危害,“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称之为隋代销古钱之后的又一大变[28]647~648。当时,凡是开局铸钱之地,钱质皆急剧下滑。据松江府人士叶梦珠回忆,“崇祯之际,通用新钱,无一佳者”,“钱色日恶而价亦日贱”,钱价从千文兑银九钱跌至六钱,最后跌至三钱[29]170~171。钱币学研究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变化,明制钱的品质(包括大小、重量、铜质)在天启年间开始下降,至崇祯通宝,大都轻薄不堪②比较遗留至今的明代制钱,万历通宝平均重4.5克左右,天启通宝有不少已轻到3克多,崇祯通宝几乎都在4克以下,大部分不及3克(《中国钱币大辞典·元明编》,“明代铜钱”,中华书局2012年版)。。
滥铸制钱,在行钱之地推动银两的流通向小额交易扩散,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在有用钱传统的松江府,叶梦珠记录了崇祯元年(1628)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各种物价,大都用银表示,少数铜钱物价同时换算成银两价格(“折银”或“准银”)。一些价格极低的商品,如盐每斤六七厘,葛布每尺七八厘,合铜钱十数文,也以银计价[29]153~172。在钱质败坏的环境中,民间用钱交易支付,用银记价记账,是“小数用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分析曾羽王《乙酉笔记》和姚廷遴《历年记》所载明末清初上海县物价及家庭收支记录,日常零星开支仍以铜钱居多,但物价多以银两计或者银、钱价格并存。其原因仍在钱质芜杂,“钱看大小作价”[30]。当小数用银增加时,一些从前用细丝银的地区也转用低银,如苏州府流行银色先降至八成,后低至四五成[31]193~195。松江府亦“行银滥恶,通用不过六、七成”[29]192。
明末清初,钱法败坏,银荒日甚。振兴鼓铸,重钱轻银又一次成为流行的舆论,直接影响了清前期的货币政策[32]。但解决铜钱危机绝非易事,“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欲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28]648
五、结语:货币金融史研究的创新
银钱并用货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波及明清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世界货币史的一般规律而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必然取代实物货币,进而贵金属货币相对于贱金属货币占据上风,最后是货币信用化。但揆诸史实,币制演变并非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简单线性发展。比如中国的贵金属货币发育成熟很晚,信用货币(纸币)的发明流通反而超前,主要原因在于贱金属铸币的特殊地位。白银货币地位在明代确立,固然由经济变革的外力推动,货币体系内部的重要原因——铜钱危机也不容忽视。金融史的传统观点重银轻钱,认为在“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体制下,银两不断排挤铜钱,“从明清时代的几百年间的货币流通看,银两对于铜钱,在重要性上是逐渐占据上风的”[33]60,或者说,银钱并用是“发展过程中的银本位货币制度”[34]17。然而,金融史的实际变化方向是相反的,银两在明代获得压倒性优势,过度流通(表现为小数用银);入清以后,优质铜钱供应持续增加,铜源渐广,到清中叶时,大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发生“以钱代银”以至“大数用钱”的转变。岸本美绪注意到这一变化,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清代货币史上非常有趣但是过去却很少被关注的问题”[35]300。笔者以金融史上
闻名遐迩的宁波过账钱为例,对此做过初步探讨[36]。另一方面,货币流通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从来不是普遍适用的原则。明代的官私文献屡屡言及“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在不用钱的地区,大小数皆用银,其影响直达清代早期。
传统观点对银钱并用币制的误读,主要原因在于民间货币流通的史料零星分散,故难以知晓各地商情民俗的差异,更难进入古代民众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使用货币的实际方式。这是中国金融史研究的老大难,致使货币史一直为学术冷门。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的史料较为丰富,拓宽搜寻史料的视野,大体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除正史、政书、文集笔记等传统文献外,应着力搜罗档案、日记、碑刻、契约等文献中的第一手货币史料,并善于利用考古和钱币学的实物史料。同时,充分利用电子文献检索技术,如通过四库全书、实录、经世文编等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将其中生僻的货币史料一网打尽。这是本文写作过程中的用力所在,也符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2]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刘光临.银进钱初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J].河北大学学报,2011,(2).
[4]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5]汪圣铎.两宋货币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7]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黄阿明.明代前期的救钞运动及其影响[J].江汉论坛,2012,(2).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2).
[10]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8[M].济南:齐鲁书社,1997.
[11]康海.对山文集[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
[12]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2[M]//杨一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13]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21[M]//酒井忠夫.中国日用类书集成:第四卷.东京:汲古书院,2000.
[14]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结构和规模的初步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1).
[15]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J].明史研究,2007,(10).
[16]董谷.碧里杂存[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朱淛.莆田钱法志[M]//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南京:金陵书画社,1983.
[18]滨口福寿.隆庆万历期钱法新展开[J].东洋史研究,1972,(3).
[19]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29[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影印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20]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1]董份.御史大夫左司马崌翁张公定浙变记[M]//黄宗羲.明文海:卷380.北京:中华书局,1987.
[22]张晋生.四川通志:卷十五下[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3]游日升.臆见汇考:卷四[M]//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南京:金陵书画社,1983.
[24]谢肇淛.五杂俎:卷12[M].上海:上海书店,2002.
[25]胡我琨.钱通:卷2[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6]黄阿明.万历三十九年留都铸钱事件与两京应对[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5).
[27]户部尚书候恂条陈鼓铸事宜[M]//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8.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28]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陈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29]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0]清代日记汇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1]叶绍袁.启桢记闻录:卷8[M]//梁方仲.梁方仲读书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
[32]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M].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
[33]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34]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M].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
[35]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6]张宁.制钱本位与1861年以前的宁波金融变迁——兼与“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说商榷[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1).
[责任编辑:李严成]
K24
A
1001-4799(2014)06-0092-07
2014-04-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1YJC770083
张宁(1971-),男,陕西岐山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货币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