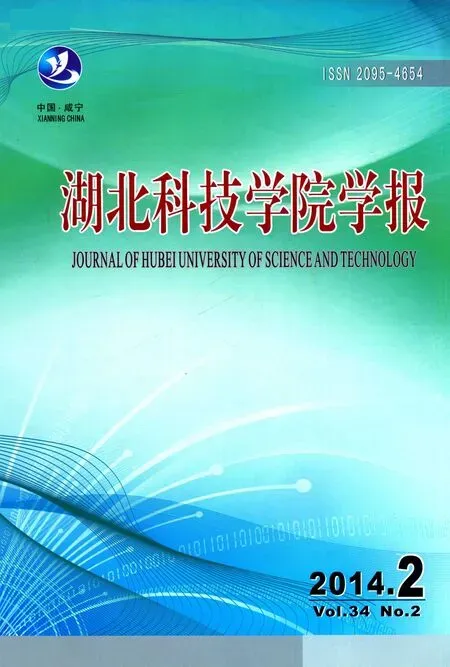浅谈托尼·莫里森小说里黑人自由的危险性
冯英,游前程
(1.湖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咸宁437005;2.潘家湾中学,湖北嘉鱼437000)
托尼·莫里森作为美国黑人杰出的女作家,她所关注的是美国族裔黑人生存环境和他们的精神状态;她作品描写的是黑人男性与女性,种族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她用独特的视角探讨在白人文化冲击下非洲裔美国黑人在黑白文化夹缝中的精神生态困境。所谓精神生态,鲁枢元认为精神生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精神生态思考的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的精神生态的失衡和错位,探讨人的异化问题。在莫里森作品中非洲裔美国黑人在受到白人文化积极因素吸引的同时又想固守黑人传统文化[2]。这种精神生态的困境在莫里森的小说里表现为黑人团体的社会功能失常,社会关系失衡。纵观她的小说人物,要么完全被白化而失去自我身份;要么固守黑人传统而缺乏社会认同;要么游离于黑白文化而成为自由人,被黑白社会团体所抛弃。本文尝试从精神生态视角考察由于受到黑白两种文化夹击,游离于两种文化之外的黑人群体以及他们自由的危险性。
一
《秀拉》是莫里森同名小说中的主人翁,她自幼生活在黑人社区,从小目睹黑人生活的艰辛,她发誓要过一种与父辈不一样的生活。在和自己有着相同追求的好姐妹内儿也走上父辈的生活轨迹时,秀拉离家出走,在各大城市游走学习。十年游历,秀拉回到了故乡。那个曾经用小刀割伤自己而吓退欺侮同伴的白人的无畏少年不见了。秀拉第一件事就是把养育自己的外婆伊娃赶出家门,送到养老院,成为黑人社区不孝的代言人。接着,在美德林,秀拉和不同的男性发生关系,甚至和儿时好友内儿的丈夫上床,她成为故乡女人憎恨的蟑螂和娼妇;第三,秀拉在上教堂做礼拜时不穿内衣,成为社区家长教育小孩的伤风败俗的典型代表。除了精神上的朋友夏德拉克,秀拉在美德林没有朋友,镇上居民见到她来了会远远地躲开。儿时满怀“不愿意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要创造我自己”[3](p92)的梦想离家游学,十年追寻,一心想要找到自我身份、找到人生价值、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感。然而,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美国各大城市游历十年,秀拉所遭遇的仍是白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这是秀拉所不愿意认同的。百般无奈她又回到了摒弃已久的故乡,却也不愿意承袭黑人传统的观念。尽管秀拉回来后曾试图像其他黑人女性一样过着有牵挂的生活,她和Ajax的交往过程中对他的控制和依恋是她人生价值的投射。正如莫里森评述,她主要的责任感被根除后,她要过一种实验性的生活。自我追寻的经验告诉她自我也靠不住,黑人传统的生活体验教导她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她没了中心,没了生长点。”没了生长点的秀拉就成了一个怪人。[4](p67)
二
非洲裔美国黑人经历百年被奴役的历史,奴隶制被废除后在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在美国这个社会环境下,感到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种文化,两个思想不可调和的争斗常常让他们心力交瘁,仿佛对立的两股力量在撕扯他们,让他们的灵魂受到无尽的煎熬[4]。在这两种思想的夹缝中,美国黑人男性首先开始沉沦,失去理性力量,不但没有能力保护黑人女性,反而成为压迫女性的帮凶。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反映在美国社会生态环境下,美国黑人精神扭曲和异化的一部力作。小女孩佩科拉的父亲乔利从小被母亲抛弃,在别人的嘲笑下慢慢长大,认识了波琳,他的第一次性行为受到了白人青年的欺凌:白人青年要乔利和波琳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完成性爱。她和妻子波琳从南方种植园来到北方,以为北方有不再受欺凌的生活。虽然北方没有奴隶制,但是无形的文化冲击让乔利无所适从。乔利没有工作,整天无所事事。靠妻子给别人当保姆的钱生活。他成了流浪儿。他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受苦的女儿,在醉酒状态下,在充满对女儿的爱和内疚中,他强奸了自己的女儿佩科拉,让其生下一个死婴,成为佩科拉精神崩溃的导火索。乔利出生在奴隶制的南方,黑人完全和牲口一样被白人驱使,从小没有父母的关爱,备受欺凌。到了北方后,黑人受到歧视,乔利失去了工作,当妻子也在白人文化冲击下晕头转向成为白人化的奴隶时,乔利最后的家庭精神依托也坍塌了。“他逐步疏离了社会中人的责任感,变得自由得吓人。自由地去感知任何感受——恐惧、歉疚、羞愧、爱情。背上、怜悯。自由地去温柔或狂暴,去吹口哨…”[5](p125)。人与自然间需要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更是需要精神纽带。乔利自己的道德、亲情都丧失了,一个崩溃了精神家园的人怎么能给他人以爱?两种文化的夹击,种族歧视使得乔利精神失衡,精神错位。他成了黑人和白人文化的流浪儿,自由到把强奸女儿与爱女儿混淆一体。
如果说乔利的自由是卸去了社会责任感后,人的价值沦丧从而导致心无所依;《秀拉》中夏德拉克疯狂表象下的自由则是因为精神家园的丧失而自建虚拟的安全和自由的王国以逃避恐惧和担忧。夏德拉克是经历一战战火炮轰的退伍士兵。从战场上回到故乡,夏德拉克是自由的:他独自住在河边,他几乎从不和人交往,对白人世界的认知让他感到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对故乡底层人他表现出率性的疯狂:他行走时当着女士们的面袒露他的生殖器,还毫无顾忌地在人前小便;他目睹了秀拉无意中把名叫小鸡的小孩旋进小河里却保持了沉默。对生活的无奈和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做出要把死亡节定在每年的1月3日的疯狂决定。而莫里森关注的是底层人对疯子夏德拉克创立的“全国自杀节”认同并参与庆祝活动的背后原因:“如果一年中有一天交给它(死亡),每个人便可将其抛在一旁,一年的其他日子变回安全和自由。”[3](p14)夏德拉克用疯狂来逃避白人的歧视和黑人同情,在疯狂的表象下,他自由到狂野:免受黑人社区道德约束,游离在社会行为人的价值和责任之外,终于在一年全国自杀节庆祝活动中,“底层人”游行时触发了隧道的坍塌,大量“底层人”死亡,夏德拉克紧握着颈铃,停止了歌唱,仿佛明白了他假想的安全和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如此不堪一击,并要付出如此的代价。
三
在莫里森小说,黑人总在不间断地或游历或游荡。不管是游历还是游荡,女作家想要让读者思考的是让非洲裔黑人游历或游荡的原因:他们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极端生存环境,这种环境让他们在既不丢失自己的黑人本性又不漂白自己灵魂的挣扎中被撕裂开来,他们找不到自己自我的平衡点,精神上无所依托,他们思想上的冲突纠结,让他们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他们表现出的是对自由和飞翔的追逐,而这种追逐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狂野。《秀拉》中的埃贾克斯就是这样一个追逐自由和飞行的人。表面上埃贾克斯是一个自信的风流黑人男子,实际上他需要从不同的女子身上找到自我的肯定,所以他从未和任何一个女性有很长的关系,他对黑白文化中恒久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漠然是他在面临黑白两种文化冲突时无从抉择的一种态度。经过十年游历的秀拉有着其他黑人女性没有的特立独行和与他一样的捉摸不定;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真正的对话,这让秀拉误以为找到了那个尊重自己,不压迫她不命令她的人而有了自我价值的映照。秀拉想和埃贾克斯稳定关系的举动让他从未有过责任感的心灵恐慌不已,他再次逃走了,去不同的城市飞机场看飞机的升降,飞机飞翔是他所向往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和不受社会行为规范约束的思想,对飞行的追逐,对天空和自由的渴望实际上是他对爱情和家庭的一种逃避。
结语
莫里森作为黑人女作家,以敏锐的观察、细腻的文笔、不同寻常的构思叙说着美国黑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非洲裔美国黑人在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来到了美国,他们失去了栖身之所的同时,精神生态也因为主流文化的冲击和种族歧视而失去了平衡。他们挣扎在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的身份纠结中:他们有的迷失在白人文化中失去了自我本性;有的固守黑人传统却不被主流社会认同,有的则游离在两种文化的真空地带而无法体现人生价值。正如墨里·布克津在他的《什么是社会生态学》中所言,“几乎所有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例如民族问题,文化和性别冲突问题是最为严重的生态混乱的核心问题“[6](p137)。美国黑人的精神失衡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态混乱的问题。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在精神生态困境中挣扎的各具形态的美国黑人形象。如何融合黑人和白人文化,既保持本民族传统又吸收白人先进的文化技术,黑人同胞如何摆脱本民族的精神困境,平衡了社会生态生存环境、保持精神家园,这些都是作家思考也通过文字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严肃问题。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48.
[2]焦小婷.寻找精神的栖息地[J].山东外语教学,2004,(1).
[3]托尼·莫里森.秀拉[M].胡允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德小说创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
[6]余昌谋.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