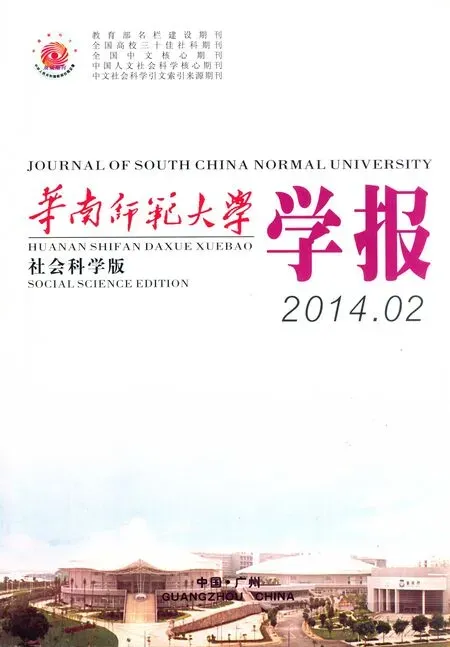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
张 霖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
1962年夏天举行的大连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会议之所以引人瞩目,与其说是因为会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两个著名论点,不如说是因为这次灾难性的会议让周扬、茅盾、邵荃麟、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大批党内作家身陷囹圄甚至失去生命。有关这次会议的相关材料正在不断被披露,但目前仍有不少重要的历史细节存在缺漏,亟须更正或补充。大连会议的具体历史细节,除了参考当时的会议纪录外,还有很多背景资料散见在当代文人、学者的日记中。笔者通过检阅茅盾、顾颉刚等人在1962年7月至8月的日记,又发现了一些可以补正现有史实的重要证据。本文将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一是周扬参加大连会议的时间;二是沈从文是否参加过大连会议,他参加了哪几次会议。
一、当代文学史上的“大连会议”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协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旅大市(今大连市)大连宾馆举行,这次会议简称“大连会议”。该会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动议,由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协党委书记)和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共同主持,参加者有侯金镜(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方冰、陈笑雨(时任《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胡采、黎之(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干部)等。这次会议的主旨在于试图打破“农村小说”日趋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在文学题材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追求多样化,以期使现实主义得以深化。这些观点在1964年后的文艺批判中被概括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另外,周扬、邵荃麟、茅盾等人还公开为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赵树理平反,重新确立了他的农村小说“铁笔”、“圣手”的地位。
应该说,大连会议是“十七年”中比较难得的一个作家们能够畅所欲言的机会。根据黎之的回忆,这是一个真正的“神仙会”。只成立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由邵荃麟负责,侯金镜、陈笑雨、黎之为小组成员,只在会议中碰了几次头;在开会的过程中,不设主席台、首长席,也无开幕式,作家们依自己喜欢的姿势随便坐在沙发中漫谈。邵荃麟在会议中定下了“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调子,鼓励作家们对于农村问题作实事求是的发言。①黎之:《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在某种程度上,大连会议上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是党内作家和评论家试图改变“十七年”来文学创作日趋单一、同化的一次理论探索。这次会议也可以被视为位居党的文化核心的文艺家们对日渐僵化的“工农兵文艺”创作现状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调整或突围。
然而,1962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风向再次出现了急转。1963年、1964年,毛泽东连续发表了《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为了应付这次运动,文艺界再次开始“整风”。大连会议上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被抛了出来。邵荃麟作为“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替罪羊,被免去党内一切职务,调到外国文学所去当一名普通的研究员。①黄秋耘:《“中间人物”始末》,载《文史哲》1985年第4期。但有学者指出,邵荃麟并非这次运动的真正目标,邵荃麟的去职,实际上是剑指茅盾。果然,在1965年初茅盾即被免去文化部部长的职务,其中原因与他是“中间人物论”的真正发明者和后台有直接关系。②丁尔纲:《茅盾研究难点试论》,载《文史哲》1994年第4期;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一)》,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然而,丢掉邵荃麟和茅盾这一“卒”、一“车”,也未能保住大连会议上的另一位“主帅”周扬。1966年,对肯定“中间人物论”负有主要责任的周扬也被打倒,囚禁于秦城监狱。然大连会议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未到此为止。“文革”爆发后,大连会议被定性为“企图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反党黑会”,会上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在江青的《纪要》中被诬陷为“文艺黑八论”之二,遭到严厉批判,以致1971年邵荃麟惨死在秦城监狱中。③丹晨:《邵荃麟的悲情人生》,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1期。而其他与会者也在“文革”中受到牵连。首当其冲的是赵树理,这位大连会议上树立起来的写“中间人物”的标兵,在1968年就先于邵荃麟在山西被迫害致死;④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第56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侯金镜由于是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中的助手,在1964年被迫封笔检讨,1966年被停职检查,1971年在“五·七干校”下放时因病去世;⑤胡海珠:《侯金镜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批评家陈笑雨除了卷入“三家村”外,大连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也使他罪加一等,他在1966年自沉;身为作协河北分会主席的李满天和来自中宣部文艺处的干部黎之也因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文革”中加重了批判;⑥黎之:《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代替马烽来开会的山西作家西戎,因其小说《赖大嫂》在大连会议上被树立为写“中间人物”的样板,也在1964年整风运动后不断受到冲击,“文革”爆发后和赵树理一起被关进了牛棚;⑦杜学文:《革命战士 人民作家——西戎的生平与创作》,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大连会议上唯一一位来自南方的作家周立波和另一位“山药蛋派”作家李束为也因大连会议上的发言而不断进行检讨;⑧杨品:《从战士到作家——李束为的生平与创作》,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期;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1961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被侯金镜调入作协的唐达成,仅仅因为担任了会议记录就在1964年被再次逐出北京,流放到娘子关外。⑨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第81-82页,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
二、大连会议与周扬
目前,有关大连会议的情况及其后来在1964年整风运动中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情况,正在随着当事人回忆文章的发表和研究者对现存史料、档案的解读逐渐清晰起来,但有关周扬参加“大连会议”的时间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当事人邵荃麟、侯金镜、黎之三人的回忆,周扬到会的时间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一说是在会议进行到一半的8月7日或8日;一说是在会议开始时。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根据黎之、侯金镜等人的回忆或交代材料,周扬是在8月8日才从沈阳赶到大连的。黎之在1997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周扬在8月8日从沈阳来到大连,住棒槌岛东山宾馆二号楼。到大连的当天周扬听了邵荃麟汇报会议情况。当晚大连市委还为周扬举行了欢迎舞会。⑩黎之:《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这一说法和1966年下半年侯金镜撰写的有关“大连会议”的交代材料非常接近。侯金镜在材料中写道:“周扬到大连时间比较晚,大概是8月7、8日才到的。”他和邵荃麟去见过周扬两次。第一次是在周扬到达大连的当天,第二次是在周扬到达的第二天。根据《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所收录的周扬《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标注的时间为8月10日,也就是说,侯金镜见到周扬可能是在8月8日或9日。
但是,邵荃麟在1966年下半年所写的交代材料中所记录的周扬到会的时间与侯金镜所交代的不同。他说:“会议开始时,周扬从沈阳知道后,即在安波陪同下赶到大连来。第二天,我和侯金镜去汇报,主要谈会议准备如何开,以及我讲话的要点。在谈到创作问题时,我记得还是谈到中间人物的。……在他讲话之前,我和侯金镜又去汇报了一次。”①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可见,邵荃麟也记得他和侯金镜曾两次去见周扬。但在他的记忆中周扬到会时间并不晚,是在“会议开始时”,但没有提供具体日期。那么,周扬究竟是何时到达大连的呢?
大连会议的另一位重要的与会者茅盾,在1962年8月2日至16日的日记中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过程。在8月2日的日记中,茅盾写道:
二日(阴,雨,后转暴雨,五级至八级风,入夜更大[八级],廿六、七度,下午六时消息,台风方向变为偏东,故本市可免)……九时到大连宾馆,出席创作会议,十二时返寓……三时许,周扬、安波来访,四时许辞去。六时赴市委等为建军节举行之宴会,……席设大连宾馆,约有七、八桌,……文艺界又有顾颉刚、沈从文等。在此开会之作家们亦全都参加。七时半宴会毕,看电影,此为苏联旧片《第伯聂河,你好!》六一年长春厂译制,九时许映毕,即返寓。②茅盾:《茅盾全集》,第39卷,日记一集,第3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由此可知,周扬在1962年8月2日大连会议召开当天即赶到了。而茅盾本人早在7月31日就到了大连,③根据茅盾家人的回忆,这次“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之所以在大连召开,就是因为要配合茅盾参加政协1962年7月-8月间组织的政协委员大连休养的时间而确定的。当时茅盾住在枫林路的大连市委招待所,与周扬和与会作家们不在一处。参见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一)》,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从周扬8月2日下午冒大雨专程来见茅盾的情况判断,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上午的开幕式。这就无怪乎黎之、侯金镜有周扬到会较晚的印象,而且把周扬到会的时间和他发言的时间混淆了。
事有凑巧,有关周扬到会的时间,除了茅盾外,和茅盾一起参加宴会的顾颉刚也在他的日记中提供了周扬在场的证据。1962年7月至8月,中国人民政协组织委员们偕家眷赴大连海滨休养。政协委员顾颉刚也参加了这次休养,并在1962年7月至8月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大连之旅。《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这次旅行的日记共33篇,从7月23日自北京出发至8月24日返京,共33天,一日未缺。
根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62年7月24日,顾颉刚带着三个孩子顾洪、顾湲、顾堪来到大连,住在连捷路休养所。在一个月的休假中,顾颉刚不仅听说了中国作协正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而且还在大连宾馆见到了与会的作家们。
1962年8月2日,也就是大连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顾颉刚到大连宾馆参加大连市委的宴请。在这次宴会上,他见到了周扬、邵荃麟、茅盾、赵树理等人。这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大连会议的文学现场作更客观的审视。顾颉刚1962年8月2日当天的日记如下:
八月二号星期四(七月初三)
王却尘夫妇自京来。收到静秋托带钱信。与王芸生、沈从文、周之风、赵公勤同到大连图书馆参观,又由周之风、王衍爵(士修)导至大庙,观书藏。十一时半归。
……五时,到大连宾馆,赴宴,遇周扬等。
饭毕,先归。洗浴。十时,儿辈看电影归。十一时服药眠,翌晨七时醒。
今晚同席:张奚若高崇民周扬赵树理邵荃麟沈雁冰王绍鏊夫妇王芸生夫妇林葆骆夫妇楚溪春夫妇沈从文李连捷参加作家会议诸同人(以上客)许西(市委书记、市长)胡明(市委书记)谭松平(副市长)姜培禄(副市长)(以上主)共八桌。④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9卷,第517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这则日记证明8月2日大连会议召开的当天,周扬就已经到达大连,而且与所有与会作家们一起吃饭。由于顾颉刚和茅盾的日记是事件发生当天的原始记录,应较为准确。这两条材料足以证明邵荃麟的回忆是准确的,黎之和侯金镜所谓“周扬到会较晚,8月7、8日才来”的说法有误。而且,根据茅、顾二人日记的记载,大连市委并没有为欢迎周扬而举行舞会,而是一个宴会,并在餐后招待看电影。这次宴会邀请了周扬、大连会议的作家们,以及先于他们到达大连的政协委员们一起参加。
三、大连会议与沈从文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茅盾和顾颉刚所列的同席人中,居然有一位在1949年以后就从文坛上销声匿迹的作家——沈从文。众所周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郭沫若斥为“反动文人”的沈从文不胜政治压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行从事历史研究。大连会议的与会者中并没有沈从文的名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场合中呢?
根据收入《沈从文全集》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记载,1956年1月10日,沈从文被增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①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见《沈从文全集·资料·检索》,附卷,第49,5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顾颉刚在7月25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了“同休养人:黄琪翔夫妇及其女平、王芸夫妇、李连捷及其子爽、沈从文”的内容。②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9卷,第511页。由此可知,沈从文参加了这次政协组织的疗养,他未带家眷,独自一人和顾颉刚等其他委员来大连。在这个宴席上,沈从文不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现的。应该说,他和周扬、邵荃麟、茅盾、赵树理等人的相遇,完全是一个偶然。再对读《沈从文年表简编》,还会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情况,即沈从文也接到了大连会议的邀请:“7-8月,在大连休养一个月。适逢在此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主持者邵荃麟相遇,受到邵邀请参加座谈,他以非正式邀请,不便去。”③沈虎雏:《沈从文 年表简编》 ,见《沈 从文全集· 资料·检索》,附卷 ,第49,58页,北 岳文艺出 版社2009年版。但是,在《沈从文全集》的《集外文存》中,又收录了《关于大连会议的事情》一文,明白记录了沈从文最后还是去旁听了这次会议。
《顾颉刚日记》明白地显示,沈从文与邵荃麟的相遇就发生在这次旅大市委组织的欢迎宴会上。那么,当中国作协大张旗鼓地要解决农村小说的题材和人物描写的“多样化”问题,面对邵荃麟等作协领导的邀请,沈从文这位昔日的乡土文学大家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他怎样看待这次会议?他为什么拒绝参会?又为何最终还是去旁听了?
于是,笔者沿着《顾颉刚日记》所提供的线索去查阅沈从文的书信,果然发现在《沈从文全集·书信》第21卷中收录了1962年7月至8月自大连发出的三封家书,分别是1962年7月29日《致沈虎雏》的一封信和1962年8月1日和3日《致张兆和》的两封信。沈从文8月3日《致张兆和》信中非常清楚、具体地谈到了8月2日旅大市委在大连宾馆举行的这次招待宴会:
昨天市委请大家吃饭,一共六桌……到时才知道葛琴夫妇侯金镜等通到了这里。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市长还高高举杯祝“创作会议”成功!来的全是“写短篇”的,似有李准、还有个山西李什么。沙汀、艾芜却不来。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这里。大约谈的也是短篇问题,邵说,你来参加吧,但不正式邀请可不好去。或许有机会听一、二次。他们住的是大连宾馆,在市中心。和我们住得相当远。……侯金镜说“打电报”要你来吧。我说:“我可快要回去了,限一个月。”说:“既来了,北京天气又热,多拖几天好。”④沈从文:《沈从文全集·书信》,第21卷,第230,234页。
……这里的创作会议,怎么不让刊物编辑处看小说的改小说的也来两个人列席听听,并就谈谈看稿总印象?⑤沈从文:《沈从文全集·书信》,第21卷,第230,234页。
这封信写于8月3日,是仅次于茅盾、顾颉刚日记的最接近当时情况的又一材料,它再次证明周扬是8月2日到达大连的,而且,侯金镜也在场。更重要的是,这封信还提供了沈从文被邵荃麟邀请出席大连会议的具体情境。沈从文连第一次文代会都没有资格出席,却由作协党组书记、大会的主持人邵荃麟提出邀请,让他参加一个由中国作协最高领导组织、由各省文联负责人和党内作家参加的会议,对沈从文来说恐怕震惊不小。而当沈从文以“未接到正式邀请”婉拒时,作协党组成员、大会领导小组成员侯金镜又主动提出补拍邀请电报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作协方面的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从这一邀请的行为看,大连会议的确是一次开放尺度相当大的会议。但沈从文早已成惊弓之鸟,他以行将返京为由,没有接受参会的邀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关心这次会议的,以至于对参会的人员以北方作家为主,而“沙汀、艾芜不来”感到不满,又对没有邀请编辑参会感到遗憾。当然,他的这些牢骚也只能在家信中抒发,而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了。
现有的会议记录、邵荃麟和侯金镜的交代材料以及与会者的回忆文章中,的确没有沈从文参会的记录。沈从文已经在8月2日明白地谢绝了邵荃麟的邀请,他又为什么去旁听了这次会议呢?除了邵荃麟、侯金镜的热情鼓励外,恐怕也和他在大连的心情有关。
根据《顾颉刚日记》记载,在大连的旅行中,顾颉刚曾和沈从文作过三次长谈,分别是7月28日与王芸生、沈从文的谈话;7月31日与沈从文在大傅家庄海滩的谈话;8月12日与沈从文在夏家河子海滨的谈话。有关这三次长谈,顾颉刚在日记中只记录了谈话的时间和地点,对谈话内容并无说明。
好在沈从文在1962年8月1日《致张兆和》的信中提到了7月31日这天的活动,包括捡石子和他与顾颉刚在海滨聊天。在信中,大连海滨的石子,对沈从文而言别有含义。沈从文写道:
从小石子让我想起卅年前在青岛种种,上白云洞时你的尴尬处,到北九水洗手时我告你写小说的事,——也捡了好些青红圆石子,和这里的竟差不多,特别是在一处崖边得到的硬度较高的长长的石子,这里也有,和宝石差不多。有些近于“乌金墨玉”。小妈妈,你那时多结实年青!我因此特别捡了些近于“乌金墨玉”的石子作个纪念,别人看来无意思,给你却有意思!……回来时,我带了约五斤重石子。①沈从文:《致张兆和》(19620803),见《沈从文全集·书信》,第21卷,第224-225页。
沈从文信中所提起的“卅年前在青岛种种”,指的是1932年至1933年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整整三十年前的1932年8月,沈从文赴苏州张家正式向张兆和求婚。1933年初,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并介绍张兆和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这年春天,沈从文与张兆和游崂山,路过北水时,因为见到一个葬礼中奉灵幡引路的小女孩,便与张兆和约定要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小说《边城》。②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见《沈从文全集·资料·检索》,附卷,第16页。1932年至1933年的青岛时期,沈从文开始进入创造力最旺盛的写作阶段。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季,对沈从文来说肯定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这些记忆被大连海滩上斑斓的石子唤醒,或许在他心中形成了某种时光倒流的错觉,这些石头的重量,或许象征着他心中被长久压抑着的写作热情。正是在这天下午,政协同人到了“大傅家庄”海滩,沈从文和顾颉这位老朋友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和顾颉刚作“老太太”在沙上帐幄下谈天。还看到海军在远处打飞机靶,大有金门岛的意味。……天清气朗,正和有年在昆明乡下看最后一次轰炸声音差不多,谁也不会感到什么恐怖,孩子们口中还学到乒乒碰碰,不可能明白廿年前是什么情形!③沈从文:《致张兆和》(19620801),见《沈从文全集·书信》,第21卷,第225页。在沈从文信中,“大傅家庄”写作“大扈家庄”。
沈从文在信中再现了他与顾颉刚长谈时的情景。因为第二日是“八·一”建军节,沈从文所提到的飞机打靶,可能是大连空军为次日的表演而进行的彩排。面对一个无产阶级挂帅的新时代,两位同是胡适门生、又都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旧知识分子,在日渐严峻的政治低气压下,他们内心的焦虑惶恐不言自明。或许正是这种相似的失落感、紧张感和压抑感,顾颉刚在这天的日记中补充写道:“沈从文患失眠,不亚于我,我二人皆神经质人也。”④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9卷,第514页。这应该是他们这天下午谈话的内容之一。可见,顾颉刚和沈从文颇有同病相怜之感。
当然,他们的忧虑不仅与个人的荣辱沉浮有关,还与国家的文化工作有关。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从大连文化生活匮乏写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忽视,从而表明了他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担忧:
想起这些,看到这些,多只是一鳞一爪,不知为什么,却容易引起人心中深处一种难于言说的忧虑。觉得目下国家对于“教育”,只像是学校里的事情,一出学校,即宣告结束,……这影响且是多方面的。表现到一切的。首先标语广告即不易动人。宣传画也不易提高,……报刊文章多不带劲,杂文也四平八稳,少性格,不深刻,待改进,可没有人把这一环当成一件事来认真调查研究一番。水平低估价却易高,也将成为特种工艺品,好大一种浪费!懂得这是一种十分浪费的人却不多。⑤沈从文:《致张兆和》(19620801),见《沈从文全集·书信》,第21卷,第229页。
从这封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于工农兵文艺日趋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深感忧虑。而大连会议就是党内作家呼吁文学多样化的一次集体突围,或者这也是让沈从文最终克服内心的惶恐,去旁听会议的原因之一。当然,沈从文完全没有料到这次会议会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又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会议上大胆、尖锐的发言即将变成每个参会者的反党罪证。沈从文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一共参加了几次会议?他是否受到了触动?最直接的线索可以在沈从文的一篇交代材料——《有关大连会议事情》中找到。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有人写大字报说我曾参加过大连会议,我应说明一下。
这是周扬黑帮有计划布置的一次创作会议,据近日公布材料,真正参加的全是党内名作家和各省作协负责人,我非党员,事实上又已多年未写小说,联系不上。只是最后一次邵荃麟、茅盾作总结报告,东北作协(或大连市长,已记不清楚)做主人请客,我适因政协有一批人在大连休息,才被邀请吃饭,并听了一次总结报告。邵与茅盾二人南方下江口音本来即听不懂,座位又远,所以听完以后,只懂要“扩大写作范围”,至于如何扩大,写些什么,我都不明白。会后吃了一顿饭,饭后即转到另外一座大楼屋顶舞会,只见红绿灯彩十分热闹,可能当地文工团和戏剧界均参加。我一人不熟,且从来不喜欢热闹场面,因此不到廿分钟,就由一青年杨同志送我下电梯回家了(这就是我参加的全部过程)。
这个会的内容,我一个党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何况我久已离开写作,十六年中一个短篇也未发表过。即听到说有“扩大写作范围的建议”,毫无现实生活的我,也引不起重新执笔来写短篇小说的妄想和兴趣,……
老话说,人心不可二用,我过去虽写了廿年小说,解放后经过学习已认识到工作对人民无益有害。工作岗位一转移,很自然便放弃了。……至于大连会议的事实,知道的大致便是这一些。①沈从文:《大连会议事情》,见《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第187-189页。
这个交代材料在《沈从文全集》中没有标明时间,但从已将周扬称为“周扬黑帮”,可推测应该是在1966年“文革”爆发、周扬被打倒之后写成的。按沈从文的说法,他直到会议结束时才去旁听了一次邵荃麟和茅盾的总结报告,并且这天会议之后还举行了晚宴和舞会。回顾前文,黎之也提到大连会议上为欢迎周扬曾举行过一次舞会。那么,沈从文所描绘得栩栩如生的这次热闹得让他呆不下去的舞会和欢迎周扬的舞会是否是同一次呢?根据茅盾日记,在大连会议期间的确举行过一次舞会,而且仅此一次:
九日(晴,廿九度左右)……今日上午休会,……下午三时赴大连宾馆开会,今日下午为周扬讲话。六时许散会。七时许,沈阳分会宴请开会诸作家,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以及何书记、许市长等均出席。宴会后有跳舞会,又有电影,……归寓时已十一时。②茅盾:《茅盾全集》,第39卷,日记一集,第334页。
从这则材料中我们终于弄清楚了黎之有关“舞会”的记忆是从何而来的,这个舞会虽不是为欢迎周扬的,但是在8月9日周扬讲话的当天晚上举行的,因而舞会与周扬这两个事件在黎之的记忆中出现了重叠。根据沈从文本人提供的参会细节,可以肯定他在交代材料中所承认旁听过的大连会议就是8月9日周扬讲话的这一次。但奇怪的是,8月9日并非“会议结束时”,而且当天只有周扬一人发言,邵荃麟和茅盾都未作总结报告。那也就是说,沈从文肯定在这个交代材料中说了谎。这恐怕是沈从文在运动中为与周扬划清界限而故意隐瞒了这次旁听,而只交代了另一次听会的事情。因此,有理由推断沈从文不止去旁听过周扬的讲话,还“在会议结束时”又去听了邵荃麟和茅盾的总结报告。
根据黎之的回忆和茅盾的日记,邵荃麟一共有三次重要发言,分别在8月2日、8月7日和8月14日。③黎之:《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而茅盾是在8月12日上午9点开始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8月14日上午为大会议结束的总结报告,由邵荃麟一人完成。8月15日休会,与会作家赴旅顺参观。8月16日上午9时开会,11时茅盾即返家。④参见茅盾在1962年8月12日的日记。茅盾:《茅盾全集》,第39卷,日记一集,第335页。可知上午只有一个简短的闭幕仪式。那么,除了8月9日外,沈从文究竟还去参加过8月12日、8月14日、8月16日会议中的哪一次呢?
根据《顾颉刚日记》中8月12日至8月16日的记载,在这几天中,他在8月12日、13日、15日、16日都与沈从文在一起。8月12日的日记中他和沈从文在夏家河子海边谈话。因此,沈从文不可能去旁听8月12日茅盾的发言。8月13日,顾颉刚记下了沈从文等同人因旅途劳累和食物等原因,“皆病腹病”之事。8月15日顾颉刚还特意“到沈从文处问疾”。8月16日,沈从文则回访顾颉刚。只有8月14日,顾颉刚和王芸生夫妇到旅顺参观,没有和沈从文在一起。①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9卷,第523-525页。由顾颉刚日记可推测,沈从文很可能还去旁听了8月14日邵荃麟的总结报告。在8月14日的邵荃麟总结报告中,他强调小说题材的多样化,并对茅盾鼓励写中间人物的意见表示赞同。这一天虽然只有邵荃麟一人报告,但他也对茅盾有关“中间人物”的观点表示了赞同。这或许就是沈从文为什么说“邵荃麟、茅盾总结报告”的原因吧。
尽管沈从文在8月2日以未受到正式邀请、时间不够等理由婉拒参会,又在3日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参会的诸多顾虑,并提到自己的住处与会场很远,甚至通过顾颉刚日记可以知道沈从文在8月13日他还患上了腹疾,到15日也并未痊愈,但是,沈从文仍然克服了心里的惶恐,不辞劳苦和疾病,不止一次地专程赶到会场去聆听周扬、邵荃麟、茅盾等来自党内核心文化圈的突围之声。可见,沈从文虽已经被逐出了文学界十余年,但他本人对文学界的事情依然关心,特别对大连会议的议题格外重视和感兴趣。可惜由于缺乏更多的史料,笔者目前无法知道这次会议是否对沈从文直接产生过什么触动,现在只能从沈从文的交代材料中看到他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为撇清与周扬和大连会议的关系所作的违心的伪饰和辩解。
综上所述,通过对1962年7月至8月间顾颉刚、茅盾的日记和沈从文书信的阅读,我们可以更正周扬参加大连会议的一些重要史实,并把沈从文与大连会议的关系整理如下:
(一)有关周扬与大连会议:周扬到达大连的时间是1962年8月2日下午,而并非8月7、8日,他很可能未赶上当天上午的开幕式;周扬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间是1962年8月9日下午,而非《周扬文集》第四卷中所记载的8月10日。
(二)有关沈从文与大连会议:沈从文本人承认他偶然在大连遇到参加大连会议的作家们,并“只在会议结束时才听过一次邵荃麟和茅盾的总结”。但事实上,他一共与大连会议的参会者见过三次面。第一次肯定是在8月2日晚,他偶然在大连宾馆举行的宴会上遇到周扬、茅盾、邵荃麟、侯金镜、赵树理等所有参会作家。席间,邵、侯主动邀请他参加大连会议,被沈从文婉拒,但他后来还是去旁听了会议。第二次是8月9日下午去旁听周扬的讲话,并参加了当晚沈阳作协分会举办的晚宴和舞会,他在舞会开始后不久离开。第三次很可能是在8月14日上午旁听邵荃麟对大会的总结报告。沈从文没有听茅盾在8月12日的讲话。
尽管现有的文学史研究已经对大连会议有了比较全面的展现,但是,从当代学人、文人的日记中去搜寻这个历史现场,也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文学考古。那些散落在日记和书信中的一些看似不重要的细节、不相干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对重要的文学事件的历史背景、事件过程、事件影响,及文学史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做更准确的记录、更深刻的把握、更细致的描绘,从而在第一时间、第一手资料中将一幅更为准确、全面、真实的文学史拼图展现在研究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