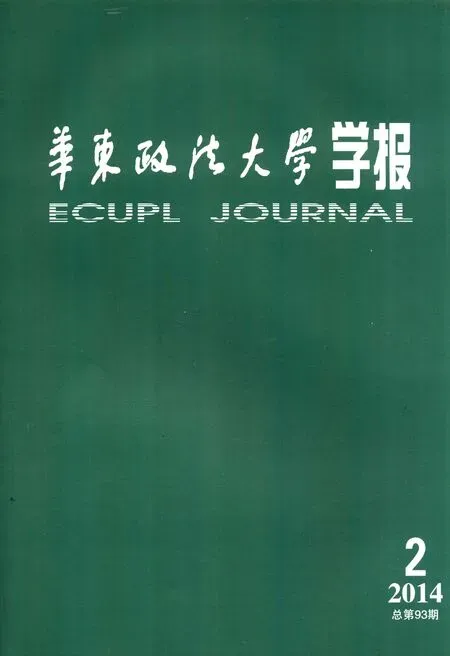中国传统法“共犯”概念的几则思考
[德]陶安
一、作为教令犯的正犯
关于唐律的共犯概念在滋贺秀三与戴炎辉二位已故的老前辈之间曾经有过一番论争,为学界所周知。〔1〕[日]滋贺秀三:《唐律における共犯》,载《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創文社1984年版;戴炎辉:《唐律通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373-399页;戴炎辉:《关于清律的共犯》(《国家学会杂志》85-5/6,1972年);[日]滋贺秀三:《唐律疏议译注篇一》,载律令研究会:《译注日本律令五》,东京堂1979年版。当时教唆犯为主要分歧点。戴先生主张教唆犯与普通共犯有别,唐律除了共犯之外还另设“教令犯”一类犯罪类型。共犯之“造意者”系“置身在事内,与随从者共同谋议,而分担实行行为之一部分之人”,而“教令犯”则“置身事外(教令人本身在实行行为之外),教导、唆使他人犯罪”。〔2〕戴炎辉:《唐律通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390页。换言之,参与实行行为与否是区别共犯之“造意”与“教令”的主要标志。唐律虽然没有相关的专条,但在戴先生的理解中,唐律中存在教令犯的一般原则,即“就一般犯罪,教令犯均能成立”。〔3〕戴炎辉:《唐律通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390页。关于教令犯的处罚,戴先生认为,教令犯系“利用他人行为之犯罪”,所以教令人与被教令人均在自己的责任能力范围之内对该犯罪行为“负全罪”。
滋贺先生从三方面反驳戴说。第一,所有教令犯都“负全罪”,这一假设会导致一些与我们健全的“法律上的平衡感觉”相互矛盾的情况。比如,罪犯A服父母丧,平时与他玩惯的伙伴B为他安排一座筵席,让他换换心情,痛玩一夜。按照戴说,除了A犯了“忘哀作乐”应该判“徒三年”之刑,B的教唆行为也构成教令犯,相同地处以全罪,这恐怕不免过于严重。第二,如果将参与实行行为与否当做区别“造意者”与“教令犯”之标准的话,实行前离开现场反而会比留在现场受到更严重的处罚。比如,A困于还债,党羽B劝他杀掉债主,A听从劝说与党羽C、D一起杀害债主。按照戴说,B如果在实行之前离开现场,他将与A相同地要判斩,但如果他留在现场,而“不加功”,量刑则为“流三千里”,〔4〕按照滋贺先生的理解,“造意者”总只有一个人,如果A在现场指挥C与D共同杀害债主,而B仅站在旁边望风的话,A为“造意者”,B为“从而不加功”。反而变轻。这种结论不太合理。第三,唐律虽然没有“教令犯”的专条,但是有几条相关的特别规定,大多涉及一些具备某种职业知识的人员在背后操作的特殊情况。唐律将这种特殊情况与普通的共犯区别开,是为了加重对这些恶劣的教唆犯的惩罚。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唐律的此种用意,将特殊的教令犯与普通的教唆犯混为一谈,而归纳出新的教令犯的一般原则。〔5〕参见[日]滋贺秀三:《唐律疏议译注篇一》,载律令研究会:《译注日本律令五》,东京堂1979年版。
尤其是第三点更值得我们进一步玩味。在唐律有关教令的特别规定中,不难发现两种情况,都是所规定的教令行为明显比普通教唆行为具备更高的恶性,但是所规定的惩罚与戴先生所设想的教令犯的一般原则大致相同。第一是《诈伪律》的“诈教诱人使犯法”条,第二是《斗讼律》的“以威力使人伤杀人”。〔6〕“威力制缚人”条第二项。二者都用欺骗、暴力等本来就非法的手段达到教唆的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下手执行杀伤的人甚至成为教唆者手里的工具,与所谓“间接正犯”接近;教唆的目的又是陷人于罪、杀伤人等,这都对法律秩序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总之,这两种教令犯的犯罪情况非常恶劣。但是,量刑分别为“同坐”与“重罪”。“重罪”与下手者的“减一等”相对,意思是将威力教唆者当做“造意者”判刑,量刑也不超过戴说的普通教令犯。如果普通的教令犯都处以全罪的话,那么这些恶劣的教令行为不应该另外加重量刑吗?与此相似,《名例律》的“老小废疾”条规定,教令“老小废疾”等人犯罪的话,将教令者当做主犯判刑。这种犯罪情况与“威力使人伤杀人”相近,是将缺乏刑事责任能力的“老小废疾”等人当做工具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也可以理解为“间接正犯”。但是本条也仅规定“坐其教令者”,量刑不超过戴说所设想的“全罪”。既然有多种特殊的教唆犯或教令犯也仅仅处以“同坐”等刑罚,那么将所有教令犯一概处以“全罪”的一般原则不会过于僵硬,太忽略不同犯罪情况之间的轻重平衡吗?这些都是让我们难以接受戴说的理由。
二、造意与实行
然而,滋贺先生的理解也存在一些问题。滋贺先生认为,在唐律中,现代刑法所谓的教唆犯的内容大多数包含在对普通共犯规定中。教唆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受到名例律“共犯罪造意者为首”条的“造意者”或“随从者”的惩罚。〔7〕参见[日]滋贺秀三:《唐律疏议译注篇一》,载律令研究会:《译注日本律令五》,东京堂1979年版。其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名例律的“共犯罪造意者为首”条。该条规定:
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
按照滋贺说“造意”不外乎是“造出犯意”之义,也就是为了形成并持续共同犯意做出主导贡献的意思。“随从者”则是指不扮主导角色的其他共犯。换言之,在形成犯意时是否起主导性作用成为区别“造意”与“随从”的主要标志。“造意”概念与犯意的密切关系又使滋贺先生更进一步把实行的层次从原则上与“造意”、“随从”两个概念区别开。他主张共犯在各自实行犯罪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所扮的不同角色(即各自在行为上的地位)都是用“下手”、“加功”、“行”等概念来概括的,与“造意”、“随从”两个概念所管辖的“犯意”简直属于两个不相关的层次。因此,“造意者”既可以参与实行行为,也可以不参与,“随从者”亦然。〔8〕参见[日]滋贺秀三:《唐律における共犯》,载滋贺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創文社1984年版。
其实,针对犯意与实行的看法正是滋贺说与戴说最大的分歧点。戴说将参与实行行为与否视为区别普通共犯与“教令”的标志,滋贺说则将主导犯意与否当做区别“造意”与“随从者”的标志。戴先生将“共犯”限为“共同实行犯罪”者,〔9〕参见戴炎辉:《唐律通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380页。因而不得不另外寻找与现代所谓教唆犯相应的概念,最后构成一个唐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教令犯”的一般原则;滋贺先生则避开“实行”的问题,纯粹从犯意来解释“造意”与“随从”之别,因为教唆犯与犯意的形成密切相关,所以很自然地就把教唆犯纳入普通共犯之内。
但是,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绕开“实行行为”这一问题吗?名例律所规定的“诸共犯罪者”到底能否包含未曾“共同实行犯罪”的人员呢?滋贺先生不从正面讨论这个问题,而仅从“造意”的字面上立说。我们很容易能看出一个问题,“造意”与“随从”毕竟是从“共犯罪者”孳乳分出来的两个概念,想要确定三者的准确含义,非从“共犯罪者”入手不可。如果戴先生对“共犯罪者”的理解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唐律的“共犯”概念限于“共同实行犯罪”者,“造意”与“随从”就无法包含其他成分,滋贺先生的“犯意”说则归于泡影了!
从唐律的明文规定来看,“共犯”似乎不应该包含“共同实行犯罪”以外的人。这个道理与戴先生的教令说不成立相同,主要可以从相关的特别规定中看出,唐律不承认相关的一般性原则。比如《贼盗律》“谋杀人”条规定:
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
注云:
雇人杀者亦同。
如果“共犯”本来已包含“不行”者,唐律何故多此一言?正如戴先生所说,这则条文“须解为系特例”。换言之,“共犯罪者”所指的,“就一般而言(通例)……乃共同实行此一体的行为之人。”〔10〕戴炎辉:《唐律通论》,台湾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387页。另外,贼律“共盗并赃论”条规定:
若造意者不行,又不受分,即以行人専进止者为首,造意者为从。至死者减一等。从者不行,又不受分,笞四十。强盗杖八十。
如果“共犯”以及“造意”本来已包含“不行”者,这则条文则变成针对共盗造意者的减轻规定。这是因为其他犯罪的造意者,即使“不行”,也应该按照《名例律》判为“首”,而只有共盗者的“造意”判为“从”,与“首”者相比减一等。这种结论恐怕不太合理。盗犯经常是一些有组织的罪犯,取缔盗犯的要害在于抓住窝主等在背后操作的罪犯,严加惩戒。本条前段规定:
造意及从,行而不受分,即受分而不行,各依本首从法。
正是这种用意,“受分”本来不属于“实行犯罪”的范围,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事后共犯”。〔11〕不过,本条所谓“受分而不行”指共谋“共盗者”中没有参加实行行为的人员,与“知略和诱强窃盗”条所规定的纯粹的事后共犯又略不同。本条将其纳入构成要件的用意不外乎在于扩大普通共犯的适用范围。这才可以合理地解释本条后段规定“造意者不行,又不受分”判为“从”的原因,是为了限制前段的扩张,为其划出明确的界线。如果名例律的“造意”概念已包含所有“不行”者的话,我们就难以理解本条何故为了“不行,又不受分”的盗犯创造特例!
总之,唐律对于广义共犯中的“教令”者和“不行”者都设立了一些特例,这足以证明唐律没有相关的一般性原则。换言之,教唆行为既不包含在《名例律》的“共犯”之内,又不宜一律判以“全罪”。除了特例之外,教唆行为似乎都不应该单独构成犯罪。
三、违法性外延的扩张
教唆不构成犯罪,对很多读者来说这一结论也许不好接受。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共犯概念就应该以共同实行犯罪者为核心。这是因为这些犯人最容易引起官方的注意,最开始要取缔的就是这些人。随着刑事政策的发展,官方也开始注意到一些在背后操纵犯罪,但总不出面的共犯。这些广义的共犯实际上危害很大,盗犯的窝主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从刑事政策的需要来说,针对这些特殊的共犯只要设立一些特例,就有充分的法律根据来进行取缔。唐律很明显就是采取这种态度,而且,唐律并不是孤例。在中国,早在秦代以及汉代初期的律令中已经能看到相同的共犯概念,在国外,英美法系至今仍坚持相似的基本态度。在此先介绍秦律以及汉代初期律令的基本情况。
秦律已经明确意识到共犯与同时犯之别。这可以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的下引一条看出:
012甲乙雅不相智(知)。甲往盗丙,毚(纔)到,乙亦往盗丙,与甲言,即各盗。其臧(赃)直(值)各四百。已去而偕得。其前谋,当并臧(赃)以论。不谋,各坐臧(赃)。
提前共谋并赃论罪,没有共谋则各自论罪,这不外乎以共同犯罪意思为共犯的基本要件。关于不参与共同实行犯罪的广义共犯,也可以在《法律答问》中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盗犯的事后共犯见于下一则答问:
009甲盗,臧(赃)直(值)千钱,乙智(知)其盗,受分臧(赃)不盈一钱。问乙可(何)论。同论。
此处“受分”与唐《贼盗律》“知略和诱强窃盗”条的“受分”应该是相同的意思,只是唐律规定“减一等”,而秦律则“同论”。教唆犯的例子如下:
067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磔。
这则答问所描写的犯罪情形与唐名例律“老小废疾”条的最后一段相似。“高未盈六尺”指未成年人。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简65-66)的明文规定,汉代初期“盗杀伤人”处以“磔”,可以看出答问的结论与唐《名例律》最后一段“即有人教令(老小废疾),坐其教令者”一致。
“谋”概念在秦汉法律史料中常见,值得我们简单整理一下。《二年律令》贼律规定:
022谋贼杀,伤人未杀,黥为城旦舂。
此处的“谋贼杀”是指一种“未遂犯”,本来打算贼杀人(即故意杀害人),但是没能杀成,仅伤人未杀。这种犯罪情形与唐《贼盗律》“谋杀人”条所谓“已伤者”相似,但是汉代初期的“谋贼杀”仅涉及“未遂犯”,不提到“预备犯”,唐贼盗律所谓“谋杀人者”似乎还不构成犯罪。〔12〕虽然谋贼杀的相关规定似乎不包含,但是“预备犯”构成犯罪的情况已经出现,详看续文。随着语境之不同,秦汉的“谋”概念也可以表示另一种的意思,比如《二年律令·贼律》另外规定如下:
026谋贼杀、伤人,与贼同灋(法)。
在此第二个“贼”字是指实行犯罪的正犯,与此相比“谋贼杀、伤人”则不外乎是指不临场的共谋者。《汉书·薛宣传》所提到薛况“赇客杨明……令明遮斫(申)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的案情属于这种情况。廷尉将薛况的罪行拟为“与谋者”,此一词也见于《二年律令》:
这一则条文将前两条规定合并,仅将简026“贼伤人”的罪名省略。“与谋者,皆弃市”是“谋贼杀,与贼同灋(法)”的另一种说法;“未杀,黥为城旦舂”则是“伤人未杀,黥为城旦舂”的省略体。
为什么秦汉律能将“未遂”与“共谋”或“教唆”等内容都容纳在同一个“谋”的概念下呢?笔者认为,“谋”的概念是为了扩张相关罪名的适用范围而产生的。“贼杀”、“盗”等普通罪名似乎都以完整的实行行为为中心,全面实现犯罪意思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而这种“完整”的犯罪行为周边的其他行为都须要以特别规定的形式明文化才能构成犯罪。与全面实现犯罪意思的犯罪行为相比,可以将这些周边的行为称为“不完整的犯罪行为”。
“盗”犯的一些不完整犯罪行为都还比较容易找到客观行为上的表现,如上述的“受分”为其一例。〔13〕《二年律令·盗律》称为“智(知)人盗与分”(简57)。所谓“受分”者一般是指没参与实行而事后分赃的行为,〔14〕唐《贼律》“共盗并赃论”条所谓“受分”稍特殊,详看前文。光靠诸如《二年律令》盗律(简055-056)关于普通盗犯的明文规定难以为这种不含有完整实行行为的罪行构建违法性。所以上述《法律答问》(简009)以及《二年律令》盗律(简057)等特意用“同论”、“同法”的逻辑构建违法性。下引《法律答问》中的“抉钥”也应该如此理解:
030抉籥(钥),赎黥。可(何)谓抉籥(钥)。抉籥(钥)者已抉启之乃为抉,且未启亦为抉。抉之弗能启即去,一日而得,论皆可(何)殹(也)。抉之且欲有盗,弗
031能启即去,若未启而得,当赎黥。抉之非欲盗殹(也),已启乃为抉,未启当赀二甲。
“抉钥,赎黥”系秦律佚文,其所谓“抉钥”即撬开门锁是盗窃行为中较普遍的一种着手行为,即使没能达到盗窃的目的,也不难看出犯罪意图。秦律则利用这种犯意的客观表现,为盗罪周边的不完整犯罪行为构建违法性。
但是,“预备”、“未遂”、“共谋”、“教唆”等等不完整的犯罪行为,其情形是多样性的,如果逐一用明文规定的方式构建其违法性,恐怕不免过于烦琐。上引《答问》已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被当做盗窃着手行为的“抉钥”概念比较清楚,不会产生任何疑问,不管门锁最后撬开没有,只要罪犯动手撬锁,着手行为完整,盗窃的未遂即成立。纳入制定法作为独立罪名的“抉钥”则不同。尽管大多数的“抉钥”都是盗窃的着手行为,也存在一些与盗窃无关的情况,这就造成新的分歧,导致上引答问的出现。其他不完整的犯罪行为也会造成相似的问题。比如上述“贼杀”的未遂犯在外表上与已遂的“贼伤”行为难以区分,与现代刑法上的杀人未遂罪和已遂的伤害罪一样,只能依靠犯意加以区别。在笔者的理解中,“谋”的概念是一个具备较高灵活性的工具,可以为千差万别的不完整犯罪构建其违法性。
秦汉时代的立法者却没有漫无边际地扩张所有犯罪的适用范围,它并没有像欧洲大陆法系的“未遂犯”、“教唆犯”那样,为“谋”建立一个普遍的原则。它采取了个别化的方式,即择出从刑事政策等角度需要扩张的罪名,为其逐个制定特别规定,以明文规定的方式限制“谋”概念的扩张作用。汉代初期的《二年律令》即有如下的特别规定:
1.谋反:
001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
002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
2.贼杀、贼伤:
·未遂:
022谋贼杀,伤人未杀,黥为城旦舂。
·共谋、教唆:
026谋贼杀、伤人,与贼同灋(法)。
3.盗犯:
·教唆:
057谋遣人盗若教人可盗所,人即以其言□□□□□及智(知)人盗与分,皆与盗同灋(法)。
·共谋:
058谋偕盗而各有取也,并直(值)其臧(赃)以论之。
4.劫人:
068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完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徧)捕,若告吏,吏
069捕得之,皆除坐者罪。
5.盗铸钱:
208诸谋盗铸钱,颇有其器具未铸者,皆黥以为城旦舂。智(知)为及买(卖)铸钱具者,与同罪。
虽然个别的规定与唐律有所出入,但是以特别规定规制“预备”、“未遂”、“共谋”、“教唆”等不完整犯罪的基本范围却与唐律没有太大的区别。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唐律不设相关的一般原则,而以特别规定扩张个别罪名的适用范围,这并不是偶然性的产物,而是一个很有传统、行之有效的办法。
最后,秦代以及汉代初期的法律似乎还没有将共犯在行为上的不同地位反映到量刑上。《法律答问》云:
137夫、妻、子十人共盗,当刑城旦,亡。今甲捕得其八人。问甲当购几可(何)。当购人二两。
“夫、妻、子十人共盗”,其中每个人所扮的角色、为了共同犯罪得以实现所作的贡献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夫、妻、子十人”都相同地“当刑城旦”,不加以区别。上引“受分”、“与谋”等例子也都忽略个人在行为地位上之不同。因此,只能认为当时还不存在“首从”等区别。“首从”等区别在共犯概念的历史发展上似乎属于较晚的孳乳分化现象。
四、结语
滋贺秀三与戴炎辉二位前辈都在东京大学受到大陆法系的熏陶,二位都试图用“扩张的正犯概念”全面概括唐律中的“共犯”,可以说是其教育背景的自然结果。滋贺先生曾经用“理论性非常强”与“从实际出发”〔15〕[日]滋贺秀三:《唐律における共犯》,载《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創文社1984年版,第385页。两种说法分别形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共犯概念。二位先辈所选择的是大陆法系的“理论”之路,而秦汉以及唐律所采取的,即以特别规定规制共犯周边的教唆行为,则似乎更是从实际出发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简单地与英美法系的共犯概念进行比较。英美法系将广义的共犯分为“principal”与“accessory”两类。前者是指在现场实行犯罪的罪犯,可以译成“正犯”;后者则是不参与实行行为而以其他方式所牵连在内的罪犯,比如事先参与共谋、事后分赃或帮助逃亡等等犯罪行为都归为这一类,可以译为(狭义的)“共犯”。受到惩罚的主要是正犯,狭义的共犯在于具有诸如“accessory before the fact”(事先共犯)或“accessory after the fact”(事后共犯)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而不是所有的共犯都可以毫无条件地与正犯一同判处刑罚。另外,正犯又按照其在行为上的地位细分为“principal in the first degree”(一级正犯)与“principal in the second degree”(二级正犯),其大致可以理解为自主实行犯罪与帮助实行犯罪,即首犯与从犯。
虽然,英美法系的共犯概念在细节上与中国传统的共犯概念也有不少出入,但是二者的基本框架很相似。二者都以实行犯罪的罪犯为中心,按照行为上的地位将其分为“首”、“从”两类,并在此外另设特别规定取缔一些不直接参与实行行为、但是对法律秩序有较大危害的相关人。这种框架不仅是从实际出发的,而且在两种不同法系的国家中都曾经行之有效。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借用诸如“扩张的正犯概念”等大陆法系的概念,削足适履地将其套在唐律的共犯概念上。
中国传统法很重视制定法主义,在这方面与大陆法系颇有相近之处,但是同时,中国的传统法也具备诸如“奏谳”、“秋审”、“比附”等将判例经验迅速反馈到制定法里的渠道,可以说在制定法主义中含有相当浓厚的判例法主义成分。大概是这一判例法成分使中国传统法坚持与英美法系相似的实践指向,而与大陆法系那样的理论指向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不难想象与英美法系的比较还在更多其他方面会使中国法制史研究者大开眼界,但这已远远超过拙稿的讨论范围,在此不再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