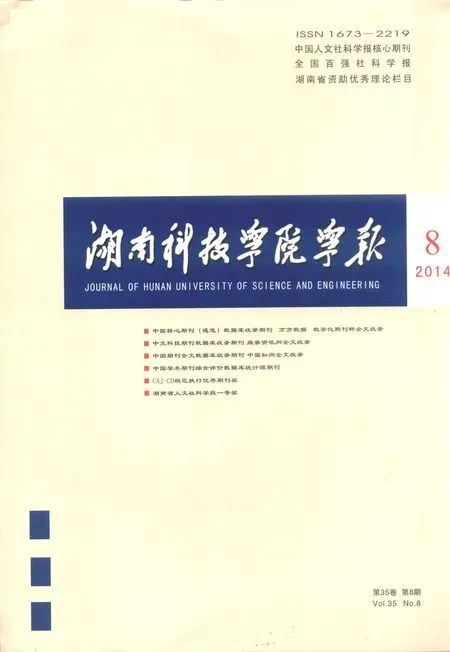《黑暗的心》的“文明”伪命题研究
谢冬文
(湖南科技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永州 425199)
当以占有和掠夺为主要目的殖民统治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人时至今日尚无法完全褪去他们自以为是的、虚伪而高傲的外衣。然而文学家约瑟夫·康拉德在殖民猖獗之时就清醒地揭露了其虚伪性。殖民不是个体的行为,不是某一个西欧国家的行为,是当时的西欧强国均牵涉其中的行为。“殖民主义是一个体系。”[1]P9康拉德通过《黑暗的心》告诉大家欧洲在世界的殖民与古罗马的征服战争本质上是一样的,“只需要有残暴的武力就够了”[2]P488。两者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殖民主义给自己强加了一个“观念”[2]P489。这个观念的核心是利他主义,即教化土著、传播文明。既然殖民被描述为一项利他的事业,那它自然就是正义的事业,值得歌颂的事业。且不论殖民正义与否(当今的世人都知道它是非正义的),殖民主义的利他主义宣扬有一个看似完美的假设前提:西方人是文明的,非西方人是不文明的。殖民主义于是成为了文明的殖民者怀着崇高的利他主义精神帮助不文明的土著居民。殖民者成了“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2]P517,文明的使者。
然则在殖民的世界里只有一种文明:“西方文明”。(Kidd认为这种文明体系不是Teutonic or Celtic or Latin civilization,被称为 European civilization也不贴切,最合适的称谓是Western Civilization。)[3]P121将整个世界描述为一种文明与多种不文明的二元对立是粗暴的、武断的、不可取的,这种“文明”注定是一个伪命题。
一 “文明”的虚伪性
殖民世界所谓的“文明”是殖民主义者为殖民量身定做的。著名的殖民主义者,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殖民主义世界的“文明”有过一次精准的定义:
文明不是改进的同义词,而是与原始或者野蛮直接相对或相反的词。我们称之为野蛮生活习性的东西,与其相反的,或者社会用以摆脱这些习性的品质,就构成了文明。因此,野蛮的部落包含一些个人,游荡在、或者稀稀落落地分布在一大片野地里:反过来,人口分布很稠密,有固定的居所,且大量集中在城镇和乡村的,我们叫做文明。在野蛮生活中没有商业、没有制造业、没有农业、或者几乎什么也没有:一个农业、商业、制造业成果丰硕的国家,我们称作文明。在野蛮群体里,除非战争来临,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忙碌,我们很少看见他们采取联合行动;野蛮人常常也不会在自己的社会里发现多少乐趣。人类在大集体里面为了共同的目的一起行动,并且在社会交往中享受快乐,我们称作文明……[4]P120
在这个文明的定义中,殖民者假设出了一种绝对的“原始或者野蛮”的状态,通过对野蛮的定义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凡是与野蛮相对的就是文明的。在这种看似荒谬的背后,那些所谓“文明”的特点竟然如此惊人地无一例外地可以适用在当时的西欧殖民列强身上。穆勒机巧地以一种荒谬而又看似客观的方式将当时西方发展阶段的所有特点迂回成为文明的内涵,企图将文明内在为唯一的西方文明,进而粉饰殖民主义。穆勒认为,“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合作的能力和克制的能力。这是文明的西方人与非西方人的重要区别。《黑暗的心》对这两个特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贸易站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的自私主义与不合作造成的。“道德派”站长库尔兹因为自私与贪婪罔顾公司要求其回中心站的决定,决然走进殖民地的深处。自私与贪婪的膨胀激起了他强烈的占有欲望。“‘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贸易站,我的河流,我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他的。”[2]P553中心站长感受到了贪婪的库尔兹的威胁,置公司事业于不顾,处处为难他并趁库尔兹生病之时,不发医药补给、延误救治时机,费尽心思置其于死地。在所谓“文明”的殖民群体中,合作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康拉德以为土著黑人在饥饿威胁面前所展现的克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认为饥饿是人类最难过的一道坎。“没有哪一种恐惧顶得住饥饿,没有哪一种耐力能熬得过饥饿,厌恶不存在于饥饿存在的地方;至于说迷信、信仰,或者什么你们不妨称之为原则的东西嘛,还不如微风中的一把稻草末。”在饥饿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被称为野蛮人的土著们在饥饿面前所展现的克制却是“深奥莫测”。[2]P541与克制的黑人不同,正是代表“文明”与“道德”的库尔兹在诱惑面前无法克制自己。库尔兹的“商业秘密”就是“毫无节制地满足他的种种欲望”[2]P566,最终被自己的欲望吞噬。
二 “文明”的利他主义
Kidd认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利他主义”[3]P45,而这种自封的特征得到殖民国家的一致认同。Kidd举例说正是因为这种利他主义驱使西方有识之士促成奴隶制的废除,他似乎忘记了正是所谓西方文明人的残暴与贪婪造就了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事实上,殖民主义者时时刻刻高举着利他的口号。叙事者马洛的阿姨在他临行前一再嘱咐他要“使那千百万愚民摆脱他们可怖的生活习惯”[2]P497。库尔兹宣称:“每一个贸易站都应该像道路上的一盏能够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路明灯,它当然是一个贸易中心,但是也应该是一个博爱、进步和教化的中心。”[2]P528西方媒体报纸上充斥着这种博爱利他的言辞,西方人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国际禁止野蛮习俗协会”并且委托库尔兹“撰写一份报告”。库尔兹“居然有时间来写下密密麻麻的十七大页”,且有着“庄严静穆的仁爱胸怀,异乎寻常的浩然之气”。在最后一页还有一个“类似注解性的东西”。这段文字“娓娓动人,足以激起各种利他主义情感”。[2]P555在殖民者的文宣与话语中,殖民成为了一种纯粹利他的自我牺牲性行为,他们最重要的动机与目的似乎是引导“野蛮愚昧”的土著走向进步与光明。
库尔兹还常常谈论“博爱、正义、品行”,他似乎成了“道德”的化身。库尔兹的话语一向冠冕堂皇,他还时时提醒自己的追随者“必须注意动机——正确的动机——永远要注意”[2]P583。所谓动机就是永远利他的话语。他一方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宣扬利他的动机,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攫取象征财富的象牙。殖民世界里的所谓“西方文明”的利他主义只是一种欺骗与掩饰,欺骗殖民地人民与公众舆论,掩饰因为自己的贪婪与残暴在殖民地所做的种种恶行。康拉德通过这位时刻注意利他主义正确动机的库尔兹之口道出殖民者真正的殖民目的:“我的象牙,我的贸易站,我的河流。”殖民真正的目的就是占有与掠夺。利他主义将土著视为需要帮助与引领的对象,而殖民的目的瞬间将他们客体化为“敌人、犯人、工人”甚至“反叛的人”[2]P568。马洛所看到的殖民者赤裸裸的贪婪、自私、占领与掠夺让被宣扬的“西方文明”的利他主义特征变得苍白无力,变得虚伪荒唐。
三 为什么是唯一的文明
在殖民体系中,殖民者是文明与道德的。殖民主义者将自己的文明定义为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不是因为他们过于自大。这不是纯学术意义上的文明探讨,文明与道德已经成了殖民者的一种工具与手段,他们玩弄文明只是为了殖民的目的,为了让殖民道德化。斯宾塞早就强调过了“为了目的而调整行为”[5]P13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手段的形成与西方殖民者所拥有的不对称的强大力量是分不开的。康拉德认为他们的“力量仅仅是从别人的软弱中产生出的一种偶然”[2]P488。在历史的长河中,力量的此消彼长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重要的是殖民者对力量的运用。殖民列强使用这些力量将非西方的世界客体化、黑暗化、野蛮化。凡是非欧洲的地方都是黑暗的,而库尔兹呆在“黑暗的心脏”。
殖民列强为自己设立标准去定义文明道德与野蛮,然后自封为文明的化身。尼采对这种自封模式进行过精彩的推理:
“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从这种保持距离的狂热中他们才取得了创造价值、并且给价值命名的权利……以每一种工于心计的精明,以每一种功利的算计为前提—不止一次的,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永久的。[6]P12
殖民者利用偶然强大的力量强行夺取话语权力的高地,将自己定义为好的、高贵的、高尚的、有道德的、文明的,将殖民地居民定义为坏的、卑微的、没有道德的、野蛮的、无知的,从而在白色人种和其他人种之间埋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进而赋予白人世界唯一的“文明”。
殖民者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将自己与殖民地居民区别开来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殖民者“诠释、赋予、美化、诗化的力量”[7]P247。西方列强只有将自己美化诗化为唯一文明的代表者,才能定格自己文明、进步、道德的形象,才能合理化自己道德的制高点,进而让“西方文明”所谓的利他主义成为一种必要与必然,并最终将殖民粉饰为一种利他的体系,为殖民合理化、道德化提供话语保障。尼采认为“粉饰是力量增大的结果。粉饰只不过是胜利意志的一种表述”[7]P241。粉饰是自以为胜利之时将自己进行美好包装的一种心虚的行为,是一种自圆其说。无论粉饰得多么美好,殖民体系的邪恶本质无法被去除。“看待一种美好的东西必然要看它的虚伪性。”[7]P247无论西方列强怎样绞尽脑汁使用自己所谓的理性与逻辑牵强附会地勾勒一张伟大的利他文明图景,他的伪命题本质丝毫不会有所改变。
[1]Sartre,Jean-Paul.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M].London:Routledge,2001.
[2]约瑟夫·康拉德(袁家骅,智量等译).康拉德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Kidd,Benjamin.Social Evolution[M].New York:Macmillan and Co.,1894.
[4]Mill,John Stuart.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ume XVIII[M].London: Routledge, 1963.
[5]Spencer, Herbert. The Principles of Ethics[M].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7.
[6]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周红译).论道德的谱系[M].北京:三联书店,1992.
[7]Nietzsche, Friedrich.The Will to Power Vol.II[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