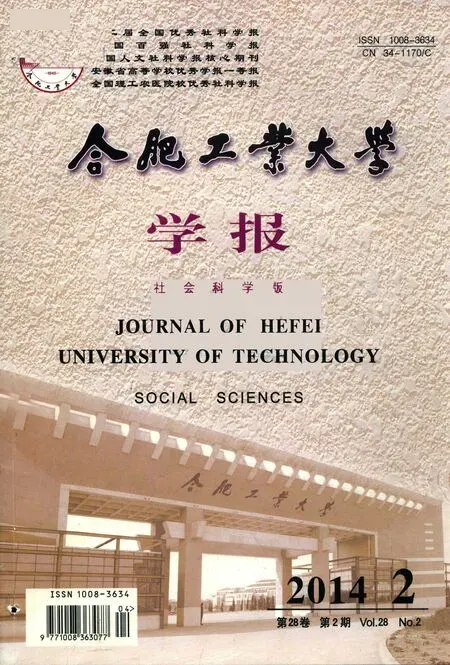自我·他者·责任——《受害者》中的伦理思想之管见
赵秀兰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2.西北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兰州 730070)
《受害者》(The Victim,1947)是美国犹太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早期的小说。贝娄曾表示,该小说是严格按照福楼拜的文学创作标准创作的,由于过于注重锤炼词句,以致不能流畅自如地表达思想,因而他不愿多提该小说[1]8-9。但评论界给予该小说以较高评价,如:沃伦认为,《晃来晃去的人》和《受害者》非常出色地沿袭了詹姆斯-福楼拜传统,已经显露了贝娄的创作才华[2]9。法莱利认为,《受害者》进一步稳固了贝娄在当代文坛的地位[3]30。可见,《受害者》也是贝娄重要作品之一。
贝娄的主人公多为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传统信仰疏离,与他人和社会处于冲突的状态中,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困境。克莱登提出,在早期创作中,贝娄受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道德模式的影响,颂扬人的尊严[4]141。布拉德伯里认为,《受害者》反映了个人意志对于社会环境的决定性作用的抗争[5]32。“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6]14。贝娄作品对行善、兄弟情谊、社区和生活意义的肯定和对责任感的强调表明了犹太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犹太教的特征,犹太教传授给其他民族的东西,是它对世界的伦理肯定:犹太教是一种伦理乐观主义的宗教”[7]72。本文从道德成长、爱邻如己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来探讨《受害者》所反映出的伦理思想。
一、道德自我
贝娄认为作家应该用他的想像力来表现美德,文学旨在提出道德问题[8]58。他在作品中着意刻画社会、他人和命运的牺牲品,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探索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的方式。“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和伦理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也是和道德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8]19。
犹太教是“一种关于善的学说,向人提出问题,在‘你应该’意义上给人以正确的回答”,而非遁世或旁观者的自满自足[7]74。受犹太教的影响,贝娄在作品中肯定存在的意义和世界秩序是为善而创造的,相信自我、邻居和人类,通过展现个体自我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他们的道德选择,及他们自我救赎的途径,来启迪现代人如何自救。
贝娄文学创作的关键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人物,即让人物发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谁”[10]9,其小说表明,对生命的敬畏和信仰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部分信念。《受害者》中讲述了主人公犹太人阿萨在与反犹白人阿尔比的斗争中逐步认识自我、从道德上完善自我的故事。小说背景为拥挤的大城市纽约,人物的社会地位不高,活动场所相对孤立,主要是在办公室、公寓、酒吧和咖啡店,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不密切。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调敝,竞争非常激烈,失业率很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非常艰辛,人不仅要与其他人斗争,还要同非人的外在力量抗争。
故事开端便展现了一个孤独的形象,阿萨的父母双亡,妻子不在家,与亲戚好友关系往来较少,与同事关系疏远,被淹没如小山似的稿件堆里。阿萨善于自省,有强烈的自尊心,渴望稳定有序的生活,但在潜意识中充满了对失败的恐惧(幼年时失败的父亲造成的阴影)和对精神失常的隐忧(他母亲过世前精神失常)。虽然有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但作为犹太人,他总是感觉到不安全,即使在睡眠时,也觉得自己会受到威胁。“他一直担心突变已经到了,所有的好运都终止了,所有的恩惠都化解了”[11]79。他尽量少与他人往来,独善其身。
费夫尔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中指出,西方现当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导致理性常识化和“去道德化”,理性和常识观对道德情感领域的全面侵占,引起个体道德观念常识化与价值评价中立化,道德情感的中立使人失去独立评判的能力。《受害者》表现出,理性侵入了人类的心灵、情感等非理性区域,渗入人类社会日常行动和情感领域,削弱了人类情感,造成了对道德标准的践踏。喧嚣拥挤的生活空间,繁重枯燥的工作,压抑紧张的人际关系,消解了阿萨的真实自我和道德情感,接受了社会意识形态赋予他的社会自我,从而信奉一条非常理性的处世原则: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遇到什么事都是自顾自”,没有任何事情能诱使他化解自己[11]123。每个人都在重复着《圣经》中所宣扬的“为人人”,而实际上,却在“为自己”[11]159。
空虚乏味的生活中,阿萨唯一的乐事便是阅读妻子热情洋溢的来信和明信片。侄子米基生病打乱了他的生活,他不得不放下案头令他烦恼不已的工作,不得不去照顾弟弟的家人。雪上加霜的是,他竟然遭到落魄的反犹主义者阿尔比的责难、纠缠。阿萨诚实自省,相信通过个人努力能够取得成功。而失业的阿尔比则认为,靠自我奋斗出人头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个人被当做梭子拨过来推过去,无法战胜命运。于是他完全堕落为酒鬼,弄得家庭破裂、一文不名,直至流落街头,而他却责难阿萨致使他失业、毁了他的生活。这不仅增加了小说的深度,也使小说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从表面上看,阿尔比是受害者,实际上,真正受害者却是阿萨。小说虽按线性时间安排,但主要情节(阿萨与阿尔比之间的斗争)和次要情节(阿萨照顾弟弟家人)几乎同时展开,将阿萨置于一个复杂的道德困境,让他开始认识自我,思考人性、生活的意义和个人的价值等问题。贝娄设置了如此糟糕却又真实的情景,让读者从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开始逆向思维,来观察人们的感情生活[12]271,展现阿萨为“做自己灵魂的主人”而与非人化斗争的过程[13]96。通过自我反思,阿萨逐步认识到,也许在潜意识中,他是想报复阿尔比的反犹言行才冒犯了阿尔比的老板,有意无意地造成了阿尔比的失业。他从阿尔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激发了他内心的善良本性,使他克服了自己的傲慢和自尊。阿萨从厌恶、敌视阿尔比,转向认同阿尔比,帮助阿尔比,这种改变为阿萨的道德成长奠定了基础,最终使他突破社会自我,实现了道德自我。
阿萨的经历表明:当人们遭逢逆境、怀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时,要仔细看清楚身边的事,在我们能够造成变化的地方去找自己问题的原因,用内在的生活反抗外部环境,在自身寻找生命的意义。苦境或受难是贝娄为主人公认识自我、体现正义、道德和仁爱所设置的场景,便于主人公以“他者”为镜,在人身上寻找深度、奥秘和意义,自我主导,将灵魂从物质的容器中解放出来。人的改变取决于人的内在要求,为了在困境中活下去,人必须要乐观向上,存有希望。贝娄承认社会道德的败坏、人的脆弱,但依然肯定人的宏伟,相信基本的人性限制是道德的而非肉体的。只有超越自我,超越鄙陋的世俗,感召内心的光辉,跨越精神的荒漠,才能面对真实,扬善避恶,发现真实自我,达到心灵的平静。“贝娄的作品试图通过重新确认世人对道德的需求和对回归犹太人文主义的希望来重新确立社会的道德基础”[14]29。贝娄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体现出传统的犹太道德观,即个人向善的信念和道德意志的强化。
二、爱邻如己
贝娄对主宰现代文学的“荒原观”持批判态度。他觉得,虽然作家在现实地创作,却渴望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环境,突出人物行为的重要性,以展示着生活的魅力[1]13。现代社会的生存境况不尽如人意,但人不该屈从于环境的影响,只要我们关心他人、相信人类会继续存在下去,作家就有必要继续通过创作来展示在当今世界少有的、美妙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受害者》是其最具犹太文化色彩的小说,体现出贝娄对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来说,该小说“处理了犹太文化意义上的迫害和犹太人对于兄弟情谊的渴望”[4]30。
犹太教对人自身、邻人和人类精神生活现实性保持乐观主义态度,不仅相信个人能够在自身中实现善,而且认为,每个个体具有个体性,他在内心里与我亲近,是我的邻居和兄弟。阿萨的转变和道德提升是从他逐步学会关爱他人开始的。贝娄认为,作家应该运用想像力,表现人的价值,证明人的伟大[15]14-15,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一个个独立的细节,真实地讲述令作家感动,也会感动他人的情感、精神,传递正能量,展现对情感的坚定信念[10]10。当阿萨第一次看到阿尔比时,他没有认出阿尔比来。阿尔比看起来就像是马路上看到的酒鬼,使阿萨感到恶心。阿尔比的跟踪使阿萨意识到自己被挑选出来,成了某种“怪异、疯狂活动的目标”,“心里充满了恐惧”[11]31。阿尔比责难阿萨为了报复自己的反犹言行,在面试时有意冒犯了他的老板鲁迪格,致使他被解雇,这令极力保持头脑清醒的阿萨心乱如麻。但后来,在与阿尔比的接触中,他逐步放弃了对阿尔比的憎恨,改变了态度,开始同情阿尔比。第二次见到阿尔比时,面对浑身酒气的阿尔比,阿萨感到一阵恶心,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11]69由于阿尔比的不断纠缠,阿萨开始扪心自问,也许真是他有意无意地造成了阿尔比的不幸。阿尔比求他帮忙介绍工作时,他的态度已经变得和善了。看到半夜来找他的阿尔比,他突然间对阿尔比、他的面孔和身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切的感觉,一种他在动物园中就经历过的亲近感。他留宿阿尔比的那一晚,一个梦境令阿萨顿悟到,“人人都会犯错”,他感到洞若观火,如释重负[11]39。阿萨从阿尔比身上看到了自己,将阿尔比视为自己的“另一个自我”,因此,愿意帮他摆脱困境。当阿尔比告诉阿萨,若他妻子还活着,失败也不会如此令他伤心的,阿萨怀着哀怜之情瞅着大哭的阿尔比,并开始关心、照顾醉酒的阿尔比。而阿尔比更是通过种种手段试图接近阿萨。阿尔比偷配阿萨房门钥匙,随意使用阿萨的私人物品;通过偷看玛丽给阿萨的来信,来窥探阿萨的秘密;甚至带妓女回家,占用阿萨的床,以此来达到与阿萨的亲密接触。在与阿萨谈论创世纪中世界对人应负的责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爱邻如己时,阿尔比甚至称阿萨为“善良的老利文撒尔!好心的利文撒尔”[11]160,并承认,“我该受责怪。我知道。亲爱的!”[11]161最终,阿尔比洗心革面,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另外,阿萨在帮助远在他乡为生计奔波劳累的弟弟照顾侄子的过程中,他开始学会关心照顾他人,体会他人的感情和心情。刚开始,由于小侄子米基生病,弟媳爱琳娜求助于他时,他才去了弟弟家。渐渐地,他开始主动关心弟弟的家人,帮米基联系医生,说服爱琳娜送孩子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他还利用周末带菲利普去动物园和看电影。当他看到,为了照顾米基,爱琳娜身心俱疲,爱琳娜的母亲脚踝肿胀时,阿萨觉得难过极了,他开始同情爱琳娜,理解爱琳娜的母亲,对弟弟的不负责感到非常愤慨。对过早面对死亡的菲利普他充满了怜爱之情。当施洛斯伯格说,“缺乏人性不好,超验人性也不好”时[11]112-113,他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但现在他认识到,“‘人性’就是有责任心”[11]129。阿萨下班后,会跑两个小时的路去医院,为的就是陪米基十分钟。看到棺材里米基毫无萎缩或恐惧迹象的面部表情时,他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本来准备好劈头盖脸训弟弟一顿的,可看到弟弟痛苦浮肿的脸庞、廉价的西服、积满灰尘的皮鞋,他的低声哭诉让阿萨顿生怜爱,因此,他放弃了对弟弟没有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责任的指责和抱怨。小说最后,他将长期缺席的玛丽叫回家,这些均证明阿萨超越了自我,朝着爱护和关心他人的方向转变。
可见,贝娄偏离了现代主义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主题,即人的异化和人的无能,但他并不避开异化和绝望的生活状态,将人物塑造得仅次于天使——虽然外界的非我力量很强大,生活很悲惨,但他们至少具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各种羞辱、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他认为,为了活下去,受难和软弱也是有意义的,想像力能够揭示人的伟大;相信个人的存在就是爱,而作家的创作就是在展示他的爱[15]20,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爱本身证明了个人生活的价值。
三、社会责任
犹太教的乐观主义还表现在对人类的信仰上,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之子,他们由于共同的任务而被结为共同体。因此,对社区的信念是传统犹太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对生活的肯定是犹太文学的特色。贝娄作品中主人公最终走出异化状态,与他人妥协,与社会和解,表达了他肯定社区对个人的重要性和积极入世的生活观。
就像弗洛姆所主张的那样,人必须顺从伦理、道德和良心等理性的权威,在与他人的相处中求同存异,在主动、负责的参与行动中,获得自我身份感,发展自己。贝娄将犹太人阿萨置于一种伦理困境中,犹太人信仰上帝、人自己、邻居和人类,而且每种信念都包含着责任感。因而,阿萨负有三重责任:对上帝的责任、对邻居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在满足上帝对人要行善的道德要求的同时,他必须平衡其中的两种责任——他对他人的责任和他对自己的责任,也即,他要平衡他对科比的责任和他对自己应有的道德责任。贝娄作品中的人物,虽处于费弗尔所谓的个体 “生存的去责任化”的“后情感主义”的西方现当代社会,但阿萨通过反思自我、思考人生,在与他人的摩擦和冲突中,认识到他人同样具有和自己一样的个体精神性和个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并积极地转变观念,从对别人的漠不关心,开始关心爱护他人,显现了其个体性和通过伦理道德选择展现了其善良本性,发现了自己灵魂的价值,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信仰自己、信仰他人,形成人类生活具有同一性观念,一个人的自我和他的同胞的自我才会相互关联[7]75。
贝娄一生皆视言说这些精神需求为己任,他笔下的人物与外界进行思想斗争中,体现出善恶共存、人性本善、通过“爱人类”来建立“共同体”的信念。他们一方面要求付诸行动,与他人交往和积极入世;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安静、沉思默想和孤独。他们以自己的内心感受和自我意识为向导,不断地修正自我,努力在鄙俗的现实中寻找共同人性的迹象,最终通过喧嚣到达宁静地带,获得精神慰藉,找到心灵的归宿。贝娄的作品告诉人们:对每一个人来说,“存在都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的多样性“有着某种意义,某种趋向,某种实际价值”,使人们对于“真谛、和谐以及正义有了指望”[13]97,希望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四、结束语
20世纪前半叶,战争的血腥和生活的动荡,使得评论界向“一切同一性开战”,宏大叙事遭到拒斥,怀疑论取代了赋予个人生活以超验意义和目的的宗教。“上帝死了!”世俗主义成为主流,而贝娄却在作品中塑造着找寻赋予他们的精神生活以意义的人物。贝娄拒绝体认现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丧失和生命意义虚空的观点,他的小说主人公均在去人性化的社会环境中,努力从普通生活中寻找人性、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可能性,抱持个性、道德完整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维护个人尊严,表现出对个性、人性和爱等传统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坚守,承载着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虽然贝娄的主人公多为犹太人,但贝娄的小说既包含了丰富的犹太文化元素,又超越了狭义的犹太性,主人公最终从异化走向与社会的和解,达到内心的平静和平衡,肯定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贝娄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性、个体价值及生活意义的探讨,体现出贝娄宽厚的人文情怀,他的作品注重人的精神品性、主张个性、爱人类、执守道德标准,反映出他亲近社会的伦理意识和对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的礼赞。
[1]Gordon Loyd Harper.Saul Bellow[C]//Earl Rovit.Saul Bellow: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75:5-18.
[2]Robert Penn Warren.The Man with No Commitments[C]//Harold Bloom.Saul Bellow (Modern Critical Views).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9-12.
[3]John Farrelly.Among the Fallen[C]//Gerhard Bach.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5:30-31.
[4]John J.Clayton.Saul Bellow:In Defense of Man[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5]Malcolm Bradbury.Saul Bellow's The Victim[C]//Gerhard Bach.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5:32-41.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7](德)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M].傅永军,于 健 ,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8]Saul Bellow.“The Writer as Moralist”[J].Atlantic,1963,(Mar):58-62.
[9]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6-24.
[10]Robert Boyers.Literature and Culture:An Interview with Saul Bellow[J].Salmagundi,1975,(30):6-14.
[11]Saul Bellow.The Victim[J].New York:Penguin Books,1947.
[12]Matthew C Roudané.An Interview with Saul Bellow[J].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84,25,(3):265-280.
[13]Saul Bellow.It All Adds Up:Fro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M].New York:Viking,1994.
[14]祝 平.索尔·贝娄的肯定伦理观[J].外国文学评论,2007,(2):27-35.
[15]Saul Bellow.Distractions of a Fiction writer[C]//Granville Hicks.The Living Novel.New York:Macmillan,195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