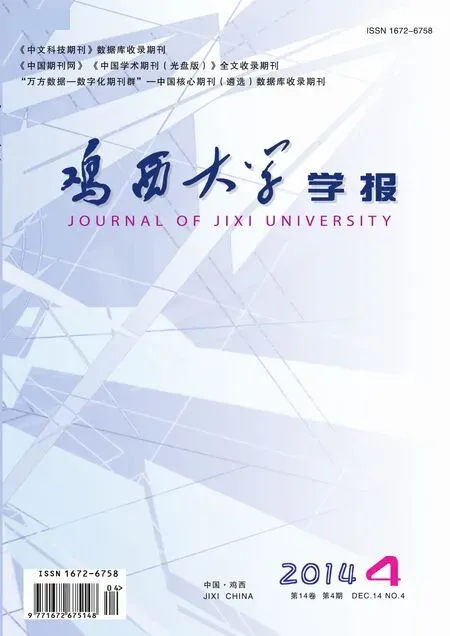《特别响,非常近》的创伤解读
杜 珊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作为美国当代文坛的新秀,《特别响,非常近》是其第二部长篇力作,该小说讲述了九岁小男孩奥斯卡在“9·11”事件中不幸失去父亲后偶然从其遗物中发现一个写着“布莱克”的信封和一把钥匙,于是便开始了不停寻锁的旅程。通过寻找,他走进了历史和背负着创伤生活的各色人物的世界。关于此部小说的解读,前人多从儿童文学视角出发,本文则旨在从创伤理论来解读小说中各人物的创伤体验,揭示受创者的心路历程。
创伤不仅指真正病理意义上的创伤,也指类比意义的创伤。当代创伤研究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创伤经验从精神学分析上是指特定经历某些灾难性事件而使心灵遭受强烈伤害,甚至是心理发展过程中驱赶不散的阴影。[1]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伤研究繁荣发展,美国学者卡西·克鲁斯在她的《沉默的经验》中首先提出“创伤理论”这一术语。她将创伤定义为“主体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这种突如其来的裂口阻止了心灵全面认知创伤事件”。[2]当代欧美创伤理论者主要的关注点是创伤的真实再现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记忆颠覆和揭示边缘群体真实创伤历史的功能,以及如何帮助人们从创伤中复原。[3]本文将着重从创伤再现、创伤记忆与历史以及创伤复原三个方面来解读《特别响,非常近》中主人公及各色人物的创伤。
一 创伤再现
创伤记忆不像普通记忆一样以文字的、线性的叙述被编码,它缺乏语言叙述和语境,通常被以栩栩如生的感觉和形象来编码。[4]文学的言辞表达仍然是使创伤得以感知、使沉默得以听见的基础,因此书写成为创伤再现的主要形式。[5]创伤书写主要是表现创伤的展演,即受创者的创伤症候及其影响。创伤经历在受创者心灵不断回闪,迫使受创者产生不同的症状如情绪情感障碍、重复强迫症、失语症和自闭症等。克鲁斯指出,伴随创伤而来的情绪包括责任归因产生的自责和愤怒等各种情绪情感性障碍。年仅九岁的奥斯卡亲眼目睹了双子塔的倒塌,父亲的突然离世给其心理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幼小的他倍感焦虑,彻夜失眠,也开始害怕各种噪音,怕坐地铁,怕高楼,怕电梯等。寻锁之旅中住在卡罗纳一栋公寓9E的A·布莱克希望奥斯卡可以上楼,但奥斯卡说:“我不能上去,因为你在九楼,我不能上那么高,不安全。”奥斯卡在纽约不停地寻找不同的布莱克,不停地给不同的人写信,反复幻想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发明,总爱穿着沉重的靴子,还不停地自虐。创伤经历来得太快以至于奥斯卡不能全面地认知它,因此他会不由自主地重复某些行为企图由此化解创伤。因在二战的德国德累斯顿大轰炸中痛失亲人的奥斯卡祖父老托马斯·谢尔患上了失语症,依靠左手写YES右手写NO来与人交流。这一经历造成祖父内心巨大的创伤,他痛恨自己:“在我或许能够挽救她和孩子或者至少和他们同归于尽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安娜”。[6]失语既是他的无意识机制对抗可怕灾难记忆的结果,也是他拒绝忘却过去的体现,就像祖父写到:“我试图不去记住那个我不想失去但还是失去了而且还不得不记住的生活”。除此之外,小说中的老布莱克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见证了不同的战争,妻子死后的24年来他不曾下楼,拒绝戴助听器,自此患上自闭症,战争的创伤不仅折磨着他的心理健康也打乱了他的正常生活。
在创伤的展演中,创伤的影响不仅打破了主体对周围世界的认知能力,还粉碎了受创者得以与他人交流和维持关系的自我架构。小说中各色布莱克们过往的人生里都经历过不同的创伤事件,使他们孤独无助,缺失交流。奥斯卡一家沟通也变得困难:祖父通过简单的手势将交流降到最低;母亲看到奥斯卡身上的四十一个伤痕,但是什么都没有说。此外奥斯卡还遭遇了身份危机,周围人对奥斯卡的看法也反应了这一点。在同学们眼中奥斯卡是“怪异的”,在心理医生眼里他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在世纪老人布莱克的卡片库里他是“儿子”。[7]创伤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伤害,给受创者造成深深的压抑甚至威胁自身存在的感知,从而陷入自我缺失的身份危机中。
二 创伤记忆与历史
罗斯在《讽刺者的牢笼——记忆、创伤与历史的建构》中曾讨论过历史叙事与创伤记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想要弄明白人们如何建立起与过去之间的联系,就要重点分析历史记忆。创伤作为追溯历史痕迹的一种独特而合适的方式,也是呈现我们与过去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特别响,非常近》中主人公一家及其布莱克们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灾难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通过展现创伤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小说表现了当代主体所遭遇的创伤,也肯定了历史的客观存在。受创者的创伤记忆就是历史的显现,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受创者面对创伤形成的心里防御机制使他们在本能上意欲规避创伤历史,慰藉受创的心灵。然而,创伤在现实生活中的持续影响迫使受创者在历史叙事中表现创伤的展演,这也启发我们在历史背景的帮助下探索创伤的原因,战争、灾难作为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之一,是不容忽视的。
小说中对德累斯顿大轰炸文本记录就是通过历史的见证人祖父的创伤记忆完成的。在大轰炸前夜,他刚获知女友有孕的喜讯,而厄运却转瞬而至,轰炸时的情景像画面一样清晰地存留在祖父的记忆里,令人心生畏惧:“燃烧着的猴子在树上哀鸣,翅膀着火了的鸟儿在电话线上歌唱;腿和脖子到处都是,我看见人融化成一池浓稠的液体,我看见人体像灰烬一样脆裂,还有成群人的尸体;从楼房的坍塌中,我听见了沉默婴儿的咆哮;晕头转向的动物在痛苦和混乱中哀嚎”。[6]大轰炸带来的死亡与毁灭给其身心留下巨大的阴影,以至于长达几十年的创伤记忆长期压抑在心中。除了老布莱克、老托马斯等灾难见证人外,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经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采访录音中日本女性幸存者一直在讲女儿死亡过程,不禁令人唏嘘:“她的伤口里有蛆,还有一种浓稠的黄色液体,她的皮肤在脱落。蛆从她全身上下爬出来。九个小时以后,她死了”。[6]她将个人创伤从宏观历史中展现出来,像她所期盼的,“如果每个人都见过我见过的,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战争”。201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将人类灾难推向新的高峰,作为该小说的故事背景,这一悲剧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双子塔的倒塌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这是人们经历它的方式,也是人们铭记的方式。小说中奥斯卡作为“9·11”事件的见证人,其内心的创伤记忆也是对这一历史的展演。
三 创伤复原
创伤经历受到意识的压制潜伏在潜意识层面,无法言说无法知晓。当潜意识里的创伤记忆上升到意识层面,由内在记忆转换为外在现实时,创伤记忆才可以转化为受创者可接受的意识,最终达到复原。根据心理学研究,创伤复原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加强安全感,让受创者坚强面对创伤体验。第二阶段,恢复受创者的记忆,将对创伤的痛苦体验表达出来。第三阶段,重建受创者记忆,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软环境,使受创者回归正常生活。
首先,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创伤复原的基础,给他们创造一个认同其创伤经历的安全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受创者可以将自己的创伤经历讲述给倾听者,倾听者可以帮助受害者将潜意识的创伤记忆上升到意识层面,重新对创伤经验进行评价,使自我重现。小说中,老布莱克、威廉和祖父等都是奥斯卡的倾听者。当奥斯卡发现威廉由于跟自己同样的原因,即没有在父亲临终时跟他道别而备受煎熬时,他感到了人心的相通,并且选择向他倾诉深埋已久的秘密,向创伤复原迈出一大步。“他不断重复说有人在吗?电话响啊响,而我却动弹不得,他需要我,而我却不能接电话”,在这一倾诉中,奥斯卡把内心深处的伤痛展现出来直面创伤事件。另外,奥斯卡在与布莱克们接触的过程中,也倾听着他们的回忆,布莱克们不仅重新面对自己的创伤,并且与奥斯卡互相关怀,一起走向复原。其次,创伤叙述作为复原的一个必要过程,它帮助受害者直面创伤记忆并与外界取得联系。因此书写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这一行为有助于宣泄自我痛苦,统整自我意识,给幸存者与他人联系的机会。奥斯卡喜欢阅读霍金的《时间简史》,不断地给霍金及其他人写信,双向的书信往来也帮助奥斯卡走出创伤。霍金的最后一封回信中写道:“这个时刻是这么美丽,太阳正低,疏影正长,你要再过五个小时才会醒来,但我不禁感觉到,我们正在分享这个清爽美丽的早晨”,[6]这昭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的开始。奥斯卡还自己随身带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一记录簿,它收集了在奥斯卡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种书写叙述中,受创者心中的创伤得以释然。此外在创伤中受创者的自我被毁灭,信念被动摇,因此重建自我很重要。奥斯卡从起初不理解母亲的漠不关心到最后了解事实后的恍然大悟:“我的搜寻之路是妈妈写好的剧本,当我开始的时候她已经知道结局了”,与母亲相拥而泣,在母亲怀抱里,他的身份得到重新建构。
本文揭示了小说中人物从创伤再现到创伤复原的历程,这一历程既是创伤研究者强调的“从哀悼到展望明日”的经历,也是主体从自我走向他者的过程。创伤理论为人类了解自身心理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文学评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通过解读创伤理论,有力地揭示了小说中的创伤,其发出的警示之声不但“特别响”,而且离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近”。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灾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是无法抹去的,但是我们应该在创伤中反思、成长,积聚力量,这也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身边的创伤群体,帮助他们走向平静的恢复之路。
[1]Freud, 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M].London: Hogarth Press, 1962.
[2]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师彦灵.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 兰州大学学报,2011(3).
[4]朱蒂斯·赫曼.创伤与复原[M].杨大和,译.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
[5]Hartman,G. Trauma Within the Limits of Literature[J].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003.
[6]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特别响,非常近[M].杜先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曾桂娥.创伤博物馆:论《剧响,特近》中的创伤与记忆[J].当代外国文学,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