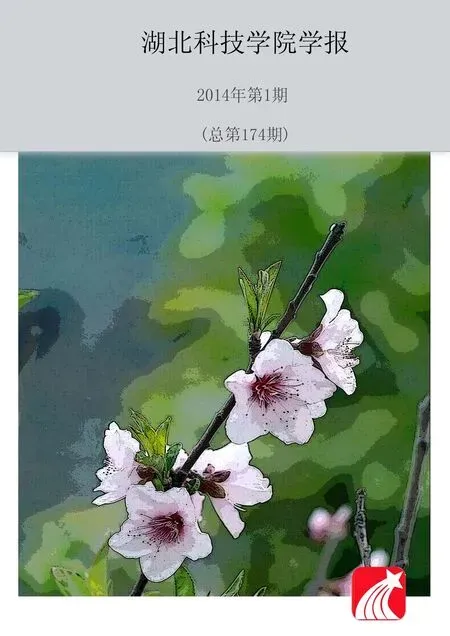司马迁《史记》历史叙事的今文经学视野*
丁凯旋
(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9)
*收稿日期:2013-10-02
今文经学是西汉时期主导型学术样态,也属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由于秦汉之际错乱的政治世事,致使先秦时期开放的学术局面趋于黯淡乃至消逝,至西汉初年,由于先秦诸子典籍失佚,遂产生了以口耳相传为学术范式的儒学样态,称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学术旨趣和文化模态,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最具代表性。作为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跻身于官方学术体系之中,并通过将孔儒学说中的伦理纲常理论作系统化、教条化的义理阐说,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专制制度提供意识形态理论话语支持。由于今文经学的内在理路和精神旨趣与先秦孔孟学说具有天然的血统联系,因此也造成了今文经学的内涵与发展印有鲜明的孔儒理论烙印。承袭阐发孔儒学说,努力服务专制集权,是今文经学的第一要义,这也是其最终成为官方学术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
今文经学另一大特点便是排斥其他诸家思想,独尊儒学。在西汉初年,并不以儒术为然。文景两朝治国为政,杂糅各家,以黄老为主。汉武帝祖母窦太后,更是偏爱黄老,不容他人非议。直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问世,才得以让儒术享有尊崇之势。“天人三策”之第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以儒术为天道之正说,进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今文经学的使命。
今文经学的这两大特质,同样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著述。在《史记》的历史叙事中,司马迁承袭了今文经学宗法孔孟之道的原则,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以孔子的伦理标准,诉诸道德评判。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道德褒贬黑白分明。承袭孔儒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司马迁的历史叙事,人们从中无法窥测到历史发展的真正进程。人们看到的是成王败寇的历史审判,其中忠奸善恶曲直分明,胜利者英明至圣,失败者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后世唾弃。至于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的人文立场更是难以看到。其次,在《史记》中,鲜有先秦其他诸子思想言说的记述,庄子的自由诗意、杨朱贵己、墨子兼爱的济世意识,公孙龙的形而上思辨哲学,都没有了踪迹。人们看到的是以孔儒为核心的话语世界,先秦诸子百家自由、开放的人文精神光谱,删除殆尽。司马迁和其他今文经学家们一致努力,把孔子推到历史的制高点,成为中国文化的至尊。后世之人,只知孔孟之辈,鲜闻其他思想,即使略闻一二,也早已删改的面目全非。
司马迁承袭孔儒思维的著史意识,使其面对殷周剧变之际的那段历史茫然无识,同样诉诸了黑白分明的道德审判。代表正义的一方,当然是姬氏家族。于此相对的是,商纣王的暴虐无耻。武王伐纣,因此也就被描述成正义的姬昌战胜了荒淫的纣王。这种简单平面化的历史刻画,使得司马迁无法面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剧变。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2]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商周之交的历史剧变。“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西土” ,[2]这句更具微言大义,道出了周室的姬氏家族并非上华夏上古文明的正宗承传者。因此,“殷、周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而周制与殷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周以前,中国原本是一个诸侯联盟的联邦国家,而殷商只是作为诸侯之长而联系各诸侯国,那时的天下不是某一家族的私产,作为诸侯之长的殷商和当时各诸侯国的地位是一样的,因此文王在征伐殷商的战前动员中,才会称呼各诸侯国为“友邦君”。然而这一切在姬氏家族的那场伐殷战争中毁灭了。与殷商及殷商以前的文化政治制度相反,姬氏家族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并创制了与华夏上古文化迥然相异的文化模式。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在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弟子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2]姬氏家族不仅使天下变成了姬姓,而且实施了一系列与专制集权相匹配的文化制度,即周公的“德治”。“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2]周制文化的内涵便是通过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使天下成为姬氏家族的“家天下”。因此,姬氏家族征伐殷商的战争,灭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有殷商背后的华夏上古文化。
华夏上古文化,以生命的无言无为为旨归,于此相对称的国家形态是小国林立,那时人民浑朴自由。至周,这一切完全改变。小国寡民变成了中央集权,自然无为变成了尊尊亲亲,自由变成了等级,无为而治变成了人治,政治伦理化,道德政治化,这一切都在姬氏家族“不可示诸于人”的贪欲中完成了。
而姬氏家族的这场伐殷战争,也鲜有正义可言,这是姬氏家族四代人共同策划努力实现的。
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3]。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3]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子发立,是为武王。[3]
周公在武王死后,对武庚的讨伐,不惜杀死自己的一胞同足: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4]
面对殷商遗民群饮,周公则暴力镇压: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4]
连年的征战和暴力镇压,使周朝和周制最终得以建立。而在司马迁的笔下,则是一边倒地通过突出商纣的暴虐来彰显武王的英明与正义。这具体体现在司马迁与《尚书》截然不同的商纣罪名的编造上。
在《尚书·太誓》中“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4]《牧誓》中“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4]从武王在战前动员中所表述的纣王罪名则是听信妇人之言。而来自殷商一方的大臣如祖伊“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4]如微子启“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4]两位殷商大臣对纣王的指责也不过是“淫戏用自绝”、“沈酗于酒”。后来周公在《尚书·酒诰》中也证实了殷商两位大臣的说法“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4]综合双方对纣王的指责来看,纣王之过不过酒色而已。然而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则变成了:
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勣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於是纣乃重刑辟,有砲格之法。[4]
这与伪古文尚书里对商纣罪名描述如出一辙: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4]
由此可见,受制于今文经学的司马迁在《史记》著述中,由于承袭孔儒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观念,对历史的叙事充满了偏狭的道德审判。司马迁受制于今文经学的另一表现,便是在《史记》中,将先秦开放、多元、丰富的诸子人文思想光谱,删剪成以孔儒学说为中心话语的简单图景。先秦,是个众语喧哗的时代,没有任何中心话语可言。孔丘学说,只是众多诸子话语中的一元,而且颇受奚落。然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却不见其他诸子踪迹。且不说其他,连孟子都承认,“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5]然而杨朱、墨翟之言说在《史记》中完全阙如。崇尚贵己的杨朱,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位高扬人的权利的大家。其“迫生为下”所高蹈的人的尊严意识,即便在当下都有极大的人文意义。墨翟,类似于基督的伟大行者,其强烈的兼爱平等意识和反战意识,更是弥足珍贵。在先秦,庄子逍遥的自由立场,公孙龙白马非马论的形而上思辨,和其他诸子一同组成了华夏文明浩瀚的人文思想谱系。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宁愿将孔子与帝王并列,将孔子弟子编排到列传之中,也不愿将更为绚烂的其他诸子思想留下历史印记。这与其说,司马迁历史思维过于偏狭,不如说受今文经学影响太深。
由于先秦以前的历史记载过于稀缺,《史记》便成为我们研究先秦、西汉初期历史的重要媒介。然而司马迁过于受限今文经学,致使其历史叙事充满偏狭和简单,不具有较为客观的历史视野和较为独立的人文立场,从而也使得其历史叙事留下巨大的缺憾。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8):561.
[2]王国维.王国维集(第四册)[M].周锡山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郭仁成.尚书今古文全璧[M].长沙:岳麓书社,2006.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