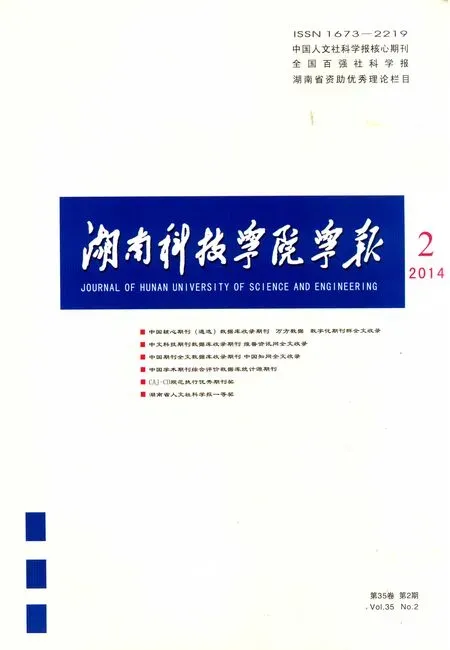狂欢化的刑罚与变异的权力——《檀香刑》的主题意蕴
赵先锋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莫言残酷的天才禀赋,奇诡的想象力和汪洋恣肆的文笔常常让人惊叹不已。小说《檀香刑》鬼斧神工地展示了一个令人悸动震撼的世界,桩桩酷刑和使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令人在阅读的快感中伴有生理上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颤栗。作家不厌其烦地抒写着酷刑的历史和血淋淋的场面,透过刑罚狂欢的喧闹场面,折射出人类对权力的迷恋和对古老文明掩饰下国家专制权力体系变异下轰然崩溃的尖锐审视,体味对我们古老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批判立场。
一 刑罚与狂欢
莫言在《檀香刑》中有意避讳知识分子一贯使用的话语的修饰和表达习惯,抛弃了美和丑、善良和恶毒这样简单的二元比较,表现出了对和错、美和丑模糊不定、难以分辨的情况。作家自始至终以极端欣赏的姿态对惨不忍睹的酷刑过程作淋漓尽致的精细描写,行刑者的技艺日趋炉火纯青,行刑的场面也越来越壮观。小说对酷刑的观赏性场面描写详尽,充分刺激了统治者的观戏欲,也刺激了统治下民众的好奇心,趋之若鹜地奔赴刑场去看“一场华美的仪式”。
《檀香刑》“实际上是一场大戏,刽子手和犯人的联袂演出”,这场大戏“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们邪恶的审美心”。所有人似乎都抱着一种邪恶的心理期待,犯人若现出孬种相,看客们就精神振奋鼓噪加油,让他扮演一个英雄好汉,从欣赏同类的痛苦和恐惧中获得某种快感。在书中第一个刑罚场面中,刽子手若活儿做得不利索,就犹如一个名角唱破了嗓子般让看客失望,人群就喝倒彩起哄甚至愤怒出现要把刽子手活活咬死的奇特狂欢景观。赵甲的师傅余姥姥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三纲五常的仁义道德,另一面却是嗜血纵欲的男盗女娼。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前来观刑者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烈女,面对被刀脔割着的美人的身体,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刺激看客们虚伪的同情心,满足着内心见不得光明的邪恶的审美心,刽子手消灭的是人的肉体,而看客们虐杀的则是人的精神。其实观赏表演的人比执刀者更为凶狠冷酷。这也正印证了鲁迅揭示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的真相:“暴君的臣民,只愿意暴政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的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啊呀’,活的高兴着。”[1]P366
书中刑罚最极致的狂欢高潮是檀香刑的实施场面,以援救孙眉娘为序幕,这场乞丐们“叫花子节”狂欢声势浩大,秩序颠倒。他们涂脂抹粉盛装异服,唱着猫腔在县衙前游行,典型化的颠倒调唱词和杂乱铺陈的场面蕴涵了狂欢化的精神特征。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奇特的狂欢式景观在狂欢节时空中遵循“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对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产生一种颠覆作用,而诞生了一种消除等级的平等对话。[2]P3
孙丙被押在囚车里奔赴刑场的游行场面描摹将狂欢化表演进一步推向高潮,如同阿Q临刑前努力想把圆圈画圆一样的心态,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演出,他将自己想象成威风浩荡的岳飞将军,边走边唱,鼓励乡亲们揭竿而起保家卫国。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学猫腔调为他唱和,杀气腾腾的刑场变成万猫嗥叫、百兽率舞的天空,场面气势恢宏浩大,弥漫着反抗的情绪和色彩,袁世凯等强权统治者皆被吓得面如土色。他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中引吭高歌,引得高密东北乡的猫戏班子在升天台对面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刑场大戏,万众若狂,情绪亢奋的看客和表演者都沉浸在癫狂、狂欢之中置生死于度外。莫言就是这样用夸张的手法和戏剧化的文字将刑场行刑狂欢化、戏谑化以解构权力,刑场是权力专制顶峰的舞台,是毁灭死亡之所,而看客们的出色表演,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狂欢节庆典,法律被颠倒,权威受嘲弄,罪犯成了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3]P61
二 权力的变异
在专制社会里,酷刑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罪犯的惩罚,更是以儆效尤,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在行刑过程中展示给民众的是专制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让权力对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威慑,以便做顺民和奴隶。公开处决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无论是满清的咸丰、慈禧,还是袁世凯,甚至是德国总督克罗德,统治者之所以极尽刑罚之能事,无非是显示强权对围观者的震慑和控制,以实现杀一儆百巩固权力的意图。刑罚以肉体作为政治权力的演练对象,在狂欢恣肆的外表下隐喻着统治阶级近乎疯狂的残暴专制本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有过这样的揭示,“残暴是一种机制的固有现象,这种机制在惩罚本身的中枢产生可见的犯罪真相,真理——权力关系,始终是一切惩罚机制的核心”[3]P67。当真理一再被权力淹没或遮掩时,也就昭显了权力本身的畸变和衰落之势,暴露了这种极权的异化本质。
巴尔扎克曾说人物是他们的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就了一批刽子手这样病态而扭曲的人物。他们执行各种酷刑的同时又是全身心的欣赏者,在欣赏着自己的技艺中感受着自身“价值”的表现。刽子手赵甲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更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创造的专家。他年少孤苦,阴差阳错地入此行当,却不料成了一个被体制化的杀人工具。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
这样的一个人,本质上就是一个借助专制统治的权威来迷恋权力的国家统治牺牲品,赵甲把一份历来被众人所鄙夷的职业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工作就是为了配合专制者对他的臣民的统治,也为了迎合专制君主和大臣们的欢心。他将涂上鸡血后的自己视作国家权威的象征,他瞧不起技不如己的刽子手,他甚至瞧不起那些正宗科班出身的朝廷命官:“其实,你干的活儿,跟我干的活儿,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办事,替皇上效力,但你比我更重要。”刘光第感叹道,“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百条律法,最终还要是落实在你那一刀上。”[4]P258更重要的是他疯狂地迷恋权力,在袁世凯面前骄傲地说:“小的斗胆认为,小的下贱,但小的从事的工作不下贱,小的是国家威权的象征,国家总有千条律条,最终还要靠小的落实,为盗杀人,于理难容;执法杀人,为国尽忠。”[4]P114
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刽子手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法律的化身,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刽子手的敬业精神暗合了统治者的权力意志需求。正如福柯所言,人体在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后变得顺从、配合、灵巧、强壮。权力的增强了人的才能,同时又使它变得更加驯服。这是一批病态而扭曲的人物,在执行各种酷刑的同时又全身心地自我欣赏,感受着自身的“价值”表现。赵甲本质上是借助专制统治的权威来迷恋权力的国家统治牺牲品,他却把一份历来被众人所鄙夷的职业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自己当作当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认为自己拥有统治者所授予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力,他甚至瞧不起那些正宗科班出身的朝廷命官,在犯认为人面前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是大清的法律之手。在他的心中,执行各种非人的酷刑,倒成了“正义”之举,从而达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目的,而且刽子手对犯人最大的怜悯就是把活儿做好,你如果尊敬他,或者爱她,就应该让他现出来的技艺表现出来。
他希望朝廷把刽子手列入刑部的编制,按月领取份银,他希望朝廷能建立刽子手退休制度,让刽子手老有所养,不至于流落街头。他还希望建立刽子手的世袭制度,使刽子手这一古老的行业成为一种光荣,他为了维护权力地位,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如何残酷地折磨犯人上,他名义上替国家执法,但内心时刻想着个人私利,为国家执法成了一种赚钱与捞名兼得的正道。
实施檀香刑一石三鸟,不仅可赚的丰富的钱财,而且可获得非同一般的名声,还能改变儿子和家庭的命运,实现刽子手的世袭,他一心想将儿子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不遗余力地向儿子灌输“杀猪下九流,杀人上一流”的思想,并且在执行檀香刑的过程中开导训练儿子。赵甲看似关心儿子爱小甲,实则不爱,他只是想让自己的手艺、事业能够后继有人,通过血缘关系巩固自己的事业,通过世袭制度来提高刽子手职业的社会地位。这种没有职业道德的权力迷恋,无异是对刽子手权力的异化。
书中另一主要人物知县钱丁代表着朝廷专制机构的权威,他竭力维护着朝廷的尊严和权力,娶“冷冰冰”的妻子而终不敢言弃,仅仅是因为其妻子是曾国藩的外孙女,代表早已仅存逝去的权力符号;当赵甲依仗慈禧所赐的椅子这个权力的代码令其下跪,钱丁后发制人,打掉赵甲的两颗牙来维护西花厅的威严;疯狂的钱丁最后希望借助于赵甲的特殊身份,不惜牺牲孙丙的生命为代价,妄图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权力存在的意图,更是权力对其赤裸裸的异化。
赵甲和钱丁都是为封建专制统治者服务的,本身都是国家的政治工具,统治者希望通过刑罚的过程来重振被犯人冒犯的权威,然而封建专制的神圣权力用在观赏犯人受刑舞台上,提倡极致残忍的刑罚——檀香刑,这是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变异权力后的最终产物,作家正是从刽子手这一血淋淋的职业中剖析着封建专制的扭曲和病态。
三 权力的崩溃
可以说自古以来,刑罚与权力紧密结合,国家统治者利用权力通过刑罚这一特殊手段来儆戒民众,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建立统治者的权威。在原始社会我们靠追捕猎杀同类彰显个人的生存权力;在封建社会民众靠围观反叛者的受刑场面分享君主生杀予夺的特权,宣泄权力以维护个人或国家意志。《檀香刑》却通过中国传统刑术文化,揭露其内在的权力颠覆和崩溃。那些刑术已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意义,更增添了一种草菅人命的随性和荒诞,沦为统治阶级以生命取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民众调剂贫乏生活激活内心残酷的特殊庆典。刑罚所体现出来的真实意义,某种程度上是对法律本身的嘲讽和消解,更是对权力变异带来必然崩溃后果的责难和诘问。
莫言以刑场为纽结点,以猫腔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汹涌的殉道精神,打开了民众愤怒的出口,使得沿袭数千年的封建皇权出现了病态化的变异,表明刑罚这个极权的政治代码,在维护社会机体正常运转的权力演变中逐渐变异为统治者自行取乐的病态手段,从而展示权力体系的即将崩溃。刑罚场面狂欢化的奇异景观,是作家以狂欢化的方式来颠覆神圣的权威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而狂欢后原本的正常人因过分迷恋权力而最终异化为国家的行刑工具,成为了史上最残忍刑罚檀香刑的主角。
檀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是一种高贵气质的象征,是高雅文化的喻体,却成为小说中空前绝后刑术中的重要道具,所以连忠实封建统治的钱丁也感到不可思议,并愤愤骂道:“谁见过檀香橛子把人钉,王朝末日缺德刑。”这种刑罚无疑暗示一种权力体系的腐朽崩溃。封建专制权力力图构建文明秩序,绝不应该依靠残忍刑罚以恶制“恶”来威慑,因为文明的终极本质就是为了恢复人类应有的尊严,让生命回到自由、平等、关爱的理性层面上来,绝不是以某种近乎麻木的癫狂形式,来标榜某种极权专制的威慑力量。
中国什么都落后唯有刑罚最先进,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作品借德国总督克罗德之口说出了中国刑罚的实质。能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后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这是中国专制铁血政治的真实内涵的绝妙反讽。在“钱丁恨声”章节,他对大清朝的皇权体制也有十分清醒的认知,太后擅权而皇帝傀儡的阴阳颠倒,雄鸡孵卵而雌鸡司晨,整个统治阶层呈现出非正常黑白混淆状态。他很清晰地意识到小人得志、妖术横行的社会现实,发出这大清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的慨叹。
残酷的刑罚扑灭不了人们奋起反抗的怒火,反而加速专制统治的崩溃。两丈高的木头高台,三班轮倒的精兵护卫,将刑场装扮得庄严肃穆,可在实施世所罕有檀香刑的宏大刑场这一最能体现神圣国法与统治者权威的地方,作家将赵小甲塑造得如同“狂欢节文化”中的小丑,对其进行了致命的颠覆与消解。他“嚼着烫嘴的油炸鬼,腮帮子鼓鼓的,满脸的喜气”;他“嘴里哼唧着‘爹,俺要吃肉’”;他“想往他的老婆那边去,去摸摸她的奶,去嗅嗅她的味。”更为滑稽的是半生不熟的油炸鬼撑得他肚子一夜发胀,连环屁发与小山子的臭屁让最庄严最肃穆的刑场场面变成了最丑陋最肮脏不堪的调侃。
当然,酷刑是个华美的仪式,整个大戏似乎都在等待着最精彩的奇异高潮。莫言通过屠刀碾压的亲情,把抗德英雄孙丙在残酷的背景下像浮雕一样凸显出来。整个刑场的万人狂欢场面,如泣如诉的悲凉不绝于耳的背景音乐,都成了孙丙的生命告别演出。在刑场的以庄严的刑场做舞台、在神圣的升天台下唱猫腔戏、引起千万的民众的共鸣,从而掀起民间大狂欢的举动更是惊世骇俗标新立异,义猫对知县的劝喻置若罔闻,这是过于“嚣张”的危险之举,有向统治者和行刑者挑衅的嫌疑,[5]P55充分表达对刑罚的讽刺和对皇权尊严的嘲弄,就连孙丙奄奄一息的肉体都表现出了对强权和刑罚不屈不挠的蔑视。“知县绝唱”一章,当钱丁看到夫人遗书的自白后,终于反抗以杀死孙丙为手段,宣告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最终崩溃。在小说的结尾,孙丙短短的呓语“戏……演完了……”,如同华美乐章的戛然而止,彻底把已经成为病态的变异权力体系送进了历史的坟墓。如同谢有顺所说,英雄的血或许就是使更多人从屈辱、闭抑、奴隶的生存中觉悟过来,该付的沉重代价。[6]P26
《檀香刑》以神来之笔,如庖丁解牛般恢恢乎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和人性之间,快意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行刑之上的权力、历史的幽深晦暗。[2]P27他的刑场行刑文字更是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无所不用其极,调动一切的感官感觉,通过对不同残酷的刑罚和鲜血淋漓的受刑场面的描写,展示了变态生命体验下的狂欢景致,透过赵甲钱丁等人对个人权力的变态迷恋和国家专制权力的颠覆这些非常态的社会现象,审视了古老文明掩饰下的权力变异和权力体系的崩溃,并以此获得暴力之外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1]鲁迅.暴君的臣民[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张伯存.挑战阅读[J].当代作家评论,2001,(5).
[3]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
[4]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5]赵云洁.众声喧哗悲唱民族哀歌——论莫言《檀香刑》中猫腔的艺术价值[J].昭通学院学报,2013,(2).
[6]谢有顺.当死亡比活着更困难——《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J].当代作家评论,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