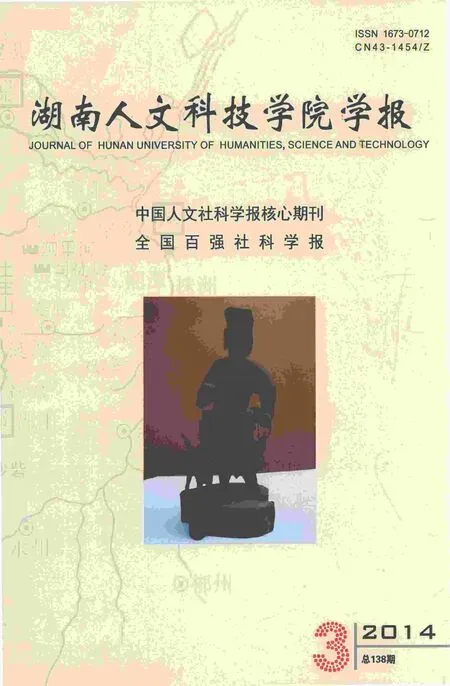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不同阶段风格的比较与分析
郭思遥
(私立华联学院音乐表演系,广东广州510663)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生于德国波恩,是德国伟大的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其作品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被世人尊称为“乐圣”。贝多芬自幼就显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他的音乐启蒙来自于他在波恩教堂当歌手的父亲。父亲希望他能成为第二个莫扎特,逼着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1787年贝多芬在维也纳时曾为莫扎特演奏过,莫扎特当时就预言他前程无量。
贝多芬的音乐才能初露峥嵘时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音乐主要是为了取悦听众,或是为宗教仪式和皇室活动服务。这些作品曲风大多轻松、诙谐、朴素,不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贝多芬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状态,他的音乐自由地抒发内心丰富的感受,极具鲜明的个人特性。可以说,贝多芬是音乐发展史上一位最重要的革新者。
贝多芬所创作的作品涉及各种音乐形式,包括:交响乐、室内乐、器乐独奏曲、歌剧、清唱剧、弥撒曲等等。而他的钢琴奏鸣曲的出版可以说是音乐史上的一个高峰,贝多芬对奏鸣曲及奏鸣曲式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是难以估量的。他的32首钢琴奏鸣曲被后人称为音乐《新约全书》[1]。这32首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些创作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人,与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并称为钢琴文献中的史诗性巨著。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按照时间和风格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早期(吸收、同化时期)、中期(现实主义时期)、晚期(冥想沉思时期)。
一 创作早期(1802年之前):吸收、同化时期
在这个时期,贝多芬的创作处于一个学习、继承、摸索与创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品也是最能清楚地体现出贝多芬对古典主义传统的依赖。在早期的创作中,贝多芬延续了巴赫、海顿、莫扎特惯用的传统奏鸣曲的创作模式,他的前3首奏鸣曲在主题和旋律的处理上都带有海顿的影子[2]。同时,贝多芬尝试将奏鸣曲从过去的三部曲式中分离出来,他早期创作的奏鸣曲通常有4个乐章,在传统的3个乐章的模式中加入小步舞曲或诙谐曲,但是这种4个乐章的结构很快就被他抛弃了。贝多芬通过创作实践,不断地探索发展奏鸣曲的新形式。尽管贝多芬在后来的创作中大多沿用3个乐章的奏鸣曲创作模式,但他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的奏鸣曲中快、慢、快的曲式结构顺序,而是重新加以安排,如他将第12首奏鸣曲(Op.26)的第2乐章写成了诙谐曲,并将第3乐章安排为缓慢的葬礼进行曲;第8首《悲怆》的第1乐章中,加上了慢的法国序曲性质的缓版(Grave)前奏[3]。
值得一提的是,第12首《降A大调奏鸣曲》是一首完全打破传统奏鸣曲各个乐章习惯顺序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首作品中,没有一个乐章是用奏鸣曲式写成的,4个乐章被安排为变奏曲、诙谐曲、葬礼进行曲和小快板回旋曲,这标志着贝多芬开始成功地摆脱海顿、莫扎特奏鸣曲对他的创作所带来的影响。贝多芬在之后的几首作品中也延续了这种创作模式。另外,在贝多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极具个性的调性处理。如第1首奏鸣曲,贝多芬用了在古典主义时代并不常见的F小调;而在第2首奏鸣曲中,第1乐章的第2主题开始在属小调E中,立即在一个上升的低声部线条上面转入G大调、降B大调,抵达高潮性的减七和弦,然后落在呈示部结尾的E大调中[4]。这些无不体现出贝多芬对传统奏鸣曲结构的革新。
除了对曲式结构及调性上进行创新以外,在对作品内涵的要求上,贝多芬也注入了新的元素。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们能听到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丰富的情感,他使奏鸣曲超越了最简单、最原始的优美动听的层次,使之更具深刻的内涵。在创作第8首《C小调奏鸣曲》(Op.13)时,贝多芬正受到耳聋的严重打击,从作品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他那种悲伤、愤怒、无奈与抗争的情感。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创作早期继承并发展了巴赫、海顿、莫扎特的传统的创作模式,开始初步形成他的特殊的音乐风格。
二 创作中期(1802-1816):现实主义时期
中期是贝多芬创作的旺盛和关键时期,并开始走向成熟。贝多芬并没有让古典奏鸣曲的形式束缚自己的创作,他不断地对奏鸣曲形式进行探索和改进,寻求表现力更强、更为新颖的奏鸣曲结构[5]。在这期间,耳聋对贝多芬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但他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而是与命运展开坚决斗争。
经历了创作早期不断的摸索、创新,贝多芬在这一阶段的作品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个人风格。与早期相比,这一阶段贝多芬在创作中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在曲式结构上,他完全摆脱了传统奏鸣曲的创作模式。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2首奏鸣曲中,只有6首是3个乐章,有5首仅有两个乐章。在第19首《G小调奏鸣曲》、第20首《G大调奏鸣曲》以及第33首《F大调奏鸣曲》中,贝多芬将慢板乐章加以省略,保留了传统的回旋曲;第18首《降E大调奏鸣曲》,是贝多芬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唯一一首4个乐章的奏鸣曲,但这首曲子并不同于他之前创作的传统的4个乐章的奏鸣曲模式,贝多芬试图将奏鸣曲的长度加以扩展,使每个乐章更加充实、饱满。在对调性的处理上,贝多芬延续了早期创作中非正统的调性处理手法,如在第16首《G 大调奏鸣曲》(Op.31 No.1)中,第2主题以B大调代替了原来应当出现的D大调;第17首《D 小调奏鸣曲》(Op.31 No.2)开始于一个定位在属调上的引子及一个快板的乐句,但随后反复引子时却出现在C大调上,直至第21小节之后才正式进入了乐曲的主调D小调[6]。
另外,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机械工业的崛起,带动了整个钢琴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贝多芬在创作过程中也大胆地利用了新的钢琴技术以不断探索和发展自己的创作[6]。在第18首《降E大调奏鸣曲》中,贝多芬加入许多断奏(Staccato)和颤音(Trill)技术,这也使他的作品更加立体、完善。
《黎明奏鸣曲》(Op.53)和《热情奏鸣曲》(Op.57)被认为是贝多芬奏鸣曲中期创作的顶峰,而这两部作品问世也标志着贝多芬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成熟、稳定的个人风格。相比于早期作品中带有明显海顿、莫扎特的创作特点来说,贝多芬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中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用夸张的对比、极具戏剧性的音乐来表现,展现出他独特的创作个性。但之后的几部奏鸣曲与中期的创作风格开始脱离,带有憧憬和感慨的思想意味,这也预示着贝多芬创作生涯晚期的来临。
三 创作晚期(1816-1827):冥想沉思时期
在贝多芬一生最后的5年中,他没有再创作过奏鸣曲,第32首《C小调奏鸣曲》(Op.111)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首奏鸣曲。贝多芬的音乐创作晚期处于欧洲大陆最黑暗的时期,而他在经历了辉煌的创作中期之后,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混乱,健康状况也持续恶化,他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他。就是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贝多芬依然坚持他对音乐的那份执着,继续进行音乐创作,完成了他的最后5首奏鸣曲。
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贝多芬的奏鸣曲与前两个时期的作品有了更为不同寻常的变化,不仅更加趋向于幻想性,而且他对传统的奏鸣曲乐章次序也做了改变,用进行曲代替了谐谑曲。另外,贝多芬晚期的作品规模更加庞大,内容也更加丰富、深刻。这个时期虽然只有 Op.101、106、109、110和111五首作品,但却展现了贝多芬卓越的创作成就。贝多芬尝试在作品的一个乐章里,融入新的素材来打断原有的乐思。第28首《A大调奏鸣曲》(Op.101)是贝多芬献给学生埃特曼的。在这首作品中,贝多芬几乎放弃了传统的创作标准,乐曲的第1乐章可以算是贝多芬所有奏鸣曲中最短的一个第1乐章,第2乐章用活泼的快板代替了谐谑曲,而这一乐章中复杂的节奏能让人联想到舒曼后期的作品,这也预示着贝多芬的创作开始出现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贝多芬晚期的创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复调的使用。如果说巴洛克时期的复调技法是一种音乐的创作形式,那么贝多芬奏鸣曲中所使用的复调则是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手段。事实上,贝多芬从创作早期开始就注意到复调写法,在第9首奏鸣曲第1乐章中就用到了简单的复调手法。而在晚期的作品中,贝多芬对复调的运用更加常见,而且比以往有了更大的超越,如第29首第3乐章中,贝多芬创造出一种赋格中又套着赋格的新的复调形式,这个新的主题与原来的主题结合,并发展扩大,使原有的主题更加丰富;第31首《降A大调奏鸣曲》(Op.110)的最后一个乐章,贝多芬更是在展开段中加入赋格段和整个赋格曲乐章。同时,在贝多芬在晚期的创作中还加入了以往没出现过的即兴乐段,如Op.101的慢板乐章、Op.106末乐章的广板引子和Op.110的柔板,这些即兴乐段不断丰富着贝多芬奏鸣曲的创作[7]。第31首《降A大调奏鸣曲》(Op.110),是贝多芬创作生涯最后阶段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几乎囊括了贝多芬成熟时期的奏鸣曲中的所有特点:曲式结构上的自由解放,扩展中的豪华壮丽,运用赋格和咏叹调手法改变古典奏鸣曲式的框架,以及所有主题间的内在紧密联系。
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是音乐发展史上一部不朽的巨作,这部巨作不仅反映了贝多芬一生的创作经历,也向世人展现了贝多芬对音乐不懈追求的执着;不仅反映了那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进步思想,而且更完美地展示了一个天才作曲家精湛的创作才能。这部巨作体现了贝多芬特殊的音乐风格和音乐语言。它的巨大价值在于发展和提高了现代钢琴音乐的表现力,成为音乐发展史上宝贵的文化财富。
[1]于润洋.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音乐卷·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325.
[2]闵敏.贝多芬晚期五首钢琴奏鸣曲的创作特征和演奏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音乐学院,2006.
[3]张式谷,潘一飞.西方钢琴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99-216.
[4]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里斯卡.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570-587.
[5]颜婷婷.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早、中、晚三个时期代表作品的风格比较[J].考试周刊,2009(1):215-216.
[6]余志刚.西方音乐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65-167.
[7]卡尔·车尔尼.贝多芬钢琴作品的正确演绎[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