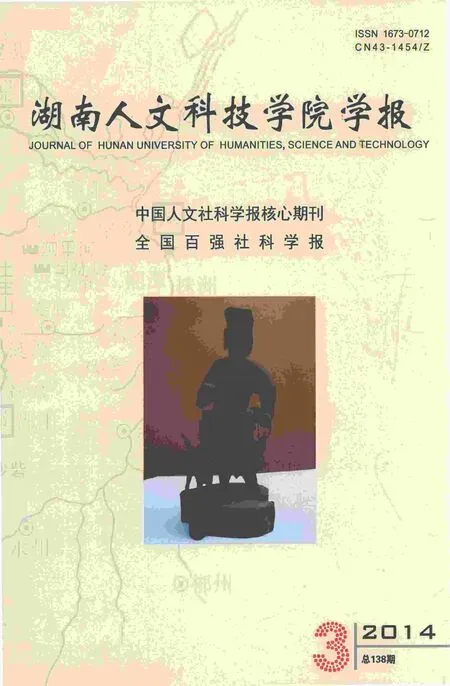从抗日神剧的热播看消费社会历史建构的困境
钟 珊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所谓抗日神剧,是指在当下中国制作,在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下生产,将残酷的战争进行游戏化处理,对抗日历史的纪念和反思被游戏狂欢所掩盖的抗日题材电视剧。消费社会的热播“抗日神剧”与传统“抗日题材影视剧”的区别主要在于:传统抗日题材影视剧勃兴的年代是新民主主义胜利后,它只要承担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和教化功能,只要非常好地讴歌抗日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即可。此外,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单纯,对共产主义绝对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绝对信赖,因此当时的传统抗日电影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而如今的抗日剧不仅要承担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和教化功能,经济利润的获取更成为文化机构包括电视事业的首要目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民眼界开阔,思想接受了各种现代新思潮,怎么才能让抗日题材剧重新受到人民大众的热捧,这成为执政者和电影电视工作者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抗日神剧就是当下摸索,实践的产物。我们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以下简称抗日剧),特别是近两年抗日剧,为了经济和政治的双赢,将爱国主义情怀隐藏在儿女情长、痴男怨女和血腥、暴力及完全脱离现实的夸张失实下,虽然它的收视依然坚挺,但还是引起了广大有识之士的质疑。
影像作品对历史的建构总是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抗日题材的特殊性在一定范围内限定了该类文本的建构尺度,因为抗日剧不仅是当代国人获取抗日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再现并形塑中国民众对非常岁月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在此意义上,抗日剧被赋予了除娱乐功能之外的教育意涵,从而也引发了我们对大众传播中抗战历史建构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当下抗日神剧的历史建构存在怎样的困境?该困境产生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文化反思?
一 喧嚣与躁动:抗日神剧的纷繁乱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达5 000万,历经大小10余万次战争,这是一段惊天地、泣鬼神、激昂悲壮的反侵略史。传统抗日题材影视剧主要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期间的英勇表现,如《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夜幕下的哈尔滨》等,这些电影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激起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的作用。而现在的抗日神剧为了表现我军的神勇,就可以让其丢个手榴弹就把飞机炸下来;为表现鬼子的愚蠢,就可以让小孩子轻松偷袭得手;为让情节更丰富、更符合娱乐精神,就可以设计女角色在遭轮奸后拔地而起,瞬间秒杀几十人。所以近两年,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抗日剧的批评都一直不绝于耳,直到2012年一张惊世骇俗的背对镜头、面朝我军战士、相互敬礼致意的窈窕全裸女图片的横空问世,终于引爆了对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抗日神剧的讨论与质疑。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在2013年4月10日严厉批评了抗日剧的粗制滥造,直指抗日剧越来越俗、越来越二的现象[1]。
对抗日剧最早的批评声音来自网络。纵观当今抗日神剧的创作,其历史建构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倾向:
第1种倾向是武侠科幻化。武侠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习武强身的民俗,在抗日剧中适当演绎本也无可厚非。但在这些电视剧里,抗日英雄一个个仿佛李寻欢附体,取鬼子性命易如反掌,唾手可得。这根本不是真实的抗日历史,活脱脱就是一部部武侠科幻片。但就是这些剧情夸张、超乎逻辑、与历史相去甚远的抗日剧,却常常拔得收视头筹。抗日剧中的武侠因素备受中国市民阶层青睐,有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动因,“东方文化是一种求内的含蓄型文化,但中国自古又有一种强烈的尚武传统,武侠剧的诞生为爱面子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释放生活中的各种暴力压抑的完美渠道”[2]。抗日神剧利用中国市民阶层的心理,为了收视率,不顾抗日历史的真相,片面夸大功夫和冷兵器在抗战中的作用,这种做法不仅让部分国民误以为依靠这些功夫和冷兵器就能真正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严重的是会潜在地在受众中滋发一种“暴力娱乐”倾向,使观众在获得心理快感的同时,加剧人们对暴力的麻木感和宽容度,暗示在生活中解决争端的唯一方式就是武力抗衡。但抗日历史真是这样的吗?不,抗日神剧中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据《南方周末》纸上忠烈祠(2003年8月23日)上的报道:“中华民族全民抗日,历经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其中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全军覆没。”[3]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演变为个人竟然可以玩凌波微步,空中翻转720度,在日军重武器齐备的情况下,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杀鬼子如同儿戏一般的战斗。如此狗血的剧情,使抗日神剧的播出备受质疑,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嘘声。
第2种倾向是偶像滥俗化。如今的抗日剧大量启用面貌俊美的年轻男女演员,采用新潮时尚的造型服饰,加入诸多暗恋、单相思、虐恋等爱情戏戏份或偶像剧元素来吸引青少年受众。2012年下半年,多家卫视一口气推出多部抗日偶像剧,抗日剧男女主演几乎个个都是俊男靓女,吴奇隆、刘恺威、王雷还有朱雨辰等的加盟让抗日剧立刻受到年轻观众的力捧。像《向着炮火前进》中吴奇隆饰演的雷子枫,《战旗》中王雷饰演的金戈,《一触即发》中钟汉良饰演的阿初和阿次的形象等都是偶像剧中典型的高富帅形象。显然,抗日剧的偶像滥俗化与剧目出品方的受众策略有关。当下电视观众日趋老年化,年轻观众大量流失,而广告的消费对象又主要是20-45岁之间的观众,所以出品方不得不在剧中加入偶像因素,以此吸引年轻受众。“偶像化并非抗日剧‘泛娱乐化的’原‘罪’”[4],但抗日剧不应只流于依靠特定时尚元素的表面形式,而更应使受众在感受青春激情的同时,心灵被净化、道德被升华。
第3种倾向是人物脸谱化。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大众文化的载体,具有建构社会形象意义或模式的功能,但在实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所再现出来的日本士兵形象具有形象刻板化的倾向,影响了受众对日本士兵形象的认知。在这些抗日神剧中,日本军人总是很邪恶猥琐、衣冠不整的,见到平民百姓就喊“八格牙路”,在八路军、民兵等抗日英雄面前,他们均是不到5秒钟便抱头鼠窜、大呼“饶命”的弱智形象。当正面人物被神化,反面人物被丑化时,娱乐效果呈现出来了,但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人无法深入思考引发战争的原因,未能反映残酷战争施加于军人的种种回响,没有展示士兵对战争的恐惧,没有反映战争对人的异化。更没有从人性上予以反思:是什么让日本兵从也是对父母亲孝顺的儿子,有爱的兄弟姊妹,在家乡安分守纪的公民而蜕变成了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机器,在毁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同时,最终也毁了他们自己的人生?
“在这些抗日剧中,历史的真相与当下的真实已经被娱乐得无影无踪,这绝非爱国主义,而是愚民主义。这种泛滥和幼稚化倾向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不能任由电视台和投资方为了收视率肆意的涂抹。”[2]央视《新闻1+1》栏目中的这段话无疑是对抗日剧现状最好的警醒。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里如是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5]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历史还可能重现。面对抗日剧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沉重的历史主题,中华民族抗战的悲壮和牺牲的惨烈,我们怎能以这种游戏、娱乐、狂欢的方式来解构战争的残酷,来消解民族英雄的崇高,来亵渎血与火的苦难历史!
二 欲望与消费:抗日神剧热播的社会语境
在消费主义肆虐的背景中,对于意识形态的管控和对于经济利润的欲望的合谋,是当今抗日神剧热播的主要社会语境。有学者曾将当代电视剧艺术生产的境况概括地描述为:“政治力量与市场力量通过权力的较量、谈判、协商,建构了主流电视剧的特点,实现了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6]抗日剧的产制同样要受到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效益服务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一部分,抗日剧的写作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符码的组织生产,要以此证明通过革命手段缔造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与合法性,这是国家主流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个体,并施以不可抗拒的教化的工具。另外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这种变化影响到文化领域,形成了相应的变革:“第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事业都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都以一种产业化的模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第二,既然文化被产业化,那么,商品逻辑和市场逻辑就一跃成为左右文化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文化场’越来越受到‘经济场’的制约。”[7]
这样,一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断然不会放弃其在所控制领域内的文化监护和文化培育的权力和责任,电视剧的创作和播出方向一直受着主管部门的调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效益,电视工作者要不断追求更高的收视率,要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电视节目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就需要电视节目符合人们内心更本能的需求,因为只有满足这种需求才能获得一种普遍的接受与认同,这种需求就是死亡、性与享乐等,简言之,就是对人体感官的直接性刺激。政治话语和经济力量的角逐与合谋,使抗日神剧的一统江山地位建立了起来,看似非理性的电视潮流实则是中国电视剧从业人士在题材选择上四处碰壁后极其理性的清醒选择。
由此,通过现象剖析本质,官方之所以允许抗日神剧的热播,其实武侠、魔幻、偶像元素都只是表象,官方真正要宣传的还是日本官兵对中国人民的残酷杀戮,共产党英勇抗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功绩。像《箭在弦上》从一开始徐一航的自叙和她手中第一箭的射出就使用了魔幻剧的手法,这只占据画面大部分的箭闪着冷冽的青光,翻滚着从抗日胜利的那一天一直穿越回了她爷爷前清武探花的靶上。荣石去溶洞中拜访钱旅长,为他的同学、身为共产党抗日义勇军大队长的张贺购买武器时,溶洞中的场景完全是按游戏中的场景布置的:游戏中张牙舞爪的青铜龙头,在龙头旁飞来飞去的蝙蝠。这些场景的设置意在拉近与青少年的距离,在消费主义盛嚣尘上的时代,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杂糅、拼贴等手法,在潜移默化中输入主流意识形态,并提高收视率,以此获得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在剧中着重表现的都是日军对平民的杀戮,像在徐一航的婚礼上,日军对徐家上下及宾客几百口人的屠杀,旨在激发民众对日本残暴的恐惧和仇恨,以此衬托以张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率领的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战的伟大功绩。电视剧文本通过武侠、魔幻与偶像等元素将共产党打下江山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给不接受赤裸裸抗日宣传的青年一代的意识中,“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8]。笔者认为,这才是抗日剧拍得如此雷、如此二、如此滥仍然得以一路顺畅播出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三 对策与思考:抗日剧如何建构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已过去60多年,我们的前辈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因为侵略者人性中的恶,也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明上的落伍。随着经历如火如荼战火硝烟的老人的一一离去,当年的亲历者、见证者越来越少,对峥嵘岁月的追忆会逐渐只能依靠间接的史实传递来实现。如何客观真实地铭记历史,永远传承华夏民族英勇不屈、顽强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是一代又一代国人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抗日剧创作中,传奇英雄、革命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都是必要的,但“度”的把握仍是关键。抗战背景所要求的历史真实、现实主义所追寻的审美诉求仍然必须是其必备的根基。抗日剧创作应符合美学原则,应具有革命历史时期所要求的精神价值,创作者应处理好基本精神价值和现代观念的互动关系。
(一)尊重历史,理性书写
建国以来,很长时期内,影视艺术被迅速地纳入“一体化”的格局,甚至在政治权力的绑架之下,主动出让自己的话语权力,以其“虚构”的特性,使叙事意义和传播效果显得单薄脆弱而且可疑。这在米歇尔·福柯看来,则是一个权力的游戏,他认为:“虚构有可能在真理中起作用,虚构的话语可以产生真理的效果,真实的话语可以产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东西,对它进行‘虚构’。我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这种现实使它真实,我们也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9]事实上,国产抗日剧属于“双重虚构”,即用虚构的电视剧来虚构历史。
针对以上现象,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文化审核机构应该给影视松绑。长期以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地雷”无处不在,很多导演在拍摄敏感题材时如履薄冰,历史真实自然不能客观呈现。第二,编剧、导演等文艺工作者们要有文化担当,要懂得对艺术良知的坚守,电视可以娱乐,但历史不可以调侃。第三,重建影视剧的评估体系,在消费社会,票房和收视率是评价影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影视剧拍摄和制作机构为了追求高票房和高收视率,想方设法吸引观众,完全不顾历史底线和道德底线,导致大量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充斥荧幕或者荧屏。影视剧的评价体系应该开放、多元,不能把票房和收视率作为唯一的风向标。第四,观众应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在收看影视剧的过程中懂得鉴别、思考。
(二)尊重人性,彰显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所有人、所有生命的关注和重视,超越民族、阶级、国界等,我们的抗日剧到底该表现什么?最起码,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庸和扩音器,也不应该沉湎在戏剧情节里不能自拔,用暴力与情色来满足人们的低级好奇与快感,而是应提升人文精神内涵,提升艺术价值,以此来赢得社会的尊重与喜爱,达到所有艺术作品努力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抗日题材影视剧不仅要表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与痛苦,让中国人记住本民族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战争对所有人的生命的摧残、对所有人的生活的伤害,最终表达全人类反战、追求和平的愿望,深化主题。
以美国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剧《兄弟连》为例,《兄弟连》以人为本位,处处体现对每一位士兵的关怀,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在《兄弟连》第三集的末尾,即空降兵团休整完准备重新开赴战场的时候,马拉其带着晋升的喜悦去蓝太太的洗衣店取衣服,蓝太太问马拉其是否可以帮其他士兵拿一下衣服,他们可能忘记来拿了。马拉其呆了一下,脸上沉重了起来。随着蓝太太一个一个地报着那些再也回不来拿衣服的士兵的名字:伊凡斯中士、二等兵摩亚、布劳泽、葛瑞、米勒、欧文……镜头掠过一个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士兵们的衣物时,深沉的配乐响起,感觉就像掠过一个个士兵的衣冠冢,体现了深重的悲哀和难以言说的苦楚。最后在黑色荧幕上打出了这样的字样:“E连29日撤离前线之前,已经失去了65名兄弟。”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战争中的每一次升迁,每一次荣誉获得的背后,是许许多多年轻士兵们的受伤,甚至死亡。他们不能再见到明天的太阳,他们永远不能再和亲爱的家人们在一起。通过一幕幕的场景,《兄弟连》深刻揭示了战争本身的悲剧内涵,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价值判断,张扬了一种反对战争、尊重生命价值的世界性价值观。而在神剧《抗日奇侠》中,团长刘建功率领的独立三团,在一次残酷的战争后,一个团死的仅剩十几个人,可是剧中画面展现的只是战后缴获武器的笑脸,报告战功时的喜悦,没有体现半点失去这么多战友的忧伤。战争到底是什么?抗日剧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文艺模式,很多情况下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人道,忽视对战争中的人的感性命运的揭示,在血与火的壮丽描写中放弃了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思索,在冲锋陷阵的枪林弹雨中看不到个人牺牲的悲苦和家庭破碎的心酸,现在更加上插浑打科、不着边际的恶搞,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予以理性的审视与反思。
由上观之,抗日神剧的风靡一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播现象与文化现象。这轰轰烈烈的收视热潮映射的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一场狂欢式娱乐。借助“抗日”的惨痛历史,抗日神剧将陈旧的叙事文本加以重新演绎,其本质不过是一次意识形态符码的组织生产,一次对经济利益的毫无节操的攫取。如何才能改变抗日剧的现状呢?正如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教授谢飞所说:“将现行的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变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由人治过渡到法治。”[10]应多给从业者一些自由创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电视人在抗战剧创作中也应该不断探索现代性意识形态与大众美学的平衡与结合,努力突破抗日剧中传统意识形态的窠臼,多一些对战争的思考,努力提升人文精神,理性真实地书写历史。唯其如此,抗日剧才能冲破传统性的束缚,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才能在实现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社会和文化收益的双赢。
[1]央视批抗日剧粗制滥造:越来越俗 越来越二[EB/OL].央视新闻1+1[2013 -04 -11].http://news.qq.com/a/20130411/000182_1.htm.
[2]林移纲,唐时顺.浅析武侠剧暴力内涵的文化根源[J].电影文学,2007(11A):47-48.
[3]魂兮魂兮:纸上忠烈祠[EB/OL].[2007-08-23].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823/cul/news/2007 08/t20070822_23934.htm.
[4]刘虹利.主体认同与“红色”偶像剧的可能性[J].四川戏剧,2013(8):40-44.
[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8.
[6]尹鸿.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现代传播,2001(4):1 -6.
[7]祁林.电视文化的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93.
[8]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
[9]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0.
[10]钟茜.谢飞公开信炮轰电影审查制度[EB/OL].成都晚报:电子版.[2012 -12 -17].http://www.cdwb.com.cn/html/2012-12/17/content_17543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