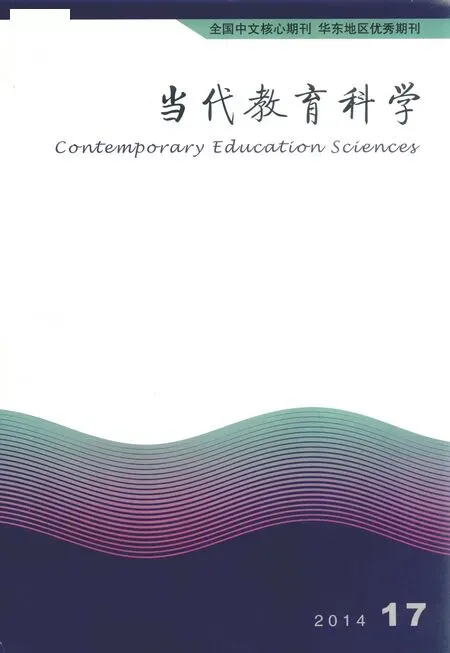论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广度与深度*
●吴卫军 张倩倩
论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广度与深度*
●吴卫军 张倩倩
近几年学生起诉学校的案件频发,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学校行政行为之界定非常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困境叠现。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从司法审查之广度看,学校对学生的严重纪律处分行为、招录行为,以及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行为等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应当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从司法审查之广度看,法院应侧重于审查学校行政行为的程序正当性,且在审查时应当适用实质性审查的证明标准。
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广度;深度
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加快和法制理念之普及,学校学生的权利主体意识日益增强,涉及学生与学校行政行为之间的争议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行政诉讼法对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相关规定却极为模糊,引发司法实践中困境叠现。这一现象逐渐增多,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广泛争鸣。在我们看来,理性审视我国立法现状,系统研究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广度与深度问题,对于推动学校法治化进程与助力行政诉讼法之修改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界定
所谓学校行政行为即学校管理行为,是指依法设立的学校基于法律法规之授权,依照法定程序单方面做出的对被管理者的权利、义务造成影响的具有行政权性质的行为。从对象上看,学校既要对教师进行管理,也要对学生进行管理。由于对教师的管理属于人事法律关系的范畴,本文只涉及对学生之管理行为。此外,学校行政行为有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之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没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学校行政行为是学校的具体行政行为。[1]在我们看来,这一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管理性。学校与学生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而是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强烈的单方意志性,符合行政法律关系之特征。二是授权性。学校的管理职权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具有制定规章、学籍管理、颁发证书、招生、组织教学、奖惩等方面的职权。因此,尽管学校不是行政机关,但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学校拥有对学生的管理职责,可成为依法实施行政权力的行政主体,具有行政职权。三是专门性。学校是以教学、科研活动及服务社会为主业的社会法人,其行政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色彩,特别是涉及学术评价的行为,需要专门知识与特殊技能才能弄清,这就决定了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应保持必要的克制与谦抑。四是效力先定性。这是指已经做出的学校行政行为不管合法与否,即被视为有效的行政行为,在没有被上级部门或法定审查机关的撤销之前,相对人必须依照行政行为的要求行事。[2]这一特点决定了学校行政行为符合一般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对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依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3]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决定了法院可以对哪些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学校行政行为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的特征,理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但审视《教育法》等单行行政法律及行政诉讼法,不难发现,这些立法并未对学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有明确的规定。这种情形导致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由于管辖法院不同,其是否受理、如何审查存在较大争议,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功能的有效彰显与学生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该解释第二款还明确列举了排除司法审查的事项。仅仅从该解释的内容看,学校行政行为似乎并未被排除审查,但由于立法及司法解释的模糊化处理,导致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致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对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广度与深度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思路,可以在有效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同时,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正常有序进行,推动学校管理行为朝着法治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二、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广度
司法审查制度的广度是指司法机关能否审查学校行政行为,以及对哪些学校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司法审查。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借鉴域外其他法治发达国家、地区现有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当前国情加以确认。我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法典编撰、诉讼程序、法律思维、法律技术等方面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相似,因此,在探讨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广度问题上应当优先考虑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相关经验。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对其制度及实践进行考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起源于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①,将学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但是随着宪政发展以及现代法治观念不断进化,这一理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弊端,导致行政权力肆意扩张,相对人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早在1956年就有德国学者提出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衍变成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该理论认为属于基础关系的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可以受到司法审查;属于管理关系的行为是内部管理行为,不受司法的监督,不能提起诉讼。学校产生、变更或者消灭学生在校接受教育机会的行为属于基础关系,应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1972年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判决逐渐形成的“重要性理论”,把凡是涉及到学生基本权利的行政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这一理论扩大了基础关系的范围,进一步发展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是,德国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具有一定局限性,覆盖面不宽,很多方面都未涉及,因此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德国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过。[4]
通过对德国特别关系理论发展的描述可以看出,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具有相对性和特殊性,从最初的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到现在随着判例的出现,学校重要的行政行为逐渐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我国,学界虽然很少有学者把学校行政管理关系视为特别权力关系的一种,进而主张不进行司法审查,但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时很明显受到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其表现就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外。我们认为,审视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广度可参考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明确学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确立能够进行司法审查的基本立场。
如前已述,学校行政行为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中的一部分行为是依据学校的学术权和自主管理权而做出的。[5]若是所有学校行政行为都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必然会对学校的学术发展及正常教学管理秩序造成影响,因此,在确定司法审查的广度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一问题,在不侵犯学校学术权和自主管理权的情况下进行审查。我们认为,只有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学校行政行为才是司法审查的内容,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事项:
一是开除学籍处分与退学处理决定。开除学籍处分与退学处理决定会影响到学生与学校的在学关系,导致这一关系归于消灭,同时也在根本上影响到学生的受教育权。因此,应当将这类处分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允许法院对这类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符合“重要性原则”的要求。
二是招生录取行为。学校招录行为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学生在被学校录取之前,虽然与学校不是在学关系,但是学校是否录取的决定涉及到学生正常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因此应当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类行为主要包括限制考试资格、取消录取资格、拒绝公布考生成绩等所有影响学生入学就读机会的具体行为。
三是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行为。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中学历证书(主要表现为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等)与学位证书是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一般认为,颁发毕业证书是学校的固有职权,颁发学位证书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由于学历证书之颁发涉及到学生就读上一级学校、毕业派遣等问题,可能影响学生继续接受教育、正常参加工作等基本权利,从重要性考虑应当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而颁发学历证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既涉及对学生学术水平的评定,也涉及学生继续就读、工作等重要权利,因此也应允许学生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司法救济。
三、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深度
司法审查制度的深度是指司法机关对学校行政行为如何审查,审查什么的问题,也有论者称之为审查的强度。[6]如果说司法审查广度是衡量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范围的概念,则司法审查深度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力度与影响力。从理论上分析,法院对学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要在制约行政权、实现权利的有效救济与尊重学术自治、维护学术尊严之间寻求妥当的平衡,也是说让行政司法权在能动与被动之间彰显应有的价值。
在我们看来,基于学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除非涉及的事项简单、依据普通人的常识理性能够做出判断的事项(如遭致处分的打架斗殴与考试作弊等行为)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般不宜审查学校行政行为的实体性问题,其理由除了尊重学术自治、维护学术尊严外,还在于实体事项的内容大多涉及专业问题,法院及法官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能力与客观标准。因此,法院的司法审查应当主要着眼于程序性审查,即审查学校行政行为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遵循了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最低标准在于:“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必须给予他知情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对决定者而言,就是履行告知和听证的义务。”[7]学校在做出影响学生基本权利的行政行为时,也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与行政主体实施的普通行政行为不同,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属于学校内部事务,法律法规对其方式、方法、步骤、时限、顺序等干预不多,大多数程序性内容主要见诸于学校的内部规章制度。这就意味着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一方面要关注已有的法律法规乃至主管部门的政府规章(如《教育法》、《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中规定的程序是否被遵循,若存在重大或明显瑕疵时应当考虑撤销学校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法院还应重点审查学校内部规章制度中的有关规定是否得到遵守,如学位(学术)委员会、校长会议、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等决策机构的组成是否符合规定,表决方式有无瑕疵,学生的辩解与申诉权是否得到落实等等。
此外,在学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深度方面还需注意的是,由于这些行政行为涉及学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因此除了恪守学校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要求外,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涉及事实的实体性与程序性问题都应坚持实质审查的标准,即学校行政行为的作出应当有实质性的证据支撑,且这些证据应当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能够接受的。[8]这意味着学校举证即便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至少应当比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要高。
总之,随着学校行政行为争议案件的日益增多,将学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完善其司法审查制度已是必然之趋势。无论是从审查的强度还是审查力度看,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已远远落后于司法实践中对学校行政行为进行有效审查的客观需要,应当尽快修改完善。但另一方面,在立法及司法解释尚未修改前,从“以人为本法”法律观出发,[9]法院应当秉持“有权利即有救济”的司法能动主义立场,积极受理涉及学校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切实有效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实现对行政公权力及类似于行政公权力性质的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这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和应有态度。
注释:
①“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将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的所有争议都排除在法院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当行政主体行使的行政权属于“特别权力关系”范畴时且该行为侵害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时,相对人只能通过行政内部途径来寻求救济。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17-321.
[2]欧爱民.论学校行政行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3):25-28.
[3]韩欣欣.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范围和原则[J].辽东学院学报,2006,(3):119-125.
[4]于安.德国行政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34-38.
[5]程雁雷.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与司法介入之范围[J].法学.2005,(12):34-39.
[6]傅国云.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司法审查强度探微[J].浙江学刊,2000,(2):91-93.
[7]张文显.法理学(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7.
[8]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46.
[9]吴卫军,陈璇.“以人为本”法律观的理论传承与现实解读[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64-69.
(责任编辑:刘丙元)
*本文系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13年项目“我国城市群体性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吴卫军/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学研究
张倩倩/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