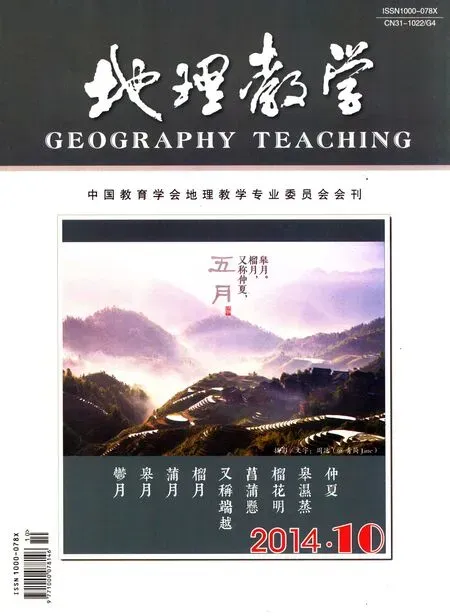我国乡土地理教材:历史变迁与发展思考**
张 海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我国乡土地理教材:历史变迁与发展思考**
张 海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乡土地理教材是乡土地理知识的主要载体,也是乡土地理教育的主要依据。乡土地理教材开发对落实课程改革精神、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促进学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各地开发乡土地理教材的热情高涨,已开发出来的教材数量非常庞大,但总体质量却并不高。乡土地理教材在基础教育界的影响力与其应有水平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不过笔者认为,有一个原因必须给予格外关注,那就是对乡土地理教材的历史研究的忽视。“欲通今则必先知古”,要有效解决今日乡土地理教材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首要任务是溯本追源,透彻分析乡土地理教材的历史变迁及其特点。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回顾我国乡土地理教材开发的历史,梳理其变迁特点,为乡土地理教材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
一、乡土地理教材的变迁过程
1.乡土地理教材的萌生阶段:清末到民国时期
在我国,具有现代教科书意义的乡土地理教材萌生于清朝末年。当时,一些学者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学习西方和日本乡土教育的经验,率先尝试编写了一部分乡土教材作为中小学教科书。蔡和铿于1898年编写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以“乡土地理”为名的乡土地理教材。[1]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提出在小学阶段讲授本乡、本县、本府和本省的乡土知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要求小学“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兼破其乡曲僻陋之见。”教师应“先自学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间亦带领小学生寻访古迹为之解说,稗其因故事而记地理,兼及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船之交通、物产之生殖,并使认识地图,渐次由近及远,……”[2]为保障教材质量,清政府还于1905年制定了《乡土志例目》①,以指导和规范全国的乡土教材开发。
为了响应新学制的要求,并尽快解决新学制学堂普遍面临的教科书短缺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如国学保存会[3])开始自编各种乡土地理教材。侯鸿鉴的《锡金乡土地理》(1904年)是目前能见到的(有确切年代)成书最早的乡土地理教科书。[4]谢葆濂的《余姚乡土地理历史合编》(1906年),马钟璓的《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年),陈庆林的《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黄节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年)[5]等均成书于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乡土地理教材是直接以“乡土志”为名的。有学者评论,清末的地理学“影响最大的既不是中国地理教育,更不是世界地理教育,而是乡土地理教育。”[6]
民国时期,乡土教育和乡土地理教材开发依然受到重视。1914年,教育部曾催促各县编纂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1916年,教育部规定“教授地理宜先注意于乡土之观察,以引起儿童之兴味及其爱乡思想”;1933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小学法》,第九条规定小学教科书应注重各地方乡土教材;1937年,教育部又颁布训令,“二年制短期小学教材应采用部编课本为原则,各地方为适应需要起见,得酌量编订乡土补充教材”。[7]对此,有学者写道“最近我国教育界提倡集中于乡土教育”。[8]1940年至1941年间,国民政府出台了《修正初小常识科课程标准》和《重行修正初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前者规定乡土教材“以第一二学年从本乡(镇)出发,扩大到本县(市),第三四学年从本(市)到本省(市)为原则。”后者明确提出了乡土地理的要求,“初中地理应自乡土教起,各学校应将本县本省之地理详加讲授,教材另编。”[9]此时期留存可见的乡土地理教科书有《荣成乡土地理教本》(1928)、《上海乡土地理志》(1927)②等。此外,乡土地理研究与乡土地理教材研究都逐渐增多。著作如葛绥成编的《乡土地理研究法》(1939)、林超等编写的《乡土地理调查手册》(1941)等,论文如胡焕庸的《初中添授乡土地理和省区地志编辑问题》(1939),强生的《地理教材拾遗及乡土地理之编辑》(1943)等等。
2.乡土地理教材的曲折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
我国的乡土地理教材建设在50年代末和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两次小高潮。1950年,我国学习苏联经验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而各类乡土教材的开发未受到足够重视。推行全国统编教材的政策在保障和促进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出现了教材内容过于整齐划一、脱离各地生产实际等众多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与7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时指出:“教材要有地方性,应该增加一些乡土教材。”[10]1958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指出“中小学地理、历史、文学等科目教学都要讲授乡土教材”,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应当负责编写、审查乡土教材。[11]此后三年左右,我国出现了一个乡土教材建设的小高潮,江苏、上海、河南、广东等许多省份都出版了本省的乡土地理教材,苏州、淮阴等一些市(县)也开发出版了当地的乡土地理教材。与此同时,国内翻译出版了苏联加里宁的《中学乡土地理教学》(1957)一书。
文革期间,我国教育发展近乎停滞不前。文革结束之后,学校教育回归正轨,乡土地理教材开发再次纳入教学计划。1978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地理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指出“乡土地理是中国地理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可包括本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理和本县地理。”此后,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陆续编写出版了本地区的乡土地理教材。1987年,国家教委召开了乡土教材工作会议,批评一些地区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很突出”,并指出我国“初、高中毕业生的绝大部分都要留在本地工作”,而他们又“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很不了解”,所以“加强乡土教材建设是改革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12]当时,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都编写了乡土地理教材,有些地方还编写了县级范围内的乡土教材,其中浙江省85%的县,湖北省32%的县,云南省22%的县都编写了乡土地理教材。[13]此次会议之后,各地的乡土地理教材开发迅速升温,并很快向县级层面扩展。如1990年,山东省80%的县、安徽省70%的县已经编写了乡土地理教材。[14]在当年召开的全国乡土教材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获奖的乡土地理教材占乡土教材总数的45%。[15]上海、四川、广东、辽宁等许多省份还在专门的地图出版社出版了本省乡土地理图册。这一时期,乡土地理研究与乡土地理教学研究均获得了较大发展。杨慎德、陈胜庆、景春泉等分别编写了与乡土地理教材相关的书籍。
3.乡土地理教材的蓬勃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
世纪之交,我国启动了第八次课程改革,倡导教材开发的多元化,鼓励各地开发地方课程与教材。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实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2001版和2011版《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均明确规定“乡土地理是必学内容”,这为乡土地理教材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使我国乡土地理教材开发迎来了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局面。
目前,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已开发了本省(区)的乡土地理教材,而市、县一级的乡土地理教材更是不胜枚举。省一级的乡土地理教材多以《××地理》、《××乡土地理》为名,如《上海市乡土地理》、《广东地理》、《甘肃地理》等。县一级的乡土教材常常以《我爱××》、《美丽的××》等为名。有一些实力较强的中学也尝试开发了校本课程类型的乡土地理教材。此外,随着新世纪初国际交往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西方国家由民间组织发起编写乡土教材的模式也被引入我国。如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欧西部基础教育项目等资助开发的乡土地理教材,对国内乡土地理教材开发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推动作用,如北京天下溪开发的环境教育主题乡土教材受到众多好评。
这一阶段,有关乡土地理教材研究的期刊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均大幅增加。CNKI共收录了2000年以来以“乡土地理”为关键词的文献约550篇,其中硕士论文67篇。不过与论文的高产相比,著作的出版数量相对较少。从引文来看,王静爱编著的《乡土地理教学研究》、《乡土地理教程》对相关研究有较强影响力。
二、乡土地理教材的变迁特点
我国的乡土地理教材脱胎于清末的乡土志,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先后共出现了清末民初、20世纪50年代末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期的四次开发高潮,其目的、功能、结构、体例等等都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乡土地理教材目的的变化
清末的学者编写乡土教材是基于国家危难的背景,其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情感(当时称为“爱国必自爱乡始”)。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是基于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背景,是为了培养了解家乡并富有经验的,能够留在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直到新世纪初,乡土地理教育逐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2.乡土地理教材功能的变化
清末的乡土地理教材(以及许多乡土志)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小学堂的教科书。乡土教育课程是当时的核心课程,占据了相当多的课时。民国后,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步形成现代教育制度,依照国家课程标准(或大纲)统一编写的教材逐步增多,乡土地理教材所承载的教科书的重要地位逐渐下降。时至今日,大多数乡土地理教材主要用于初中阶段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3.乡土地理教材结构的变化
早期的乡土地理教材几乎都是地方志式的内容结构。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资料性著述,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常被形容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地方志式的乡土地理教材通常类似一本地方志的简缩版。建国以后的乡土地理教材大多采用地理学科式结构,按照地理学的内容框架编排。一般 “以罗列和叙述当地地理要素为主,通常采用‘地理八股’,即按位置、地形、气候、河湖、工业、农业、交通、城市的顺序加以排列。”[16]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专题式的结构。专题式乡土地理教材常以地方发展中的某一个专门问题为核心知识来组织教材的章节内容,如环境保护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随着“多元文化”理念渐受重视,民族文化、性别平等、社区发展等专题也受到不少乡土地理教材编者的关注。
4.乡土地理教材体例的变化
早期的乡土地理教材体例差别较大,有叙述为主的,有诗歌形式的,也有问答形式的(如1933年黄守孚编写的《嘉定地理》)。[17]而当前的乡土地理教材绝大多数以客观的第三者陈述为主,较为严格地遵循了课文系统(基本知识材料)、图像系统(包括景观图、统计图表、地图、示意图等)和活动系统(提供给学生的活动指示、作业)的设计体例。这种体例能够更好地兼顾可读性、科普性、趣味性和参与性。
5.乡土地理教材与其他科目关系的变化
乡土地理与乡土历史由一体演变为分科的变化值得关注。清末民初的较长时期内,独立成书的乡土地理教材虽有但并不多,乡土地理知识大多与乡土历史、乡土格致等相融合,以“乡土志”的名称作为中小学教材。民国初期,随着“新学制”的建立,乡土格致从乡土地理中分出。民国中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乡土地理与乡土历史大多分离,独立成书。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早期乡土志主要由各地受到新式教育影响的地方官吏、知识分子编写,而民国以后则大多由系统接受了新式分科教育的专门人士开发,故而乡土史地分科出现情形较多。二是乡土历史的内容大多比较稳定,而乡土地理的内容除了自然地理部分变化较少外,人文地理的内容通常变化较大,需要经常修订。三是因为乡土地理内容一般争议较少,而乡土历史教材经常容易引发争议,其编写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三、乡土地理教材的发展思考
考察我国乡土地理教材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乡土地理教材在西学东渐中自国外移植引进,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历经了从乡土志到乡土地理的蜕变,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快速成长,在新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切合了课程政策的契机,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天地。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将日益受到重视,乡土地理教材对学生成长、对区域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教材研究和教材开发的视角反思当前乡土地理教材开发现状,可以发现乡土地理教材建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理论层面
从现有文献来看,乡土地理教材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有学者称之为“理论意识不够”。[18]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的理论视角单一。研究者大多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介绍乡土地理教材开发的相关理论,如陈胜庆的《乡土地理教育新论》、景春泉的《中学乡土地理教学与乡土地理研究》、王静爱的《乡土地理教学研究》等,而从其他学科视角的理论探讨很少。其次,现有研究缺乏对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深入思考。对已有的乡土地理教材的内容、方法、效果以及开发模式等研究很少。这使得可借鉴的成熟的乡土地理教材开发模式少之又少,以至于许多地理教师开发教材时不免陷入“地理八股”的老套之中。再者,乡土地理教材的理论体系尚未建构起来。乡土地理的概念怎样阐释?其范围其类型结构有哪些?对于学生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价值?如何准确定位才能使乡土地理教材得到切实应用?如何处理好与国家课程层面的学科课程的关系?如何协调与其他乡土科目的关系?如何彰显乡土特色?现有研究对这些方面所述甚少。
加强乡土地理教材理论研究有很多途径,但运用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来丰富和支撑理论创新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从乡土地理教材的本质属性来看,教育性是第一位的,所以除了地理学之外,还应该从教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视角来寻找理论基石。笔者认为,由格尔茨等人类学家提出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理论对乡土地理教育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地方性知识是指在一定的情境(如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种族的等)中生成并在该情境中得到确认和辩护的知识体系。”[19]它为乡土教材的开发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借鉴以及方法上的指导,使得乡土教材的开发能够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石上,具有现代性和国际化视野。[20]“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具有相似的含义,包含了地理、历史、文化、艺术等各门知识。尽管乡土以外的人可能难以接受和理解这些知识,但它对于生活在乡土之上的人的发展,对这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含义。例如黄土塬上的地坑院,在外人看来会感到压抑,但事实上地坑院式的住宅不仅避风保温,冬暖夏凉,还减少了对木材、耕地等当地稀缺资源的浪费。竺可桢先生曾形容地理课程为“联络各科之枢纽也”,其实乡土地理课程同样处在枢纽位置上,它显然更适合吸纳并融合乡土历史、文学文化和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构建起一个整合地方性知识的教育平台。
2.实践层面
1.3.5 流动性的测定。采用固定漏斗法测定休止角以比较颗粒的流动性:将3只漏斗竖直方向连续固定,漏斗置于其最底端距下面水平放置的坐标纸1 cm处,将样品自漏斗壁倒入最上面的漏斗中,由最下端流出形成圆锥体,样品加入量以形成的圆锥体尖端接触到漏斗底端为准。然后由坐标纸测出圆锥底部直径(2R)、3个漏斗的高度,按以下公式计算:
在教材开发过程中,教师作为教材开发主体的地位亟待加强。清末的乡土地理教材开发以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师为主体,民国时期以地方知识分子和学校教师为主,解放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以学校教师为开发主体,但在当前,能够参与乡土地理教材开发的教师却并不多。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很多教师缺乏编写乡土地理教材的基本能力。笔者曾访谈一些参加2012年“国培计划”的省级骨干教师发现,“不知道怎么开发”、“文字表达能力欠缺”是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有老师认为,“关于这片土地,我知道的确实很多,但我写不出来,也写不好”。毫无疑问,教师最具有条件也最应该成为乡土地理教材的开发主体。要提高教师的乡土地理教材开发能力,一方面应该培育和成立乡土地理教材的学术组织,建立有较大影响力的定期会议交流机制,扩大教师获得专业支持的渠道。另一方面,还可以借鉴国内外“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计划”的经验,构建中小学教师与大学专业研究人员联合的专业共同体,在课题合作、研究互动中逐步提升教师的开发能力。
在教材使用过程中,乡土地理教材难以进入课堂教学,“有而不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已开发的乡土地理教材常面临三类问题。一是没有课时。根据课改方案,乡土地理教材可以使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课时,但事实上这些课时常常被其他教学科目占据。大部分乡土地理教材只好供学生课外自学使用。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许多教师愿意参与教材开发过程而不愿参与教材使用过程。教材一旦开发出来可以作为评职称的成果,但承担乡土地理教学工作却难以被现有的以成绩为主导的教学考核机制认可。三是经费保障不足。很多地方财政和教育部门并没有专门的乡土教材预算支出项目,学校更难负担印刷成本。所以不少乡土地理教材只使用一两年就悄无声息了。甚至在一些地方,乡土地理教材开发出来后的主要功能是应付上级检查和作为学校的宣传材料。
乡土地理教材的有效使用必须基于一套有力的政策保障,这必然涉及现有教育系统的许多改革措施,需要各方面的深入思考和不断改进。但有一点应该成为共识,乡土地理教育提供了人的成长不可或缺的经历和体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乡土志例目》把乡土地理课本命名为“乡土志”,而非“乡土教科书”,反映出传统学科分类思想的影响。参见王兴亮.清末江苏乡土志的编纂与乡土史地教育[J].历史教学,2003(9).
②此处只列了在孔夫子旧书网见到正式印刷书籍的照片,笔者未能亲见,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也未检索到。
[1]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96.
[2]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96.
[3][6]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6.
[4] 王兴亮.爱国之道,始自一乡[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87.
[5] 陈泽泓.爱国未有不爱乡——试析黄节编著广东乡土教科书[J].广东史志,1999,(2):50-54.
[7] 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中国地方志,2004,(2):45-50.
[8] 葛绥成.乡土地理研究法[M].上海:中华书局,1939:2.
[9] 杨尧.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32-139.
[10][15] 柳斌.重视和加强乡土教材建设——在全国乡土教材建设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J].课程·教材·教法,1990,(8):1-2.
[11]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編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8, (5):120-122.
[12][13] 王明达.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推动乡土教材的建设——在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J].课程·教材·教法,1987,(11):1-5.
[14] 佚名.全国乡土教材建设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J].学科教育,1990,(4):6-8.
[16] 孙大文,陈澄,陈胜庆.试论乡土地理教材的改革[J].学科教育,1990,(4):7-10.
[17] 巴兆祥.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J].安徽史学,2006,(6):52-58.
[18] 滕星.“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J].中国教育学刊,2010,(1).
[19] 王鉴.地方性知识与多元文化教育之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4):1-5.
[20] 刘卓雯.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乡土教材开发及使用[N].中国民族报,2009.
* 本文系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SKQNYB11012)的阶段性成果,研究还得到香港乐施会乡土教材开发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CHG-94705-01-0707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