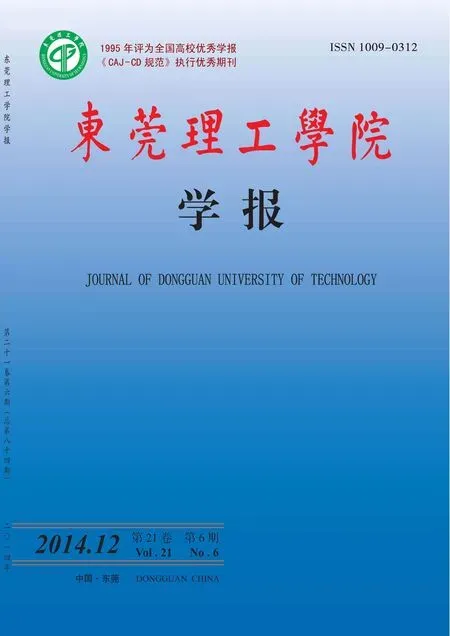生态学原理在毛泽东诗词翻译中的运用
曾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公共外语教学部,湖南长沙 410205)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自然界中的相互作用、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相互作用。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伴随着文字的创造、语言的产生和文化的形成,不同语言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活动就没有停止过。而翻译活动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其诞生和发展也始终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受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又对人类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翻译生态学,主要研究翻译本体与翻译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影响翻译活动的翻译生态环境以及翻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给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1]。
一、翻译生态学及其基本原理
(一)翻译生态学
翻译生态学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外,皮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2]于1988年在其出版的教材中最早使用“翻译生态”这个概念,提出整个翻译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生态学特征。而“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翻译理论家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的《翻译与全球化》一书中,Cronin[3]将翻译生态学定义为:一种由小语种的使用者和翻译者来控制的翻译实践活动,由他们来决定外界语言和他们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内容、时机和方法(a translation practice that gives control to speakers and translators of minority languages of what,when and how texts might be translated into and out of their languages)。并认为,生态翻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文化控制相关的。在国内,许建忠教授怀着“对翻译生态学做系统性探索并完成将生态学这一自然学科和翻译学这一社会科学(在西方称为人文科学)充分融合来研究翻译”的强烈愿望,完成了对翻译生态学初步的较为系统的总结。翻译生态学, “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和翻译研究,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4]。此外,刘国兵[5]、黄家欢和顾飞荣[6]、王亚敏[7]、代国晶[8]等很多学者以翻译生态学为视角,对翻译活动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研究。曾清和刘明东则以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为例,研究了翻译生态的内在功能和外部功能,揭示了毛诗翻译的内在运作关系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9]。
(二)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生态学原理就是生物在其存在的各个水平上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环境的平衡与均衡关系[10]。而翻译生态学不论是研究个体生态,或是群体生态,不论是翻译生态的小系统,或是大系统,也必然存在与自然生态类似的现象以及相应所遵从的原理。本文以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生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其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与最适度原则、翻译的节律以及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
二、毛泽东诗词翻译的生态学原理研究
(一)限制因子定律
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西(Baron Justus Liebig)发现,作物的产量并非经常受到大量需要的营养物质的限制(它们在自然界中很丰富),而是受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限制,因为,虽然作物对这些微量元素的需要量很少,但是土壤中的含量也非常稀少。因此,他提出“植物的生长取决于处在最少量情况食物的量”的主张,即最小因子定律。后来,人们发现某些因子的量过低或过高都限制着生物的生长、繁殖、数量和分布,并把这些因子叫作限制因子。从翻译生态的角度来讲,限制因子不仅包括自然因素,而且包括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此外,限制因子的限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个体生态的影响。
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生态而言,翻译活动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因子。自新中国建立之日起,文艺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也逐渐兴起,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开始出现毛诗的英译。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经济活动几近停滞,而文化教育也近乎荒废,这时,影响翻译生态的社会因子过低,翻译活动也基本停止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行业蓬勃发展,之前制约翻译生态的社会因子恢复正常,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也重新开始兴起。
此外,译者的精神因素也是影响翻译生态的一个重要限制因子。翻译策略上的选择受制于翻译主体的翻译目的,翻译目的又受制于主体的人生态度和个性气质。比较明显的差异体现在中译本和外译本之间,以及官译本和民译本之间。汉语讲求内敛和含蓄,注重意会而非言传,诗词更是强调其中的意境。要想做好诗词翻译,首先要求译者本身能够对原诗有深刻的理解,其次才能考虑翻译。而外国人对中文的学习和理解,尤其对诗词的理解,很难达到足够的深度,在这一点上远不及中国人对英语的理解程度。因此,中国人翻译的译本和外国人翻译的译本之间还是存在相当的差距。另外,在国内出版的译本又可分为官译本(官方组织翻译的译本)和民间的译本(如赵甄陶、黄龙、辜正坤、许渊冲等的译本)。官译本受历史条件影响,政治色彩稍显浓厚,翻译的策略和方法也不及民译本丰富充实。以上两方面的差别,充分地体现了译者的精神因素这个限制因子对翻译生态的影响作用,即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以及对原语语境的理解制约了译文效果。
(二)耐性定律与最适度原则
1913年,美国生态学家谢尔福德(V. E.Shelfort)指出,一种生物能够存在与繁衍,要依赖一种综合环境的全部因子的存在,只要其中一项因子的量和质不足或过多,超过了某种生物的耐性限度,则使该物种不能生存,甚至灭绝。这一概念即被后人称为谢氏耐性定律。因此,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有一个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界限,生物只有处于这两个限度范围之间才能生存。在此基础上,梅耶(Mayr)提出物种分布最适度原则,此原则在翻译生态学上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翻译生态的个体、群体、系统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周围环境的各种生态因子都有自己适应范围的上限和下限。要保持翻译生态的和谐稳定发展,这些生态因子最好保持在此范围内,否则翻译活动也会受到各种制约。
对诗词的翻译而言,如何表达中国古诗词在音、形、意上的特点,以及如何正确传递毛泽东诗词中所普遍包含的各种典故[11]和数词[12],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这里必须考虑译语读者的文化差异和思维习惯,也要结合译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如果纯粹保留中国文化典故的特点,或者简单地直译数词,高估了译语读者的知识准备并忽略了译文的可理解性,可能会使译语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很难体会原诗所要表达的意思,也不能顺利地传递其中的中国文化。反之,如果过度“归化”,译语读者倒是可能很容易看懂译文,但是原诗中所包含的信息被大量遗失,未能传递出去,也失去了诗词翻译的意义。以上两种情况都是诗词翻译生态中耐性定律的体现,而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其诗词中所蕴含的艺术性、思想性和革命性是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在翻译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表达。因此,需要根据生态原理的最适度原则,在翻译时考虑翻译生态环境的各种生态因子的适应范围,尽量让它们都处于上下限之间,这样更加有利于保证翻译主体的生存与发展。
那么在翻译诗词的时候,如何考虑满足这种生态的最适度原则呢?许渊冲根据中国古诗词的特点,提出“译文应该尽可能传达中国诗词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为了传达诗词的上述三美,译文‘意似、音似、形似’的程度是可以变更的”[13]。从具体的翻译方法上来说,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诗人的名句和词汇,使之“洋为中用”。例如莎士比亚的名篇《奥赛罗》(Othello)中有一句:The chidden billow seems to pelt the clouds.可以借来翻译“白浪滔天”:The clouds are pelted by breakers white. 有时,毛泽东诗词中有些意美的词汇在英语中找不到意似的译文,这种意美有时还是音美或形美造成的。这时,要传达毛泽东诗词的意美,可以选择和原文意似的绝妙好词,也可以借用英美诗人喜闻乐见的词汇,还可以借助音美、形美来表达原文的意美[14]。这种方法就是生态理论中最适度原则的生动体现和灵活运用。
(三)翻译节律
生物节律,又称生物钟、生物韵律,指的是生物体包括生理、行为及形态结构等随时间作周期变化的现象。这一点在人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每个人自诞生起都在按一昼夜为周期进行作息,而人类的时间也是按照太阳(阳历)或者月亮(阴历)的运行周期进行计算。在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翻译节律。
首先,对于翻译活动来说,存在着从兴起到低谷,再到高峰的发展节律。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最早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195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19 首译诗,算是国内最早的比较集中的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15]。此后,受文革等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的翻译进入了一段低谷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鲜有译作问世。直到1976年,《毛泽东诗词》英译本才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随着改革开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翻译活动迎来了大发展时期。1992年到1993年,赵甄陶、赵恒元、黄龙、辜正坤和许渊冲分别出版了自己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其次,汉语本身就是一种音律性很强的语言,而诗词则更是音韵和节律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曾说:诗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见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译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见《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里“形象思维”是指意美;“大体整齐”是指形美; “押韵”是指音美[14]。音和形都可以看作是节律。从音上来说,中国诗词有节奏、押韵,毛泽东的诗词讲究平仄;译成英语时也需要注意押韵,可以采用英美诗人喜见乐用的格式,采用抑扬格和扬抑格,选择和原文音似的韵脚,或借助双声、叠韵、重复等方法来表达译文的音美。如《蒋桂战争》,上半段押韵的“变”、“战”、“怨”、“现”,翻译成rain,again,pain,vain[16],就十分成功。
最后,从形上来说,中国古体诗主要是五律和七律,不仅长短上有要求,用词上有时还会有对称,即便是词曲也有固定的格式和曲调。而翻译成英诗时,最好也能够做到形似,至少也要做到大体整齐,因此可以借用英诗的形式,如亚历山大体或英雄体。例如,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不但对仗工整,而且有叠字。译文为:
In the steep sky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
On the vase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16]
这里译者不但做到了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状语对状语,而且还用了“sw”的双声来译“滚滚”,用“gr”的双声来译“微微”,最后,在结尾还用了by 和high 来完成押韵,在很大程度上传达了原文的形美和音美。
(四)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
从系统论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来看,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有机整体,系统中的各单元和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参数及其变量,彼此间具有互相协调和制约的作用,从而产生整体效应。这就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4]。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生态来说,译者与译语读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译者与译作的研究者之间也相互作用,而译者、译语读者和研究者的翻译、阅读和研究过程又必然受到各自所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一种动态的交互过程,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诗词翻译生态的局部来说,需要注意各因子的耐性范围,不要让某一限制因子超出其耐性极限,从而影响翻译生态的平衡和稳定。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形、音、意兼顾,考虑到中西方语言和诗词的差别,可以采用等化、浅化、深化等方法,尽量发挥译语的优势,必要时可以考虑再创造来找到更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而从翻译生态的整体来说,则要注意保持翻译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平衡,因为有了合适的翻译生态,自然就会产生相应的译作,这是符合翻译生态的内在功能的[9]。反过来,翻译生态内部的稳定也会有助于保持外部生态环境的和谐,从而维持翻译生态这个大的系统正常运转。
三、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除了物质产品出口之外,我们也应该开始重视文化输出,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刘明东[17]指出,要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国,都离不开翻译这一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手段。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是介绍传播中国诗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看,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也需要遵从相应的生态原理,如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与最适度原则、翻译的节律以及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要想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就应该尊重这些原则,任何违反原则的行为都会破坏这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发展。如果当译者、译语读者和研究者都和谐相处,翻译、阅读和研究行为都正常运作,翻译所处的生态环境稳定良好,那么整个翻译系统的生态功能就能得以保持正常,翻译系统才能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
[1]刘爱华. 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辩:“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1):75-78.
[2]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rtfordshire:Prentice-Hall,1988:102-109.
[3]Cronin M.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 London:Routledge,2003:167.
[4]许建忠. 翻译生态学[M].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3.
[5]刘国兵. 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外语教学,2011(3):97-100.
[6]黄家欢,顾飞荣. 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十七大报告英译研究[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374-375.
[7]王亚敏. 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实践中的“平衡”与“失衡”[D]. 天津:天津理工大学,2010.
[8]代国晶. 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中译英教学[D]. 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2011.
[9]曾清,刘明东. 毛泽东诗词翻译的生态功能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1):118-121.
[10]郑师章,等. 普通生态学:原理、方法和应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31.
[11]曾清. 毛泽东诗词中典故的文化翻译[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30-133.
[12]曾清. 毛泽东诗词中数词的翻译研究[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3):10-12.
[13]许渊冲. 如何翻译诗词:《唐宋词选》英、法译本代序[J]. 外国语,1982(4):12-18.
[14]许渊冲. 如何译毛主席诗词[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2):1-6.
[15]张智中. 毛泽东诗词英译综评[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1):75-78.
[16]许渊冲. 毛泽东诗词与诗意画[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26.
[17]刘明东,陈圣白. 翻译与文化软实力探析[J]. 外国语文,2012(4):9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