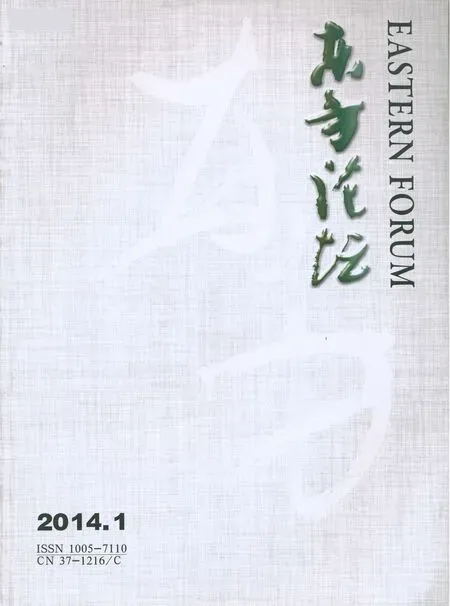禅宗心性论要旨及其在唐代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张锦辉 苑丽丽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2.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化与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禅宗心性论要旨及其在唐代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张锦辉1苑丽丽2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2.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化与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文人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二重性,是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通过对禅宗心性论要旨的论析,可以发现:心在文人禅诗中主要体现出禅心、尘心和猿心三种内型,并且与文人形成互动,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文人禅诗;禅心;尘心;猿心;互动
禅诗,顾名思义,即跟禅有关的诗歌,是一种融通宗教(禅)与文学(诗)的特殊创作。文人①文人在中国社会中,不仅仅就是传统所称知识分子,应当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文人阶层由英国人麦高温在其专着《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中提出,龚鹏程先生《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此有专门论述,本文在写作中采用文人称谓。禅诗,即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作为有唐一朝文学的代表——唐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据对清人所编《全唐诗》和今人所辑《全唐诗补编》的检索,我们发现生活于大唐时代的文人,几乎都有诗歌流传下来。唐代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儒﹑释﹑道三教在相互融合中发展,由此造成唐型文化②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由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提出,傅先生在其文章《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对此做了详细论述,可参看。的多元性,正如吴怡先生所言:“在唐宋间的中国思想界根本是一个大熔炉。这时期,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学说,都是兼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1](P28)因此,在唐代我们很难说哪位文人只受到一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身上往往会呈现出多家思想的影子,③例如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所受的思想并非是单一的。在李白的身上,既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同时还有像佛教、道家、道教、游侠等思想;杜甫的身上,同样也是在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之外,还有像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浸染。除此之外,像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唐代诗人,他们所受影响基本如是。而在这其中又以一家思想为主。唐代文人在浓厚的诗歌氛围熏染下,又直接接受禅宗教义的浸淫,那么作为其思想的载体——唐诗,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时文化的特色,文人禅诗即是如此。在这些诗歌中,我们随处可以染指到禅宗思想的气息,相比于禅宗典籍的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缺乏艺术美感,文人禅诗在让我们享受唐诗无与伦比的艺术美感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博大精深的禅文化。有鉴于此,本文即尝试结合禅宗哲学心性论对唐代文人禅诗作以阐释。
一、禅宗心性论要旨
心性论是整个佛教的核心理论,中唐圭峰宗密大师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道:“一藏经论义理,只是说心。”[2](P28)这更是禅宗哲学思想的精髓。“心”在梵文中义为“集起”,指各种心识功能的合集,是人们心理活动﹑精神现象﹑内在生命的主体。“性”也称“自性”﹑“本性”,指一切事物固有的性质﹑本质。《黄檗断际禅师传心法要》曰:“心性不异,即性即心。”[3](P26)合起来“心性”在梵文中义为“心实相”﹑“心真如”,指的是个体自身本来所具有的澄澈清明不变的体性。禅宗将印度佛教心性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最终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禅宗心性论。由于对“心”的强调,故禅宗又称佛心宗或心宗,元代禅门高僧中峰明本禅师曾说:
禅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禅之体也。……然禅非学问而能也,非偶尔而会也,乃于自心悟处。凡语默动静不期禅而禅矣,其不期禅而禅,正当禅时,则知自心不待显而显矣。是知禅不离心,心不离禅,惟禅与心,异名同体。[4](P73)
至于心性论在禅宗中的地位和作用,方立天先生是这样说的:
从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来看禅宗的基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5]
可见,心性论是了解禅宗思想的基础,不对禅宗心性论的要旨有所认知,恐怕也难以叩开禅宗这笔蕴含无尽文化宝藏的大门。至于禅宗心性论的变化和发展,前贤论述颇多且中肯①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方立天先生有《心性论——禅宗的理论要旨》(《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4期)、《简论中印佛教心性论思想之同异》(《佛学研究》1996年第5期)、《印度佛教心性思想述评》(《佛学研究》1995 年第4期)、《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中国哲学史》1992年第1期)等文章,论述详细,可参看。,笔者不再赘述。
首先,禅宗心性论认为心是万法之基础,处于核心地位。相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6](P10)此后从达摩创宗开始,他的徒子徒孙便一直将心放在首要位置,强调“诸佛心第一”。达摩在其《悟性论》中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二祖慧可“是心是佛”,“是心是法”[7](P107);三祖僧璨“心若不异,万法一如”[8](P4);四祖道信“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9](P12);五祖弘忍“守本真心”[10](P177)。到了六祖慧能,他在继承前辈禅师关于心性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自心(自性)本觉在禅悟中的地位,认为:“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11](P66)在他之后,其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更是为禅宗心性论注入了新的活力,直接将一切归结为心,指出:“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12](P2252)“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7](P610-11)以上是禅宗历代祖师关于心性在禅宗中的表述,不难发现,禅宗历代祖师对心之重视,无心则无禅,无心则一切都会变的混沌或者停滞。
其次,禅宗心性论注重主体对自我心灵的体认,即对本心的认识。《坛经》云:“何期自性本身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11](P20)可见,对自家自性本心的体认是禅宗心性论的关键。临济义玄大师曾大声疾呼:“汝等诸人,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诸人面门出入。”[13](P70)“赤肉团”指由五蕴合成的我们的肉体,而“无位真人”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在禅宗看来,只有回归本心自性,世俗眼中的善恶﹑美丑﹑是非﹑迷悟﹑色空﹑长短﹑有无等相对的二元观念,此时才能在澄明的本心中得到超越。正如吴言生所言:“本心的特点是超越性,超越有无﹑净秽﹑长短﹑取舍﹑生灭﹑去来。”[14](P13)本心的状态是什么?吴言生是这样论述的:“本心自性如同虚空,广袤无垠,清虚灵明,不动不摇,无圣无凡。”[14](P14)在对本心自性的体认下,主体才不至于舍父逃走﹑迷头认影﹑才可以“净裸裸,绝承当;赤洒洒,无回互。踏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15](P282)所谓本来面目②本来面目,也叫本地风光、本觉真心、本分田地、自己本心等,是本来的自己,人人本具,超越一切对立。吴言生师在《禅宗哲学渊源·禅宗哲学本心论》中对“本来面目”做了详细阐释,可参看。,其实就是每一个主体没有蒙受世染时的原真心态,是我们纯真的人性,它“号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来面目,亦曰第一义谛,亦曰烁迦罗眼,亦曰摩诃大般若”。[6](P1267)禅宗心性论注重对个体心灵的体认,强调回归自己的本心,其实就是要求每一个个体在探寻生命的历程中,要善于把握自己的生命,换言之,生命就在自己的心中,莫向外求,一旦本心不识,就会破坏本初状态,产生妄心。在禅宗看来,妄心并不是每个个体内部的那颗血肉之心,而是对所见之境产生的诸种念头和思想,即“六尘缘影”。妄心一旦生起,也就坠入了二元对立的世俗界,各种无明烦恼自然也就纷至杳来。
最后,禅宗心性论强调对心的体验和心灵的感悟,要注重在当下生活,即日常生活中去把握。在禅宗看来,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佛不但存在于每个主体的心中,而且也存在于当下生活﹑日常生活中。只有将自己的心修好,才能获得大智慧,大珠慧海禅师说:“心者,是总持之妙本,万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无住涅槃。百千万名,尽心之异号耳。”[12](P2267)但是为了修心,许多人煞费心机,访寻名师﹑禅堂打坐﹑诵读经书等成为他们的必修课,结果到头来并未能真正领悟禅的精髓,于是才有了开悟之后,酣畅淋漓的真心之言:
这里无祖无佛,达磨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6](P374)
所以必须以平常心去体验当下的生活,享受眼前的生活,如此才会修成正果,就如马祖道一禅师所言: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12](P2252)
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去看待周围的事和物,彻底消解心性本源所带来的二元对立,以般若利剑斩断污染与清净﹑烦恼与菩提之间的距离,自然就会发现生命之美的灵光﹑活泼的生命流程,最终超越现实,到达禅悟的最高之境。其实这与禅宗要求从“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16](P204)中参悟禅道,从“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7](P170)中寻觅禅意如出一辙。所以,禅宗反对割弃现实丰富多彩的当下生活而不顾一切的扭曲自性去寻求所谓的超越,它强调的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11](P73)
总之,禅宗心性论认为修禅成佛,其实就是修心,包括“治心”﹑“安心”﹑“定心”﹑“识心”等过程,只有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禅悟体验后,才能使自己的心回归于本初,识见自家本性,实现最终的超越,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就有了对心的不同体认与感悟。
二、禅宗心性论在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禅宗对心的高度关注也反映到唐代文人禅诗中,遍览整部《全唐诗》,我们发现不少文人在自己的禅诗中言心,归纳起来,心在文人禅诗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类:
禅心(无心)。“教义名词。禅定之心。此心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状态,进入泯绝一切外物的境界。或指通过禅定修习而证得的本来清净心。”[17](P1225)换句话而言,禅心即禅者的心,它既是一种心无杂念﹑清净禅定的心境,也是所追求的觉悟之心﹑佛性之心。较早在诗文中言及禅心,可上溯到(南朝)梁文人江淹,他在《吴中礼石佛》一诗中写道:“禅心暮不杂,寂行好无私。”[18](P114)唐代文人禅诗①由于文人禅诗中涉及到空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关系,此处只举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中,禅心也屡次被文人提及,如:
水入禅心定,云从宝思飞。(宋之问《奉和幸大荐福寺》)[19](P471)
禅心超忍辱,梵语问多罗。(李嘉祐《奉陪韦润州游鹤林寺》)[20](P2157)
君问穷源处,禅心与此同。(李端《宿深上人院听远泉》)[20](P3246)
窗牖月色多,坐卧禅心静。(施肩吾《宿南一上人山房》)[20](P5632)
高阁清香生静境,夜堂疏磬发禅心。(温庭筠《宿云际寺》)[21](P731)
可见,无论是初盛唐还是中晚唐,文人都喜欢在自己的诗歌中使用“禅心”这一术语,其原因显而易见,唐代文人更多的是将佛教作为医治自己受伤心灵的清凉剂,而“禅宗寻求内心的宁静恬淡,确有引导诗人逃避现实的消极面。”[22]正好契合了当时文人之所需,故用其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作为禅心的同义语,“无心”也被唐代文人常常提及,如:
杖锡闲来往,无心到处禅。(刘长卿《喜鲍禅师自龙山至》)[23](P459)
往往无心云,犹起潜龙处。(钱起《归义寺题震上人壁》)[20](P2617)
万缘销尽本无心,何事看花恨却深。(吴融《和僧咏牡丹》)[20](P7944)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渔翁》)[24](P1252)
无心,即自己的本心超然于妄念。在禅宗看来,妄念源自于妄心,妄心则就像幻影,一旦生起,则阻碍众生回归于自性,使众生无法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有僧人问:“什么是心的解脱?”百丈曰:“既不求佛,也不求理智;既不怕地狱苦难的威胁,也不必羡慕天堂乐趣的诱惑,一切法都不必拘泥,这就叫解脱无碍。”(《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葛兆光先生针对禅宗这一特点,曾作过如下分析:
我心是佛——我心清净——依心行动——适意自然,这种宇宙观、时空观、人生哲学、生活情趣极为精致的结合,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顺序十分自然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慧能、神会之后,几乎每一个禅宗大师都要大讲这种“适意”的生活情趣与现世自我精神解脱的人生哲学。[25](P106)
唐代文人在自己的诗歌中反复吟咏禅心﹑无心,其实就是源于自己对禅宗的向往。文人在宦海沉浮中,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痛苦与辛酸后,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宗教,尤其是当时盛行的禅宗,其意旨很明显,就在于通过禅宗的修行法门,摆脱尘世生活的烦恼,使自己迷失的本心重新回归于禅心或者无心,实现自我的精神解脱。《坛经》讲“立无念为宗”,就是让世俗之人放下对立的二元思维,以平常心去看待一切,正如尚之煜先生在《碧岩录》第八十则后的点评所言:
学道之人要复如婴孩,离分别取舍心,面对荣辱功名、逆情顺当,眼见色与盲等,耳闻声与聋等,如痴似兀,其心不动而又寂照不止。[26](P403)
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不为外物所干扰﹑打动,也就是《佛国品》所说“毁誉不动如须弥,于善不善等以慈”。禅宗将其归纳为“八风吹不动动天边月”,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一颗禅心或无心。可是,综观有唐一代的文人,又有多少文人能真正做到呢?我们不能否认唐代社会对文人的各种诱惑,许多文人都以“济苍生,安黎元”为己任,然而现实与理想是有差距的,当他们遭受挫折之后,这才意识到尘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影,一切所谓的物质﹑名利等诸相其实都是由人的妄心引起,此时才将心栖于禅门,才开始了对自家本心的追寻。
尘心。即带有二元对立思维之心,简言之指还没有脱去俗念的“小心”。二元对立思维不被泯除掉,“小心”就会与任何其他事物有所连接,自然各种世俗尘念就会产生,例如生与死﹑善与恶﹑净与垢等。体现在文人禅诗中,则表现为既有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积极用世心态;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苟安心态;也有恬淡去欲﹑心如止水的佛老心态。如: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王维《桃源行》)[27](P16)
寂灭应为乐,尘心徒自伤。(钱起《哭空寂寺玄上人》)[20](P2621)
到此既知闲最乐,俗心何啻九牛毛。(段成式《题僧壁》)[20](P6823)
更悟真如性,尘心稍自宽。(耿湋《题惟幹上人房》)[20](P2981)
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许浑《记梦》)[20](P6192)
禅心一旦被尘心所蒙蔽,那么真实的自我也就被虚幻的自我所障碍。尘心起,禅心就会被遮蔽,禅心被遮蔽,各种尘念顿时就会产生,即“心心相异”。此时智者变为愚者,悟道者变为迷途人,禅心也就变成尘心。一旦尘心动,相应的尘念就会产生,禅心也由此被障蔽。正如有学者指出:“心一旦被污染被分裂,完整才是禅境,分裂就是尘心。”[28]如何让自己从纷纭骚乱的尘心里走出来?如何将自己的“小心”与“大心”融为一体?很多文人将目光转向了禅宗。禅宗讲究明心见性,就是希望芸芸众生能在日常修行中体悟自家澄明心境。有学者指出“禅认为心态的完整和分裂,不仅是成功和失败的关键而且是烦恼和幸福的关键。”[28]据此我们来审视唐代文人,虽然摆在他们面前有很多机会,但是如何处理好这些外部的机会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是他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不少文人却未能将自己的心修好。因此,从最初唐代文人心被外物所束缚,禅心被尘心所障蔽,再到最终“小心”与“大心”背道而驰,一步步的滑向深渊,唯一的拯救办法就是只有从自我的“小心”中解脱出来,从心与心﹑自我与自我的清净完整心态的蒙蔽和障碍之中升华出来,才能把心心相异的尘心升华到心心相印的禅境,也就是“小心”与“大心”合二为一。
猿心,也称心猿,佛教语,指“心神散乱,把握不定”,俗谓之“心猿意马”。猿猴生性好动,长于攀援,故其心是颠狂的﹑放荡的﹑乖劣的,就如普通人的思想和欲望不受控制那样,所以通常就说心即是猿,猿即是心。佛教中经常以猿比喻放纵不羁的心灵,如《心地观经·观心品第十》曰:“故心如猿猴,游五欲树,不暂住。”[29](P67)
《涅槃教诫经》曰:
汝告比丘:巳能住戒,当制五根,勿令放入于五欲。……譬如狂马无钩,猿猴得树,腾跃跳踯,难可禁制。[30](P50)
猿心一旦生起,则会误入歧途。唐代佛禅兴盛,“心猿”或“猿心”也成为文人笔下常见的意象,如:
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萧翼《答辨才探得招字》)[20](P506)
客到两忘言,猿心与禅定。(钱起《杪秋南山西峰题准上人兰若》)[20](P2608)
自为心猿不调伏,祖师元是世间人。(赵嘏《四祖寺》)[20](P6431)
寓形齐指马,观境制心猿。(包佶《近获风痹之疾题寄所怀》)[20](P2144)
一自禅关闭,心猿日渐驯。(韦庄《不出院楚公》)[31](P238)
在这里,心猿(猿心)的频繁使用,更多指的是他们燥乱不羁的心,以此作喻将他们放荡不羁﹑无法平静的内心为我们展示出来,很明显是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文人们希望通过禅宗的修行,控制自己内心所产生的各种欲念,最终使自己的心趋于平静,寻找自家本来面目,在禅诗中更多的是展现了他们对空门那种超然物我生活方式的向往。
三、禅宗心性论与文人禅诗的互动
心在文人禅诗中表现出禅心﹑尘心和猿心三种主要类型,反映出唐代文人生活的不同状态,对于了解禅宗修心和到达禅心(无心)提供了方便。同时,禅宗对心的高度重视,也使文人在禅诗中形成了以心构象,任凭心性裁熔客观物象的心性表现方式和创作手法,最终使得禅宗心性论与文人禅诗之间形成了互动。
唐代文人在禅诗中频繁谈心,其实也体现出禅宗的修心过程,即息心→洗心→净心→识心。由于对自家本心的不识,以致在尘心和猿心的干扰下,主体出现躁动和多变,被名利﹑地位﹑欲望﹑情绪﹑冲动等牵着走,所以在修心过程中首先要将自己放荡不羁的心平息下来,就如唐代文人在自己的诗歌中反复吟咏一样:
栖身齿多暮,息心君独少。(韦应物《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32](P385)
息心归静理,爱道坐中宵。(皇甫曾《赠鉴上人》)[20](P2185)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20](P2623)
永欲卧丘壑,息心依梵筵。(阎防《晚秋石门礼拜》)[20](P2843)
世俗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是充满诱惑的,虽然不少文人以禅客自居,但实则对禅仅仅只流于形式,禅对他们只是点缀而已。自然,他们的心就不能平静,热衷功名却执于功名,以致处处受挫,陷入世俗生活的桎梏。无奈之下,只好重新审视自己,一旦认识到宇宙间的一切都是幻想,便首先将自己疾驰的心息却下来,之后便是洗心。用什么洗呢?正如前文所述,唐代是一个多文化融合的时代,不少文人视佛教为清凉剂,尤其是禅宗,它们对心的重视可以说是佛教其他宗派所不能比拟的,于是文人们通过栖心于禅宗,开始将自己妄却疾驰的心用禅法去清洗,如:
松露洗心眷,象筵敷念诚。(宋之问《游法华寺》)[19](P515)
平生洗心法,正为今宵设。(白居易《送兄弟回雪夜》)[33](P519)
患身是幻逢禅主,水洗皮肤语洗心。(杜荀鹤《送僧赴黄山沐汤泉兼参禅宗长老》)[20](P8027)
洗心听经论,礼足蠲凶灾。(徐浩《宝林寺作》)[20](P2246)
洗心之后,便开始净心,让自己的心回归于本初的原真状态,赤裸裸﹑干净净,唯有如此,才能识心,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在禅宗看来,众生之所有痛苦﹑烦恼,就在于没有识心,即没有认清自己的本心。吴言生师在自己《禅学三书》中,根据自己多年来对禅宗思想的研究和体证,提出禅宗思想体系由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和境界论组成,换句话而言,也就是个体在不断探寻生命真谛的过程:本心→执着→迷失→回家,正好与唐代文人的修心过程相契合。
提供了由世俗之心到禅心的法门——传心。禅宗不依赖于文字,靠心去体悟。但是众生还是希望通过一些法门获得禅髓,就像当年的慧可向达摩大师寻找安心的法门一样。所以在唐代当文人向往于禅宗时,也希望通过一些法门获得禅心,这也就留下了不少从尘心和猿心到禅心的禅诗,如:
白日传心静,青莲喻法微。(綦毋潜《宿龙兴寺》)[20](P1371)
达磨传心令息念,玄元留语遣同尘。(白居易《拜表回闲游》)[33](P2158)
长绳不见系空虚,半偈传心亦未疏。(司空图《与伏牛长老偈二首》)[34](P117)
立谈禅客传心印,坐睡渔师著背蓬。(韩偓《江岸闲步》)[20](P7872)
以传心作喻,其实象征对禅法的皈依。通过传心,获得心心相印。在未传心之前,尘心和猿心障蔽了我们的本心,真实的心性就无法显现出来,以致于我们执着于地位﹑权力﹑声名﹑衣食等,对外在的相看不清﹑看不真﹑也看不破,看不破自然就放不下,放不下就迷惑颠倒,就痛苦。可是,一旦获得修心法门,心自然就会清凉,菩提大智慧自然就会显现,就像古人以磨铜镜,去污则明。
禅宗心性论的精髓在于使人从心灵中寻求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故注重对自我心灵的体认,反映到文人禅诗中形成了以心构象,任凭心性裁熔客观物象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手法。综观有唐一代文人禅诗以心为中心,构成了诸多意象,如禅心﹑无心﹑尘心﹑猿心等,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拓宽了唐诗的意蕴。对心的高度重视,也使得有唐一代文人高度重视自己内心的抒发,表现在诗歌中就形成了任心性裁熔客观物象,敢于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往往会造成天马行空﹑浮云流水似的构思,所以较之宋人诗歌常会出现离奇的想象﹑跳荡的思绪﹑怪诞的比附和大胆的夸张,例如李白﹑韩愈﹑李贺﹑孟郊等诗人的作品。
综上所述,禅宗心性论以心是一切的基础,心处核心地位。注重主体对自我心灵的体认,即对本心的认识。强调对心的体验和心灵的感悟,要注重在当下生活,即日常生活中去把握为要旨,深深的影响到唐代文人禅诗,以致心在文人禅诗中表现出禅心(无心)﹑尘心和猿心(心猿)三种主要内型,同时与文人形成互动,即文人在禅诗中表现出息心→洗心→净心→识心的修心过程,也为文人获得禅心指明途径,即要传心。禅宗对心的高度重视,也对文人以心构想和发挥主体的创造性提供了有益借鉴,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1] 吴怡.禅与老庄[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5.
[2] 宗密撰.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诠集都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3] 裴休撰.宇井伯寿注.吕宝水译校.裴休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 明本.天目中峰和尚广录[M].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8册[C].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
[5] 方立天.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M].哲学研究,1995,(3).
[6] 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衣川贤次,西口芳南点校.祖堂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僧璨.信心铭[M].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94册[C].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91.
[9] 净觉集.楞伽师资记[M].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1册[C].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
[10] 弘忍.最上乘论[M].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101册[C].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92.
[11] 慧能撰.郭朋校释.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13] 慧然辑.杨曾文编校.临济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14] 吴言生.禅宗哲学象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5] 绍隆等编.圆悟佛果禅师语录[M].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1册[C].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
[16] 密菴咸杰.密菴咸杰禅师语录[M].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5册[C].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
[17] 任继愈主编.佛学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8] 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M].北京:中华书,1984.
[19] 沈佺期,宋之问撰.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0] 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1] 温庭筠著.刘学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2] 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3] 刘长卿著.储仲君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4]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5]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6] 圜悟克勤著.尚之煜校注.碧岩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7] 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8] 姜超.禅——完整的心态[M].东岳论丛,1997,(4).
[29]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67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9.
[30]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24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7.
[31] 韦庄著.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2] 韦应物著.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3]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4] 司空图著.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文集笺校[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Embodiment of the Zen Mind-nature Theory in the Zen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ZHANG Jin-hui YUAN Li-l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Zen poems have religious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poets of such poems integrate their Zen refl ections into their poetic compositions. Analysis of the Zen mind-nature shows that the Zen poems, full of Zen fl avors, meanings and interests, exerted great infl uences on the writing methods, content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Tang poems.
Zen poems by scholars; Zen mind; worldly mind; troubled mind; interaction
I207
A
1005-7110(2014)01-0080-07
2013-10-07
张锦辉(1984-),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与文学;苑丽丽(1988-),女,山东青岛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文化与艺术学院教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