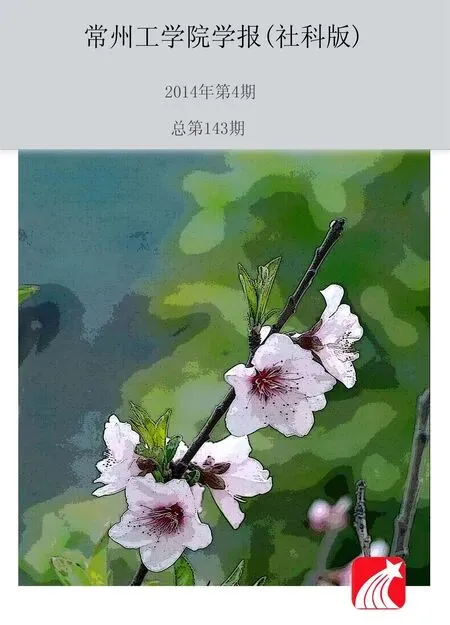无根的抵达
——从《抵达之谜》看奈保尔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熊亚芳
无根的抵达
——从《抵达之谜》看奈保尔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熊亚芳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在他的高度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中讲述了一个具有双重移民背景的天生流放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苦苦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文章从社会学和后殖民文学批评视角再现了作者在此历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原本期望找到精神的归属地,在实现自己的作家梦后能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然而,在三番五次的“抵达”后,却发现依然身似浮萍,体验的是希冀和焦虑、欣悦与痛苦的各番轮回。
奈保尔;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危机”一词最初用于医学领域,指的是生病时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一段时间。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管是在个体还是在集体水平上,危机几乎变成了地方性的问题。……只要是个体或集体生活的重要目标的活动突然出现不适时,‘危机’就会存在。”①因此,对于现代人,生活在多元文化融合的现代社会,当个体追寻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时,就会经历各种危机:“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陶家俊在《身份认同导论》中集中分析身份认同问题时将其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其中,自我认同指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是以自我为核心,也是启蒙哲学、想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他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在每一特定历史语境中,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通过对自我存在的反思,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而在此身份选择过程中个体会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经历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也就是说,在此找寻自我的过程中,会经历各种危机。
奈保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称为“世界文学的漂流者”。其高度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再现了作家的寻根寻梦之旅,以及在此追寻过程中深陷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时的主体体验。在小说中,作家将自己的生活转化成了写作的材料,主角以第一人称叙事,其经历与心路历程其实正是奈保尔个人生命的写照。奈保尔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在写《抵达之谜》的开始部分时,我在描绘英国乡村景色,发现有太多用英语表述的东西……我不得不确定我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观察周围世界的眼睛,我感受周围的这个人不能是我虚构的一个角色,我想我应该让他成为作者本身——先确定这一点,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创作整个小说文本。”②因此,可以说整部小说是奈保尔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生涯进行的一场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反思,在反思中审视自我,以求确立一个明确的身份。然而,在其身份选择的过程中,他最终还是未能完成完整意义上的抵达,其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所历经的各种危机在书中一一呈现,无处不在:一方面,在寻找灵魂归属地的过程中,历经多次抵达,却无法找到一片心灵的归属地;另一方面,想通过写作实现作家梦,成为作家后赋予自己一个确定的身份,却最终发现自然的我和作为作家的我始终存在着裂缝。
一、根在何处?——与归属地分裂
奈保尔是典型的双重移民,他和自己的“母国”印度的分裂从其祖辈在19世纪从印度移居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就已经开始。他一出生就拥有双重身份——天然的印度裔种族身份和不可变更的殖民地移民身份。作为天然的印度后裔,他“对于印度人社会的各种仪式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和同情,然而这个人也有另一面:他并没有真正加入到那个社会的生活和各种仪式中去。在印度大家庭中他并不幸福,他不信任较大的群居的集团”③。作为一个天生流放者,奈保尔对自己作了客观冷静的旁观者式的观察。在《抵达之谜》中,对于印度,他只是一名旁观者。在他租住的庄园中,当隐居的房东为表示对他的欢迎,给他送来几首自己写的关于印度天神克里希腊和破坏神湿婆的诗时,奈保尔异常惊讶,因为他完全没料到,在大英帝国这片土地上,竟会有人提到印度神话中的这两个人物。从这份礼物中他看到房东对印度的眷恋,但认为这种眷恋“与他的生活环境,与我,与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或我的抱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④。虽然他身上流淌着印度人的血液,拥有印度婆罗门种姓,可是那片土地对他而言,也不过跟这位英国殖民者房东一样,只是拥有承袭而来的“一种比较老的,甚至是陈旧的情感”⑤。小说的最后,在妹妹的葬礼上,奈保尔看着祭司主持印度教土地祭祀仪式,“分享”(其实是买卖)他认为的印度最好的经书《薄伽梵歌》,祭司临走时却承认由于工作繁忙,几乎找不出时间阅读此经书。在仪式上,祭司突然满怀激情地讲起国内印度人关心的政治问题。祭司角色的错位让奈保尔意识到离开印度的移民包括他自己已经不再被充满神秘感的印度辉煌的过去、圣土、神灵所主宰,印度的神圣世界已不复存在。对每个远离印度的人来说,现在这个时代使他们更远离那些圣洁。他们无法回到从前,“现在没有古船可以带我们回去,我们已经走出梦魇,而且我们已经无处可去”⑥。
奈保尔的童年和少年早期生活在特立尼达,一个融合了殖民文化和不同移民文化的孤岛。在那个殖民地的、种族混合的环境里,“他有的只是他的时代的种种偏见,他极为无知”⑦。在那里,他从小接受英国式教育。在特立尼达这样一个特殊的边缘地带,宗主国教育体制的影响无处不在,他们从思想、文化和教育上进行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按照自身的目的强行实施殖民教育。这种教育使奈保尔进一步脱离了古老的印度传统,使他梦想在外国取得成就,也使他拥有要成为一位作家的雄心壮志,他希望自己能像萨姆赛特·毛姆一样“优雅,博学,毫不惊奇”。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进行全盘否定的奈保尔,他无知,他怀疑一切,他的希望在别处,他渴求改变,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他选择了逃离,带着奖学金,带着写作的抱负,向他的过去告别,向他的殖民地的过去、亚洲人的过去告别。可是坐上飞机,那场“高升”带来的强烈美好体验后却是一种“实在的惊惶,然后是一种自我意识的逐渐缩小”。逃离特立尼达,从边缘来到中心,没有想象中那样持久的狂喜和激动,反而有“一种正在迷路的感觉,一种没有完全面对真实的感觉”⑧。这时的奈保尔只觉得有脱离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一种“抵达的屈辱”。
然后,他来到了伦敦——帝国的中心。这座从不休眠的城市夜间灯火通明的车站,连续不停放映的电影,凌晨时分也不间断的列车声,一切都完全不同于他来自的那个小岛,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然而,早上去地下室用早餐时,他却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现实的世界”。很快他便意识到伦敦市场在走下坡路。随着多次外出游览,他开始慢慢感到:“我来英国来得太晚了,无法找到原先的英国,她已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帝国的中心模样。”⑨在特立尼达岛上,殖民地人的神经促使他朝着前方,朝着国外的英国看,可当自己身处伦敦时,却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像他向往中的世界那样完美,他想象的那个完美世界存在于另一个时段,一个更早的年代。在伦敦,他只是个“过客”。
经过多年的漂泊和旅行之后,奈保尔带着一种萦绕在他脑间挥之不去的感觉——“那种废墟和被抛弃的念头,那种无所事事的念头”,来到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一个半被遗弃的庄园里休息,一座充满了往昔爱德华时代的纪念物的庄园,与当今很少联系”。刚开始,他带着一种不愿打扰任何人的陌生和慌乱,这个外来闯入者认为“这个峡谷的这些庄园和大房子中有一种古怪之气”,而他自己在这个地盘上则更是一个漂泊不定的“古怪之物”。在这片土地上,他只是个陌生的外来者,他无法像当地人杰克那样成为一个“完全适应这里景物的男子汉”,拥有一种“真正的﹑根基扎实的﹑完全适应的生活”⑩。但在这片土地上多次漫游、散步、发现和反思后,作者似乎开始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美,内心产生了强烈的爱,因为他似乎在威尔特郡感受到了第二次生活的赐予,“是第二个,也是更幸福的童年”。于是,他把两间无主的农舍改造成自己的家。然而,拥有一个安全家园的梦却被一个即将离世的老太太的造访彻底惊醒,老太太由孙子领着,来看这个她还是小姑娘时曾经和她的当牧羊倌的爷爷住过的小屋,当作者发现老太太完全被变了样的小屋“弄懵”了时,他假装自己“不是住在那里的”。
遗传而来的殖民地人的敏感神经使得奈保尔在任何一块土地上都无法安“家”,印度回不去,在特立尼达选择逃离,帝国中心却在衰落,不再是理想之地。家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永远的梦,每一块土地他只能停留,却无法驻留,他注定不能融入任何一块他经过的土地,在任何一块抵达的土地上他都没有归属感,和土地的分裂让他无法完成完整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危机时刻存在。
二、梦中迷失——与“写作的自我”分裂
奈保尔的作家梦很早就开始了。童年时迷恋电影院,因为电影院对他来说是“充满想象的地方,我的生活最深沉的地方”⑪。电影院里的外国电影使他意识到自己性格中有一种巨大的天真无知。于是,从有自我意识起,他就投身于学习,然而,抽象的学习内容跟他身处的环境毫无关联,他只好发挥自己无穷的想象力,想象自己在另一个国度的文学中生活,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使他否定自己所处的世界。另外,父亲对他写作梦想的影响很大。奈保尔的父亲在特立尼达西班牙港的《卫报》从事记者工作,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但他一生生活困顿,文学才能有限,却始终没有放弃当作家的梦想。后来他不得不把这种梦想和希冀寄托于儿子身上。可以说,父亲是奈保尔的第一个文学导师,塑造了奈保尔“写作的自我”。在奈保尔与家人的通信集《奈保尔家书》中,父亲告诉儿子:“文学创作是一种执着而孤独的奉献。”⑫他坚信儿子的文学时代正在到来,不过,“在你‘抵达’之前,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障碍,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成功者的‘预考’”⑬。奈保尔努力通过了这场“预考”,最终获得了作为作家的成功。然而,在成功前后,他都经历了自己作为自然人和“写作的自我”之间的种种分裂,和为融合分裂而努力时遭遇到的种种危机。
首先,在搜寻素材时他自我迷失。18岁第一次从特立尼达去往伦敦旅行时,奈保尔买了一本小横格本和一支永固型铅笔,因为他要像真正的作家那样旅行,必须积累写作素材。他开始写日记,寻找素材,“个人冒险”是确定的主题,然而他却不敢把自己旅行的体验和因旅行产生的内心寂寞以及在他个性上引发的变化一一记下来,因为这些东西“与我理想中的作家的日记或我正在为自己准备的作家体验很不相称”⑭。作为一个自然人,他还太天真无知。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旅行着要成为一个作家的男孩,他正在旅行以便奉献出自己”。他寻求冒险。在旅行的第一天,他认为他发现了冒险,开始与自己的无知面对面。“这种无知伤害着、嘲笑着这位作家”,他所记载的冒险故事就像他在旅途中碰到的特立尼达黑人举重运动员身上穿的那件借来的紧身夹克一样,根本不属于自己。小说中提到在创作第一部作品《节日之夜》时,他努力搜寻大都市素材,删掉了许多他不愿直面的东西:有色人种身份;出租车司机多收费;宾馆里遇到的黑人事件等等。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种族身份,也不敢写下让自己蒙受屈辱的事情。想成为作家,他就得隐瞒经历,自我欺骗,否定自己的身份,并否定因此身份带来的各种心理体验,他一开始就迷失了。他承认“在作家身份的掩盖下,隐藏印度侨民身份的做法,无论对我的素材还是我本人都带来很大的损害”⑮。“在这个写日记的人和这个旅行者之间已经有了一道裂缝,在这个人和这位作家之间已经有了一道裂缝。”⑯写完《节日之夜》后,他发现已无素材可写,认识到自己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作家的能力都在缩小。于是,他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关注并试图促进人与作家的融合。他构思了一部关于殖民地的小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开始承认自我,终于明白“我的主题既不是我的敏感性,也不是我内心的发展变化,而是我的内心世界以及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经过漫长的分裂和融合后,奈保尔似乎实现了作为作家的成功。可在抵达之后,他又发现:“成为一名作家不是一种状态——能力或成就的状态,名声或满足的状态——一个人达到它并且待在那里。总有一种特殊的焦虑依附于这个生涯。”⑰经历过素材收集时的自我迷失后,奈保尔在写作的焦虑中再一次迷失自我。他觉得自己被已经完成的东西嘲弄。完成的作品似乎属于一个模糊的时间,永远的过去。作为作家,他又感到新的空虚与不安,这种空虚与不安不是来自外部,而正是“出于我内部的根源”。作为作家,他必须再次开始另一部作品,再次开启那折磨人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写作的焦虑一直伴随着他,撕裂着他。来峡谷前不久,他信心满满,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一本关于他出生地的历史书,却没能取悦当初委托他写的出版商,他发现自己被不上不下地悬在了空中。作品无所归属带来的悲哀出现在恶梦中——“每个梦都是这样结束的,这场爆炸把我扔起来,我仰面倒在地上,倒在一群人的面前……我感觉我不可能幸存,事实上我正在死去……我正在目击我自己的死亡”。写作带来的各种焦虑让“死亡确定无疑的梦”发展成一个真实的死亡之念,让他每天早上醒来就要面对,并要花去整个白天“才能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才能变成一个男子汉,一个干事的人”⑱。奈保尔的体验正是莱恩所称的“内在死亡”,即本体不安全的个体也许不能获得关于其生命持续的观念。莱恩引用卡夫卡笔下一位人物的表述:“我从来没有确信自己在活着。”奈保尔在写作生涯中也经历了这种“内在死亡”,各种不安全感撕裂着他,让他体验“不活”的状态,死亡的状态。这种感觉不仅出现在梦里,清醒时也常现。他曾提到,在他将要写完一本有关美洲的书籍时,就“曾经想象自己是一具尸体,在一条小河芦苇中轻轻地摆荡”⑲。作为作家,他看着自己“死”了。
三、结语
在《抵达之谜》第二卷的开篇,奈保尔介绍该小说名源于偶遇的一幅画作——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尔吉奥·德·基里科的早期绘画。画作的题目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到这个题目以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方式使他意识到自己生命体验中的某种东西。画作呈现了经典的中世纪古罗马场景——一个码头,在几道围墙和门口以外,一艘古代海船桅杆的桅顶,僻静街道上裹得紧紧的两个人。这个“述说着抵达的神秘”的场景使他开始想象自己的故事发生在同样的背景下,同样有一个抵达的人,在抵达的码头上,“他正在变得无路可走;他将失去他的使命感;他将开始知道他只是迷路了。他冒险的感觉被惊慌失措所替代”⑳。虽然他最终没有写出这个想象的故事,只是用看似轻描淡写的笔调述说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写作生涯。但是,书中一浪接一浪的反思和重述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让读者感受到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文学旅人在宗主国为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抱负,想通过写作证明自己的身份,苦苦追寻自我身份认同时所历经的各种危机和挣扎。
从奈保尔的人生轨迹——从母国印度到殖民地特立尼达,从特立尼达到宗主国英国,以及成为名作家后的各种旅行可以看出,他穿梭出入于各种文化之间,历经了多次流亡。然而,这些流亡,不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在抵达目的地后均没带给他所希冀的身份认同。从后殖民社会来到宗主国,从边缘到中心,一路走来,几经磨难,抵达后却发现自己依然身似浮萍。无根漂泊的挣扎之痛,追寻认同无果后强烈的心理体验,在全球化日益纵深发展的今天,正侵袭着大多数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现代人,恰如同基里科的画作让奈保尔想象到主角在“抵达”后所经历的茫然和失措。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6页。
②Feroza Jussawalla.Conversations w ith V.S.Naipaul.University Press of M ississippi Jackson,1997,p163.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⑭⑮⑯⑰⑱⑲⑳[英]奈保尔:《抵达之谜》,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第113页,第221页,第352页,第113页,第115页,第133页,第12页,第118页,第109页,第151页,第112页,第102页,第105页,第109页,第99页。
⑫⑬[英]奈保尔:《奈保尔家书》,北塔、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第26页。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2-218.
[2][英]奈保尔.抵达之谜[M].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3][英]奈保尔.奈保尔家书[M].北塔,常文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26-182.
[4][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8-112.
[5]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37-44.
[6]梅晓云.从《父子之间》看早期生活对奈保尔文学创作的影响[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18-123.
责任编辑:赵青
I106.4
A
1673-0887(2014)04-0035-04
10. 3969 /j. issn. 1673 - 0887. 2004. 04. 009
2014-04-02
熊亚芳(1974—),女,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