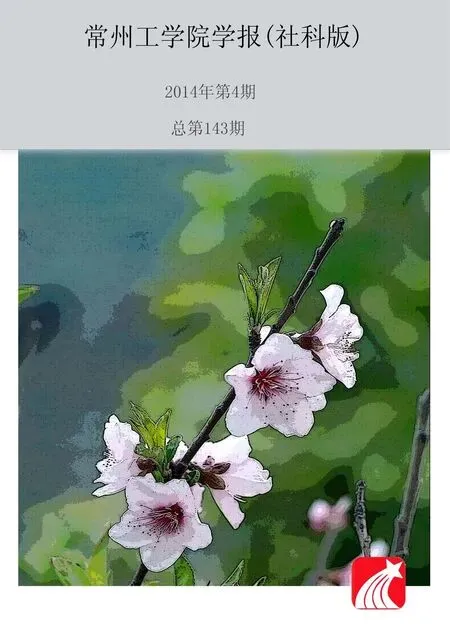朱天心访谈录
司方维
朱天心访谈录
司方维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访谈者:司方维
被访者:朱天心(1958—),台湾著名女作家,作品有《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等。
时间:2010年10月22日
地点:台北希罗斯咖啡
司方维(以下简称司):老师几个月前出了新书《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我们就从新书谈起吧。老师的新书是写中年爱情的,这个应该不是您和唐诺老师,你们感情是很好的。既然您的生活不是这样,怎么想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呢?
朱天心(以下简称朱):我觉得一个认真或称职的小说家,也许从自己经验出发,可是应该不是眼里只有自己的,很多很多是自己观察到自己这个年龄的普遍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一种写法是只写我们这个例外,那肯定并不是我的动力,我想写的是这个普遍的状态。
司:书里写的中年爱情读起来挺可怕的。但我觉得这本书写的不单单是爱情,而是一个生活的状态,是人的生命状态改变了,也不只是爱情改变了。
朱:对。我不知道其他作家,他是已经了然于胸,有十足把握才把胸中的东西写出来。对我自己来讲,好像办个案子一样,有个问题在,然后你会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觉得写作对我很大的一个诱因,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你就看到你的同年纪的很多,什么都有,没什么忧烦,有时候内心恍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好像是我接到的一个案子,我试图去找它的答案。不只是爱情,可能写的是中老年的状况,然后女人的老法是怎么样,男人的老法是怎么样,再推回到人类学,到底是不是从根源处就会很不同,包括年轻一代是怎么样。
司:老师对年轻一代好像还蛮严厉的,对他们有不少批评。我也听过另外一种说法,是一位年纪较长的老师,他体谅年轻人的“堕落”很大原因来自于现实的压力,好比工作难找、房价过高等等。老师为什么选择严厉呢?
朱:同样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好比在看我的小说的时候,说你怎么对我们这一代这么严厉。多年来,也许过了30以后吧,我不断看到我们写作的同业,简单讲,每个人都非常怕批评年轻一代,因为比你年轻就等同于你老了,很多人会非常习惯地对不同的世代绝对不说任何话,不然就是你老了你保守。那我对这一点从头到尾毫无负担,我甚至会说不要痴长年龄,你起码应该勇敢地把这个不同或是这个差异给说出来,要是你活到五六十岁或更老,看到年轻人只能说真好真了不起,你白活了,干嘛有你呢,当我们一个拉拉队,你没有说出你走到人生早前我们几十年,或你比我们多阅历这么多年,你像个先遣部队一样,你到前面看到了什么,也许有好风景,也许有危险。应该有这个责任义务讲出这个差异,所以我始终一直觉得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天职。我把我们这一代已经写得很狠了,这样我写其他世代才有正当性。
司:老师有很多外省人题材的作品。老师写到外省的认同,普遍处于一种很焦虑、漂泊不定的状态,老师认为这是外省人的一种普遍状态吗?
朱:我觉得可能是外省人每个阶段认同上的问题不同。我觉得在还未本土化,20年前,大概1949年到1988年,那个比较单纯的,就很素朴的一个乡愁吧。因为很多,像我父亲他们来的那一整代人,有些就是早上到田里,然后就被拉夫拉来了。他不晓得被拉进部队来几十年就再回不去,有些家里有老婆小孩,有些家里有高堂父母,他们都没空说声再见,甚至要去哪里都不知道。还有就是,像我父亲,因为家族史的关系,对共产党是很大的一个拒绝的,跟着国民党来台湾有一些他的理想性,可是他也不会想到是追随来就半世纪回不去。还有很多很多,只是大男生,都20岁左右,去台湾像过个暑假,就回不去了,而且那种回不去是连通信也没有办法。你甚至在怀乡的时候,很有趣的,清明节,我住的地方附近是墓地,老的坟场,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本省人在扫墓,对小孩子来讲那个墓是代表各种鬼故事的,很狰狞,但又好奇各种扫墓的仪式,那时候村里的气氛很奇怪,你玩了回家以后,就看很多父辈也准备了祭品,可是那个表情,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大陆的父母是死是活,不晓得要把他当死人祭还是当活人。那是比较单纯的乡愁。
我觉得到1988年以后,李登辉上去以后,我到现在都觉得李登辉开启了潘多拉盒子,开启了台湾省籍恶斗的元凶。他接的时候知道位子不稳,可是我觉得他用了一个最不道德的方式。潘多拉盒子是不可能选择的,不能只要好东西出来坏东西留在里头,动用了省籍的时候精准地像个导弹一样只针对我的几个政敌,整个社会都在蔓延这个空气。所有外省人都被讲为既得利益者,你们是统治阶级,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非常少数的那种将官级或是国民党为官的后代,可是更多的,我看到我的父辈,我父亲的朋友们,他们很多的人来了台湾,前十年国民党明令不能和在地人结婚,那时候觉得随时会回去,所以不要跟在地有任何纠葛,第二是大约怕有很多民事纠纷吧。那时候很多人偷偷结了婚,得不到任何军中的补助,军队的薪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娶妻生子简直是活不了。我看到我很多父辈到七八十年确定回不去了才想办法去结婚,自己拿的是死薪水,在台湾能娶到的都是婚姻市场淘汰掉的人。穷人跟穷人的联姻就是永世不得翻身,子女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甚至很多娶的是外籍新娘。我住的地方,靠山那一带所谓的违建,乘捷运傍晚的时候会看到祖孙和乐图,都是他们的小孩,看着都觉得好绝望,怎么带大他啊,你能带几年?简单讲,我看到的大部分外省人,不仅跟统治阶级没有关系,也不是既得利益者,跟台湾的经济起飞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享受到台湾经济起飞的任何成果。那这样的一大批人,我都觉得欠他们道歉。那时候那个气氛动不动外省人应该跟台湾人民道歉,我在想马英九他们道歉一下也许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占尽外省精英的便宜,可在我看来金字塔低端庞大的外省人,时代欠他们一个道歉吧,他们要向台湾人道歉什么?在那个气氛里,他们成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羊,我很替他们不平。
我在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会想要把他们的整个处境写出来。那时候我有很多外省朋友,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学生,写了两篇文章把我骂一顿,他觉得外省人为什么要自己对自己那么残忍,他觉得我那个残忍是在向台湾人输诚的感觉。我完全不是这样想,与其让人家来随便解剖你,不如自己好好自剖,不为人知的委屈要说出来,可是自己也有很多不堪的,不是完人吗。
刚才讲的外省的焦虑,前半段是乡愁式的。我觉得1988、1989年以后那种焦虑就很不同,因为你被当替罪羊。甚至对很多外省人来讲,一辈子在台湾在底层过,都还心甘情愿。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念头,和当初来台湾一样,我们要保家卫国要保护人民,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爱国的意识形态或一个想法、一个感情,很素朴的。可是到刚刚讲的1988年以后,你这个信念就变成一个笑话,被讪笑甚至被羞辱,那种感情对他们来讲是最不堪的。唯一的信念被讪笑,我经常为他们不平。有很多的评论一直在谈我那时候的作品会说我的那个焦虑是外省人的失落,我完全不同意。失落的意思是曾经有过才有所谓失落,他们谈的都是权力,觉得说外省人肯定高高在上有权利。我父亲,也许在文学上有他很高的位置,可是在军级上他只是个上校,退役的时候,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他没有过什么怎么会失落。
司:那您觉得现在还是这种状况吗?我感觉现在比较平和,我接触过的台湾同学朋友中还没有人在为省籍烦恼。
朱:我觉得本来就不该有很大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讲的,1988年以前,那个省籍是有差异的,大家乡音不同,历史记忆不同,一些喜欢看的戏曲次文化的东西都不会不同,可是仅止于差异,并没有到鸿沟,因为我们还是同样肤色的人,用的文字一样,甚至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差异就是被政治斗争给放大了,夸大到势不两立,好像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民族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很少意识到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陈水扁执政这八年,已经操作到极限。大家都执政过了,你有什么能耐彼此都很清楚了,所有的族群又回到起跑点了。大家都很疲惫了,都心知肚明这不是族群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是阶级的问题,但凡有这么高的权力,什么人都一样。我觉得2008年以后,台湾族群问题好多了。我一直也觉得始终没有清理过战场,没有真正地各自反省过是怎么一回事情。
闽南的小孩,一般城市化得很厉害,除非在乡村长大,不然他会说英语,会说日语,可是他不会说闽南语。与很多外省小孩没有任何差别,可能对他们来讲,流行的系谱分别你是日式的你是美式的,那个差别大过族群的。
司:通婚也是很大的原因,到第三代从血缘上也比较难分辨到底是本省还是外省。
朱:我有写过一个不成功小说《南都一望》,到最后做那个结尾,就是你岛上还在吵说本省外省的,他想做的事情是我要到法国南部去,到加州……到第三代,某方面来讲,我如有机会这个岛上我根本连呆也不要呆了,要去当其他国籍的人。我也很有意地用这个作一个讽刺,当我们第一代第二代还在吵,人家才不要当你这个地方的人,人家已经有办法,已经跑掉了。第三代根本不要选择本省外省,根本不要做这个地方的人,如果我们要继续吵下去的话。
司:我的论文选题是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研究,老师介意我们称呼您为外省第二代女作家吗?
朱:不介意。
司:我看到蒋晓云老师写的《都是因为王伟忠》,她在里面写到眷村内外的外省人是不同的。写到眷村生活的时候,她用了一个词“简单笃定”,但我看老师写的是本省人“笃定安稳”,外省人是焦虑、飘荡不安的,我看苏伟贞老师的《离开同方》里的眷村也是这样的。老师您怎么看这种差异?
朱:差别非常大。就像我们说台湾人不是铁板一块,台湾人也有李登辉这样的人,有许文龙,奇美电子的,也有张荣发,长荣的老板,他们上一代是日据时代的台湾精英分子。如果不了解台湾的近代史,好比外省人,你会觉得台湾人都跟他们一样,都是精英,跟日本人合作愉快,没有受到迫害,甚至享荣华富贵,那就大错特错了。大部分台湾人在当时是佃农,很辛苦,吃番薯签,过的是最贫穷线下的生活。不了解的外省人会说,像马英九,像连战,都是吃香喝辣,战争中没吃多少苦。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他们点名的几个人都是,可是就那么几个,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外省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眷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时宋美龄募到一笔钱,要安置两百万大军,在最偏远土地不要钱的地方盖眷村,很封闭。如果生活系统完备,一辈子都不用出眷村进城。我后来离开眷村,才有很多其他外省的朋友,那些外省朋友比较多是国民党的文官系统,一般外省人分军公教,他们可能是公教、公务人员和教育,像平路爸爸是大学教授,像导演杨德昌爸爸是“中央印制厂”厂长,高级文官住的不仅不是偏远地方,而是城市的精华地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跟在地的台湾人隔绝,会讲闽南语。文官来的时候和军队不同,军队是不能携眷的,不是老婆小孩扔在大陆,就是单身很久才能娶,文官是可以携眷来的,像杨德昌是1947年生的,抱着来的,他还有哥哥、妹妹,文官的子女年纪也偏大,他们待遇比较好,跟台湾人没有隔绝,马上就可以融入台湾人的生活,然后也比较生财有道,一来收入本来就比较多,二来他们在城市区很可能经商,在政府工作之外做一些股票什么,跟军人死薪水封闭在眷村是不同的。他们的小孩因为在城市里受教育的条件比较好,他们也大概都会出国去念书,出国后不管留在那里还是回来,他们大概都有搭到台湾经济起飞的便车,很早那时候台币兑美元,在美国的留学生一年打工的钱寄回来在台湾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他们立即在经济条件上是可以翻几番的,跟眷村永远在那一动都不动是不一样的。
1988年以后,我就发现,这真的是很微妙,刚刚讲的眷村老一代的爱国信念被糟蹋被羞辱,不仅被本省人,同样会被外省人糟蹋羞辱,被刚刚讲的公教的那群外省人。因为他们融入台湾社会融入得非常好,他们简直都会觉得很像穷亲戚,他们不仅不能去体会说同样外省人你们一点不能翻身,甚至会觉得拜托你们不要再讲了,拜托你不要被认出来好不好。王德威很长一段时间评我的东西,我就让他很不安,好像我们小时候玩躲猫猫,大小孩最讨厌小小孩跟屁虫,大小孩躲得非常好,小小孩露个腿露个胳膊甚至会大嗓门说我们都躲好了,然后就泄露行迹,你就被逮了。我觉得王德威很长一段时间对我就是这样,我们好不容易躲得很好,你们为什么跑出来替外省哇啦哇啦说话,害得被台湾社会当场万箭穿心。他们的民主启蒙也比我们早,跟在地人接触比较早比较密集,他们看到真实的台湾人的处境,不会像我们还“大中国梦”,某方面可以说是跟台湾社会脱节的。他们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早早就清楚,包括像蒋晓云讲的,他们甚至说我才不要跟国民党,我只是没有条件在香港呆下去,也没钱去美国,我一个都不想跟,我无可奈何来的,跟眷村那种我要誓死跟随国民党是两样的。在那个时候其实最残忍的羞辱就是外省的公教,他们会觉得不要再讲了,像王德威说的不要被人家发现啦,说最好听的话就是赶快地融入,赶快地接受当下,不要再去讲那些可笑的陈芝麻烂谷子事,包括平路也是这样的,在我看,所以她会很自在很轻松地在民进党时期当官,倒过头来会劝我们。
司:老师是女性作家,但并不是以女性题材为大宗。老师经常在作品中为各种弱势群体代言,你写女性的作品,像《袋鼠族物语》是写母亲,《新党十九日》写家庭主妇,感觉也是其中的一种。老师可以稍微谈谈您的女性观吗?
朱:眷村有一点非常好,男女是平等的。在台湾社会有一个说法,就有一个刻板印象,不要娶眷村女孩,眷村女孩最烂,家事都不会做。确实,上一代丢个光,来这边连规矩都不记得,原始家庭,乱世过来好不容易有自己的儿女,疼都来不及。所以我跟唐诺就争辩过,好比我到他们家我就很不习惯,他们永远是把我当客人,姐姐妈妈在厨房,还有阿嬷,外面菜放好了,就是他爸爸、他、我,偶尔他哥哥。在我们家就是全家坐下来一起,我就很不习惯,菜又很好吃到底要不要吃完,后来才发现说他们都很节制也不吃完,我们就离开了,坐旁边泡茶,姐姐妈妈她们会来。我后来多次发现这是他们的习惯,好封建哦,台湾家庭就是这样啊。后来我也觉得我们眷村的那种男女平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特殊时空的产物。我们家三个女生,我也很难感觉得出男女不平等是怎么样。我经常好奇男生的世界,因为在外边玩疯了,每次时间到了各自就会把小孩喊回家,就觉得这些大人活生生把你的好朋友们都拒绝了,只好回家。然后好奇那些男生回家在干什么,女生回家在干什么我太知道。我一直对男孩子的世界,他们私下在干嘛,会非常好奇。更不用说到后来因为青春期的关系,他们就不跟我们玩了,本来哥们一样,这让我惆怅好久。我一直觉得成长跟童年、跟记忆、跟眷村全部是在一起的。
我觉得在我生活中重要的男生,我父亲或唐诺,都是那种非常给你空隙给你自由,好像本来是不该给的一样。他可以把自己做到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我觉得我的自我非常非常的完整,我很难像其他女性主义作家,也许受制于她的成长经验,强烈地感觉到男女不平等,感觉到父母亲的重男轻女,在职场上感觉到身份被歧视。我没入职场,人家编辑只认你的文章,不知道你的性别。我真的在性别上没有任何压力或创伤或压抑,甚至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我有醒觉。这对我来讲,从来不会是一个题目。
我很缺乏性别意识,甚至很困惑。从小到大,我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我是个男生,和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更觉得自己是男生,我非常珍惜跟他们相处的那种男孩子关系。我知道女孩子恋爱期间会给男孩子很多考验,我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我对朋友是很耐烦很细心很温暖的,独独给他苦头和折磨,我多年后看回去,一句话我恨或者说抵抗他把我变成一个女孩子。因为他的关系,你认了吧,你还是有女性的部分,那个折磨是在抵抗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这个问题的困惑要多过作为一个女性社会性那个角色的部分。
司:我发现老师写的女性题材作品,大多数都是已婚的家庭主妇或者妈妈,其他的诸如职业女性就比较少。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吗,还是有目的在?
朱:有时我会把文学创作看做是一个分工,让她们最有切实感受、有急迫性地去写吧。作为一个文学圈来讲的话,可能有人在种玫瑰花,有人在等个乔木的长成,都很好,就去做自己最擅长的,感觉最急切的。就像我做弱势群体,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做性别?在我感觉,她们已经很多人了,战斗力很强,虽然在她们主观上很少。我去那个人力比较少的,比如动物保护,动物是弱势中的弱势。在写的时候也是,职场写的人很多。这本书(《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这个年纪的女性什么都有了,有车子有房子有儿子还抱怨什么,真讨厌,我也觉得讨厌。可正因为这样她们的处境是不被人着墨的,用爱情这个字你都觉得脏了爱情。我大概还是会对,不管大家疏忽了还是不屑于写的那样的领域比较有去探险的兴趣。去写那种无人地带的,好像这对我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动力,是我选择题材和关怀的一个真相吧。
司:老师也写了很多都市题材的作品,您觉得都市文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我自己的担心是很中产的那种,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希望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从一个写东西的人来看,或你做弱势人权的,最怕中产的那种,他会很理智,很实际,可是理智、实际的另外一面是很算计的、很冷漠的,于己有利的我就去做了,不是切身相关的他基本上是非常冷漠的,很自私的,很讲究干净,很讲究效率,对一个国家整体来看,要进步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稳定推助进步的力量。可是你置身其中,好比做弱势人权,我就会痛恨中产,痛恨到极点。好比最简单,我在做流浪猫的时候,有一个很豪华的社区,公共空间照理不可以圈起来,可我们台湾照样圈起来。×区是连着山,开放空间那么大,两三只猫,照顾得好好的,也绝育了,也提早打预防针,天天也是我们去喂,没有任何可抱怨的,可居民跟我们讲我们有交管理费它有交吗,我想说你丢人你跟只猫计较。它没有交为什么可以住在我们的资产上?非常中产阶级的语言。要不就说人活不下去都会自我了断,去烧炭自杀,你就不要喂它吗,不要喂它它也会去自我了断。就是那种很残酷,或者那种权利义务,我花了钱交了税。那只是代表你暂时在台湾这个地方,地球不是你的,不是只有人才能住的,其他的物种或于你没有利的就置之不理。
我最怕的是这种中产的残酷。我觉得在陈水扁时代就大力发扬了这个中产的,他当时把公娼赶出去。中产的想法就是人人有老婆啊,要解决性需求有老婆或者女朋友,要不去很高档的酒店,这是中产的想法。他不会想到很多,好比外籍劳工,月收入不到几千,或者一些老先生,已经丧偶很多年,靠子女孝敬一个月几千块,这些人的性需求都不是吗,只有你中产的才是正当的,他们无视这些。我最早对他失望的时候,是看到他这一点,觉得台北这个城市好可怕,只能够让那种住得起的人住,住不起的人一概滚出去。他还有很多政策都是围绕这一点,都是为交得起税的人服务,那不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我觉得人的心态都会改变,对很多很多的弱势他们会觉得我们不需要照顾你,不仅不交税还要占我们的社会福利,我们交了税还要来养你,差不多一点吧,自己知趣走开吧,我自己要是对台湾、台北,要是有任何不安、很不舒服、极度不满的话,就在这里。中产性格的自私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会更多倍,人的残酷性常会让我很失望,我很少对任何事情会很沮丧,可是我听到这种残酷的时候会让我对人性很失望。
司:老师今天讲了很多,听了很有感触,谢谢您!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 3969 /j. issn. 1673 - 0887. 2014. 04. 003
2014-08-02
司方维(1983—),女,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以《台北人》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