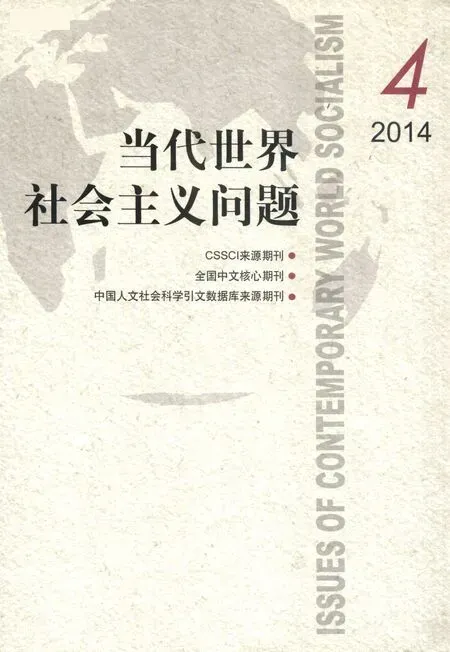苏联民族理论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得失
左凤荣
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苏联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保持民族多样性,开发民族地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那些以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原来落后的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除国家侵犯一些少数民族的利益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是和平与和睦的,民族间通婚的现象很普遍,绝大多数居民都把俄语当成自己的民族语言并能熟练运用,发生的民族冲突并不多,冲突也主要发生在被斯大林迫迁的少数民族与当地居民之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苏联潜在的主要民族矛盾在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其实质是地方政权对联盟中央过分集权不满。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后,潜在的民族矛盾浮出水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最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开始追求自己的主权,并走向了独立,联盟变成了空壳,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自行崩塌,一分为十五。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首先,民族理论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改变,教条主义地奉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反对民族文化自治,但承认民族自决权。被看成是布尔什维克民族问题专家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认为:“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①《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6—307页。1917年10月列宁说:“我们希望俄罗斯 (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②《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0页。。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突出强调“民族自决权”,反对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旨在尽快摧毁俄国这个多民族大帝国,其核心是民族独立和分离权,主要是为了赢得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支持。
在1917—1921年的革命年代,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内宣布成立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政权,俄国各民族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列宁的民族自决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实行以主体民族冠名加盟共和国和划分行政区域,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是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正是通过民族自决,已分崩离析的沙俄帝国蜕变成了苏联。有学者认为是列宁承认前沙俄境内各族拥有自决权利,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这是没有把列宁的理论与政策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当然,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也有理想的成分,他当时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希望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能够加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来。斯大林曾反对列宁的联邦制设想,认为列宁的设想不可能实现,“如果您认为仍在旧俄国的民族联合成联邦的框架内,这还能理解,如果您认为德国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按乌克兰的资格到您这加入联邦,那您就错了。如果您认为甚至已经变成了具有各种特征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波兰将来也会以乌克兰的资格加入联盟,那您也错了”③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перекресmке мнений.20 - е го∂ы. Докуменmы и маm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2,C.210.。
但是,恰恰是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把列宁神化,民族自决权理论自然不能被违背,民族特征也被不断强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至少在名义和理论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既是一个联邦,又是由各族群的政治单元所组成。事实上,在国内战争后的十多年里,像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的乌克兰人这些民族都享受着超越领土的特权,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在其他民族的共和国中建有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机构。苏维埃的实践是对意识形态需求的最大妥协,但是对这些做法将产生的后果,人们的预期只能是:对‘民族’原则的这些让步将会导致‘族群性’的强化而不是消亡。这种预期对于那些 (人口)较大的民族而言已经得到了证明:苏联并没有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新民族’的孵化器”①Ronald Grigor Suny,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转引自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的〈历史的报复〉》,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21426344.html。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斯大林仍坚持少数民族有自决权,加盟共和国有从国家分离出去的权利,在1936年宪法中还为这种分离提供方便条件和法律依据。
在斯大林时代,一方面,苏联进一步以民族为特征划定行政区和区域边界,又新建了一大批以主体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尽管有些加盟共和国的命名民族人口并不占多数。另一方面,斯大林不断完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乌克兰、白俄罗斯还加入了联合国。斯大林以后的领导人,也教条主义地坚持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1977年苏联宪法重复了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内容。甚至在加盟共和国已经纷纷通过“主权宣言”,要脱离联盟时,戈尔巴乔夫仍然重申要坚持民族自决权,还为加盟共和国开展对外交往提供方便。这种教条主义、盲目乐观地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自然无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民族自决权原则在十月革命前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把这一理论和政策绝对化则带来了很多问题,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 (苏联的多民族又是聚居型的),需要做的不是鼓励分离,而是巩固统一,增强国家认同感。苏联的经验表明,民族自决权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第二,不断强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强了各族群的“民族意识”。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初倡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致力于进行世界革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放弃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想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体现的是族际主义原则,是各民族兄弟般团结的象征。列宁所宣称的国际主义原则,体现在倡导各民族都具有平等地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权利上。为此,1924年第一部苏联宪法和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宪法颁布后,苏联都曾重划民族区域,使苏联的成员增至11个:三个斯拉夫国家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一分为三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0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芬战争后,苏联在新吞并的芬兰领土上建立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0年8月又把并入了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升格为加盟共和国。1956年7月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降格为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
苏联实行的是民族多重自治的政策,在联盟中央之下设加盟共和国,在加盟共和国内有自治共和国,还有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等。例如俄罗斯联邦有16个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乌兹别克有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格鲁吉亚有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阿扎尔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阿塞拜疆有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 (位于亚美尼亚境内的阿塞拜疆人自治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 (亚美尼亚人自治)。塔吉克有戈尔诺巴达赫什自治州。苏联最终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单位共有53个之多。这种做法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等级制度,并没有实现苏共所宣传的各民族的平等。在苏共中央高度集权统治下,各民族的不满暂时被压了下去,各民族间还能相安无事,一旦中央政权变弱,这种国中有国的情况就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苏联如此,其他按苏联这种民族联邦制原则建立的多民族国家也如此,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
俄罗斯帝国是通过对外征服不断扩大的,其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边疆地区,这种马赛克式的结构在苏联以民族划分行政区的体制下得到了强化。苏联以民族原则划分行政区、以民族区域自治方式建立联邦制,带来以下消极后果:
首先,民族间等级关系的形成,不可能建立起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埋下了民族不满的种子。为什么有的民族建立的是加盟共和国,有的建立的是自治共和国或者自治州,有的还没有建立自己民族自治体的权利,有的建了自治共和国后又撤了,这些划分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些没被命名、没有自己民族区的民族无法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在努力保障自己文化和各种权益方面力不从心,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内心充满焦虑和不满。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时随意性比较强,并不完全根据命名民族人数的多少来决定,使占人口多数的俄罗斯族感到不平等。如在哈萨克斯坦,到1981年其1505.3万人口中,哈萨克族才有528.9万人,俄罗斯族则有599.1万人。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联邦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命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在5个民族自治州中,没有一个命名民族人口占多数,如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两个民族自治区的命名民族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甚至超过半数。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感觉自己处于不平等地位。同时,民族自治区域内的非命名民族也感觉不平等,民族“领土化”导致各民族共和国内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生活在这些民族自治区内的许多俄罗斯族人,感觉是二等公民,受歧视,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人问题”。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激进派要求“主权”、“独立”,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族人对自己地位不满的反映,对联盟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
其次,人为制造民族区别,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即苏联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共同特点。”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2页。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大跃进”,并不是苏联的现实。1977年苏联宪法把“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列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苏联人”没有变成现实,与苏联机械地按民族划分行政区直接相关。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实行所谓自治的做法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增强。苏联有些民族行政区是历史形成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有些则是人为制造的。苏共这种缺少灵活性、教条主义的做法使苏联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然后才是国家属性。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民族地区的第一把手必须来自主体民族,不管此人是不是胜任,人们认同的首先是民族归属。勃列日涅夫促使干部本地化,大力提拔任用本民族的人担任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形成官官相护的民族帮派集团,这种现象在乌兹别克特别突出。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解除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的职务,任命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接任,引发了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大规模抗议。
苏联长期坚持以民族划分行政区的办法,不是淡化,而是加强了各族群的“民族意识”。国内的族群被提升到国家民族、政治民族的高度,这种做法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融合趋势相背离。一些民族聚居到以本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如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9年阿塞拜疆人占该共和国总人口58.4%,到1989年升至82.7%;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1939年占82.8%,到1989年增至93.3%;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乌兹别克人1939年占64.6%,1989年占71.4%;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格鲁吉亚人1939年占61.4%,1989年占70.1%;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土库曼人1939年占59.2%,1989年占72%②Хресmомаmия по оmечесmвенной исmории (1946 —1995),М.,1996.С.346.。命名民族把以本民族命名的民族自治体视为“自己的”国家,把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视为“外来民族”,并采用各种手段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如在阿塞拜疆的飞地——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1926年时有15%的亚美尼亚人,到1979年,亚美尼亚人的比例下降为1.4%,相应地,阿塞拜疆人的比例则从85%增长到96%。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必然出现人口的迁移和民族的自然融合,但民族共和国对本地民族人口比例的下降充满忧虑,如1939年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人占77.4%,1970年降至56.8%,到1989年只占52%;爱沙尼亚1939年爱沙尼亚人占总人口的91.8%,到1970年降至68.2%,到1989年占61.5%。这一因素成为波罗的海国家反对联盟中央的重要原因,他们不满本民族人口比例的下降,对联盟中央的政策不满,对中央安排大的建设项目进行抵制。按民族划分行政区使苏联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民众心目中的国家意识和对于联盟的认同弱于对本民族共和国的认同。苏联民众的国民意识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民族出身,然后才是国籍。
再次,联邦体制的建设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既然苏联是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那么在中央权力机关中应该注意各民族代表比例的平衡,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被重视。1987年苏共中央机关成员的民族成分显示,在机关工作人员中没有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只有一名乌兹别克人、两名摩尔达维亚人,一名爱沙尼亚人。民族共和国的代表只在党的组织、宣传和农业三个局中有①В Полиmбюро ЦК КПСС ...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m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има Ме∂ве∂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1985 —1991),2 - е изд.,исправ.и доп.М.,Горбачев - Фонд,2008.С.226.。组成联盟的各加盟共和国实力悬殊,俄罗斯联邦无论是人口、面积,还是经济实力都居绝对优势。苏联的实际运作也不是按联邦制进行的,其最高苏维埃内的民族院既按加盟共和国,也按民族自治地区推荐代表,结果导致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占多数和各加盟共和国权力实际上的不平等。当然,无论是大的加盟共和国,还是小的加盟共和国,都同样听命于联盟中央,听命于苏共,没有多少自主权,苏联只是名义上的联邦制国家;而由于俄罗斯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联盟实际上是依托俄罗斯联邦运作的,这又使其他加盟共和国把对联盟中央的不满发泄到俄罗斯人头上。
苏联成立时采用这种联邦制,是特定条件的产物,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联邦制形式客观上不断强化民族观念,使生活在某个联邦主体内的各民族公民并非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苏联所以能存在七十多年,主要是靠统一的苏联共产党这条纽带在维系。而这种条件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发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情况,苏共受到削弱并联邦化,联盟便解体了。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并未切实尊重民族自治权。
从表2可以看出,存在亚健康状况的学生中肝器官能量阻滞的现象比较少见,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肝器官能量不足,其中男生13人,女生22人,占亚健康人数的70%.肝器官能量偏低表示有轻度的肝气郁结,容易胸闷、紧张、烦躁、发怒,还会出现轻度的食欲不振、口苦等现象.
1892年,当有人问恩格斯,德国社会党如何看待和解决法德两国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领土争端这一问题时,他回答说:“我希望,经过十年左右,德国社会党将取得政权。它首先要办的事,就是让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这一问题将在没有任何法国士兵的参与下得到解决”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2页。。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确实给了各民族自决的权利,但是,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各民族的权利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在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无论哪一级的民族自治区域,实际上都没有多少自治权,正如俄罗斯民族学家契斯托夫所说:“虽然斯大林被认为是一位‘超级’民族问题专家,但是在他执政时期,甚至在战前的一段时期民族主义的火焰就被点燃了。一方面,因为斯大林设想构建单一制国家;另一方面,您大概也知道1936—1938年期间发生的事件,一夜之间就逮捕了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说他们是叛国者,是间谍”①[俄]В.А.季什科夫:《学术与人生:俄罗斯民族学家访谈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把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后,苏共便否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鼓励异族通婚,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等等,如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所取代,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对此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②[哈]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对此苏共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用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压制。
首先,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常常忽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不顾各民族的意愿和经济发展水平,强行搞农业全盘集体化,给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带来严重灾难。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许多人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迫害致死。
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和汉族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等,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1940年8月苏联强行把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自己的版图,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内地,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二战后期,斯大林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有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一时期共迁走64万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21.5万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19.4万克里木鞑靼人,17.2万远东朝鲜人,10万麦斯赫特土耳其人,9.2万卡尔梅克人,4万亚美尼亚人,从黑海沿岸的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迁走3万希腊人,6000伊朗人。据统计,从乌克兰共迁走57万人,从白俄罗斯迁走6万人,从摩尔达维亚迁走4.6万多人,从亚美尼亚迁走1.5万人。被镇压的苏联公民人数将近350万。”③Е.Н.Трофимов,Госу∂арсmвенная нацианальная полиmика России:законо∂аmельный аспекm(1906 —2007 го∂ы).М.,Изд - во РАГС,2008.С.148.许多人在迁移途中死亡。“被惩罚民族”的民族自治实体同时被撤销,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实体并没有得到尊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虽然后来为这些受迫害的民族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某些民族自治实体,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些民族问题的后遗症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为了体现民族的融合,人数较少民族的权益得不到尊重,受到压制,这从苏联人口普查所确定的民族数可以看出来。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有190个民族,1937年有168个,1939年只有62个,1959年109个,1970年122个,1979年123个,1989年128个,而2010年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确定的民族数为193个。
其次,名为联邦制,实为集中制,带来严重问题。从表象上看,苏联解体表明苏联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不成功。从形式上看,按民族划分行政区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有人认为,对民族共和国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换来他们对联盟中央的忠诚,如格鲁吉亚,1977年宪法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在民族院里有32名代表,但给格鲁吉亚的名额是59名,而人口比之多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只有32个名额,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格鲁吉亚是最先从苏联分裂出去的①Е.Н.Трофимов,Госу∂арсmвенная нацианальная полиmика России:законо∂аmельный аспекm(1906 —2007 го∂ы),2008.С.165.。但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中亚这个长期受到中央政府优惠政策扶植的地区对联盟的忠诚度是最高的,在全民公决中主张保持联盟的人数比例远超平均值。许多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要求分离出去,主要原因在于联盟或所在的加盟共和国对之不公平,限制了其发展。因此,这里恐怕不是给不给少数民族地区优惠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尊重地方的权利,保障各民族都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苏联成立后,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后,一直纠结于宪法上的分权与实际上的集权,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1922年成立了苏联,确立了苏联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共和国拥有民族自决权。在实际过程中,现代化的矢量要求国家的民主化,而苏联政府却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现代化要求各共和国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而帝国矢量却在朝着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各个共和国都在苏联时代获得了工业的、社会的和文化上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民族独立的经济条件,这就是国家现代化过程对帝国的结果的瓦解过程,当这个帝国的结构还在起作用、还没有把权力下放给各个共和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在理论上讲,它就是现代化过程和帝国结构上的矛盾。一旦经济上的统一性丧失、共产党失去政权,马上就会形成独立的意愿和事实。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已经看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们既没有意愿,也缺乏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因而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而苏联本来可以在不解体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个矛盾”②刘涧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谈苏联解体原因》,载《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1期。。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过分集中的国家管理体制造成的,是加盟共和国对这种体制的反抗。
再次,宪法与实际的矛盾,为民族分离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但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除了军队和外交机构外的所有设置。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需的所有管理机构,有自己的国家象征 (国旗、国徽和国歌),一旦有条件独立时,这些加盟共和国很快就可以独立。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央和共和国之间 (在共和国内部,则是首都和自治区之间)由历史延续下来的不公正的政治关系,由于各民族已有能力自我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在后斯大林时代,面对由官僚化中心主义所推行的发展限制方面,无论是加盟共和国中的命名民族还是共和国中的少数群体都表达出他们不断增长的挫折感。”③Ronald Grigor Suny,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转引自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的〈历史的报复〉》,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21426344.html1924、1936、1977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没有具体细则,本没打算实行。但是,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这就为民族地区脱离联盟提供了法律依据。以主体民族为主组成的领导班子往往在谋求独立中起组织和推动作用,苏联解体时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就是这么做的。
第四,没有处理好与主体民族的关系。
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俄罗斯族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其他加盟共和国是按民族区域自治原则、根据民族自决权建立的,而俄罗斯联邦不是,它是传统的地域国家,其内部又建立了民族自治实体。俄罗斯族人在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地位问题并没有解决,俄罗斯联邦没有像其他共和国那样完整的国家机构,没有自己的共产党组织。虽然联盟的高级领导层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族人,但他们是从联盟的利益而不是俄罗斯联邦的利益来进行决策的。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起了急先锋的作用,认为自己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谋求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消除民族地区的不满,勃列日涅夫在经济上加大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力度,实行低水平的“拉平”政策,让发达地区支持不发达地区,俄罗斯人觉得自己成了“奶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及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地区,1980年全联盟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加168%,其中俄罗斯增加了158%,白俄罗斯增加了318%,格鲁吉亚增加了195%,阿塞拜疆增加了204%,立陶宛增加了225%,摩尔达维亚增加了220%,吉尔吉斯增加了253%,塔吉克斯坦增加了265%。这种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拉平的政策既助长了一些落后民族的依赖心理,也引起了一些发达民族的不满,反而助长了民族意识,加剧了民族矛盾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俄罗斯人认为自己长期帮助落后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要甩掉包袱;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都认为联盟使它们落后了,对俄罗斯人不满。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出现了俄罗斯人运动和俄罗斯民族主义。
要求大民族处于不平等地位,以补偿在生活中形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做法,导致了新的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在教育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据1990年的统计,在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摩尔多瓦人是125,车臣人是151,乌克兰人是163,阿塞拜疆人是172,拉脱维亚人是182,吉尔吉斯人是188,俄罗斯人是190,亚美尼亚人是207,立陶宛人是208,爱沙尼亚人是213,哈萨克人是230,格鲁吉亚人是274,俄罗斯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并要求独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联盟并不代表其利益,一些俄罗斯人并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俄罗斯要独立,苏联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说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大民族对小民族的“补偿”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应该有所改变和调整。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努力摆正各民族的关系,强调俄罗斯族是核心,作为人口最多的俄罗斯族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再强调民族平等,但强调公民权利平等。
第五,没有警惕和有效遏制民族极端主义。
苏联的民族极端主义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改革伊始,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接受的是苏共长期宣传的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观念。事实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民族问题是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这里既有民族理论本身的缺欠和民族政策的失误,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有国家体制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在改革年代民族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少数民族要求保障自己的权益也是合理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误在于没有正视这一问题和及时化解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在革新联盟的问题上缺乏远见。当民族主义情绪发展,极端民族主义出现并威胁到联盟的生存时,戈尔巴乔夫盲目相信人们的理智,盲目相信各民族共和国离不开联盟。
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的鼓励下,到1989年崛起了两支重要政治力量:一支是以叶利钦为首的人民代表的跨地区议员团,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反对派;另一支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这两支力量的民族极端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联盟的计划和努力构成了现实威胁,但戈尔巴乔夫却应对乏策,在处理危机时优柔寡断,丧失良机。无原则地向极端民族主义让步,对鼓吹民族仇视的宣传听之任之,似乎每一个民族在联盟中都是牺牲者,任凭那些走向独立的共和国破坏苏联法律。在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苏共的变化、联盟中央权力日益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丧失了制约的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脱离了联盟中央的控制,戈尔巴乔夫只能听任联盟国家解体。苏联的解体表明,极端民族主义所散布的民族仇恨和民族利己主义,是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威胁,必须防患于未然。
苏联时期在民族理论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的最大问题是教条主义严重,理论脱离实际,有联邦制之名,无联邦制之实,实际上把沙皇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发挥到了极致,造成了各民族的普遍不满,当联盟国家解体之时,无人珍惜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