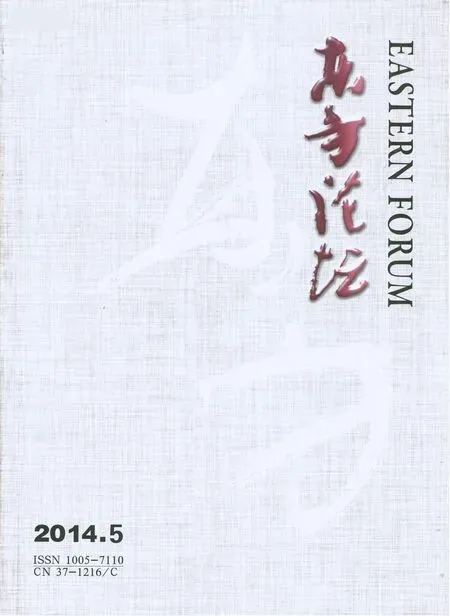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微物”的“神”性——论阿兰达蒂·罗伊视野中的贱民形象
黄怡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是一位很特别的作家。她蜚声国际文坛,但她至今只创作了一部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1997)。她的出版物很多,除了《微物之神》这部获得1997年英国布克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之外,她的大部分文字是与印度时政紧密相连的中短篇评论文章。她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人们在提及她时,往往会同时突出她的另一个重要身份:积极介入时政评议、维护底层平民利益的社会活动家。其实,《微物之神》这部小说也与印度的时政密切相关。本文试图借由阐述《微物之神》小说中维鲁沙、瑞海尔和维里亚巴本这三个人物身负的个人力量,分析小说的题眼“神”字,从而试评作者罗伊对印度底层民众作为个体如何成长并获取力量的思索,及其对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的价值。
一、卑微者的力量
罗伊在谈及自己的写作时说,“我没觉得《微物之神》和我的非小说作品之间有巨大的差别”[1](P36),而且“我写的许多作品的主题,小说也好,非小说也罢,都是权力(power)与无权(powerlessness)的关系和它们之间无尽的循环斗争。……我的写作无关国家和历史,而是关乎权力。关乎权力的偏执和冷酷。关乎权力的本质特性。”[2](P14-15)罗伊聚焦权力问题源自她对印度社会现状的判断。她曾说,印度“这个分层级且水平分离的社会……没有通婚,没有社会融合,也没有人际——人道——互动以团结各阶层。所以,当社会的那底层半部分被切断并消失时,它发生得悄无声息”[3](P6);而在另一方面,“掌权者了解真相”[4](P76),但他们并不在乎,且仍会以伤害底层民众的方式固化社会形态,维护自己的特权。因此,在印度“种姓、阶级和权力大体一致的传统模式目前仍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5](P141)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也认为:“不作为仍是当前印度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表现出常见的营养不良、普遍的文盲、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形式。这是对人类应重视的基本自由的否定,而且这些不足在人们参与经济扩展和社会变动的实践中将严重限制人们的机会。”[6](P30)在印度这样一个独特的种姓社会中,处于底层的贱民群体和落后种姓显然便是承受这上述印度“中心问题”折磨的主体,是印度社会中“无权”的那一方代表。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罗伊曾明确表示自己只为“无权”的底层民众写作,并随之确立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引导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发出了声音,才有被关注的可能,才有摆脱受压迫社会地位的希望。而要发出声音,就要有能力讲述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事实,更重要的是如何讲述它。为此罗伊曾经这样表述她的写作策略:“事实并不是唯一的真相。你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叙述的形式,也是一种真相。……要以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讲故事,从那些专家、学者、经济学家和确实在进行诱骗的人们那里夺回我们的未来。”[4](P77)
在《微物之神》这部小说中,罗伊透过一对七岁双生子瑞海尔和艾斯沙未受种种社会规范禁锢的纯净眼睛来观察阿耶门连这个位于印度克拉拉邦的小村落,以两位主人公——出身信仰叙利亚正教望族家庭的离婚女子阿慕和青年木匠贱民维鲁沙——与周围人的关系纠葛和矛盾冲突,来诠释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乡村传统社会中不同阶层、种姓和性别的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斗争,展现了“权力的偏执和冷酷”和它所造成的印度社会畸象。不过,正如物理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共生共存,权势重压之处也必有反对强权的力量萌发,这正呼应了罗伊所强调的“power”一词的另一层意思,即力量①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辞典》,“power”一词作为名词,主要包含两方面意思:一为控制或影响人或事的能力,可译为“权力”;二为从事某项事情的能力,可译为“力量”。(参见《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第三版增补本)》,英国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1102 页。)。
罗伊曾在其多部作品和采访中反复强调,不论面对的是裹挟着强大资本而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还是在印度古老土地上植根数千年的传统陋习伤害,亦或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新产生的民众权力丧失等等,印度的普通民众要发掘自身力量,要“把我们的耳朵贴到地上,并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方式”[7](P46)。为此,普通民众要做的是“磨砺自己的记忆,……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习”[8](P76),最终用“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来断绝它的氧气,羞辱它,嘲笑它”[8](P77)。比如,《更大的共同利益》(The Greater Common Good,1999)一书分析了高种姓群体对低种姓群体的专制和压榨,着力于为后者拓展更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而《普通人的帝国指南》(An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2004)则揭示了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和外国资本如何联手剥夺贱民和原住民(adivasi)的利益,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依靠;在《倾听蚱蜢》(Listening to Grasshopper,2009)中,她则聚焦当代印度的民主进程,致力于创造联系,以期消除因宗教信仰和种姓阶层不同而生的对立和仇视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和伤害。而在比罗伊的大多数政论作品更早问世的《微物之神》中,她的这一理念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表现。男主人公维鲁沙这一形象就是罗伊理想中印度普通民众力量在小说中的化身。他不但在追求政治地位、情感交流和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体现出与他的父辈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况全面反叛,而且他出众的个人能力使他成为追求罗伊在小说中探索瓦解印度社会传统权力体系,达成底层民众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维鲁沙的力量首先表现在他勇于参与政治斗争活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他的勇气不仅体现在他为此采取了行动,更在于他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其他人所不具有的纯粹、坚定的态度。工会运动的发起人和印共果塔延地区的负责人皮莱把组织工会和抗议游行当成他捞取政治资本、改善个人生活的工具;工厂主恰克则把成立腌果厂工会当成他实现个人政治理想的试验田;而其他普通工人虽然多少也参与工会活动,但却没有一个真把它放在心上的。只有维鲁沙是正式党员和工会会员,而且参加了标志性的科钦游行。这展现出他鲜明的、毫不迟疑也毫无心机的向往,向往能够经由为政治理想奋斗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从而享有展现才华、改善生活的机会。当其他所有卑微的工人、仆人尚满足于眼前为人仆、为人奴的生活时,他作为一个最卑微者,对自己的未来却怀抱着如此光明的畅想。这表明维鲁沙确实如罗伊所愿的那般,是努力“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方式”的一员,而不再是其他那些被动接受现状,毫不重视自身力量的一般民众了。
在爱情中,维鲁沙同样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体现在他能够对青梅竹马阿慕奉献出最真挚且不由自主的爱情。综观整部小说,爱情是罕见的:帕帕奇与玛玛奇之间毫无夫妻之情可言,有的只是暴力控制和被动驯服;皮莱夫妇的互动中体现更多的是搭伙过日子的现实;恰克与玛格丽特的婚姻则摆脱不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召唤和追随关系的浓重意味;至于工厂中的普通工人和贱民维里亚巴本夫妻,则压根儿就没什么感情生活可言。反观维鲁沙与阿慕之间的互动:阿慕的美丽、直率和对不幸婚姻的抗争,深深地吸引了维鲁沙;而维鲁沙英俊的面孔、健美的身材、总是展现在脸上的“微笑”[9](P163),尤其是他在机械上的天分,对阿慕也有着一股不言而喻的吸引力。他们俩的互相靠近,主要是基于对对方内在和外在美的恋慕。这表示维鲁沙对自己生而为人拥有平等爱人和被爱权利具有深切认识,并且能够以纯然的、不带任何功利的眼光欣赏人类情感的美好。他对待爱情的这一态度首先是对种姓制度的蔑视。按照《摩奴法论》的规定,高种姓男子勉强可以娶低种姓女子,却从没有低种姓男子与高种姓女子这样的婚配[10](P42)。而在父亲帕蓬这位顺从的老“帕拉凡”①小说原文为paravan,贱民的一种。(见Arundhati Roy,The God of Small Thing .London:Fourth Estate,2009,p.76.)眼中,他更是具有“帕拉凡”所不该具有的“不正当的确信”[9](P68),面对爱情,想爱就爱了。其次,这也是对传统男权统治的弃绝。他并不追求像阿慕的前夫、兄长等人那样对阿慕的命运拥有统治力,而是期待与心上人平等相恋,这更体现了他对自身情感力量的肯定。
此外,维鲁沙在争取社会政治地位和个人幸福中体现出的勇气显然源自他所拥有的最优秀的职业技能。笔者认为,作者罗伊也正是借由赋予维鲁沙以认识机械构造和操纵接卸产品的极高天分,道出自己对印度底层人民如何才能“有能力讲述自己故事”的思考。维鲁沙的天资和勤劳,使之深得主人家的赏识。玛玛奇出资送他去读书,并称赞他如果“不是一个帕拉凡,那么他可能成为一个工程师”[9](P67)。恰克认为“他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实际上,经营工厂的人是他”[9](P258)。可以说,维鲁沙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腌果厂的技术重担;没有他,腌果厂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
联想到罗伊在她的新作《倾听蚱蜢》中所指出的,当今的印度政党都是在有利自己的舆论宣传之下,极力控制学校、医疗机构和灾备管理机构。“他们理解无权。他们也理解人民,特别是无权的人民,不单有实际的、单调的日常需求和渴望,还有情感的、精神的、娱乐的需要。……‘夺取权力’这一传统主流左翼理想……已不能顺应时代了。”[11](P39-40)罗伊对印度政党运作模式的这一解析表明,在保证政党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为大众或至少一部分民众,提供平民教育和人身安全保障是一个政党获取支持的关键。罗伊的这部书出版于2009年,这可说明当今的印度普通民众已普遍意识到教育权和生存权的重要性,尤其获取教育机会是提升个人发展空间的根本所在。再看小说,我们可以认为罗伊让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维鲁沙接受高于当时绝大部分贱民所获得的教育,辅以他本身的天分,使他拥有超出大多数人的专业技能,正是她心中对底层民众如何获得发展的思考在小说中的体现。
维鲁沙称得上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贱民形象,但罗伊并没有把维鲁沙的命运也同样地理想化。他的死与他所处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中的弱小有密切关系。站在维鲁沙的角度来看,与阿慕的相恋是他追求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父亲和伊培家族的激烈反应是他无法避开甚至应在预料之内的社会现实,唯有皮莱这位发动他抗争的引路人最终的背弃是他没有想到的。皮莱作为印共果塔延地区领导人和工会的发起者,只关注于追逐自身政治利益而非真把贱民种姓或工人阶级的权益放在心上,使得维鲁沙失去了社会能为他提供的唯一一重保护,被彻底地抛入了绝望之中。“革命”“党的利益”等等成了“另一种和自己敌对的宗教,另一个由人类心智所建造,却被人性所摧毁的建筑物”[9](P264-265)。回顾印度独立之后各种姓群体在政治活动中的相互博弈,可以看到:总体来讲,占据印度人口16.2%的贱民群体[12]得到了历届政府的扶持和帮助,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社会的主要资源还是把持在高种姓人群手中[13](P320-328)。同时,由于印度的全民普选制,任何党派要获取政治权力,都必须得到足够多选民的支持。于是,人口众多的落后种姓和贱民群体手中的选票成了各政党都需要极力争取的目标。这样,就出现了美国学者布拉斯(P.Brass)所谓的“极端联合”(coalitions of extremes)[14](P68),即把持权柄的高种姓政客与低种姓民众联合以获取选举胜利,而在实际操作中则往往是“高种姓领导人利用了达利特②英文为Dalit,是印度取消贱民制后对原来贱民的称呼。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alit[OL]。……工人们”[14](P69)。前者得到预期中的政治资源后,是否还与他的底层支持者们站在一起,常常要打一个问号;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面对这样的局面,往往是无力还手,只能忍气吞声。事实上,罗伊本人对这部小说名字的解释也呼应了上述现实状况,即它要表达的是“世界是如何侵入小事件和小人物的。而且正是缘于此,源于人们丝毫不受保护,……这个世界和社会机器就侵入到他们最微小又最深处的核心,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5](P305)。由此可见,在印度这样一个独特的民主社会中,出身低贱的卑微者们若光是挖掘自身的“力量”,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社会境遇,他们还需要占据社会大部分优势资源的高种姓群体中有识之士的大力援助。
二、卑微者的解放
从印度近现代史来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始终由传统精英群体掌握”[14](P67)。换言之,印度社会的任何变革都离不开上层高种姓精英群体的推动或配合。在种姓问题上,也不例外。长期主导印度政坛的国大党历代领袖便为消除种姓歧视,推动社会融合而不遗余力,其影响力并不亚于往往单枪匹马的贱民领袖。属于婆罗门种姓的开国总理贾·尼赫鲁(J.Nehru)曾表示:“大家知道,我将根绝种姓制度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导致我们国家虚弱的最主要因素。”[13](P321)在他任内,废除贱民制度,保护贱民权益的条文写进了印度宪法。另外,他的女儿英·甘地(I.Gandhi)能得国大党元老们推举为总理,理由之一也与她对待种姓问题的态度有关:“(她)在自由运动的大人物中成长起来,具有理性和现代思维,完全没有任何派别主义——邦、种姓或宗教。”[16](P140)这两位执政时间最长的印度总理对消除种姓制度影响的坚持奠定了印度政界精英群体对待种姓问题的基调。
在小说《微物之神》中,另一位主人公、阿慕的女儿瑞海尔的所作所为正体现了这一群体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作为伊培家族的一员,瑞海尔的出身带着与生俱来的神圣①瑞海尔的曾外祖父曾接受过叙利亚基督教正教总主教的祝福,后成为当地最受教徒爱戴的神父。(见《微物之神》第20-21 页。),但她并没有像家族的领导者外祖母、姑婆等人那样成为这种家族神性的捍卫者,更没有把这种宗教上的优越感带入到与低种姓的交流中②按照小说中厨佣克朱玛利亚的说法,只有非贱民才可以信仰叙利亚基督教正教。(见《微物之神》第158 页。)。童年时代,她把维鲁沙视为“最亲爱的朋友”[9](P63)。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她也一直保持着对卑微者或卑微事物的亲近之意。在修道院寄宿学校读书期间,她曾给牛粪装饰上鲜花,于是被罚当众朗读牛津字典中“堕落”一词的定义。评论家福克斯认为,她的这个举动不单是对传统规范的一种反抗甚至挑衅,也表明“她有兴趣并有能力发现卑微事物的美”[17](P40)。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她对卑微事物的欣赏,暗示了她对处于社会主流之外的社会底层民众价值观的认同和力量的肯定。而且,瑞海尔不仅具有精神独立性和平等意识,她还能把自己的力量传递给胞兄艾斯沙,助他抵御人生巨变的打击,走出上一代人悲剧命运的心理阴影。艾斯沙的身份和经历很特殊。他原本应该是伊培家族的继承人之一,但母亲阿慕与维鲁沙的私情曝光,加上伦敦来的表姐苏菲意外溺亡,一夕之间改变了他的命运。有学者因此认为,艾斯沙成年后的沉默是“对卑微者的一种极端回应”[17](P39)。一方面,他受家人操纵,违心指控维鲁沙以维护家族名誉,又无辜背负了为表姐苏菲之死负责的罪名,终被逐出家门,成了各方势力维护自身利益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客观上他是导致维鲁沙惨死的推手之一,并为此感到愧疚悲伤,可是从来没有人留意过他的这一番心绪。家族和社会中各路人马斗争的结果使他从一个富家小少爷无可抵御地沦入社会的边缘人群,深切体会了身为卑微者的悲哀,沉默成了他唯一能选择的抗争方式。由此,若对比艾斯沙与维鲁沙的命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前者生就高贵血统,成年后却落魄低贱;后者天生聪慧勇敢,却以惨死狱中了局。他们一个主动选择了沉默,一个被迫永远沉默,都是被社会遗忘的人。这样,瑞海尔对艾斯沙的主动靠近和安抚就具有了双重的救赎意味。作者写道:
“她移动她的嘴。
他们美丽母亲的嘴。
挺直坐着,仿佛等着被逮捕的艾斯沙将手指伸向那张嘴,触摸它说出来的话,握着它的呢喃。他的手指循着它的形状移动,然后触摸牙齿,然后,他的手被握住了,被亲吻了。”[9](P302)
瑞海尔和阿慕在形象上的重叠,使得两代人的情感遭遇也得以重叠。瑞海尔对艾斯沙的抚慰,同时也是给予维鲁沙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瑞海尔的举动已经超越了个体情感交流的范畴,具有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种姓的人们寻求互相理解、交流和支持的象征意义。同时,亲吻、抚触这样极亲昵的肢体动作又透露出兄妹间浓厚的温情,传递出作者所关注的人性关怀。简言之,从瑞海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期待的不是社会优势群体挟种姓或宗教优越感,行慈善之事,而是不同社会群体间基于人人平等原则而进行的对等的交流,并最终达成情感上的接纳甚至融合。
三、卑微者的“神”性
在印度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宗教国家,自古以来万物都有其“神”性①根据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报告显示,99.93%的印度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剩下的0.07%印度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未得到统计。(参见”Census of India,2001”,http://www.tn.gov.in/deptst/areaandpopulation.pdf [OL])。。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顺应世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潮流,印度掀起了种姓改革运动和贱民解放运动,连原本不洁的贱民都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的宗教神性。当时,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社会改革家都态度坚决地声讨贱民制度[13](P321),而“大雄”甘地(M.K.Gandhi)和贱民领袖安培德卡尔(B.R.Ambedkar)是其中两面最具号召力的大旗。甘地曾经在上世纪30年代为改良印度教种姓制度,废除“不可接触制”,发起为贱民争取种姓平等地位的“哈利真运动”(harijan movement)。“哈利真”一词由名词“hari”和动词词尾“jan”构成,“hari”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称号,“jan”在印地语中则意为“出生”,因此这个词意即“大神之子”。甘地用它来代替“不可接触者”,指称被排除在传统种姓体系之外的贱民群体[18]。这个名称表明甘地首先把贱民纳入到原本只接纳种姓教徒的印度教体系内,其次他还给予贱民与种姓教徒平等的教内地位。在印度这样一个以印度教为主流的宗教国家内,甘地的这一立场给建立在举世无双又“无懈可击的神学和哲学基础之上”[5](P65)的种姓制度带来的是一场强震,为贱民谋求平等、自由的发展机会开辟了一条道路。另一位改革家安培德卡尔本身即为贱民出身。切身的社会歧视体验令他在为贱民谋求在印度教体系内的“平等、民主和博爱”[19](P87)时,比甘地更为迫切。当他发现在印度教内不能获得满意的斗争成果后,不惜号召自己的数十万追随者皈依宣扬“众生平等”的佛教,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佛教运动”(Neo-Buddhism),并对佛教经典按照有利于贱民解放运动的原则进行了重新诠释。从这两位印度近现代贱民解放事业领袖的主张来看,他们都是借由肯定贱民在宗教体系内与种姓教徒的无差别的信徒地位,赋予其宗教“神性”,从而达到解放贱民群体,改良甚至瓦解种姓制度,促进印度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目的。
然而,并非每一个“微物”都会觉悟到自身所具有的“神”性。相对于归属种姓体系内的普通民众,贱民群体无疑在政治、经济、宗教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地位都处于人群的最底层。他们首先是卑微者——辛勤劳动却只能维持最低生活保障,无力更无意识对自己的命运作任何改变。小说中维鲁沙的父亲维里亚巴本就是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作者写道,他是一个“旧世界的帕拉凡,曾经历过‘倒着爬’的日子”[9](P67)。他被花岗岩碎片弄瞎了一只眼睛,而玛玛奇出钱为他安装了一颗他无论如何无法自己负担的玻璃义眼。此后,“没有人”,包括玛玛奇,“期望维里亚巴本还清”这个债务;而后者则从此对玛玛奇及其一家人“怀着一种如泛滥河水般深而广的感激之情”[9](P67)。在这件事情中,双方的态度正体现了印度村落中居于掌权地位的高种姓富有家族与处于依附地位的贱民群体之间的传统关系:在“超经济”的贾吉曼尼制度下,“低种姓依附于高种姓,前者世代为后者提供各种服务,并接受一定的实物作为报酬”;在这种“固定的主子——奴仆关系”中,高种姓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拥有低种姓的绝对忠诚[5](P249-256)。维里亚巴本的“忠诚”[9](P238)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他以主动告发儿子维鲁沙与阿慕的恋情来表达他效忠主人甚至“愿意徒手杀死他的儿子,愿意摧毁他的创造物”[9](P69)的心意。从这一角度来说,他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更多的是种姓制度所施加在他身上的奴化意识,而非他自然流露的个人情感。
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个谨守贱民言行准则的面具式人物,却也有感情外露的时候。小说中写道,他选择在一个预示神祇发怒的暴雨天,用酒麻痹了自己,又向玛玛奇历数了伊培家族历代对自己家族的恩惠以说服自己,最后涕泪交流地向玛玛奇坦白了那对青年人的一切。可见,他虽然在理性上坚定选择了“忠诚”,内心却因对儿子的“爱”[9](P238)而饱受煎熬,而他做出告发举动那一刻的大雨滂沱与老泪纵横则是他的“忠诚”与“爱”最凸显也是矛盾最趋激烈的时候,道尽了这位老人的悲哀与伤心。由此可知,作者对这一人物是“哀其不幸”的。
此外,对于维里亚巴本从无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抗争意识,作者罗伊也并未显露出任何“怒”气,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个人既不可能足够强大,亦不会太过弱小,以致可置身事外。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完全被卷入到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中去了。”[4](P49)同样地,维里亚巴本既是一个从“旧世界”过来的老“帕拉凡”,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便也只能是老式的了。只是他这番义无反顾地告发,虽然成全了自己“忠诚”的好名声,代价却是他珍如生命的儿子付出了一条性命——尤其他是明知其结果而为之,便让人在痛心于他的顺从之外,更感到一股使人不寒而栗的绝望。这在事实上是一种泯灭人性的做法,是间接的自我毁灭,也是对自我力量的彻底否定。因此,作者虽不是“怒其不争”,但始终是“叹”其不争的。而维里亚巴本坚持贱民的“忠诚”却换来凄惨晚景,这也从侧面暗示了作者对维鲁沙寻求发展自身力量的肯定。
维鲁沙本应是一个和他的父亲一样身份、地位的最卑微者,但他却成长为罗伊笔下的“微物之神”①小说中作者两次以阿慕的角度描写维鲁沙,并称其为“微物之神”(参见《微物之神》第208、304 页)。,具有了“神”的光彩。维鲁沙作为渺小“微物”的一员,却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乃至个人情感追求等方面都向强大的社会传统发起挑战,他的力量所迸发出的光芒令人炫目。他在思想上的大胆突破和在职业地位上的超然独立,无疑正符合罗伊对印度普通民众,尤其是贱民的殷殷期望。从这一角度来说,维鲁沙是当之无愧的“微物之神”。他的“神性”是他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主动冲破一切社会束缚,努力挖掘自身各种力量而获得的,早已超出了印度传统宗教和种姓制度框架内某一类人所应具备或只能具有的能力。
显然,罗伊在小说中沿用了甘地、安培德卡尔等先驱者为卑微者披上的“神性”光环,不过她笔下的这一卑微者的“神性”已大大突破了宗教的禁锢。这从作者所设置的故事背景中也可看出一二。首先,小说的整个故事发生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叙利亚基督教正教信徒社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最强调种姓制度的主流印度教文化氛围。其次,在小说的第十二章,作者对当地的卡利卡沙舞有一段专门描述:舞者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母亲贡蒂、婚生子般度五子及其私生子迦尔纳之间的故事与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描写的主要情节并无二致,但演出这部戏的舞者们却早已远离了那个信仰纯真的年代。正如作者所言:“他(指卡利卡沙舞者)诉说诸神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出自不敬神的人心。”[9](P217)由此可见,宗教神权的大大削弱,使得原本披着神性外衣的种姓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慢慢转变成一种可被改造的社会规范,不再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宗教制度的一部分。这样,小说中各种人物本身的思想和性格特质就得以凸显,从而使这“神性”转而主要表现为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人格魅力发展自己,显现力量,并最终在维鲁沙身上得到集中体现。由此,罗伊大大扩展了卑微者“神性”光环的辐射范畴,强调了印度底层民众寻求发展、自由和平等地位的主动性和必然性,并得以从人道关怀的高度来照拂她对整个印度社会发展的期待。
从维鲁沙与阿慕的故事开始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双生子返回故乡的九十年代,小说的时间跨度达三十年之久。这三十年是印度获得国家和民族独立后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印度政府持续加大对贱民群体在教育、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贱民已经崛起为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新兴力量,“种姓政治”成了形容印度政坛的关键词,其“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进入教育与官僚机构”[13](P334)。这样的变化在造就贱民精英群体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强化了“贱民”这一身份标签,使得“消灭贱民制”[13](P328)这一印度历届政府的目标化为乌有。更甚者,以“利益”[13](P339)为核心的现代种姓政治活动甚至还加剧了贱民群体内部精英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13](P335),加上不同种姓之间原有的森严壁垒,使得绝大多数仍生活在贫困和文盲状态中的贱民群体难以获得改善生存条件的机会[13](P326)。
对照现实,小说中罗伊笔下的这两代人承受着和印度社会中千千万万普通民众一样的重压,但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与个人情感的流露给这残酷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面纱,使之不再显得赤裸裸以利益为先。小说结尾一章,阿慕与维鲁沙在河岸边身与心的融合美得有如童话般不真实,但这何尝不是罗伊面对印度这样一个“分层级且水平分离的社会”的殷切期待呢?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持续进行写作、思考。我是在寻求一种理解。不是为我的读者,而是为了我自己。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推动我自己更长远和深入地看待我所生活着的这个社会的方式。”[4](P74)而她对这个社会的不断“探索”显然已向世界各地的读者们展示了“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方式”,并极大地触动了他们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看法②罗伊在接受采访时曾非常欣喜地谈到人们读了她的小说之后给她的各种反馈。这些反馈主要涉及读者对家族关系的看法、对社会关系的思索、对婚姻的体会、对童心和乡土描写的欣赏、对恐惧的克服等几方面问题。读者们或表示有所共鸣,或表示激发了新的感悟。参见Shoma Chaudhury,“Ten Years On …”,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p.236.,使人们不因“无力看到这个世界既定模式之外的样子”[2](P17)而困于绝望之中,失去力量。这就是罗伊这位曾经如瑞海尔般遭受伤害、却顽强实现自我成长的女作家,为现实社会中千千万万个“维鲁沙”和“阿慕”所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这一角度来说,罗伊本人可称得上是另一番意义上的“微物之神”。她作为第一位获得重大国际英语文学奖项的印度本土作家,其里程碑意义或许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
[1] David Barsamian.“The 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A].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
[2] Arundhati Roy.“Come September”[A].The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M].London:Harper Perennial,2004.
[3] N.Ram.“Scimitars in the Sun” [A].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
[4] David Barsamian.“Development Nationalism” [A].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
[5]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M].黄飞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 Arundhati Roy.“The Loneliness of Noam Chomsky”[A].The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M].London:Harper Perennial,2004.
[8] Arundhati Roy.“Confronting Empire”[A].The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M].London:Harper Perennial,2004.
[9] 阿兰达蒂·罗伊.微物之神[M].吴美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0] 摩奴法论[M].蒋忠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1] Arundhati Roy.“‘And His Life Should Become Extinct’:The Very Strange Story of the Attack on the Indian Parliament”[A].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M].London:Penguin Books,2009.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lit [OL].
[13] 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4] Christophe Jaffrelot,“Caste and the Rise of Marginalized Groups” [A].Sumit Ganguly,Larry Diamond and Marc F.Plattner,ed.,The State of India’s Democracy[C].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
[15] E.Nageswara Rao.“South Asian Writers in English:Arundhati Roy” [A].Fakrul Alam,ed.,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323)[Z].GALE,2002.
[16] 王红生,B.辛格.尼赫鲁家族与印度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7] Chris L.Fox,“A Martyrology of the Abject:Witnessing and Trauma in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ARIEL [J],33.3-4(2002).
[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ijan [OL].
[19] Owen M.Lynch.The Politics of Untouchability: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ity of India[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