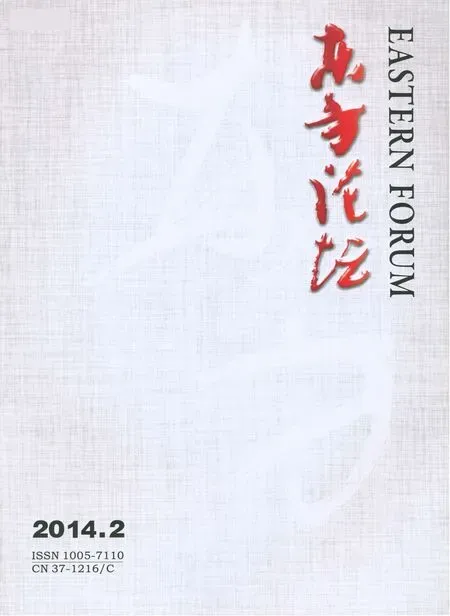心中的胯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现象探析
尹 奇 岭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29)
心中的胯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现象探析
尹 奇 岭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29)
新旧交替时代的丰富与混杂、突破与守旧,往往不是能够用进步和落后等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概括的。在“顽固”“保守”“守旧”等负面词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无数次碰壁、磨难之后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惯性。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在“解冻期”一批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还活在过去受到禁锢的年代,在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与富有朝气的时代精神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如此,既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内心阴影,又有长期禁锢带来的思想能力的丧失。
解冻期;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变革之际,人们注意力往往为新现象、新事物所牵引,容易对那些被认为落伍和顽固的旧的思想习惯统统嗤之以鼻,缺少观察和研究的兴趣。新旧交替时代的丰富与混杂、突破与守旧,往往不是能够用进步和落后等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概括的。在“顽固”“保守”“守旧”等负面词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无数次碰壁、磨难之后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惯性。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精神上的解冻期,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还活在过去受到禁锢的年代,在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与富有朝气的时代精神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如此,既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内心阴影,又有长期禁锢带来的思想能力的丧失。
一
“十七年”至“新时期”这一时段,知识分子生平遭遇方面的研究资料已有很多,而关于知识分子的生平遭遇与思想变迁的关联研讨并不深入。随着文化名人的日记、书信、年谱、回忆录等材料的大量出版,在丰富的材料中,依稀可以分辨出那个时段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深处的变迁轨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震撼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胡风在“猛烈燃烧”的情绪中写下了数千行长诗《时间到了》,表达对新政权的歌颂和欢呼雀跃的心情。[1](P368)与此同时,为了稳固政权,严厉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在开展之中,虽然不是针对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内心有强烈震撼。顾颉刚日记中就有不少对镇压反革命的记录:
“金华土改,被杀地主达三千人。”[2](P15)
“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余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地主中固有恶霸,亦有好人,今乃一网打尽,讵非冤耶?”[2](P26)
“近日上海枪决人,一日至数十,报纸登出者无几。北京亦然。……闻刘次萧亦以军统罪名被杀于青岛,此山东一老教育家也。”[2](P38)
“苏州五反亦殊剧烈,丁香巷某家为开明大戏院经理,夫妇二人,子女五人,先以线袜作绳,勒死子女而后自缢,留书于案,谓不愿子女存在人间,继续受苦。其子,大儒巷小学之高材生也,其师闻讯,为之痛哭。”[2](P218)
从上面几条记录来看,带有清算性质的新政权立威举动,也使整个时代氛围笼罩了暴力和绝对服从的空气。从后果上看,暴力思想甚至漫渗进儿童的心灵,顾颉刚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予前为三儿买《新儿女英雄传》,图游击队事,今静秋又为讲《西游记》,遂使彼辈满脑子是‘打’、‘杀’,一不称心,就说‘我要杀你’,儿童教育如此其难为也!湲儿竟向三姨说:‘妈妈要狄医生替我打针,我把她杀了吧!’”[2](P39)在新政权昂奋的精神背后,思想整肃已经在不同层面进行了,一些知识分子感觉“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1](P273)片面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刮起,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已经痛感说真话的困难。下面再摘录几则顾颉刚日记为例:
“今日之学生,学术水平不够无关系,政治水平则不容不够。”[2](P68)
“在这时候,竟不许人说良心话如此。”[2](P89)
“今日给丹枫看,说我讲胡适以前有进步作用,固是事实,但不能讲。因劝予不必用书面方式,为代拟一纲要。盖至于今日而真话说不得矣。”[2](P143)
“赵紫宸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已廿余年,解放后在院宣传唯爱主义,冲淡了教徒们仇美亲共的心理……故此次燕大思想改造,全校师生给予无情的打击,与张东荪一样。”[2](P211)
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晚清民国时期的民粹主义的流行,五四时期“劳工神圣”口号的普及,以及强调阶级的马列主义的传播,都蕴含着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内在诉求,只不过真正对知识分子形成整肃力量则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1936年前后,进入解放区并加入共产党阵营的文化人都不同程度感受到了思想改造的压力,丁玲、萧军、王实味等人被要求在审美趣味、思想观念、行为准则等等方面做出改变。文艺是容易暴露思想情感的行当,文艺作品更是容易被任意解读,无形中在心理上给文艺家带来沉重压力。1949年2月27日,胡风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作家的打油诗:“告诉我儿,切记切记,宁卖屁股,不要搞文艺。”[](P33)
新政权建立以来,政治运动持续不断,从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大跃进”直至十年“文革”发生,极“左”思潮不断高涨,一直保持着对知识分子的强大压力,急速发展的政治运动把无数知识分子抛下革命战车。在“不断革命”的形势下,无论来自重庆还是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都成为革命对象,很多人沦为阶下囚,连紧跟形势的丁玲、周扬也无法幸免,更不用说老舍、冰心等人了。1968年6月23日陈白尘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下午文联各协会与生产队联合举行斗争大会,第一次被施以‘喷气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七十,亦不免。”[4](P62)直到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开启,一些幸存的知识精英也弄不明白自己为啥被抛弃了。晚年的周扬经常流泪,“他说他每写一篇文章,每作一次报告,都要重新认真阅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也亲自给他写了三十多封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这样整他。”[5](P31)有些论者认为,进入共和国后,从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更容易和新的体制融合,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艰难的适应过程,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只要看看周扬、丁玲、邵荃麟们的遭遇就一目了然了。田汉曾在私下谈过对胡风事件的看法,他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对胡风的,而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因为它指的是‘集团’。”[6]严酷政治形势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压迫和改造是不言而喻的。在1960年的一次访谈中,张恨水说:“《北京漫画》要我写个长篇的讽刺小说,我不敢答应。因新社会的事物是不应随便讽刺的。”1961年,他说:“经过反右后,大家都不敢随便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对于领导更是噤若寒蝉”。1964年,沈从文一次访谈中也说:“我不知道现在对作品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不敢写。看了发表出来的有些作品,感到只有政治内容而无艺术性,有些发表出来的诗文简直是宣传品,口号化、公式化。我就怀疑是否现在的要求就是这样。”[7]严酷的高压容不得人不低头,“三家村”冤案其实就是在杂文中坦白说了点真话,就使邓拓等人遭到灭顶之灾。沈卫威说:“茅盾等一批作家何尝不想冲破而获得他们应有的创作自由呢?但他们不敢,也无力,因为这种外在的力量,对人的约束、控制,对人性的扭曲、改造是显现的、公开的、无法回避的。”[8]
十年“文革”期间就更不用说了,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灭顶之灾,文艺界更为严重。老舍、傅雷、董秋斯、陈梦家、言慧珠、叶以群、冯雪峰、杨朔、周瘦鹃、李广田、闻捷等等一大批著名文艺界人士人或投水、或自缢、或吞药、或跳楼、或煤气、或绝食等等,以非常手段弃世而去。
严酷的思想压制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1975年是“文革”接近结束的时候,10月8日,罗荣渠给二弟罗荣泉的信中说:“凡事不要轻易表态,只按主席的指示说话就行了。”[9](P571)这句话特别有代表性,为了自保,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说话写作不得不与主席和党报保持统一口径。在那段特殊的历史岁月,有一个真实的胯,要知识分子从胯下钻过。在要求知识分子“脱裤子,割尾巴”时代,知识分子集体经历了“钻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不能过关。这样的经历,也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烙下深深印痕,反映在新时期的最初几年的文学艺术思想和创作实践中。
二
新时期开启之初,情况并非与以前截然两样。过往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仍在起作用,人们还没有能够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中摆脱。“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社会空气有所改变,但高压仍在,知识分子心有余悸。1977年王蒙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写一个农业技术员的《项春辉》,后来在一个访谈中他说:“那个时候写起小说非常之拘谨,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敢写,什么都不敢发挥……”[10](P211)除了外在的政治高压依然还在之外,最让人唏嘘感叹的是知识分子精神心灵上的创伤。
从历史阴影下走出来的人,心头总还留有历史的阴影。有不少作家,在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风刀霜剑的磨难后又复出了,但他们在思想深处已经刻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已经逝去的时代要求。阎纲在《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一文中,描述过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柳青删减和修改的地方,基本是按照毛时代的的标准来删减和修改的。这一修改版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出版的。新版《创业史》删改最多的是爱情描写,那些表现男女情爱的微妙心理和行为动作的部分都作为“旧现实主义的过时写法”被抛弃了。如第八章:“他(梁生宝,笔者注)承认:那时间,他要是伸胳膊搂她(徐改霞,笔者注),她也许不会推开她。但他不能这样做。他相信:正因为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改霞以后更喜爱他了;喜爱里头带有尊敬,他看得出来。”如第十五章:写改霞照镜子——“她低下头,乐滋滋地瞅着过了乳峰,达到腰间的两个辫梢,带着女性共有的‘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天赋心情,揣摩生宝看见她这份打扮的心理。”如第三十章,写恋爱中的改霞:“爱情,改霞现在才体会到,对于待嫁的姑娘,简直是燃烧在心中的一堆红火。世俗的礼教、父母的干涉、舆论的压迫,常常不能扑灭这堆火。”“她将身子紧挨着他茁壮的身子,肘子擦着肘子。”“她怕他在黑夜里看不清楚她笑,又忸怩地动了动穿着夏装显得很苗条的身子……。”写恋爱中的生宝:“生宝的心,这时已经被爱情的热火融化成水了。生宝浑身上下热烘烘的”。“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一有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以上这些描写男女爱慕之情段落和字句,朴实、干净、真切、有人间气息,都被删掉或改写了,而这些被删减掉的也正是能真切表现个体人生和人性的部分。同样被删减的还有素芳和姚士杰的描写——“堂姑父的一只胳膊使劲地但是亲热地抱住她的两只胳膊,另一只僵硬的大手,可怕地……伸来了。”“女人素芳渴望着享受男人使劲搂抱和亲切抚摸的‘幸福’。她觉得这是她当一回女人的权利。”“生理上是男人而精神上是阳性动物,姚士杰给女人素芳多大的满足!”[11]
通过删改,我们发现“身体”感官性存在被放逐了,成为隐性的、后台的,被推到无穷远的边际。通过这样的处理之后,梁生宝这一形象被更加抽象化,成为更纯粹的社会主义新人。柳青对《创业史》的修改将十七年文学中已经稀薄的身体性存在,在新时期来临之际进一步抽空,以保持和贯彻被异化了的世界观和价值尺度,这样的修改,不仅没有使作品增加审美性,反而把真实的部分阉割了,变得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尺度。这一事实表明,文学艺术的创造者,在经历了巨大历史沧桑后,并不一定变得清醒,反而可能更加谨小慎微、杯弓蛇影,仅存的一点主体性也在觉醒的幻觉下自我阉割了。其实被迫修改原作,以适应时代的氛围,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是大量存在的。以沈从文为例,他就曾在1957年对发表于1930年的小说《丈夫》进行过修改,如在第十二段就增加了几十个字:“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12](P82)经过修改,小说明显增加了社会批判,矛头直指执政的国民政府,但在艺术性上被严重削弱了。只不过沈从文的修改多少有抵触和不情愿,而柳青的修改则是在忍受了极大病痛,在自动、自愿基础上完成的。
“文革”结束,让习惯于过去做法的许多人感觉不习惯。1977年1月18日罗荣渠在给弟弟的信中说:“现在校内连大字报都几乎看不到了,开会也不积极了;想当年四人帮得势之时搞运动的盛况,不能不连叫怪事!怪事!”[9](P600)“新时期”的开启,情况并非与以前截然两样。过往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仍在起作用,从上到下并没有能从这种主流意识中摆脱。在文学艺术领域,往往还依照过去的习惯思维,望文生义地把文艺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比如在朦胧诗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些著名的文化人就以“晦涩”“难懂”“灰色”抨击朦胧诗,甚至有人将朦胧诗拔高到是“资产阶级现代派”[13],是“唯我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与革命,与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制度,与我们这个虽还贫困但却蒸蒸日上的祖国……不但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14]在艺术界,1978年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本来是表现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喜悦心情的,但在一次审查中被人指责为“号召大家喝酒”。1980年苏小明在“新星音乐会”上演唱了《军港之夜》,有人就批判说“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我们的战士怎么能‘好好睡觉’而不去站岗放哨呢?”,海军机关内部有领导甚至认为“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15]
三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看到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在知识分子头上有一个真实的“胯”,就是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以符合变幻不定的政治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立威举动和稳定政权的严厉措施,也给知识分子内心以强烈震撼。随着“左倾”严重化,意识形态管控严厉,大量精神产品以“资、封、修”的名目封杀,也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反思、自省的精神资源,造成知识界普遍的思想和精神萎缩。刘心武《班主任》中写宋宝琦从图书馆偷的被禁封存的书中,就有《青春之歌》《牛虻》《战争与和平》《辛稼轩词选》等中外古今的作品。普遍的知识荒,是新时期之初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之一。阿城在一篇随笔中说,他在1984年底的一天翻看《收获》,里面有一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大为佩服,到处打听张爱玲是谁,却没有人知道,后来见了柯灵对张爱玲的介绍才明白。对于钱钟书、沈从文是小说家阿城也是在八十年代才知道。[16](P373)可见曾经的历史岁月通过遮蔽和打压,给一代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狭隘和无知。
随着“文革”的结束,极“左”思想也开始缓慢退潮,但极左思想留在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东西却不是能简单抹掉的,甚至有些“左”的思想已经内化,成为习焉不察的东西。姜文和阿城说过一段话有意思的对话——人们有追求格式化的内在心理,本来不自然的东西,时间久了,就被认为是自然了,更可怕的是当这些不自然的东西没有了,人们还在迷恋它。[17](P323-324)虽然现实中某种控制力量或机制已经弱化了,但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思想和行为定势还顽固地起作用,心中的“胯”依然存在。
作家对以往作品进行修改以自觉符合过去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做法,正是“心中有胯”的证明。意识形态对社会个体强大规范、驯服的能力,使很多人丧失了自省能力。阿尔杜塞发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将个体当作属民的质询功能。通过意识形态的质询或招呼,把个体设定为或安置为一个服从特定意识形态的属民。”[18]而意识形态力量的发挥,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反复质询并最终通过个体的自我强制来实现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巴金老人,“文革”时期,丰子恺的漫画《阿咪》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巴金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听的次数多了,我也逐渐接受别人的想法,怀疑作者对新社会抱有反感。”[19](P37)“文革”后,巴金是最早的一批觉醒者,写下《随想录》以记录自己反思和觉悟。还有一些依然沉浸在过去意识形态而自省力不够的人,比如丁玲,钱锺书说:“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5](P10)当然不仅是丁玲等少数人,这种情形也是普遍状况,韶华说:“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20]夏中义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排他性的理论模式(“苏联模式”),使社会精英阶层在学术思想方面窄化、矮化,似乎被集体施行了“脑外科手术”。[21]而这种手术的后遗症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康复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恢复生机和活力。这让我们看到历史悲剧的延展性,并不只限于一个时代。新时期的到来,有一个清寒的解冻期,解放和压抑两种力量冲撞、纠结,规定了这个时期的特殊性。
[1] 胡风.胡风全集:第9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胡风.胡风全集:第10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 陈白尘.缄口日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5] 刘再复.师友纪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6] 韩淮.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J].炎黄春秋,2013,(5).
[7] 贾俊学辑.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J].新文学史料,2012,(4).
[8] 沈卫威.茅盾的晚年——历史及其限制[J].山西大学学报,201I,(4).
[9] 罗荣渠.北大岁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0] 马原.中国作家梦:马原与110位作家的对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 阎纲.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J].新文学史料,1980,(2).
[12]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3] 程代熙.给许敬亚的公开信[J].诗刊,1983,(11).
[14] 柯岩.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J].诗刊,1983,(12).
[15] 李皖.解冻之春(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六十年三地歌”之五[J].读书,2011,(6).
[16]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A].阿城.阿城精选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
[17] 阿城,陈村.好说歹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18] 周宪.意思形态:从“自然化”到“陌生化”——西方文论的一个问题史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2011,(5).
[19] 巴金.真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0] 韶华.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J].炎黄春秋,2013,(5).
[21] 夏中义.“脑外科手术”是如何实施的——追问“苏联理论模式在中国”[J].探索与争鸣,2012,(4).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Humiliations in the Heart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1970s and 1980s
YIN Qi-ling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29, China )
The thawing period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pirit occurred during the 1970s. When people recall that historical period, their attention is always drawn by some new phenomena or new things so that they tend to ignore those old ideas and habits that are deemed outdated and stubborn, and lack interests in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In f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ity of those intellectual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carefully review those things hidden behind the "outdated" and "stubborn".
thawing period; intellectual; mentality
I206
A
1005-7110(2014)02-0095-05
2013-08-26
尹奇岭(1970-),男,安徽凤台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