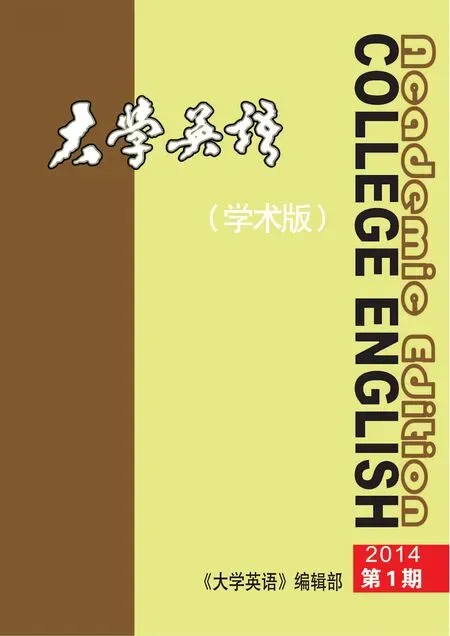透视英汉翻译中的顽疾问题及解决方案
魏晓亮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300350)
引言
根据统计,人类的语言多达三千种,可分为若干语系,分布在世界各地。如此庞大的语言系统,却无法割断人类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因为即使这些语言在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句法结构和表达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许多语言的核心句结构异常相似,几乎都有相同的主谓结构或主题-述题的结构,而表层上的结构则是由这样的一些核心句结构转换而来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翻译,作为一种基本的语言交际转换活动,自然要强调传达原作的意义,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语言之间的可翻译性是绝对的,不可翻译性是相对的。
虽然值得一提的是翻译实现了语言之间的转换,然而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生硬拗口、佶屈聱牙、实难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译文比比皆是。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有一词条:translationese,其释义为:“(表达不流畅、不地道的)翻译文体;翻译腔;佶屈聱牙的翻译语言”(孙致礼2003:95),实则是对这类语言文体的高度概括。这种翻译语言,有人称翻译体(或译文体),有人称翻译腔,有人称翻译症。那么带有这种翻译语言的译文,顾名思义,是一种病态的译文。这种译文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语言表达不顺,意思不明确,异己读者兴趣索然。例如:
When the lady ticket-seller saw her,her otherwise attractive face turned sour,violently so.(Griffin 1998)
当女售票员看见她时,她那在其他情况下还挺妩媚的面孔突然变色,变得怒气冲冲。
这个译文完全是在一板一眼地复制英语语言句型模式,无法表达出原文中所描述人物的鲜明、生动的特色,意义表达不紧凑:“when”引起的时间状语译成“当……时”,失去了“saw”和“turn”两个动作的之间紧凑感,栩栩如生的效果;“otherwise”照搬英汉词典的释义译成令人费解的“在其他情况下”;“turned sour”译成“突然变色”,紧接着再来一个“变得”。
改译:女售票员一看到我,原本颇为动人的面孔刷地一沉,变得煞是难看。
其二,语义表达不通,选词苍白、模糊,异己读者难明其意。
They(the jeans)draw no distinctions and recognize no classes;they are merely American.(Quinn 2000)
它们没有什么区别,也不分什么阶级;它们仅仅是美国人的。
原文中的“they”指牛仔裤,说牛仔裤没有什么区别,这似乎不符合事实逻辑,难道牛仔裤没有品牌、款式、档次、质量等方面的区别么?而“也不分什么阶级”、“仅仅是美国人的”这两个表达异己读者就更不明白何意了,难道牛仔裤曾经分过阶级,并且只属于美国人么?事实上,原文对牛仔裤的表述,暗指对象为穿牛仔裤的人。
改译:这种裤子对人不分贵贱,不论等级,只要是美国人都可以穿。
一、英汉翻译中的疾症
佶屈聱牙的翻译语言既然有这么大的危害,那么造成屡见不鲜的病态译文存在的顽疾又是什么呢?
1.英汉词典中“对等词”乱用
许多译者在做翻译工作时,往往会遇到一些晦涩难懂的词汇,不是根据上下文仔细琢磨该词的确切含义,而是急于到英汉词典里查找“对等词”,生搬硬套。查字典不仅要“手勤、眼勤”,还要“脑勤”,一定要多动脑筋,多加思考,特别是在查阅之前,先做好语言分析和意义推测的工作,切记不可孤立地查字典,否则往往会导致佶屈聱牙的翻译语言,甚至误解、误译。例如:
It is far more than the look of disapproval one occasionally gets.This was so exaggeratedly hateful I would have been amused if I had not been surprised.(Griffin 1998)
这比人们偶尔遇到的责难的目光凶狠多了。这是一种夸张的仇恨,我要不是因为感到吃惊,就会觉得很好笑。
在这个译文当中,如果说“责难的目光”还只是个不到位的问题,“夸张的仇恨”则有几分荒诞了。译文只是针对“exaggeratedly hateful”做了机械性的词性转换直译法,“exaggeratedly”由原文中的副词转化为译文中的形容词,在词典上的对等词条释义为“夸张的,夸大的”,“hateful”由原文中的形容词转化为译文中的名词,在词典上的对等词条释义为“憎恨,仇恨”。原文中的关键词是“look”眼神,目光,在这里,“hateful”修饰眼神应理解为“狠毒的,恶狠狠的”的意思,而副词“exaggeratedly”应理解为“过分地,过火地”。
改译:这种眼神比人们偶尔遭受的冷眼凶恶得多。那恶狠狠的样子表现得太过火了,我要不是因为大吃一惊,定会觉得很好笑。
又如:
“Linda,shut the window.I’m starving! ” And her teeth chattered as she shrunk closer to the almost extinguished embers.
“琳达,把窗子关上。我快饿死了!”她的牙齿在打颤,一面蜷缩着身子,向快要熄灭的炉火靠拢些。
“starve”的基本意义是“饿死”,但在原文中,前面是说话人下令关窗,后面是描写说话人冻得发抖,以及靠近炉火,完全和“饿死”无关,译者应该回归到原文的语言环境下,思考“starve”是否有跟“冷”和“冻”有关的意思。 在《韦氏大学词典》中释义为:intransitive verb,2 a archaic:to die of cold b British:to suffer greatly from cold。因此,“starve”应理解为“冻死”。
改译:“琳达,……
2.英文中“格式化”功能词滥用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曾在其《译意》(Translating Meaning)一书中说过就汉语和英语来说,意合和形合的对比是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孙致礼2003:73)。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句中的词语或分词之间需要功能词加以连接,而汉语则属于意合语言,词语或分词之间往往不需要功能词来连接。所以,我们在做汉译英时,原文中诸如连词、代词、介词之类的功能词,经常省略不译。而许多译者却摆脱不掉这种英语功能词的束缚,陷入“格式化”的僵死框架之中。比如,一看到 “when”引起的状语从句就译成“当……时候”,一见到“of”就译成“的”字,一见到过去分词后面接“by”就译成“被”,一见到“so...that...”就译成“如此……以至于……”。到处如法炮制的译文,必定给异己读者一种别扭之感。例如:
In the public square the tourists stand in a cluster and wave their hands when their names are called.(Quinn 2000)
在广场上,游客们站在一起,当他们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就挥挥手。
“当他们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完全是英语式的中文,冗长、枯燥,按照汉语简洁、明快的语言习惯,两者均被省略。
改译:在广场上,游客们站在一起,叫到名字就挥挥手。
又如:
...once again,the idea worked so well that word got round...(Quinn 2000)
……这个主意如此管用,以至于消息又一次传开了……
“如此管用,以至于……”是“英语式的中文”,在此颇有画蛇添足之意。
改译:这一招果然奏效,消息再一次不胫而走。
3.原文表达式误用
英语和汉语虽然在深层次中心结构上有着异常的相似度,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且两种语言隶属于两个不同语系的“非亲属”语言。在本着“语言之间的可翻译性是绝对的,不可翻译性是相对的”的翻译信念下,忽视英汉表达方式的差异性是造成翻译腔的另一顽疾。忽略英汉文化、习俗、知识、历史等方面的不同,不考虑英汉语中语言思维表达习惯的不同,对于原文中的习惯表达法、修辞比喻、句型句式、肯定和否定等等的机械移植,不但未能很好的传达原作的异国情调,反而弄巧成拙,造成令人头痛的佶屈聱牙的翻译腔。
例如:
This young man is as strong as a horse.
这个小伙子像马一样结实。
“马”是一种激情、雄壮、健硕的动物。中、西方人均爱“马”,中国古有“伯乐与千里马”的典故,西方流传着“特洛伊木马”的传奇和赛马的热情。西方人喜欢用“马”来形容人的伟岸,健壮;而中国人却习惯用“牛”来形容某人身体健壮。此源于中国人的内敛、谦虚的性格,他们在形容人时比较喜欢用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且又健壮的牛来喻人。
改译:这小伙子强壮如牛。
又如:
The people is to the people’s army what water is to fish.
人民对于人民的军队就像水对鱼一样。
汉语的否定概念常常用英语肯定句式来表达,反之亦然,这是由于两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致。原文在行文形式上是肯定的,即不带任何否定标志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意义上却是否定的。与汉语中的“鱼和水”的关系一致。
改译:人民军队离不开人民,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4.原文框架结构死用
在翻译工作中的另一个顽疾就是完完全全地遵守原文,恪尽职守地照搬原文的语序,词序等等,即实施者、行为、对象,状语的位置,无法打破原文结构的束缚,结果导致译文沾染上浓重的“洋腔”,不伦不类出现在异己读者面前。
Iwasn’t an enemy,in fact or in feeling.I was an ally.(Sanders 1999)
我不是(他们的)敌人,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情感上。我是(他们的)盟友。
原文是两句话,两句话的主语都是 “I”,但在译文中,汉语也来两句话,都以“我”字开头,难免会给人一种拖沓之感,不如跳出原文句子结构,将两句合成一句,将后面的 “I was”译成“而是”更为顺畅自然。
改译: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情感上,我都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盟友。
又如:
It used to be said that English people take their pleasure sadly.(Russell 1998)
过去人们常说,英国人郁郁不乐地享受乐趣。
显然,“郁郁不乐地享受乐趣”是对 “take their pleasure sadly”的机械直译,固执地把副词 “sadly”译成“郁郁不乐地”修饰动词短语 “take their pleasure”,译者完完全全地束缚在原文的结构框框之内,此译文实在别扭,并不符合汉语的逻辑。
改译:以前人们常说,英国人享乐时也郁郁不乐。
二、解决顽疾的方案
带有翻译腔的译文,是译者机械地模仿原文字面意思和表层结构的结果。而这些问题所在是译者翻译工作中存在的最普遍,也是最关键的顽疾所在,不解决这些顽疾问题,是无法胜任一名真正的翻译工作者的。那么如何克服这些顽疾呢?
1.积累广博的文化知识
翻译家应该是一个杂学家。除了浓厚的语言功底外,还应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会涉及到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貌、文学艺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知识面越广,对翻译的帮助越大。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知识,了解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提高汉语语言文化的修养,只有这样,译者才会形成文化差异和文化传递的意识,在翻译工作中才会考虑异己读者对译文所传达的内容文化的接受程度,有足够的准备做好翻译工作。
2.形神兼顾
做好翻译工作的先决条件,译者必然先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在内容和形式原则的关系上,一般来说,带有翻译腔倾向的译者比较重视忠实,往往不能统筹兼顾,认为翻译就是译意,形式无关紧要;而偏向“自由化”的译者则过分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即使在难以形神兼顾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形式上的对应,结果导致翻译症。著名的画家叶浅予曾精辟地论述过形与神的关系:“凡是画,都要求神形皆备,有人认为‘得意’可以‘忘形’,就是说,传神可以遗形,这是不妥当的。神是依附于形的,形不准,神也就失之真。所以,我们常说:‘以神写形’。”(许钧2001:32-33)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翻译。理想的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形神兼备,神寓于形,形似神更似,力求精确,完美地呈现原貌。
3.深解原文核心结构
正确的理解原文不仅是做好译文的前提条件,也是克服翻译腔的首要保障。理解原文不单单指理解原文的单词、短语、句法结构等和一些表层结构的东西,还要考虑到原文的文体结构,深层次语言逻辑关系,以及原文语言环境、历史背景和作者的思维方式等等全方位的透彻理解。否则译文很难复原“历史”。
4.尊重异己读者的语言习惯
在译文语言的结构安排和表达上,可以适当地照顾到原文形式上的特殊性,在必要且又允许的条件下,适度地保留原文的一点欧式句法特征。随着中西方文化不断地跨界交流,汉语语体文法也在不断地精深严密化,中国人逐渐地吸收了欧化句法的一些表达,但是在译文时,必须要把握好尺度,时时刻刻站在异己读者的立场忠实地翻译原文,即做到:能传译的则传译,不能传译的则向中国文法靠拢。
5.认真校核
译者在检查译文时可分四步走。第一步,用整体的眼光对照原文,检查是否有漏译、误译。第二步,用挑剔的眼光阅读译文,检查是否有不合汉语规范的文字,特别生硬拗口,晦涩难懂的“英式汉语”或者“中式英语”。第三步,用审视的眼光重读译文,检查是否有逻辑关系不明,且累赘的“格式化”功能词。第四步,寻求别人帮助校核。
Griffin,J.H.(1998).Into Mississippi[J].中国翻译(2)。
Quinn,C.(2000).The jeaning of America[J].中国翻译(2)。
Russell,B.(1998).The unhappy American way[J].中国翻译(1)。
Sanders,S.R.(1999).Women and men[J].中国翻译(2)。
陆谷孙 (1996).英汉大词典 [K].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孙致礼 (2003).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许钧,袁筱一 (1998).当代法国翻译理论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