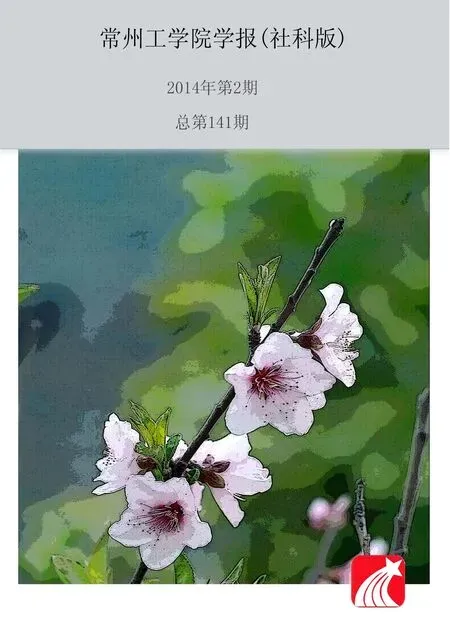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女勇士》中的“花木兰”
熊艳艳,王丹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女勇士》中的“花木兰”
熊艳艳,王丹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北京100037)
受福柯、德里达等人学说的影响,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克服了传统女性主义的弊端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其推崇的权利—话语观、反二元对立,并对男女差异的新的阐释,深层挖掘了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从而为女性主体建构拓展了新的空间。《女勇士》塑造的新的“花木兰”形象虽然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花木兰形象,但它在建构女性话语权、颠覆男/女二元对立范式及以女性自身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体等方面体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要旨。
后现代女性主义;花木兰;话语权;二元对立;女性经验
汤亭亭的《女勇士》自问世以来引发了无数评论、研讨以至论战,大都讨论这部作品在体裁、叙事形式以及主题(糅合了种族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等多个主题)等方面的创新。作为一个典型的跨学科文本,很多学者和评论家都可以从《女勇士》中找到值得研究的课题来进行研究,美国很多学者就从其自传体裁、叙事方式、女性身体与文化及华裔身份建构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因此它成为“近些年来美国大学里教授最广泛的作品之一”[1]。而国内较早评论这部作品的亓华1999年在《华裔美国女作家对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的解构》一文中就把《女勇士》定性为“一部传达女权主义思想的后现代自传体小说”[2]65,这一说法在国内评论界几乎没有异议,之后也有不少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女勇士》做过相关研究。
这些研究大都涉及《女勇士》这部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女性主义的双重性或者说其所面临的困境,这些恰恰是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固有的矛盾。通过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女性在选举权、教育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3]20。女性在家庭之外获得这些权利之后,又面临在平等工作机会与传统家庭妇女的角色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因此,受波伏娃“社会性别”这一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旨在“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3]26。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这样一来有些女性又担心会失去女性固有的特征,从而导致女性男性化进而影响到家庭生活,因此在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中,男女平等的衡量标准趋于男性的问题以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等问题就成为了绕不过去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从而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缺陷进行了矫正,从社会文化层面及意识形态领域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
成书于1976年的《女勇士》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全书描写了作者及自己的三位女性亲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从而使读者可以管窥20世纪后半叶华美女性的生活境况。与其他四章描述真实人物不同,作品第二章《白虎山学道》在改写中国传统文学里的女性形象花木兰的基础上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想象中的女勇士的形象,并糅进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一虚构的美国式“花木兰”寄托了华美女性反抗华美社区传统父权制及美国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的愿望,反映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某些思想,因此本文从建构女性话语权、颠覆男/女二元对立范式以及以女性自身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体等方面来解读作品中的“花木兰”。
一、颠覆男性话语,建构女性话语
后现代女性主义深受后结构主义大师福柯关于权力—知识形成学说的影响,福柯认为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而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也就是说话语即权力。于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在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中,女性一直生活和存在于男性所创造的男性霸权话语中,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话语权”[4]89。在她们看来,传统女性主义只是实现了表面上的男女平等,而男性话语规范并未被打破。在这一范畴中女性的自我实现仍由男性话语来规范,所以导致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女性要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就要按照男性话语所规定的标准来做,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女性在获得解放后又面临社会工作和家庭负担双重的压力。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解构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权。
汤亭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揭露了旧中国男性话语对女性的奴役以及女性自觉地以男性话语的规范来约束自己从而不自觉地强化了这种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女人胳膊肘朝外拐”[5]42-43这些话语使女性从一生下来就处于比男性低一等的地位,女孩子的满月庆典无法跟男孩子相提并论,文中的“我”在学校得了全A还是会被认为是坏丫头,在家里的地位也是跟弟弟相差甚远。女孩子从小就被灌输长大了第一要义就是要当好别人的妻子、伺候好丈夫这样的观念,女孩长大了成人妻子、做了母亲之后又会接着对自己的女儿灌输同样的思想,久而久之女性就把这种男性话语对女性的定位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则。甚至在父权制的旧中国男性利用话语权力造出了很多跟女性有关的字来表示“低贱、下等、不道德”等意思来从文字上贬低女性,汤亭亭就在《女勇士》中指出:“汉语中女子自称‘奴家’就是自己诋毁自己!”[5]43这里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男性利用权力制造出包含权力的话语,这些话语又反过来产生权力压迫女性,从而很好地诠释了福柯关于权力和话语的论说。
女性生活在男性话语构筑的社会规则中没有为自己言说的权利,只能作为男性主体的“他者”而存在,这才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女勇士》开篇第一句话“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5]1就道出了无名姑姑曾一度被排除在家族主流话语之外的遭遇,在传统父权制的旧中国,姑姑被主流话语认定犯下了通奸的滔天大罪而被逼抱着新生婴儿跳井自杀,还被彻底地从家族的历史中抹去,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而汤亭亭却把姑姑被隐瞒了几十年的故事讲出来,用自己的文字让无名姑姑有了一席之地,在想象无名姑姑故事的细节时,作者赋予了故事不同的声音,替姑姑诉说她犯下过错的缘由,不是像村民和族人那样把所有的不是都推到姑姑的身上,责难她不守妇道,而是推测姑姑可能是被迫的,因为“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是“某个男人命令她和他睡觉,成为他秘密淫乱的对象”,“她顺从了他,她逆来顺受惯了”[5]5。作者用自己的文字颠覆了传统父权话语对无名姑姑的界定,进而从女性自身对爱情、对生活的体验的基础上用女性的话语为无名姑姑鸣了冤,正了身。
有学者认为在《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汤亭亭“是在为无名姑姑的悲剧寻找解决的办法”[6],在这一章中,作者在妈妈讲过的花木兰的故事基础上想象出了一位美国式的“花木兰”。跟中国古典文学《木兰诗》多用第三人称叙事不同,汤亭亭用第一人称让女勇士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这就使女勇士跟中国传统的花木兰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在传统父权制的话语范畴中女性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是男人的话语构建了女性的存在状态,所以女性更谈不上拥有权力了,而汤亭亭却让故事里的女勇士有了为自己言说的权力,这就构成了女性作为“女性”而不是“他者”来构建自身主体性的第一步。在这个故事中汤亭亭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岳母刺字的故事移植到了女勇士的身上,岳母刺字的故事是岳飞的母亲为岳飞刺字勉励他忠君报国,而这里却是女勇士的父亲为女儿刺上了仇恨。这些刺在背上的字就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力量的话语,而这种原本只属于男性的权力现在也赋予了女性,正如女勇士自己在故事中所说的,“我看到我的背上满是一行行黑和红的字,像一排排士兵,我的士兵”[5]32。这些字也是声音的表达,女勇士除了浑身的武艺和手中的武器以外又获得了言说的权力。同时,女勇士后背上的刺字是她用身体记载了家族的历史,其个体作为家族的一分子与整个家族历史联结了起来而成为了“有身份的个体”,这些抹不去的字不仅使她免受无名姑姑那种被主流话语完全忽略的命运,而且还赋予了女勇士之后代家族发言的权力。
二、颠覆男/女二元对立的范式
妇女运动的纵深发展逐渐明晰了这样一个事实:妇女受压迫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现实,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包含了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曾指出,西方形而上学的话语把男人推到了至尊主体的地位,而女性只能是作为“他者”出现,在这种二元对立话语中,男性与女性处在一种主动与被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之中,男性通常与理性、强大、逻辑联系在一起,而女性通常与感性、弱小、混乱联系在一起。女性主义也意识到在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女性总是处于边缘地位,总是以男性的对立面出现。后现代主义主张去中心、解构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在后结构主义力图拆散的所有二元对立之中,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许是最有害的一个”[7]147。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女二元对立的范式,瓦解男女两性之间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突破以固有的男尊女卑意识为基础的束缚男女社会角色的桎梏,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为实现男女平等奠定思想基础。
汤亭亭在《女勇士》第二章中塑造的“花木兰”形象极大地颠覆了中国古典文学《木兰诗》中花木兰的形象。在《木兰诗》中,替父从军之前花木兰是一个在家里纺线织布、贤良淑德的少女,只是出于无奈才替父从军,而从军的过程始终是在男性性征的掩盖下进行的,她本身的女性特征无半点表露,因为在传统男权主义社会,女性作为弱者不能涉足领兵打仗、建功立业这种只属于男性的领域。而《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因为用第一人称叙事,虽然她身着男装但字里行间始终强调的是女性身份,处处流露出女性意识,对战场厮杀的描述只粗粗几笔带过,反而用大量篇幅描写在行军途中与丈夫相遇、怀孕生子的过程。作者还有意赋予“花木兰”力量和资本以进入二元对立意识下被男性独占的领域。《白虎山学道》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花木兰”在山上跟随一对老者习武学艺十五载,经历了各种生存考验,最后老者认为,“即使你与受过同样训练的士兵交战,即使他们大多数是壮实粗野的汉子,你也会获胜的”[5]30。这就打破了传统男女二元对立中女性弱小、依赖于男人的境况,从而获得了跟男性同样的力量而涉足女性不曾涉足的男性领域。作者还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岳飞刺字的典故和中国文化中战争之神关公的形象赋予“花木兰”力量,使她成为所向披靡、英勇威武的将领,带着大军一举攻入京城推翻了旧皇帝的统治,建立了新秩序。汤亭亭笔下的“木兰”从军故事打破了读者在传统二元对立思维中战争与男性相关联的定势,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呈现了当女性与战争相遇时的体验。
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颠覆二元对立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像第二代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凯特·米丽特在她的《性政治学》所呼吁的通过女性全面超过男性从而全面树立女性权威。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来源的解构主义曾“详细质疑和详细剖析了二元对立的本质,提示女性主义者不要陷入逆反而同构的思维模式,追求建立在女性霸权基础上的新的二元对立制度”[8],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具有较强的颠覆性,但它“期望建立一个兼容并包、平等和谐的社会,它没有推翻男性统治后登上宝座的野心”[9]。《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形象很好地诠释了这样一种承认男女两性差异、打破男女对立、追求两性协调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与《木兰诗》不同,汤亭亭塑造的“花木兰”“强调女性身份与勇士身份的共存,她的男扮女装并没有剥夺和瓦解她的女性身份”[10]106。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她的丈夫来到军营与她会合、相爱、并肩作战,作者着重描写了“花木兰”分娩前穿着肥大的铠甲,“肚子挺着,背后满是字”[5]36以及背着孩子去厮杀这样一种女性性征和男性性征结合于一身的场景,她对孩子和丈夫的爱抚并没有削减她作为勇士的威武,而同时她作为将军驰骋疆场也没有削减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温柔。孩子满月后她让丈夫带上孩子回家抚养而自己继续留在战场。战争胜利后,“花木兰”在完成自己建立新秩序的使命后又重新回归家庭,她跪在公婆面前说:“国事已毕,我要守在你们身边耕耘纺织,生儿育女。”[5]41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史以来最完美、丰满的女性形象,她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与自己的丈夫合作协调、相得益彰,共同负担了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三、以女性自身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体
由于女性在男权主义的传统中一直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的“他者”,因此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实践似乎都绕不开女性主体性建构这一话题。传统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性建构也有很多尝试,他们试图提供一种普适的、反映女性气质特点的主体性建构要旨,但因其无法逾越传统形而上和男性话语的桎梏,因而最终都摆脱不了男性话语权力的阴影,缺乏对女性自身真实体验的考量,并且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特质的女性的个体差异,因此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也就不利于女性的真正解放。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普世主义、二元对立等思想,对女性主体建构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强调女性自身体验的理论要旨。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应该对过去以理性为核心内容的人的主体性予以拒绝,彻底地摈弃男性出于对自身统治需要而言说的扭曲的女性经验,重新建构以真实女性经验为旨归的女性主体。这种真实的经验既包括女性个体因不同的种族、阶级、民族、国家以及性倾向背景而产生的千差万别的个别性经验,又涉及女性因共同的生命节律过程和生存方式以及所受到的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这类的共同经验”[11]73。
与中国传统的花木兰形象不同,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塑造的“花木兰”形象是在建构女性话语的基础上通过女性自身的体验来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她不通过跟男性的对比来显示出她的特性,不是进入男性领域以男性的标准来表现自我,而是以其自身的女性特质和自身的体验为标准来进行自我认同,展示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特性。产生于男权社会的《木兰诗》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为女性树碑立传的作品之一,但实际上其远没有为女性找到建构自身主体性的途径,骁勇善战的花木兰在拥有“主体性”的那一刻展示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在男性性征掩盖下的自我,做的是男性用来彰显自我而做的事情,丝毫没有女性的生活经验参与其中。而汤亭亭塑造的“花木兰”正是在这一点上颠覆了传统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的认识,着重渲染了女性自身的经验在建构女性主体中的重要性。在白虎山上跟两位老者习武的十五年间,生活单调而又辛苦,但女勇士作为一名女性,其独特的生活经验也使其明显不同于人们以往对武士的印象。习武到七年半的时候,小姑娘已经成熟了,跟老夫人探讨月经初潮的问题,而同时她觉得“经期也并未影响我的修炼,如平日一样,我感觉强健有力”[5]28。在水葫芦里看到父母为她举办婚礼时她也很高兴,因为她觉得“他们的爱使我感到生活充实。而且我的新郎与我青梅竹马,他爱我,宁愿做鬼夫”[5]28。而且在习武期间女勇士想念母亲时哭泣、担心丈夫和弟弟时有爱怜之情,这些对女性特殊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以及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的描写让女勇士作为一名女性其形象更加独特也更加丰满。如此一来,这里的“花木兰”在代父从军之前已经有了明确的身份认同,她是一名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而又温柔善良、情感细腻的女性。
“花木兰”在代父从军之后、厮杀疆场之时,其女性经验更加有助于其女性主体的建构。她初回到家乡时“家里人拥簇在我身边,我沉浸在爱的温暖当中”[5]31,出征前父母和乡亲们为她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拿下马身上的马褡子,塞满了膏药、草药、洗发用的兰草、备用衣服和我爱吃的桃饯。……简直就像准备嫁妆。”[5]32-33这些很女人化的经验让这个即将代父从军的“阴性的”勇士一点点地建构起来了,她不是按照既有的“阳性的”勇士的规定来建构自己,而是按照女性自身的体验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构建了一个性格鲜明、气质独特的女性个体。在战场上厮杀之时,作者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花木兰”在军中与丈夫相亲相爱、怀孕生子。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与代父从军这样的主题格格不入,但这正是真实的女性生活体验,正是女性区别于男性的所在。虽然要像男人一样去披荆斩棘,但是女将军跟男将军还是很不相同的,女将军也不必非得像男将军那样,女将军自有作为女将军的独特体验,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个会领兵打仗的女人,她身上所体现出的并不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而是女性领兵打仗时应有的气质、独有的气质,这跟男性无关,正如巴特勒所言,这些正是“做成”女人的那种东西。这些女性的独特体验让汤亭亭虚构的“花木兰”作为一名女性勇士具有了不同于传统花木兰形象的、鲜明的女性主体特征。
四、结语
汤亭亭在《女勇士》里塑造的“花木兰”虽然曾被认为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却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忽略的一页,两种文化碰撞下的“花木兰”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种种局限,昭示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建构女性话语权、颠覆男/女二元对立、建构女性主体等方面的突破,为女权运动探索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让花木兰这个艺术形象在新时代与女性主义的新发展结合起来,从而为这个中国的艺术形象增添了新的意义与内涵。
[1]Lim Jeehyun.Cutting the Tongue:Language and the Body in Kingston's″the Woman Warrior″[J].MELUS 2006,31(3): 49-65.
[2]亓华.华裔美国女作家对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的解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63-68.
[3]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5]汤亭亭.女勇士[M].李建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6]Shu Yuan.Cultural Politics and Chinese-American Female Subjectivity:Rethinking Kingston's″Woman Warrior″[J].MELUS,2001,26(2):199-223.
[7][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杨莉馨.影响与互动: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115-121.
[9]岳丽.后现代女性主义探析[J].探索,2009(6):163-165.
[10]Dong Lan.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1]冯石岗,李冬雪.后现代女性主义概观[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71-76.
责任编辑:庄亚华
I106
A
1673-0887(2014)02-0009-05
2014-03-02
熊艳艳(1982—),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