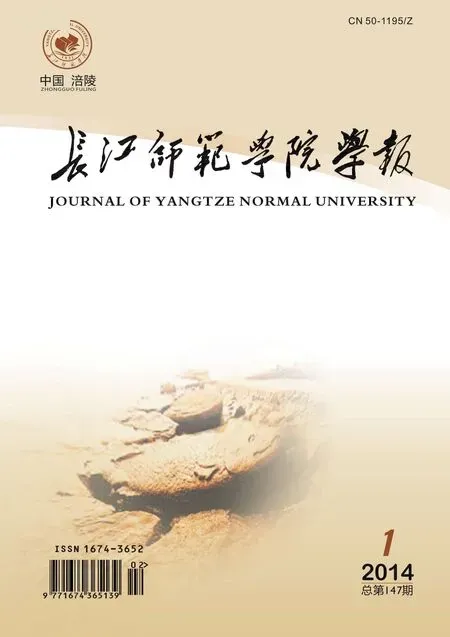试论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张 铭,李娟娟
(1.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重庆 400715;2.巴川中学校,重庆 402560)
试论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张 铭1,李娟娟2
(1.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重庆 400715;2.巴川中学校,重庆 402560)
隋唐时期,由于 “扬一益二”的经济格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作为帝王、文人等关中、河南民众逃避战乱的战略后方,巴蜀地区被隋唐中央政府倚为根本,在两朝中央政府的关注之下,巴蜀地区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巴蜀先民承接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开发态势,对巴蜀地区的生物资源再次进行了深入的开发。较之前一阶段的开发,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更为专业。无论地域、规模还是专业化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高度。这里试图将这一时期巴蜀生物资源开发进行分类整理分析,以期揭示这一时期巴蜀生物资源的开发进程与特色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生物资源;开发;交流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在长期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及优越的自然环境之下,承接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态势,其经济地位在全国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虽然司马光称为 “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 ‘扬一益二’”[1]。但是唐王朝却倚巴蜀为根本,国家有难,皇帝便逃亡巴蜀,如唐玄宗与唐僖宗奔蜀[2]。成都能成为唐王朝倚重的根本与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除了其工商业的繁荣外,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业是其发展的根本,而农业的发展与巴蜀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密不可分。这里即通过对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的探讨为契机,从一个侧面展示隋唐时期巴蜀地区资源开发的盛况。
生物资源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人类可以利用与可能利用的生物,包括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和微生物资源等,这三类资源是不同的,互不隶属。在隋唐时期,先民们生物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上面,有关微生物资源的史料较少,以灵芝为代表,主要作为祥瑞或者灾异的征兆。如 “武徳四年 (621年),益州献芝草,如人状。占曰:“王徳将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草亦木类也。”[3]为论述清晰起见,本文将植物资源的开发主要分为木材类生物资源的开发,粮食作物类生物资源的开发,经济作物类生物资源的开发,瓜果、蔬菜、香料类生物资源的开发。将动物资源的开发主要分为养殖业类型的动物资源开发、捕猎类型的动物资源开发和水产业类型的动物资源开发。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木材类生物资源的开发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巴蜀居民营建房舍、衙署、寺庙等建筑、车船等交通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具上面。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和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巴蜀地区人口密度大幅度的提高,围绕成都的益、汉、蜀、彭四州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人,是唐代相同大小区域内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4]。如当时巴蜀地区居民房屋多为木构架,众多的人口需要相应数量的房屋,如此众多的人口使得巴蜀地区生产生活用的木材数量也逐渐增加,城镇周边的林木被砍伐殆尽,逐渐地向边远地区采伐。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巴蜀地区用于运输各种物资或商品的船舶建造更加昌盛。隋初巴蜀地区就能建造容纳八百名战士的大型单体船,单体船建造技术发展很快,而舫船建造似乎没有明显的进步。唐代亦是延续隋代造船格局,即以单体船为主,舫船为辅[5]。这一时期巴蜀地区造船场主要分布在长江、岷江和嘉陵江沿线,主要有成都府、邛州、眉州、雅州、夔州、南州、黎州、嘉州、渝州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成都府、夔州、嘉州、渝州[6]。随着这些地区造船业的兴起,其周边适于造船的林木材料逐渐被砍伐殆尽,如成都府就因建筑材料缺乏及航道逐渐湮没,其造船业也逐渐衰落。当时巴蜀地区造船用木的上好材料是楠木,随着城镇周边地区楠木的砍伐殆尽,巴蜀地区也开始广泛种植楠木,当时以四川地区楠木种植最为广泛[7]。巴蜀地区在隋唐时期佛、道等宗教逐渐兴盛,这些宗教的兴盛带动了巴蜀地区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的兴建,当时成都城内的佛寺和道观建筑是仅次于官厅的庞大壮观建筑,这使得巴蜀及其周边地区适于建筑的大量木材又一次遭到砍伐。而巴蜀地区为保证交通顺畅而大量修建的栈道也使得沿线木材得到开发利用。当时巴蜀地区采盐业的兴起也使得巴蜀地区的竹木资源得到了广泛应用。当时竹类资源在采盐业中的应用主要是:巨竹固井;竹筒采卤,主要采用斑竹、寿竹、楠竹;竹制井篾,用于凿井;竹篾索,用于汲卤;此外还有竹把手、竹拭篾等,可见竹类资源在当时的应用之广泛[8]。除这些大型建筑用材外,巴蜀地区的众多生活器具也加速了这一地区木材类生物资源的开发,如当时彭州蒙阳郡的交梭、卭州临卭郡的酒杓、合州巴川郡的竹箸、书筒还作为贡品贡入中央[9]。这些生活用具,能作为贡品贡入中央,足见其质量的上乘与工艺的精湛,也只有在其大规模生产并名声在外后才能作为贡品贡入中央。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粮食作物类生物资源的开发主要表现为粮食种类的增加与粮食种植范围的扩大。隋唐时期随着巴蜀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水稻的种植范围逐渐由成都平原向北扩大到地处涪江冲积平原的绵州,向南扩大到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眉州,在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上也都有水稻的种植,但是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始终集中在成都平原及其毗邻的涪江冲积平原和岷江冲积平原[10]。而巴蜀边远地区的水稻种植业发展则很不均衡。如位于巴蜀边远地区的嶲州,唐代设置了8处屯田,约有屯田400顷。这些屯田多分布于清溪古道沿线的安宁河谷地带。南诏占领嶲州以后,将部分从事农耕生产的白蛮迁入今西昌、会理盆地等处从事水稻种植等,不过唐代嶲州需从内地转运粮食接济,估计当时安宁河谷水稻粮食作物种植规模较小,尚不足以供给当地消费[11]。而同样位于巴蜀边地的夔州城外则 “东城稻谷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丰都出现了新品种稻谷的培育,重恩稻 “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精耕细作,使三峡居民向平坝、宽谷以外的浅丘、山地进军,形成了三峡地区的畲田农耕运动[12]。不仅三峡地区如此,巴蜀内地也多缓山和丘陵,除在冲积平原种植水稻外,缓丘和山地则主要将水稻种植在梯田中,通过向山和向丘陵要田的方式扩大耕地面积,杜甫和张九龄都在其各自的作品中描写过当时巴蜀地区梯田盛行的景象[13]。黍和粟是巴蜀地区种植最为古老的旱地作物,这一时期的主要种植地区有所缩减,主要集中在今四川盆地内的丘陵低山和盆周山区,其中畬田种植黍和粟比较广泛[14]。如 “忠州刺史已下悉以畬田粟给禄食”[15]。由于巴蜀地区粮食生产的兴盛,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也开始兴盛。成都府蜀郡土贡的“生春酒”就极负盛名[16]。《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剑南岁贡春酒十斛”中的 “春酒”,亦是 “生春酒”或者 “烧春酒”。岑参诗云:“成都春酒香”,雍陶诗称:“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更身入长安”,都是对巴蜀地区所产高品质酒的赞美。由于前往关中地区的道路较为困难,往关中直接运粮较少,多以价值较高的酒类商品作为运往关中的物资。而巴蜀地区顺长江及其支流向东运粮则较多,如德宗时由于 “四镇”之乱,巴蜀粮食即 “方舟而下”转运至洛阳。
经济作物类生物资源的开发主要是隋唐时期巴蜀地区丝织品、麻织品、茶叶等生物资源的开发。在蚕丝生产方面,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丝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蜀锦在唐代与 “齐纨”、“楚练”齐名,仅四川一地就有28州产绢,占当时全国87个产绢州的三分之一[17]。这一时期重庆地区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有研究认为唐代重庆的丝织品至少有7种,但与当时成都及其附近地区以及四川盆地中部一些丝绸中心区 (如阆、果、渠州)的丝织品相比,则显得品种少,质量差。唐代重庆丝织品产地和品种在唐代后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产地主要是后期新增了昌州和夔州。这时重庆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是与今日四川紧密相连,地处嘉陵江流域的遂州的遂宁、青石二县和普州的崇龛县;其次是合州以及长江沿岸的忠州、开州、夔州等地[18]。实际上忠州的丝织业也较为发达,其产品黄绢不仅为刺史以下的官吏充俸,还作为贡品贡奉中央[19]。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巴蜀地区各州郡几乎都有各自的高品质纺织品或纺织原料进贡中央,分别是:夔州云安郡的纻锡布,忠州南宾郡的绵绸,涪州涪陵郡的獠布,兴元府汉中郡的縠,洋州洋川郡的火麻布、野苎麻等,利州益昌郡的金丝布,凤州河池郡的布,文州阴平郡的紬、绵等,壁州始宁郡的绸、绵等,蓬州蓬山郡的绵绸,通州通川郡的紬、绵等,开州盛山郡的白纻布、阆州阆中郡的绫、绵、绢、紬、縠等,果州南充郡的绢丝布、渠州潾山郡的紬、绵等[20]。以及成都府蜀郡的锦、单丝、罗、髙杼布、麻等,彭州蒙阳郡的叚、罗等,蜀州的锦单、丝、罗花纱等,汉州徳阳郡的双紃、弥牟、纻布衫、叚、绫等,卭州临卭郡的葛丝布、简州阳安郡的葛、绵、紬等,嶲州越嶲郡的丝布、花布等,戎州南溪郡的葛纤,梓州梓潼郡的红绫、丝布等,遂州遂宁郡的绫丝布,绵州巴西郡的轻容、双紃、绫、锦等,剑州普安郡的丝布等,普州安岳郡的双紃、葛布等,渝州南平郡的葛,陵州仁寿郡的鹅溪绢、细葛等,荣州和义郡的绸、班布、葛等,泸州泸川郡的葛布、斑布等[21]。巴蜀地区如此众多的州郡向中央贡奉高品质纺织品或纺织原料,足以证明这一地区纺织业的发达。隋唐时期巴蜀的丝织品在巴蜀对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唐代四川每年赐给黎州浅蛮衣3000匹使其观察南诏,唐朝官兵在战争中被南诏俘虏后,往往许以30匹绢才能赎回[22]。这一时期南诏还直接从巴蜀地区获取丝织品成品,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成都的纺织技术和技工,如大和三年 (829年),南诏引兵抵成都,陷西郭,“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23]这些 “子女、百工”多是纺织界的能工巧匠,他们的迁入直接促进了南诏纺织技术的发展。在巴蜀纺织人才和技术的帮助下,南诏所织锦绢 “密致奇采”,成为缅甸妇女的披锦缎,南诏还利用缅甸不产锦缎的情况迅速利用自身通巴蜀纺织技术的优势抢占了缅甸市场[24]。而除因政治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巴蜀丝织品对外交流外,隋唐时期巴蜀丝织品也作为大宗商品远销海内外。虽然这一时期有南诏阻隔了巴蜀地区对东南亚、南亚的丝织品贸易,但是通过邕州道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巴蜀丝绸也能转运并行销印缅。
这一时期另外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茶也开始大规模生产。由于西周时期巴蜀地区的茶叶即是其重要贡品[25],如此悠久的茶叶生产历史造就了隋唐时期巴蜀茶叶的优良品质。唐朝北方与西北方向少数民族饮茶风俗的兴起也大大促进了巴蜀等南方地区茶叶资源的开发。由于这一时期长江中部的今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各省的茶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得巴蜀地区的茶叶地位相对有所下降,但巴蜀地区的茶叶品质依然很高,自身相对于前代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四川的茶业,已经基本上与粮食生产分开,成为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极大地促进了其商品化进程,使得当时 “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26]如此优秀的品质与盛名使得巴蜀众多地区的茶叶成为唐王朝贡品,当时巴蜀地区茶叶能作为贡品的州郡有夔州云安郡、兴元府汉中郡等[27],以及雅州卢山郡等[28]。随着巴蜀地区汉代开始种植甘蔗,巴蜀地区的甘蔗种植地域逐渐扩大,到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甘蔗的主要产地已经扩大到益州、蜀州、资州、梓州、绵州、遂州、巂州等州郡。这一时期甘蔗的种类主要有两种,一类是果蔗,只能生吃,不能制糖;一类是糖蔗,虽可生吃,但主要用于制糖。制糖工艺也有很大的进步,能够生产沙塘、乳糖、蔗霜等茶品[29]。随着巴蜀甘蔗种植业的发展,巴蜀地区甘蔗及其产品逐渐成为贡奉中央的贡品,如成都府蜀郡的蔗糖、梓州梓潼郡的蔗糖、绵州巴西郡的蔗等即是作为贡品与关中地区进行交流的[30]。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产纸区域,出现了大批造纸作坊和造纸户,提高了造纸的专业性,专业化的生产使得巴蜀的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的蜀纸特别是麻纸已闻名天下,造纸原料主要有桑、麻、藤、竹、褚、麦秆、芙蓉皮等草类植物纤维,其时用竹造纸属于新工艺,而巴蜀已有大量竹纸生产了[31]。当时写成的 “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32],“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33]。蜀纸能够成为唐王朝中央的御用纸张足见其技艺之高超,而如此大量的纸张供应也可见当时巴蜀纸张专业化生产的规模与产量。中唐人李肇在 《国史补》中也提到 “纸之妙者,则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这更是对蜀纸技艺的直接赞美[34]。其时蜀中佳纸,制以为笺,早有盛名,杜甫已有 “蜀笺染翰光”的诗句。韦庄 《乞彩笺歌》之一:“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阁深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即描述了薛涛在浣花溪制笺的过程。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瓜果、蔬菜、作料类生物资源的开发主要体现在下述几种产品上面。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水果莫过于杜牧在 《过华清宫》中描述的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茘枝来”中的荔枝了。杨贵妃所吃的荔枝即来自巴蜀地区的涪州,这一时期涪州所产的荔枝品质上乘,荔枝在涪州以南地区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35]。这一时期也是巴蜀其他地区荔枝种植史上的鼎盛时期,其中宜宾地区 “僰道县出荔枝,一树可收百五十斗。”南溪县“多荔枝”[36]。乐山地区在这一时期也是重要的荔枝产地,故薛涛 《忆荔枝》赞曰:“近有青衣连楚水,素浆还得类琼浆。”这一时期沪州荔枝异军突起,仅列于宜宾之后居四川荔枝第一等第二位。杜甫尝到泸州荔枝后,作 《解闷》赞曰:“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巴蜀地区东部的万州、忠州一带也出产荔枝,白居易作 《荔枝图序》赞道:“荔枝生巴峡间,形园如帷盖。”总之,这一时期的巴蜀地区在北纬31度以南的成都、重庆、宜宾、泸州、涪陵、乐山、万县、雅安等地河谷地带都有荔枝种植,其中北纬30度以南的乐山、宜宾、泸州、涪陵四地品质最佳[37]。由于当时的保鲜技术限制,除向杨贵妃供奉的特例外,鲜荔枝的长途外运较少。当时能够贡奉中央鲜荔枝的主要是距离长安较近的涪陵地区,故其他地区了解巴蜀地区荔枝盛况主要是通过鲜荔枝的相关诗文及荔枝加工而成的副产品得知,如当时戎州南溪郡的土贡中即有“荔枝煎”。 “荔枝煎”即是用荔枝制作而成的蜜饯,适于长途贩运,故巴蜀周边地区都能获得这一美味[38]。柑橘也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重要瓜果之一,种植广泛且质量上乘,当时能将柑橘作为贡品供奉中央的州郡就有:夔州云安郡、兴元府汉中郡、文州阴平郡、巴州清化郡、开州盛山郡等[39],以及眉州通义郡、简州阳安郡、资州资阳郡、悉州归诚郡、梓州梓潼郡、绵州巴西郡、普州安岳郡、荣州和义郡等[40]。梅子也是隋唐时期巴蜀地区重要的水果之一。由于梅子的广泛种植,鲜梅子制成的 “梅煎”也是巴蜀地区的重要零食之一,更是对外交流贩运的重要商品之一。当时成都府蜀郡 “梅煎”更是作为贡品贡奉中央,这种特供也提升了巴蜀 “梅煎”的知名度,从而加大了巴蜀地区梅子这一水果的开发力度。蔬菜类生物资源的开发,这一时期巴蜀地区萝卜大量种植,以萝卜茎、叶等为原料制作的 “诸葛菜”在巴蜀地区广泛流行;元修菜在这一时期也被广泛开发成各种菜肴,在巴蜀民间广泛食用;其他如大巢菜、苦菜、蕺菜、冬葵、薤、棕笋、苦竹笋、芸苔菜、韭菜、芹菜、温食瓜、秋泉瓜、生瓜菜、菠菜、莼菜、落葵等常见蔬菜做成的菜肴也在巴蜀民间广泛食用。巴蜀人民早有食用野菜的习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广泛食用的野菜主要有野蕨菜、野生木耳、芥菜等[41]。当时巴蜀地区蔬菜中适于长途运输的蔬菜上品也有贡奉中央的,如兴元府汉中郡冬笋、糟瓜[42],以及绵州巴西郡的白藕就曾成为贡品贡入中央[43]。蔬菜类生物资源的开发必然伴随着大量作料类生物资源的开发,否则大量菜品则无从成为美食。当时巴蜀地区广泛使用的作料主要有蒟酱、姜、茱萸、花椒、桂子、食麻等[44]。由于作料便于保质和运输,也是巴蜀对外贸易的重要产品,其中的上品也是巴蜀贡奉中央的贡品,如兴元府汉中郡即以夏蒜作为贡品贡入中央[45];黎州洪源郡则以椒作为贡品贡入中央[46]。
药用生物资源的开发方面,由于唐代医药发展相当完善,除传统的私人传授外,国家也采取措施,在太医署设医学,招收学生,广泛普及医药知识[47]。在唐代医学繁荣的背景下,巴蜀地区的药用生物资源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巴蜀众多州郡中均有其上乘中药材贡奉中央,主要有:万州南浦郡的药子,利州益昌郡的天门冬、芎藭等,扶州同昌郡的芎藭,集州符阳郡的药子,通州通川郡的枫香、白药等,开州盛山郡的芣苢,渠州潾山郡的药实等[48],以及雅州卢山郡的菖蒲、落雁木等,茂州通化郡的羌活、当归等,维州维川郡的羌活、当归等,松州交川郡的当归、羌活等,当州江源郡的当归、羌活等,悉州归诚郡的当归,柘州蓬山郡的当归、羌活等,恭州恭化郡的当归、升麻、羌活等,真州昭徳郡的大黄,遂州遂宁郡的天门冬,合州巴川郡的药实,龙州应灵郡的厚朴、附子、天雄、侧子、乌头等,普州安岳郡的天门冬,渝州南平郡的药实,陵州仁寿郡的续髓、苦药等[49]。如此众多的州郡能将其土产药材贡入中央,足见当时巴蜀地区药物的丰富与开发的深入。
捕猎类型的动物资源开发主要表现在当时野生动物的获取,除获取野生动物的皮肉外,麝香也是捕猎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目标。麝香是当时阿拉伯商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贩运的主要药材,因为产于益州等巴蜀西部地区的麝香质量上乘,阿拉伯商人认为 “疗效极好”,这也加速了巴蜀地区麝香这类野生动物资源的开发[50]。当时巴蜀地区诸多州郡都有麝香进贡,主要有洋州洋川郡、利州益昌郡、凤州河池郡、文州阴平郡、扶州同昌郡、通州通川郡[51],以及嘉州犍为郡、嶲州越嶲郡、黎州洪源郡、茂州通化郡、翼州临翼郡、维州维川郡、姚州云南郡、松州交川郡、当州江源郡、悉州归诚郡、柘州蓬山郡、恭州恭化郡、保州天保郡、真州昭徳郡、昌州下都督府等,如此众多的州郡贡奉麝香,证明了巴蜀地区麝香的丰产,也证明了巴蜀地区麝这一鹿科动物分布之广泛及其捕猎程度之高。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隋唐时期中国人用犀牛角做成的腰带非常昂贵,当时野生犀牛主要分布在印缅交趾等地,但 “益、宁”也出产犀角[52],当地居民也捕猎本地野生犀牛以获取犀牛角作为加工原料,杜甫 《冬狩行》即记载广德元年 (763年)冬猛士三千在梓州行猎,“生致九青兕”的行动[53]。但是大多数犀角原料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从印缅等地输入巴蜀地区,经过当地工匠的深加工后再转销全国[54]。同时,隋唐时期巴蜀地区华南虎也分布广泛,“唐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开元 (713—741年)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55]“开元(713—741年)末,渝州多虎暴。”[56]由于虎患渐烈,必然引起当地居民组织捕杀华南虎,主要为除掉虎害,当然也不乏获取虎皮、虎骨等双重的目的。熊罴也是当时巴蜀地区的捕猎对象之一,如夔州云安郡即以捕猎而来的熊罴作为贡品贡奉中央[57]。在小型动物捕猎方面,由于此时期巴蜀地区生态环境较好,野兔、山鸡、狐狸、野生鱼较多,都能成为人们的捕猎对象,天宝十四年 (755年)“剑南道获白兔一,献之”[58]。夔州云安郡也以捕猎的山鸡作为贡品贡奉中央[59],松州交川郡即以捕猎而得的狐尾作为贡品贡入中央[60]。唐代沱江 “多鱼鳖”,峡江地区 “顿顿食黄鱼”,证明当时巴蜀地区捕鱼的兴盛[61]。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畜牧养殖业类型的动物资源开发的格局主要是巴蜀边地特别是以西部边地出产的马、牦牛、羊为主,而巴蜀内地则由于农耕的需要,主要出产水牛、黄牛作为耕作工具。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养马业已发展成为国家马匹资源供给地之一。蜀马体型小,善攀爬,能适应山区托运和行走,为茶马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运载基础[62]。这一地区所产蜀马的上品还要进贡中央,汉州徳阳郡、嶲州越嶲郡土贡中即有蜀马[63]。养牛除获取劳动力外还可提供皮、乳制品、肉等,如茂州通化郡即以干酪作为贡品进贡中央;翼州临翼郡、维州维川郡、悉州归诚郡、保州天保郡则以牦牛尾作为贡品贡入中央[64]。蜜蜂养殖也是这一时期巴蜀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养蜂除获取蜂蜜外,还要获取蜂蜡。蜂蜜主要作为食物,也可用于酿制蜜酒,孟冼在 《食疗本草》中指出蜜酒有食疗的作用。隋唐时期还发明了蜡烛,唐代学者贾公彦记载了以蜂蜡制烛的方法,蜡烛己广泛用于王侯家,永泰公主和章怀太子墓道壁画上即绘有手持蜡烛的宫女,唐诗中亦有大量描写蜡烛的诗句。除广泛用于制蜡外,蜂蜡也广泛用于印染、制作丸衣,加工成蜡丸(或蜜丸)传递重要文书[65]。如此广泛的市场,注定了当时巴蜀地区养蜂业的繁荣。当时巴蜀地区诸多州郡有养蜂产品进贡中央,主要有夔州云安郡的蜜、蜡等,涪州涪陵郡的蜡,洋州洋川郡的蜡,利州益昌郡的蜡烛,凤州河池郡的蜡烛,兴州顺政郡的蜜,文州阴平郡的白蜜、蜡烛等,集州符阳郡的蜡烛,巴州清化郡的石蜜,通州通川郡的蜜、蜡等[66]。以及眉州通义郡的石蜜、翼州临翼郡的白蜜等[67]。
隋唐时期,由于 “扬一益二”的经济格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皇帝、文人逃避战乱的战略后方,巴蜀地区被倚为朝廷根本,在两朝中央政府的关注之下,巴蜀地区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生物资源开发更加广泛和深入。如这一时期随着巴蜀地区人口的增加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林木采伐向远离城镇的更为边远的地区推进,林木的采伐量也大幅度增加;粮食生产的范围突破河流冲积平原和较为宽广的坝子,向开发难度更大的坡地推进,形成了壮观的畲田景观;由于北向路途较为艰难,巴蜀粮食外运以长江及其支流所代表的东向外运为主要路线;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巴蜀地区纺织产品在全国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能将其纺织产品作为贡品的州郡较前一时期更加众多,而且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纺织品更是行销海内外;虽然这一时期巴蜀地区茶叶生产在全国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是其品质依旧上乘,仍有众多州郡能将茶作为贡品贡入中央;在巴蜀舒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蔬菜、作料的种类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增加,烹饪出了无数著名菜品;隋唐时期医学事业的发展也使得巴蜀地区本身蕴藏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得到了广泛的开发;虽然这一时期渔猎经济在巴蜀地区仅作为补充经济,但是在巴蜀周边地区渔猎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周边州郡的贡品中不乏捕猎而来的珍禽异兽等渔猎产品;养殖业与前一阶段相比较为明显的变化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养蜂业逐渐兴盛起来,众多州郡养蜂业的副产品作为贡品贡入中央,作为商品行销全国。
在巴蜀地区对外交流方面,北向交流显现出明显的贡奉特色,即其贡奉物产占了巴蜀地区北向交流的主要部分,这主要是因为隋唐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均在关中地区。但是其间也有往复,如东都的兴起,使得巴蜀地区对外生物资源东向交流也呈现出一定的贡奉特色。在东向交流方面商业特色较为浓厚,因为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扬州等东南地区的城镇逐渐发展起来,在 “扬一益二”的经济格局下,传统农业社会中东向商品交流多与生物资源开发相关。南向交流的政治和商业特色都有一定呈现,因为南诏的兴起,使得巴蜀地区与南诏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这使得巴蜀地区生物资源开发在南向交流方面,受中央与南诏关系的影响较大,如南诏入侵成都掳走当地技工,使得南诏的生物资源开发进程得以大幅度提高,而巴蜀地区由于人才资源的大量损失使得本地区生物资源开发进程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与南诏和平相处时,与南诏交流则呈现出商业贸易的繁荣局面。在西向交流方面,随着唐代巴蜀与吐蕃地区茶马贸易的兴起,茶马贸易在巴蜀地区生物资源开发西向交流方面占据着主要地位。在巴蜀地区四个主要方向的生物资源的交流中,西向交流因茶马古道刚兴起且与吐蕃和战不定而影响较弱,东向交流因为长江及其支流、南向交流因为南方丝绸之路都较为方便,但是影响不及北向交流;北向交流因为先秦以来即已形成的交通格局且政治中心在关中的缘故,其影响最为重要,也是巴蜀生物资源贡品的主要流向。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纪七十五)[M].四库全书本.
[2]江玉祥.唐代剑南道春酒史实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3][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三十四五行志)[M].四库全书本.
[4]路 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421.
[5][10][14][29]李敬洵.四川通史(第三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398-399、285-286、286、404-406.
[6]夏自金.隋唐时期西南地区的造船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
[7]蓝 勇.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1995(4).
[8]杜绍庆.竹在井盐生产中的应用[J].盐业史研究,1988(3).
[9][16][19][20][21][27][28][30][38][39][40][42][43][45] [46][48][49][51][57][59][60][63][64][66][67][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十二志第三十二地理志)[M].四库全书本.
[11]朱圣钟.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2).
[12]蓝 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23.
[13]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269.
[15][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一感伤三古体词)[M].四库全书本.
[17][22]黎小龙,蓝 勇,赵 毅.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2.
[18]卢华语.唐代重庆纺织产品刍议[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2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唐纪六十)[M].四库全书本.
[24]孙仲文.隋唐时期的西南丝路及货币[J].云南金融,1997(11).
[25][东晋]常 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M].四库全书本. [26]陈 虹.四川茶叶生产的历史考证[J].农业考古,2000(4).
[31]邓剑呜.薛涛笺在中唐时期对四川造纸业的影响与贡献[J].中国造纸,1993(6).
[32][五代]刘 呴.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第二十七经籍下)[M].四库全书本.
[33][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第四十七)[M].四库全书本.
[34][北宋]倪 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九历代书论三十九器用之三纸谱)[M].四库全书本.
[35][37]蓝 勇.四川荔枝种植分布的历史考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4).
[3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剑南道)[M].四库全书本.
[41][44][61]蓝 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70-274、275、274.
[47]计光辅.唐代的医药机构与医科大学[J].中医药文化,2007(4).
[50]蓝 勇.唐宋川滇滇缅通道上的贸易[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1).
[52][唐]魏 征,等.隋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梁睿传)[M].四库全书本.
[53][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M].四库全书本.
[54]蓝 勇.南方丝绸之路[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99.
[55][宋]李 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六虎一)[M].四库全书本.
[56][宋]李 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六虎二)[M].四库全书本.
[58][宋]王钦若,[宋]杨 亿,等.册府元龟(卷二十四帝王部符瑞第三)[M].四库全书本.
[62]李永桂.四川畜牧史略[J].四川畜牧兽医,1995 (3).
[65]杨淑培,吴正恺.中国养蜂史大事记[J].古今农业,1994(3).
[责任编辑:丹 涪]
F329.4.7
A
1674-3652(2014)01-0017-07
2013-12-27
张 铭,男,四川德昌人,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李娟娟,女,重庆城口人,主要从事社会生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