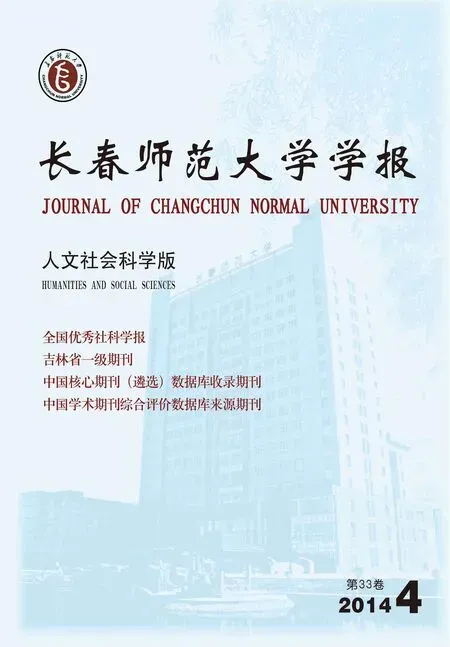在历史叙事中彰显生命意识
——试论《红高粱》与《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人性描写
于子月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在历史叙事中彰显生命意识
——试论《红高粱》与《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人性描写
于子月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莫言在写作中十分注重对生命感觉的描写。他的作品以显性的方式呈现人对历史的感悟,以隐性的方式书写历史对人物的评价。在人物与历史之间,历史只是一个被淡化了的时间背景,人对生命的感觉才是莫言创作的核心与关键。
生命感觉;历史书写;《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
人对生命的体验以及生命赋予人的感觉都是莫言写作的重要部分。莫言对生命意识的描写直观而犀利,在感官、心灵上都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然而,在这些生命感觉的背后,蕴含着的是作者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他尝试通过对个体生命意识的书写将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的部分揭示出来。《红高粱》通过“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抗战期间的民间英雄传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某种家国意识、民族意识,但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所指。作品将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以超越文明的视角展露并赞美了一种暴力的、野性的、不羁的生命强力。《红高粱》有两条故事线索:一是余占鳌组织乡野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二是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爱情故事。前者逾越了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单纯为生之自由而进行的反抗;后者则包含了野性的、激情的爱欲。二者缠绕交织,展现了异于寻常的民间野性之美。1987年,莫言开始写作《天堂蒜薹之歌》。与《红高粱》相比,这部作品将笔触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作者所处的现代社会,纪实性较强,但也没有削弱人的主体地位,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依然是对人的生命意识的呈现。
一、对生命感觉本身的书写
无论是《红高粱》还是《天堂蒜薹之歌》,都似乎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红高粱》将故事放置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中,《天堂蒜薹之歌》则置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环境中。然而,历史语境实际上只承担着故事讲述的背景作用,莫言真正在意的是那隐含在历史幕布后的生命意识。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和历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莫言善于写生命感觉的本身,这种生命感觉是脱离历史规范的,是无法用历史的准则来衡量其是非的;写到与历史相关的生命感觉时,人物对历史的体味是显性的,历史对人物的评断是隐性的。作者不再将历史作为评断人物的标准,而是反其道行之,将人物的生命体验作为评断历史的标准之一。如《红高粱》的一条叙事线索:戴凤莲出嫁时,余占鳌是她的轿夫,余占鳌试图调戏戴凤莲,并在她回门时将她劫进高粱地里。事实上,性爱自由是莫言在多部小说中反复书写的,这成为莫言笔下人物对生命自由的追寻的重要方面。《红高粱》中写道:“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她面上哗哗剥剥的燃烧。……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暗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了过去。”[1]这大胆而越轨的文字描述凸显了蓬勃的生命激情,无视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也摆脱了伦理道德的约束。莫言对这种生命形态作了直观、自由的书写,他所书写的来自民间的生命激情脱离了历史的限制,展现了强有力的生命意志。莫言在这里表达的是生命感觉本身,而不是将生命作为表达历史的某种手段。他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时说:“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时那样写得泪迹斑斑,甚至血泪斑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2]在生命和历史之间,生命是实实在在的,莫言强调的就是鲜活的生命力与人对生命的那种感觉,正如余占鳌的生命轨迹一样,桀骜不驯、我行我素,游走于历史之外,却彰显着生命的强光。
二、将历史埋藏在生命感觉之下
当然,凸显人的生命意识并不意味着莫言是在忽略历史,他只是在历史与生命之间更看重人的生命以及对生命力感的把握,这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文学描写阶级、反映唯物史观形成鲜明对照。《红高粱》中描写罗汉大爷被活活剥皮的一段文字历来被认为过于血腥:“罗汉大爷的头皮被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3]他没有直陈宏大的历史,而是以感觉的书写让人不自觉地颤栗,直逼人生的惨淡与淋漓的鲜血。通过对生命感觉的复现,莫言打通读者与人物的世界,从而让读者在细处以亲历者的姿态窥见历史。这种历史又是带有个人化色彩的,是以“我”的立场为基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红高粱》中戴凤莲被嫁给麻风病人,《天堂蒜薹之歌》中金菊被换给老气管炎病人,在女主人公的遭遇上两个故事如出一辙。前者中“我爷爷”杀人越货,实现了爱的自由。莫言并未从历史、道德的角度评断“我爷爷”的作为,而是赞颂了这种强悍的个人意志。后者中高马企图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金菊的爱情,但是他对法律的依赖、对自由的追求被生硬地打断了。高马与金菊私奔,被金菊的大哥、二哥和杨助理员捉了回来,老大老二将高马打得奄奄一息。小说中这样描写金菊的感觉:“一股腥甜的味道从喉咙深处慢慢涌上来,她一张嘴,看到鲜红的一团东西缓缓地落在胸前一株枯草上。我吐血啦!她胆战心惊;我吐血啦……”[4]147通过感觉的描写,莫言打通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感性相通,使读者理解金菊那种恐惧、那种对爱人的心痛。这时,一切历史都被遮蔽在个人感觉之下,唯独生命感觉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小说藉此使读者经由金菊的生命感觉步入历史,看到作者对那些来自于农民却又腐败、残忍的乡村干部的批判。“高马”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意象,代表着高大的马匹。退伍军人高马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健康、强劲、富有活力,这个人物身上承载着莫言对原始的、健康的人性的追求,是一个理想型的人物。高马蓬勃的情欲与《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一样,是原始的、野性的,但为什么二者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一样的,结果却是迥异的呢?不难看出,与《红高粱》纯粹的民间立场相比,《天堂蒜薹之歌》更全方位地描述了民间的情与仇、爱与恨、耿直与狡黠、残忍与善良。在写到与历史相关的生命感觉时,高马所感受到的历史是残忍而荒谬的,所以跃然纸上的便是残忍而荒谬。这已然与现实的历史不同,而是更注重于个人感觉的书写。
《红高粱》的另一条故事线索并无深刻的政治色彩,虽是战斗,但无关于战争。余占鳌伏击日本汽车队并非出自家国大义,而是出于自卫的求生本能。身处和平年代,《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人物对生之自由的追求并没有前者那样强悍暴力。高羊,人如其名,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莫言在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最朴实、温顺的农民秉性。高羊从小便任人欺负,长大后因偷葬亡母而受尽凌辱,如今只想以卖蒜薹谋生计,不想供销社反复无常,各部门变相收费。余占鳌追求生之自由的方式是强悍暴力的,高羊生存的方式是忍气吞声。然而,当高羊被莫名其妙地推进县政府时,他也变得粗野狂暴起来,他从打砸行为中获得了一种快感[4]286。这里,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只淡化为了一个模糊的背景,那些成败功过已然不是描写的重点,人物个人的生命感觉成了重心。
三、结语
历史不是与人无关的,但就莫言笔下的主体人物——农民来说,历史对于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他们而言,比历史更为真实的是个人的生命感觉。卡希尔说:“历史学家并不只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史次序排列的事件。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着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和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5]作为人学学者的莫言,寻找的正是这种充满着“行动与激情”的生活,这是传统的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中所缺失的,而在莫言这里得到了凸显。
[1]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66.
[2]张志忠.莫言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125.
[3]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34.
[4]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卡希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37.
2014-02-13
于子月(1989-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I207
A
2095-7602(2014)04-006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