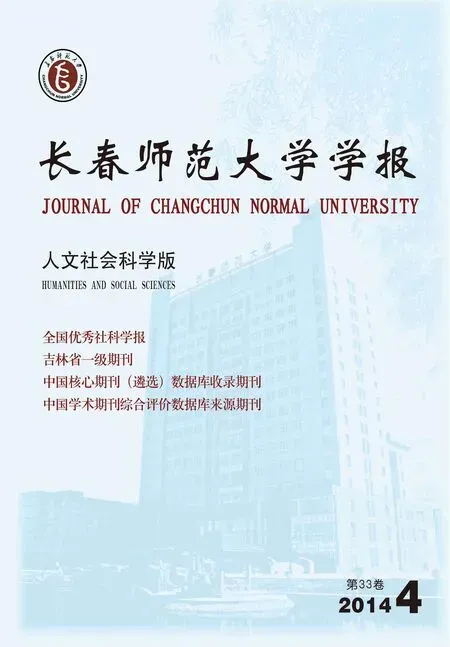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议会制度的分析与批判
陈英宝,王骥野
(1.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议会制度的分析与批判
陈英宝1,王骥野2
(1.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议会制度是近代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代议制机构的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与合理性,其实质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进行了表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适当分离的剖析,对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新制度的进步性给予了肯定,但对其阶级压迫的实质也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形式与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西方议会制度进行了认真观察,对其本质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一、西方议会制度的形成
议会源于法语,意思是“去发言”。它意味着协商和评议,也暗示着议院起到辩论室的作用。具体而言,西方的议会制度最早来源于英国封建等级会议。13世纪以前,英国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那时,国王指派僧侣、宫廷大臣和大封建领主组成“大会议”,作为处理政务的咨询性机构;同时,利用这种会议来决定增课特税。13世纪初,英国国王约翰在与封建领主的斗争中败北,被迫于1215年签署了《自由大宪章》。该宪章限制了王权,规定国王在征税前必须召开“大会议”,以征求“全国同意”,从而为议会的产生奠定了法律基础。1258年,各地诸侯又逼国王签订了《牛津条约》,决定把国家权力交给各地诸侯操纵的15人会议,并规定每年召开三次会议,这就为英国议会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后来,由于各地诸侯操纵的15人会议发生分裂,以西门·孟福尔为首的一派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1265年召集了有封建领主、骑士、城市市民等参加的“等级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代表参加,又获得了监督国王的财政收支、影响国王制定政策的权力。等级代表会议实际上成为带有立法性质的国家代表会议形式的权力机关。这便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雏形。从1343年开始,等级议会内部逐渐形成了两股势力,一股主要由大贵族、大僧侣组成,另一股主要由骑士和市民组成。前一股势力发展成为上院,即贵族院;后一股势力发展成为下院,即平民院。随着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和让·雅克·卢梭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总结英国议会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思想,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使议会制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议会形式不仅在英国发展得更加完备,而且很快风靡于美国、法国等欧美主要国家。
由于各国阶级力量对比、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民族状况等因素的差异,各国议会的具体形式有很多不同之处。大致分为英国式和美国式两类。1787年制定的美国联邦宪法将“三权分立”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确认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各下级法院。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先后颁布19部宪法,政体多次变化,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制度一直未变。德国1871年统一后也实行由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组成的议会制。瑞士不采用分权制,实行有别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委员会制,但由国民院和联邦院组成的联邦议会也借鉴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和内部组织结构的许多经验。毫无疑问,议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代议制机构的组织形式。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议会制度产生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形成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专门论述,但这丝毫不能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认识的深刻性。在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产生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和现实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议会制度经过中世纪的孕育、在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得以确立的历史事实,说明议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进步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来的实践表明,“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1]第1卷,234可以说,议会制度是以“三权分立”原则为依据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对此,马克思曾这样评论过:“在某一国家的某一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1]第1卷,99
封建时代的末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桎梏越来越不能忍受,迫切要求取得政权,以新的政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有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幻想用提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和限制王权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以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为主要代表的“三权分立”学说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和北美各国的资产阶级以流血和不流血的方式与封建势力不断斗争,最终通过暴力革命摧毁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自己的专政。显然,资产阶级议会不是封建代议机关简单的继续,而是近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的发展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议会的地位、作用和拥有的实际权力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经济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相适应的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更加趋向反动,要求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对内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外侵略和扩张,越来越感到议会制的统治形式多所掣肘。与此同时,议会原来所享有的传统权力,如核准国家预算、通过并颁布主要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等遭到严重的削弱。政府不仅不再听命于议会,相反却在实际上操纵着议会的活动。“议会至上”的时代结束了,出现了“行政专政”的局面。
其次,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贵族斗争的产物,是对贵族特权的否定,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以当时的法国为例,提出“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1]第1卷,65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明确指出:“议会在本质上是各种利益力量博弈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胜出的结果”。[2]第1卷,471英国的议会同样是资产阶级与贵族斗争的产物。从1642年到1688年,英国国内政局充满着资产阶级同被推翻的封建主的斗争。查理一世被处死后,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1658年克伦威尔病死,1660年出现旧王朝的复辟。查理二世上台后处处同资产阶级作对,其继承者詹姆斯二世也是如此。1688年,资产阶级政党赶跑詹姆士二世。英国议会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于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根据这些法律,议会在形式上成了英国唯一的立法机关,享有立法权和决定预算及其他重大权力。
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议会制度必然要以平等的形式来掩盖其不平等的本质属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
从西方政治历史的发展来看,议会是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胜利后所取得的“战利品”,也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客观需要。
首先,议会的出现和议会制度的确立是历史的进步。议会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马克思指出:“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了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了的”[1]第1卷,597-598。“公民权利”同“人权”一样,最早是由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目的是要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打破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的束缚,使广大无产者能够摆脱封建势力给他们带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半依附的社会地位,能够“公平”、“平等”、“自由”地受资本家的剥削。“他们通过了一条严峻的法律,禁止行贿、舞弊、恫吓和一切选举中的诈骗行为”[2]第8卷,398。
其次,资本主义议会制度所要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有产者的权利。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对每一个公民权利的保障都是具体、明确的,在宪法的字面上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同样的权利,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被西方议会制度的表现所蒙蔽,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里,宪法和法律宣布的这些“自由”和“权利”是狭隘的、虚伪的和残缺不全的。恩格斯对于议会制度的这一本质属性是有着清晰认识的:议会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1]第1卷,234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宪法宣布的公民权利是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被剥削制度为基础的。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因而也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其内容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资产阶级宪法宣布的公民权利是受法律限制的。资产阶级通常在宪法里冠冕堂皇地宣布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同时又在法律上加以限制或取消。马克思指出,宪法的每一章节本身都包含自己的对立面。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对劳动人民说来就只能是空话。“资产阶级和工人只有通过议会代议机关才能真正有组织地利用政权,而这个议会代议机关只有在得到参加讨论和表决的保证时才有一点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它能掌握‘钱柜的钥匙’,它才有一点价值。”[2]第16卷,81资产阶级宪法所宣布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就是资本家用金钱制造舆论的自由。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对国民议会来说,人民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议会的生活中找不出人民生活的反映”。[2]第16卷,81
再次,普选权的形成是一种历史进步的体现,但对普选权的限制使这种进步性受到了很大限制。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在自由、平等的口号下提出普及的选举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议机构等要求,用来对抗封建王权,取代“等级议会”、“等级授职制”等封建统治形式,从而对团结工农群众、进行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从本质上看,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为他们要把民主局限为有权把代表人民而又镇压人民的人派到议会中去。尽管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还是充分肯定了普选制的重大历史进步意义。恩格斯指出“普选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2]第21卷,197。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是有一个过程的,当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政治解放才能获得彻底解放时,就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起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选票在议会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自己政党组织、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再也不是无足轻重、任人摆布的对象了,普选制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进行政治斗争的广阔而合法的大舞台。当然,革命导师并没有忽略普选制的阶级局限性。恩格斯称:“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2]第21卷,198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进行了表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适当分离,在这种分离中透视了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本质属性,对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新制度的进步性给予了肯定,但对其阶级压迫的实质也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14-02-12
陈英宝(1971- ),男,吉林长春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馆员,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A811
A
2095-7602(2014)04-0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