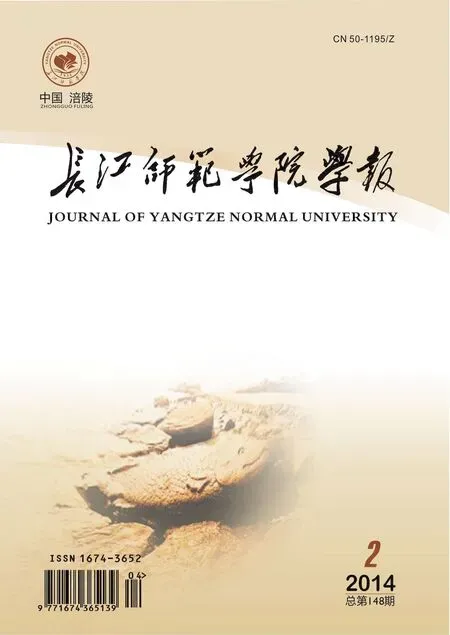明代土家族土兵抗倭的缘起、进程与取胜原因
李良品,张 芯
(1.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2.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中国土司文化研究
明代土家族土兵抗倭的缘起、进程与取胜原因
李良品1,张 芯2
(1.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2.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因明代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劫掠、破坏社会生产的严峻形势,土家族土兵毅然地参加了抗倭战争。土家族土兵在三年多的抗倭战争中,或与广西俍兵共同抗倭,或独立地参加抗倭,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争的正义性、严格的纪律性、战术的精湛性和器械的独特性,无疑是土家族土兵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明代;土家族土兵;抗倭
明代嘉靖年间 (1522—1566年),因政治腐败、边防松弛,一些中国富商和海盗商人如徐海、王直等与倭寇勾结劫掠,致使倭患愈演愈烈,祸殃沿海,危及漕运。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明政府派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东南国务大臣,征调“土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土家族土兵参加抗倭的有湖广永顺、保靖、容美、麻寮、大喇、镇溪、桑植等土司兵及四川酉阳、秀山土司兵,故这里统称为土家族土兵。史载,土家族土兵自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冬奉调抗倭,一直到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二月,前后持续三年多时间,被征调抗倭的总兵力合计约5万人次 (一说3万多人次)[1]131。这里拟就明代土家族土兵的抗倭战争作一肤浅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明代抗倭之缘起
在明朝嘉靖年间,倭患加剧,为抗击倭寇侵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明朝中央政府积极组织军队清剿倭寇。但因剿倭不力,明王朝不得不征调骁勇善战的土家族土兵参加抗倭战争。《土家族土司简史》言:“为了保卫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打击倭寇的侵略,永顺、保靖、桑植、容美、酉阳等土司和九溪卫所的土兵,积极应征,踊跃赴调。‘往往私信于在官之数,如调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六千,辄以万人’”[2]110。总的来讲,土家族土兵在抗倭战争中,英勇杀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值得指出的是,盛行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不全是 “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3]211。“倭寇”的首领及其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的商人,如倭寇的最高领导者实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他是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王直集团是故意给自己披上 “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 “假倭”,“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4]277。也就是说,徐海、王直作为倭寇的首领,他们以日本的平户、五岛等地方为根据地,率大船队攻击中国的沿海,在此过程中,日本的一些武士、浪人和奸商也加入其中[5]。故 《明史》载,当时倭寇 “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6]835;《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条所载屠仲律的 《御倭五事》甚至断言 “夷人十之一”[7]7310。可见,明嘉靖年间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较少,大多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包括当时在东亚海域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被当作 “倭寇”的同类对待。因此,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是由日本的一些破落封建主、没落武士、闯荡江湖的浪人和我国唯利是图的商人组合而成的。因此,明嘉靖年间的抗倭实际上是打击日本武士,浪人和我国以徐海、王直为首等组成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对于明代倭寇的成因,明人朱国祯在 《涌幢小品》卷三十 “日本”条中揭示了倭患猖獗的原因:“倭寇之起,缘边海之民,与海贼通,而势家又为之窝主。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同安县养亲进士许福,有一妹,贼掳去,因与联婚往来,家遂巨富。”[8]375也就是说,倭寇与沿海不法居民相勾结,倭寇以民居为据点,居民以倭寇为外援,是明代倭患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嘉靖年间,中央政府为何要调兵遣将,进行大规模的抗倭呢?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明朝官军腐败,海防废弛,致使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三月,数万倭寇在大汉奸王直、徐海的带领下,大举入犯,“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6]。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破坏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倭寇烧杀劫掠,致使百姓遭殃;其二是破坏社会生产,阻碍社会进步。
嘉靖年间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倭寇主要是日本没落武士、闯荡江湖的浪人。 《明史》有载:“倭纵掠杭、嘉、苏、松,据柘林为窟穴,大江南北皆被扰。”[6]“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9]231。当时参与抗倭的郑晓说:倭寇 “其喜盗、轻生、好杀,天然性也”[10]。倭寇这种 “习性”或 “天性”在东南沿海有种种表现,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勾勒出倭寇的形象。
杀人是倭寇司空见惯之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四次寇掠海盐,百姓死者约3 700人。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四月,倭寇进攻海盐,明军与战失败,战溺死者1 475人。倭寇乘胜犯嘉兴,午间在钱给舍宅吃饭,杀三四农夫,下午抵郡城,军民奋勇抵抗,倭寇没有得逞。又返回海盐,在经马家堰时,入一姜姓家,杀其伯侄5人。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五月十一日,石墩 (在今浙江海宁东南)贼攻澉浦城,取老百姓的门板遮蔽身体以登城,几乎攻入城中。盐典史李茂率兵用飞石击杀敌数人,敌离去。“贼回垒不得志,杀男妇千余以泄怒,见者悲痛”[11]36。同月,石墩之贼“留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11]38。此类事例在 《倭变事略》一书中俯拾皆是。
放火是倭寇经常使用的手段。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五日,有双桅大船一只,停泊于海盐县教场东,登岸焚舟,鱼贯而上,计566人。吹螺号,整理队伍,绕城扬旗进攻,城内戒严。而倭寇 “遂焚小东关及民房百余家,转掠西门。吾盐惟西市民稠货集,纵火焚劫,烟焰烛天。”[11]28同年六月,倭寇在吴江县境,“毁劫一夜,焰烬亘数百里”[11]42。对倭寇来讲,杀人和放火往往同时并行。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正月初三,倭寇出袁花镇 (今浙江海宁市袁花镇)载所掠辎重抵硖石(今浙江海宁市),为先锋的6名倭寇按剑把截硖石口镇。当时因正值过年,百姓没有想到敌人会来,男人开怀畅饮,妇女粉饰艳妆,放松了警惕。这给倭寇提供了杀人放火的好时机。《倭变事略》载:
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正月初三日,有避寇村妇数百,襁负幼小,齐渡西浦桥,值天雨桥滑,皆弃儿匍匐以渡。河畔积孩尸甚多,悲号震野。贼掠出袁花镇,载锱重由黄道湖抵硖石。有先锋六骑,按剑把截硖石口镇,值年节,男皆酣饮,妇皆妆饰,不虞寇至,燹忽四发,烟尘蔽天,经三宿烬犹未熄,死水火者无算。[11]48—49
倭寇杀人、放火的目的均为劫财。抢劫的对象是财物和人口。从嘉靖三十一年 (1552年)开始的十多年间,倭寇从东南沿海究竟抢去了多少财物,掳掠了多少人口,至今无法确知。但人们从九牛一毛的记载中,亦能认识到倭寇掳掠的惨烈。倭寇劫财对丝、丝织品、锦绣等最感兴趣,布、绵、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文钱、古名画、古名字、古书、药材等都是他们着意要抢的[12]214。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正月,贼犯松江府 (今上海市松江)“沿海地方,南翔、新城二镇尤甚,所获辎重尤多”[11]23。五月,石墩之贼沿海劫掠四十余日,所掠辎重有四船之多。六月,贼千余人犯苏州, “焚掠竟日, 载锱重百余舟”[11]36—41。 同年十月,倭寇在海盐大肆劫掠。据 《倭变事略》载:
二十五日,沙上贼数千来寇,总六十八号,每号约六、七十人,执白旗,吹螺整队而来,分八九路。是日一犯我十六都,一犯新行镇,一犯嘉兴诸乡村。其在新行者,蔓延十数里,毁掠三日,执民载锱重。二十七日还沙口,守巢者出迎相庆,以为出掠无事,且得利云。十六都贼历平湖抵嘉善,入嘉兴,载锱重百余船,北抵王江泾,出南浔,掠皂林、乌镇、双林等市。[11]44—45
倭寇这次到底劫掠了多少财物,文献上没有明确的数字,但至少在百船以上。据有关资料记载,倭寇掳掠人口,男女老幼都难幸免。《虔台倭纂》载:
最可憾者,倭性喜儿童,其韶秀警敏,得即目为奇货,虽数十百金往赎,不与也。民间为之谣同:‘怨尔倭奴性太刚,儿童掳去不还乡。分明一把无情剑,斩断人间父母肠。’故有孤嫠独子失而绝嗣者,有父母翁妪怨而杀身者。幸而得免,而城郭有限,率皆展 (辗)转山谷,岚瘴所蒸,事后疾作,不死兵而死疫者,又若干人。[13]
倭寇掳掠人口的目的有四:第一,用于作战;第二,为其工作,供其淫乐;第三,索取赎金;第四,带回国内,转卖为奴。嘉靖年间,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究竟掳掠了多少人口,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从戚继光打败倭寇后解救的人口看,其掳掠人口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据 《明代倭寇史略》载,嘉靖四十年 (1561年)的花街之战、长沙之战和上峰岭之战,共解救人口7 200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横屿之战、牛田之战和林墩之战,共解救人口3 868人;嘉靖四十二年 (1563年)的平海卫大捷和仙游之战,共解救人口6 000人。戚继光在嘉靖年间抗倭战争中有大小战役80余次,几乎每战都解救出不少被掳的民众。除上述有记载的8次计解救17 068人之外,其余战役应有人数不等的被解救者。因此,范忠义估计,那些被掠人的数量绝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12]217。
在倭寇的杀人、放火、抢掠等残暴侵扰下,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保障,家破人亡,田地荒芜,工商业萧条,破坏之惨不忍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倭寇的侵扰给当时的东南沿海百姓带来的是无穷的灾难,破坏了社会生产,阻碍了社会进步。
二、土家族土兵抗击倭寇之进程
正是在东南沿海人民惨遭倭寇烧杀淫掠、家破人亡的情况下,明王朝不得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抵御倭寇的骚扰。但官军腐败,仓促应战,在倭寇面前,软弱不堪。往往倭寇三四个人,“而至官军数百相顾披靡”。官军频频失利,毫无斗志,“以致群盗鼓行而入,攻毁县治若蹈无人之境”[6]。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明廷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御倭军事事宜。张经在此形势下,一面就地统兵筹粮,一面奏请朝廷征调大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因为张经曾任两广总督,他所调用的有广西的俍兵 (或狼兵)、湖广的土兵、广东东莞打手及廷臣议调的山东兵等。巡抚胡宗宪认为土家族土兵优势明显,“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治者,惟湖广兵钩镰枪弩之技,必须动永 (顺)、保(靖)二宣抚 (慰)司精兵”。 “湖广九溪等卫,容美宣慰 (抚)司、桑植安抚长官司、麻寮等所、上峒等峒,各有骁勇土兵,惯熟战阵,宜选各卫谋勇素著者指挥统领。”[14]总的来讲,土家族土兵参加的抗倭战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一)土家族土兵与广西俍兵共同参与的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大捷是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兵部尚书张经率领土家族土兵、广西俍兵及部分官军抗倭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明史》有 “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的赞誉,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东南沿海人民的抗倭斗争。
据 《明史·湖广土司传》载:“(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永顺土司彭翼南率土兵3 000人,致仕宣慰彭明辅领报效土兵2 000人,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带土兵3 000人,自备食粮,远行3 000余里,开赴苏州、松江抗倭前线。同年,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接征调令后,因曾孙岑大禄年幼不能指挥军事,特请示广西都督府,以女官参将总兵身份率田州以及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士兵共6 800多人,于次年 (1555年)三月来到浙江抗倭前线,在战场上历经100天左右,与土家族土兵一道,浴血奋战,立下了不世之功。
据 《倭变事略》载,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四月,各路土兵聚集松江后,永 (顺)、保 (靖)土兵与广西俍兵立即投入战斗。在胜墩,永顺土兵从北边进攻,广西俍兵从南边进攻,两面夹击,大败倭寇,斩首300余级,取得初次胜利。同月,在兵备副使任环指挥下,保靖土官彭守忠率土兵参加在常熟三丈浦的战斗,取得全胜,俘斩倭寇280余人。胜墩、三丈浦的胜利,挫败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同月,永 (顺)、保 (靖)土兵围倭寇于新场,倭寇因连遭土兵沉重打击,尤其慑于永顺土兵钩镰枪的威力,不敢与土兵正面交锋,便四面设伏。而土兵求战心切,轻入新场敌阵,永顺土兵将领田丰、田蕾,保靖土兵将领彭翅等遭倭寇伏击,捐躯疆场。这次战斗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指挥失误,敌情不明,孤军深入造成的。但在这次战斗中,瓦氏夫人则抗倭有功。据 《倭变事略》载:四月 “二十一日,贼分一枝 (支),约二三千,南来金山。白都司率兵迎击,白被围数重,瓦氏奋身独援,纵马冲击,破重围,白乃得脱”[11]52。五月 “初五日,报金山瓦氏兵剿残贼一百五十有奇,则知归巢者无几矣。初十日,柘林贼空垒而出,南围金山城大索。瓦氏缘前战解白都司围,知其骁勇,故欲劫其众也。”[11]55
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五月中下旬,倭寇大举进犯嘉兴,总兵俞大猷派永顺土兵及广西俍兵前往进剿,总督张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土兵驰援。保靖土兵出奇制胜,败寇于石塘湾,倭寇逃往平望,俞大猷命永顺土兵和官军拦截之,斩首300余级。保靖土兵乘胜追击,倭寇逃奔王江泾 (今浙江嘉兴县境),被各路官军土兵包围。王江泾大捷,共歼倭寇1 980人[14]698,史称这是东南抗倭以来的最大胜利。故 《明史》载:“及王江泾之战,保靖犄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6]994王江泾大捷是嘉靖年间抗倭以来的一次决定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重挫了倭寇主力,其 “精锐者多死”,迫使倭寇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扭转了明朝抗倭的被动局面,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倭信心。战后,朝廷赐彭荩臣银币并三品服色,进阶略毅将军;赐彭翼南银币并三品服色,授昭毅将军;彭明辅亦赐银币[1]126。
(二)土家族土兵参与的抗倭战役
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七月初三日,瓦氏夫人率领广西俍兵回田州后,史籍再无俍兵参与抗倭的记载。而土家族土兵抗倭一直坚持到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1]126—129。
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王江泾大捷后,松江柘林的倭寇1 000余人又窜扰苏州一带。彭荩臣、彭翼南率领土兵跟踪追击,并与任环率领的官兵分三路进攻,围倭寇于苏州的陆泾坝。各路土、汉官兵冒雨奋战,俘虏其首领,斩杀500余人,溺死者不计其数,取得了陆泾坝之战的胜利,肃清了苏州地区的倭寇。此时,明朝发生严重的朋党之争,严嵩以 “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张经,将永(顺)、保 (靖)土兵和广西俍兵调回原籍,直接导致了抗倭战局的不利。同年 (1555年)十一月,倭寇窜入浙江宁波、奉化一带,容美土司田九霄率土兵在绍兴后梅大败倭寇,取得后梅之捷。十二月,容美土兵与官兵配合,在嵊县清风岭伏击倭寇,“田九霄以正兵当其前”,后又尾随追击败寇,俘斩170余人,取得清风岭之捷[14]。
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永保土兵再次被征调至抗倭前线。当年七月,永顺、保靖、容美三大土司率领土兵参加乍浦战役,土官汪相、向銮率领土兵直捣贼巢,取得乍浦之捷。
七月初六日,天兵入郡,骑兵先至,驰赴吾盐。明日约十万众,入盐邑。……永保二司兵三万,容美等司兵一万,由陆路进发。合各地主客兵共二十万。时诸百执事统兵参游等官,运给兵饷,纪录军功,各司郎署,及辕门幕客,中军参谋,不知凡几。而赵侍郎衔命既至,会同总督胡公,巡抚阮公,咸驻节嘉兴,军声大振。诸贼闻之,惶怖忧懑,徐海虽降,复欲窥伺,而欲封之念澹然矣。[11]82—85
在明朝官军和永顺、保靖、容美等土兵的联合打击下,倭寇的势力有所收敛。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八月初,倭寇首领徐海请求投降,胡宗宪等本想立即诛之,但又苦于兵力不足,永 (顺)、保 (靖)土兵尚未赶到,只好佯令其自择便地居住。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八月二十日,永(顺)、保 (靖)土兵至,胡宗宪决定向徐海发起进攻,徐海潜逃至沈家庄屯住。沈家庄分东西两处,又有中绾河为堑,易守难攻。倭寇以鸟铳和佛郎机拼死抵抗。彭荩臣见不能近战,便令编竹笆以遮抵火器。《倭变事略》载:“八月二十日,永 (顺)、保 (靖)等兵进薄贼巢,擒四贼,俘军门。二十三日,诱斩贼二十余颗。”[11]92二十四日,诸路主客军凡20余支围困徐海。永顺宣慰使彭翼南军其西,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应袭冠带舍人彭守尽军其东,容美宣抚使田九霄军其南,官军军其北,四面围攻,倭贼负隅顽抗。后大倭寇徐海的首级为土兵所取。沈家庄大捷后,诸路大军乘胜进攻薄梁庄,斩获倭寇1 600余级,生擒倭魁辛五郎等。徐海、辛五郎被剿灭后,平息了浙西倭患。在胡宗宪 《胡总督奏捷疏》中,多次提及永顺、保靖、容美等土兵之功[11]93—97。
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二月,宁波舟山地区倭寇负险,在 “官兵环守不能克”的情况下,土官彭志显等率领桑植、麻寮、镇溪、大喇6 000土兵,容美土司田世爵率容美土兵,在俞大猷指挥下围攻舟山倭寇,取得舟山之捷。至此,浙江倭寇全部被肃清[1]129。
三、土家族土兵抗倭取胜之原因
土家族土兵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土家族土兵成为名噪一时的抗倭劲旅,被誉为 “东南战功第一”。土家族土兵之所以能连战连捷、屡建奇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一)战争的正义性
一般而言,正义的战争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抗击倭寇对于明王朝来讲,属于正义战争,这就决定了抗倭夺取胜利的必然性。“倭寇出没海岛中,……杀略 (掠)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15]。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淫掠,危害生灵,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他们见人就抓,《倭变事略》中有 “男则导引,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缫茧,夜则聚而淫之”的记载。更有甚者,“倭大峤入桃渚,官厅民舍焚劫,驱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婴儿 (于)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积骸如陵”(《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嘉靖三十一年 (1552年)至三十三年 (1554年),浙江一带被倭寇杀害的居民不下十万人。嘉靖中期,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四野萧条。在此情况下,明王朝顺应人民的要求,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组织了庞大的抗倭队伍,进行正义的抗倭战争。由于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正义战争,因此,抗倭斗争自始至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各族人民积极应征赴调,参加抗倭战争的土家族土兵有永顺、保靖、桑植、容美、酉阳五大土司的土兵及九溪卫所辖土属麻寮、大喇、镇溪、麻阳等土兵,共计5万余人,仅保靖土司兵就达16 000人,谱写了一首团结战斗抗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光辉华章。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倭战争中,土家族土兵听征调而不用军饷,自备食粮器具,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忱。在战斗中,土兵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英勇杀敌,不少土兵将士如彭翅、田丰年等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乐于为国捐躯、勇于反抗侵扰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土家族土兵能取得抗倭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16]。
(二)严格的纪律性
明朝设置土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生苗叛乱。民国 《永顺县志》载:
土司有担承苗疆之责。辰州西南一带,苗有镇、竿之分。恃强负固,尤非一朝。朝廷兵威,在所不惧,惟畏永保土兵,故令永保司担承镇苗,保靖司担承竿苗。如镇苗大肆焚劫,责成永顺司赎取;竿苗则责成保靖司逮。[17]
所以,土兵是长时间处于备战状态的,所谓“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于民,以习耕凿”[17]。且经常对土兵加强训练,“永顺司治西二里许,有校场坪,土人常于此处演武。又西北五里,有搏射坪,又北五里曰射圃,地势均宽敞,土人每于此二处搏射。”[17]如此训练有素的土兵比长时间荒废训练的明朝官军自然更有战斗力,而面对刚被日本割据战争洗礼、有一定实战经验的倭寇也更有取胜的把握。每次出征,土司下檄所部,在受过训练的土民中 “照丁拣选”“精选土兵”,将那些素质最好的土兵送上前线。军事长官也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对勇谋素著、“能精锐爱先锋”的将领委为指挥,并降级使用。 “将千人者得以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以军令,临十人之将”,使之将精兵勇,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每次出征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挑选敢死冲锋队员,盟誓不惜牺牲,务求必胜,以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鼓舞土兵的士气。 “宣慰吁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银副之。下令曰: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啖此牛首。勇者报名,汇而牧之,更盟誓而食之。”[17]在战斗中,土司的 “节制甚严”,进退动止皆有严格的规定。如打击敌人的方法,“止许击刺,不许割首,违者与退缩皆斩”[17]。击刺法比割首法灵活方便,没有固定的打击部位,便于伤亡敌人。同时,土司采取连坐法,土兵退斩旗长,旗长退斩司长。土司赏罚分明,对那些 “英长虎豹”获胜致捷者,实行 “嘉奖”封官、记功、赏赐,酌情赏示。严密的组织性和铁一般的纪律性把整个土兵队伍凝集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而这个团结统一的整体所爆发出的力量是无与伦比、不可战胜的。因此,湖广土兵往往 “所战必捷,人莫敢攖”,号为“天下莫强”[18]972—973。这无疑是确保抗倭胜利的保障条件。
(三)战术的精湛性
明朝嘉靖年间,土家族土兵在抗击倭寇的战场上,运用精湛的战术,冲锋陷阵,夺取胜利。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后多用游击战法,游弋于浙江沿海的群山峻岭之中。而明朝官军对付撒豆子般的游击战法,只会用密集战术进行应对,效率极低,军队机动效率极差,经常被倭寇 “绕出官军后,夹攻取胜”(《倭变事略》)。而永顺、保靖土兵战斗时采取的是 “塔”式阵型。每司设二十四旗,旗设旗头。临战时,其阵法以一人居前,其后以三、五、七人,或以三、五、七、七人横列四排五排,形如铁塔式的战斗序列;其余土兵则列于阵后,战斗时呐喊助威,以壮声势。在攻守战中,前列伤亡,后排即刻逐列进补,使战斗序列保持不变,胜负以四重或五重为限。土家族土兵这种严密的战斗组织与巧妙的阵法,可以进退自如,攻守兼备,利于发挥集体的战斗力。进则队列整齐,退则井然有序,攻则无往不胜,守则坚不可摧。并且机动灵活,根据战斗需要,既可以旗为单位各自为战,又可与其他旗相互配合,协同作战[19]。所以,当土兵与倭寇战斗时,倭寇往往 “望而生畏,屡战屡败”。抗倭名将戚继光的 “鸳鸯阵法”就是在学习土家族土兵的作战阵法基础上演变而成的。
(四)器械的独特性
土家族土兵独特的武器提高了实战功效。在土家族地区,运用毒弩和毒箭作为战争武器的现象较为常见。高其倬有 《请除苗弩毒药疏》、李绂有《陈解弩毒药方疏》,其中谈到 “臣现今亦在云贵两省内捐赏遍寻解毒之术,若毒弩可解,亦治各省苗蛮之一端也”[20]。可为土家族土兵善于运用毒弩和毒箭的一个佐证。此外,土家族土兵还有运用自如的 “钩镰枪弩之技”,使善于 “短兵相接”的倭寇难于对付,无法招架。胡宗宪也承认:“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广兵钩镰枪弩之技,必须动永 (顺)、保 (靖)二宣慰司精兵,使与此兵彼此夹持,部伍均配器械,长短相济。”[18]973《永顺县志》有 “惟永 (顺)、保 (靖)土兵钩镰枪弩之技较为精工,其调时必分永 (顺)、保 (靖)为二班”的记载,甚至 “永顺钩刀手,为广西诸徭所畏”(《明史·广西土司柳州传》)。这些器械在抗倭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正是由于土家族土兵的武器独特,对倭寇有相克功效,所以,使土家族土兵能够逢倭必胜。
[1]石亚洲.土家族军事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王承尧,罗 午.土家族土司简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3]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4]王守稼.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0(1).
[6][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明世宗实录(卷422)[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明]朱国祯.涌幢小品[M].广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9][日]井上清.日本历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
[10][明]郑 晓.四夷考·日本[A].吾学编(上卷)[C].隆庆元年(1567年)初刻本.
[11][明]采九德.倭变事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
[12]范中义.明代倭寇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明]谢 杰.倭变二[A].虔台倭纂(上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14][明]胡宗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9)[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彭官章.土家族土兵在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重大贡献[J].广西民族研究,1986(2).
[17][民国]胡履新.武备志·兵制[A].永顺县志(卷二十四)[Z].民国十八年(1929年)刻本.
[18][清]郑若曾.筹海图编[A].中国兵书集成(第15—16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19]张 凯.浅论明朝嘉靖年间的永保土兵与抗倭战争[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1(2).
[20][明]高其倬.请除苗弩毒药疏[A].兵政十九.苗防[C].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八)[Z].艺芸书局本.
[责任编辑:曾 超]
K2487
A
1674-3652(2014)02-0001-06
2013-12-21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历史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11BMZ010)。
李良品,男,重庆石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张 芯,女,重庆永川人,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