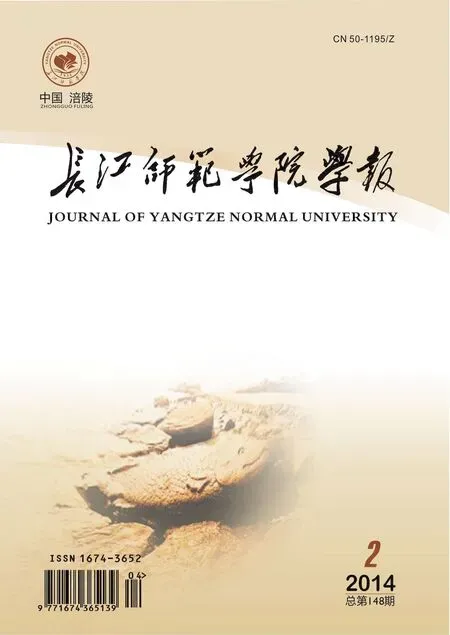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探析
张 磊,罗思洁,刘 静
(1.3.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昆明 650091;2.云南大学 滇池学院,昆明 650091)
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探析
张 磊1,罗思洁2,刘 静3
(1.3.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昆明 650091;2.云南大学 滇池学院,昆明 650091)
儒家行政思想有现代性的价值意涵,其原初关切有天下大同、修己安人、理性独立、平正中庸的特征,这对当前的行政管理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性;儒家;行政思想
一、引论
中国自被动地遭遇现代性问题以来,为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的目标,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预备立宪、共和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还有一连串以应对现代性挑战为核心的,着力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变革运动。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这一连串现代性变革运动,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大都是以欧美各国的既往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为榜样的,是一个 “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1]。在这个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和构建现代性秩序的历程中,在特定某些历史期间内,由于对 “救亡”的需要或者是由于对 “启蒙”认识的偏颇,我们曾采取了把 “传统”当作 “现代”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乃至于有了破除、毁灭的做法,视传统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现代则是发展、改革、建设的表征——先验地接受了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现代性标准。
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不能脱离传统社会而独自生长的。传统社会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及其对这些因素的发觉和培养是促进传统社会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揭示的主旨之一,也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转型国家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启示,即传统社会是孕育现代性的母体,现代社会是传统社会因应社会条件变化的逻辑结果,二者是不能割裂的,反之则是现代性的发展无持续之力量或者目标的迷失而引致社会的动荡。这样的反例,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俯首可拾,比比皆是。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西方国家发展轨迹和经验为参照的 “现代性”价值和标准是否就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作答。首先,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现代性,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西方人的富裕是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2]。但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质疑和批判从西方开始现代化进程之日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由于现代性或现代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剧时,人类逐渐陷入 “现代化困境”,步入 “风险社会”的今天,对现代性的质疑之声更加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各种对现代性进行解构和重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纷至沓来,异常热闹。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性标准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值得后来者引以警惕的。同时,如果从“多元现代性”视角来看的话,即便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性标准是正确而值得倾力践行的,由于各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迥异,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必要的 “创造性转化”。
在中国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而现代性普遍遭受质疑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各层面进行系统的审视和反思,寻找中国化的现代性发展之路,实现两者的 “优势圆融”。这样,一方面可以免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困境;另一方面,能用中国传统的智慧去疗治现代性的疾苦。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斯普瑞特奈克所言,“在这重新反思现代性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时刻,中国不仅面对着一系列问题,而且还深藏着解决问题的智慧”[3]。这正是我辈学人所必须要承担起的责任。
本文将在此前提论述之下,选取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系统支柱的儒家思想系统下的儒家行政思想作为工具,对儒家传统行政思想中现代性价值的学理前提、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及实现现代性价值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求回应上述主题。
二、儒家行政思想现代性价值的学理性前提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传统上认为儒家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授徒,其中的政事,即是后来称之为的 “经济之学”——经国济世的学问,是涵盖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内的所谓 “外王”之学问与实践。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家行政思想只是儒家思想系统中一个极小的分支,是政事学问之下的一个具体组成。
当我们谈论 “儒家行政思想”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静态的、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这种思想的,但是和儒家思想的其他构成部分一样,儒家行政思想也具备着 《礼记》所谓 “有可与民变革者,有不可与民变革者”的鲜明思想特征——这种行政思想的本质是变动的,但在变动之中却也蕴含着一些不变的价值因素,正是这种 “变动中的静止”的特征构成了儒家行政思想现代性价值的前提。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能卓然自立千年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 “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法理为中心”[4],直指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找寻依靠人的现实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只要有人的活动,就必然会产生出与人相关的各种问题,只要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就不会枯竭,而只是以符合不同时代人的特点进行必要的变革。所以虽经学派不断分裂和流转变迁,但是历代儒者却始终能在回应先秦儒家 “原初关切”的前提下,因应时代的变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儒家思想系统中,使其以强大的适应性确保了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并传续两千五百年之久。
因此,儒家思想的变迁性和适应性为我们在当前条件下讨论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前提——历史上不断成功、革故鼎新的儒家思想,在现代性的挑战下,依然能够再一次的回应现代性要求而做出必要的变革,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历史实践,另外一个方面更是基于儒家思想关注于人类现实生活之义理的学科特点。
三、儒家行政思想现代性价值的意涵
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价值一方面源自于儒家思想本身固有的变迁性和适应性,这是我们讨论的前提,只有一种在现代性挑战之下能够存在并发展的思想和学说,才有进一步讨论其在现代社会之中价值的可能性。作为儒家思想重要分支的儒家行政思想是具备了这样的一种特质的。而儒家行政思想现代性意涵则深深地根植于 “变动中的静止”的 “静止”那部分,也就是那种从儒家创立之初就蕴含在儒家思想之内的,虽经不同时代儒者以不同方式诠释,但本质不变的那些有关于行政方面的 “原初关切”,那些传之千年而不衰朽的思想,在现代性的挑战下,更显现出了它们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也许中国很难顺利走完现代化过程,但由于处在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 “和谐”和 “中庸”的思想资源,对这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给予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诠释,中国社会也许有可能会比较容易进入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5]。这些行政思想的 “原初关切”具体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天下大同的行政目标。所谓大同者,《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
这样一个高远、难以骤成、却是具体而充满吸引力的行政目标,在过去曾赋予了政治与行政最高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也曾经是历代行政人员生命意义的终极来源,是他们实践人生价值的最高鹄首,也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终极归宿。中国传统上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皆以此大同目标为滥觞,历史上的文章鼎盛、物阜民丰,虽历遭丧乱而能传续至今的辉煌,离不开这样的目标的指引和激励。
在传统行政秩序已经坍塌,公共行政遭遇价值迷失、信任危机、公民精神丧落的现今,反思传统行政目标中所蕴含的那种天下为公的朴素公共观、推己及人的责任感、互助友爱的奉献精神,对重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行政目标和行政价值,重塑现代行政秩序仍然不失其鲜明的引导性。
第二,修己安人的行政方法。儒家行政思想强调行政人员道德修养及水平在实现行政目标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所谓 “一切是以修身为本”,强调了行政人员自身道德修养和施政能力在行政过程中作为关键性的主体角色并对行政目标能产生积极的教育、感化和管理的作用,所谓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然而这种 “德治主义”又不仅仅止于此贤人行政之格局上,儒家强调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之最终目的是要 “化民成俗”,通过行政过程,完成对行政对象的道德教育和素质提升,实现 “民迁善而不知为之者”,社会整体的道德精神迁升。行政人员在此过程中承担着“天相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作用,所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孤恤而民不倍”、“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一个优秀的行政人员的基本修为,着力之处就在于儒家所推崇的所谓絜矩之道,“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非相》)。能从自己本心出发,推己及人,近取譬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和己欲达之必欲达人的忠,具备 “忠恕之道”的行政人员即是儒家所说的“仁者”,即是一个完成了修身功夫的合格的行政人员,是一个具备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素养的行政人员。
尽管儒家所推崇的修己安人的德治主义行政方法,不免有落入 “唯道德论”而忽视行政方法、技术的窠臼,但那种对行政人员行政道德的强调,对行政人员在树立社会风气的关键性角色的肯定,对行政对象道德培养重要性的坚持,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公务行政人员职业道德、提出了 “任人唯贤,以德为先”口号的当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培养公民参与意识,积累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公民自治水平,实现社会善治为行政改革目标之一的当下,儒家行政思想的德治主义方法所蕴含的宝贵思想依然不失其重要的启示价值。
第三,理性独立的行政人格。儒家从孔子之初就对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推崇备至。孔子曾言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是一种反物质和反权威的理性主义,根源于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自信把握和必然实现之的勇气,所谓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的一生,颠沛流离,受尽疾劳困苦,利益诱惑,却始终也没有放弃对自己理性信念的追求,正所谓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里仁》)正是对他这种矢志不渝、独立顽强的人格和精神的摹写。而后孟子引而发之的所谓 “不为苟得”的浩然正气之论,切实成为了千百年来无数行政人员的行为坐标,成为了他们抵抗挫折,实现人生价值的最有力的精神能量,即所谓 “穷则独善齐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样一种淡薄利益、崇尚理想的独立行政人格的塑造,在一个以商业文明为招牌的现代社会,在一个充斥着利益诱惑的市场经济消费型社会,在一个公共行政人员职业操守备受质疑的当下,对重定行政人员的心灵和价值坐标,培养职业操守,回归工作本位,再造公共精神都有着回应现实困境,寻求解决途径的积极价值。
第四,平正中庸的行政思维。所谓中庸,程子曾言:“不偏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就是辩证地看问题,解决问题,“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要看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用一种统一对立面的辩证方法来处理所遇到的事情。孔子所谓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折中主义、调和主义,而 “庸”就是平常,顺乎自然,通于人情,不做作。因此,中庸的意思就是用顺乎自然的方法来辩证的处理一切所遇到的问题。
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使我们能全面的考虑问题,寻找对策,而不滑落事物一端的陷阱中,从而以一种自然的、不具有破坏性的途径将问题加以解决。这样的一种行政思维方式,对于当前这样一个由于经济利益调整、社会转型、价值混乱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迭生、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丛生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而言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如何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社会管理的实效性,也许从 “中庸”的思维出发,掌握中庸的管理方法,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价值,更具体体现在以上所述的原初关切之中,这些宝贵的思想精华,虽经千年的流变,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而且似乎对医治由现代性所引起的行政疾患还是一剂对症的良方。因此,面对现代性的公共行政问题,从传统的儒家行政思想中汲取养分,使这些传统的行政思想成为行政转型过程中必要的文化 “润滑剂”,去减轻传统行政向着现代性行政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去救治由于现代性所引致的社会疾苦,并保证此一过程的文化连续性和系统性,使中国公共行政的重构过程更为符合民族特征和文化遗传,这对于当下的行政管理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四、儒家行政思想现代性价值的实践路径
要使传统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得以发挥,期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对传统儒家行政思想做必要的现代性诠释,赋予这些原初关切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方式,使他们更具有现代性品格,更符合现代人的时代要求。
儒家思想在唐宋之际,为了回应第一次西学(佛学)东渐的冲击,人们主动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和改造,而以宋明儒学的新面貌整合了佛学和儒学,赋予儒学在那个时期的新意义。而同样的问题,现在又再一次地出现了。面对第二次的西学东渐,当我们意识到不能舍弃传统,而必须借助传统迎接西方所带来的全面化的现代性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做必要的新诠释,以整合传统东西,重构一种符合现代性的传统价值体系,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重构起一种具有传统文化内核的现代价值体系。
金观涛在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曾提出一种系统论史观,认为一个现代社会是价值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耦合体。当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做了变动之后,价值系统也必然要做出相应的变动,否则就是原有价值系统的覆灭或者社会的动荡。因此,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纷纷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当前,作为价值系统组成的儒家传统思想也必须要进行必要的现代性重构,否则,其传统思想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是无法得以发挥的。
作为儒家行政思想的现代化重构过程,也是行政学中国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行政学说和中国儒家传统行政价值和行政传统整合的过程,是赋予儒家行政思想现代性内涵的环节,也是儒家传统行政价值在现代条件下实现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当代行政学者身上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为行政学的中国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一方面要积极的学习西方行政学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十分留心以儒家行政思想为主体的传统行政思想中具有现代性价值的内容。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将两者做整合的工作——既对西方行政学做符合中国行政传统的解构,又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进行符合现代性的诠释,从而逐步构建起中国化的公共行政学体系,只有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步骤,或者在这样的一个步骤完成过程中,儒家传统的行政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才能得以发挥;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价值体系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社会转型才能平稳、持续地进行,中国正在进行着的社会转型也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1]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
[2][美]诺 思.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3][5]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17.
[4][清]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82.
[6]王云五.礼记今注今译[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8.
[责任编辑:赵庆来]
D09
A
1674-3652(2014)02-0075-04
2014-02-20
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昆明经开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ynuy201233)
张 磊,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行政管理思想与行政管理体制研究;罗思洁,男,湖南邵阳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行政绩效与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