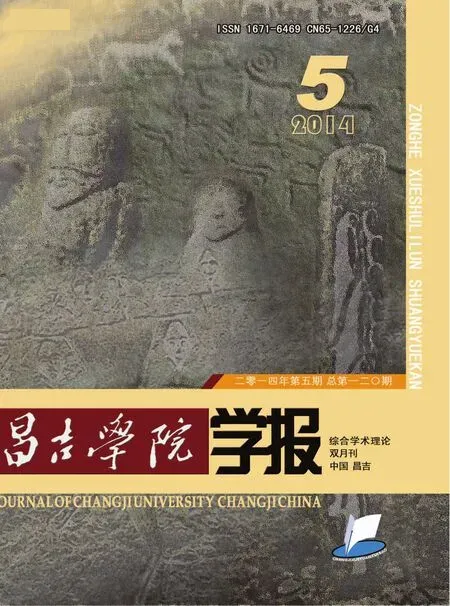论翻译效应学的理论基础
刘瑞强
(昌吉学院外语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一、引言
宏观上讲,当代翻译研究的深层理论问题主要是围绕着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的冲突而展开的。由此而导致的翻译理论探索多元化趋势使得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深化,这已是翻译理论研究无可否认的现实态势。在多元视角下的翻译探索中,翻译效应学的提出,无论是对于翻译理论还是对于翻译实践都显现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性。本文试图从“翻译效应”的概念分析入手,对翻译效应学的基础理论底蕴、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其在多元化翻译研究背景下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做一阐释。
二、翻译效应概念解析
翻译效应学(translafectology or Theory of Translation Effect)是由翻译(translation)和效应学(effectology)两个单词合成的,而效应学则是作者根据英语构词法将英语单词effect加后缀ology(科学或学问之意)演变而来。最后又将translation和effectology合成translafectology(翻译效应学)。由此可见,翻译效应学是一个新概念。笔者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狭义翻译效应学(或曰微观翻译效应学)和广义翻译效应学(或曰宏观翻译效应学)。狭义翻译效应学是翻译的本体论,属于内部研究,主要有三层意思:1.翻译史研究。主要指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2.翻译批评研究。即从翻译的性质、过程、结果及译入语读者的角度检验译文的质量,并整合中西翻译理论,提供一套易于操作的翻译评估标准;3.翻译方法论的研究。即针对不同阅读对象、不同时代背景、不同阅读目的和不同翻译场而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或方法。广义翻译效应学是翻译的应用和影响研究,主要从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研究译文对译入语国家全方位的影响。它是翻译的宏观研究,又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1]。
《现代汉语词典》对“效应”的基本解释是“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其引申意义为“泛指某个人物的言行或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所引起的反映和效果。”如“温室效应”、“社会效应”、“广告效应”、“心理效应”等等。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上讲,“‘效应’是指某种社会文化现象,即个别事件的发生所产生的普遍的社会影响或文化效果。”[2]
翻译作为由个别译者或多个译者组成的译事团体所进行的跨语言的社会文化交流活动,其结果(无论是口译的还是笔译的)对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会产生或长期或短暂、或宏观或微观、或深刻或表面的影响或效果,均可统称为“翻译效应”。“翻译效应学”作为专门研究翻译效应的一门学问,最早是由作者在2001年发表的“翻译效应学初探”[3]中明确提出,并在2005年的“翻译效应学的范畴”[4]一文中对其基本概念、原则、方法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述。
译本的产出和目的语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是翻译效应发生的两个基本前提,没有译本或译本读者,翻译效应就不会发生。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翻译效应研究是以译本进入到目的语读者人群为起点,以译本对译入语群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各种影响或效应为对象。翻译效应学就是以翻译效应为中心,对翻译过程中原语文本的选择策略、翻译的总体原则与具体方法、译文的评价、译文对译入语群体各种效应的历史跟踪等方面为问题范畴的一门学问。因此,它同以往以原文本、译者、译文本或译语读者为中心的各种翻译研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三、翻译效应学的本体论特征
本体论(ontology)一词是由17世纪的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Goclenius,1547-1628)首先使用的。此词由ont(?ντ)加上表示“学问”、“学说”的词缀——ology构成,即是关于ont的学问。ont源出希腊文,是on(?ν)的变式,相当于英文的being;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本体”的研究,在希腊哲学史上有其渊源。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希腊早期哲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组成万有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腊文arche,旧译为“始基”)。对此“本原”的研究即成为本体论的先声,而且逐步逼近于对being 的探讨。[5]
由此可见,作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体论原初含义是指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考中对构成知识的本源或本体的发问,寻求人类对世界知识的终极关怀或终极解释。当下,“本体论”概念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在各门具体学科领域研究中,无论是问题本身、提问方式,还是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只要具有本源性或终极性特征,往往被冠以“本体论”之名。其实,“本体论”概念目前除了专门用于哲学本体论阶段研究时仍保有其原初意义外,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大多是指具有本体论性质或意义的研究,如“语言本体论研究”、“翻译本体论研究”等。其提问方式和回答方式都具有强烈的理性反思特征。
作者将翻译效应学看作是具有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主要想突出的是:翻译效应是翻译现象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特征之一,它对翻译研究有着本体论性的基础地位。表面上看,翻译效应似乎可以归结为翻译行为直接结果(译本)的衍生物,也就是译本中所承载的原语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历史等对跨语言、跨文化的译入语读者群体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或短期或长期、或宏观或微观、或表层或深层。换言之,译坛较为容易接受的对翻译效应的典型理解模式是:把效应看作是翻译活动这一行为链条(原语文本——译者——译语文本——效应)的一个终端环节,甚至被看作是无法确定与把握的“或然”之物,只能留给未来社会、文化去感受和评判。
其实,译者对翻译效应的预期本身就体现着人类任何活动都内含着的一个必然环节:目的性。从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翻译目的论(Skopos Throry)[6]角度看,有组织的翻译活动本身并非翻译的最终目的,它的目标是达至译文读者,并在读者人群中产生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或短期或长久的影响。在目的论者看来,翻译目的是翻译活动各个方面所必须围绕的终极核心,可以用目的来解释翻译活动中的一切现象,如原文本的选择、翻译形式和方法的运用等。由此可见,翻译目的对目的论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着本体论的性质与地位。虽然翻译效应学在翻译策略上与翻译目的论有一定的重叠,这是其相似性(similarity),但与翻译目的论相比,其差异性(difference)是十分显著的:翻译目的论突出强调的是目的对行为的直接指导、规范作用,而翻译效应学旨在围绕译语文本给译语读者群体带来的种种影响的前提上而对整个译事过程进行专门研究。
四、翻译效应学的认识论依据
与本体论相类似,认识论概念同样源于哲学研究领域,它是继哲学本体论阶段之后对人的主观能动的认识能力、认识方法等方面的哲学追问,旨在解决“人对世界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翻译作为人类拓展知识的一个环节,特别是作为拓展跨语言、文化知识的重要环节,其本身就具有认识论意义和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不同的是:翻译的知识积累主要是作为跨语言、文化的间接经验而发生在目的语读者人群中。翻译的效应也在同样意义上发生在原语对目的语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
在认识论意义上,翻译研究的范畴不应局限于“原文本-译者-译文本”这一传统框架内。因为在这一范畴中谈论翻译的认识论价值,中心词自然要落在“译者”那里。进而言之,就是译者通过其译事行为对原语文化知识的积累过程与方式。这种狭隘的以译者为中心的对翻译的认识论理解,其结果只能限制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从认识论角度研究翻译的意义和价值,其核心是经由译者而达至的目的语文本的读者人群。他们在理解、把握、译本中所传递的原语文化的间接知识、观念等的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其自身在本民族语言文化中积累起来的直接或间接知识相结合,从而不断拓展其知识视野或范畴,增加对世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那么,目的语读者是如何经历这一过程的?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吸收译语文本中所传递的合理、积极的信息,同时摒弃消极的、不合理的信息,以达到增长对世界认识的目的?要想回答此类问题,我们首先须从翻译效应的角度对翻译的内在结构予以重新思考。
五、翻译效应学的内在机制
翻译效应学对翻译研究所具有的本体论性质和对译者、译语读者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使得我们有必要对译事过程本身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各个环节的内在运作机制做一番效应论思考。
任何效应在发生之前都必须具有以下的先在性条件:触发效应的某种过程或行为(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等自然领域的某种现象,还是社会、历史等人文领域的某种过程或行为)。效应作为以上过程或行为所触发的结果,通常表现为外在的、有形的影响,或内在的、无法直接观察的效应潜势。但将“效应”的理论研究仅仅局限于它的外在和内在影响未免过于狭隘,而应该以“效应”概念为核心,对与效应相关的各个环节做出整体的理解和解释。翻译效应的研究同样不应该局限译本在译入语群体中产生的可直接观察的或潜在的影响,而应该更深入地拓展到与翻译相关的各个层面。其中主要涉及到以下几方面:原文本及其内蕴文化作为翻译效应所依托的原初模本;译者作为诱发翻译效应的能动主体;译语文本作为译本读者人群所直接面对的效应载体。
首先,在对待原文本的态度上翻译效应学有别于其它翻译理论研究
在传统的译学理论中,原文本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翻译中强调对原文在语言、文化、功能等方面的忠实或信守,这突出表现在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对语言结构层面的强调,功能主义对语言交际功能层面的强调,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对“案本”的不可替代性的地位的强调,等等。这些理论虽然从不同层面推进了译学理论的研究,加强了对翻译标准、过程、技巧等方面的理解与应用,但它们往往因为过于突出原文本这一中心而或多或少的局限了自身的研究视野。
从翻译效应学角度看,原文本作为效应发生的原始模本或原初参照,对其语言结构、文化、交际功能等方面的特征的强调最终可以由其在原语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所产生的效应来表达。具体而言,某一作品产生的不同时代,它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是无法摆脱当时代各种语境条件限制的。这反过来又会加深、拓展读者对当时代宏观、微观的语境条件的理解,从而在读者群体中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效应。按此理解,翻译效应学作为专门探索跨语言、文化的翻译活动给译语读者群体带来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就要求从“原文本”中心转向以在译语读者中可能引发的预期效应为中心,将翻译中狭隘的工具理性转为宏观的时代理性,进而将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真正提升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交流的高度。
第二,译者作为译事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究竟如何合理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素
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翻译理论往往因其对译者的地位与作用的过分强调而使翻译实践失去了标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个体性、翻译中理解的不确定性、翻译标准的多元性以及译本的暂时性。
译者作为诱发翻译效应的能动主体,就其翻译行为自身性质而言,甚至就翻译学的学科性质而言(如果我们承认翻译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其人文性特征远远超乎其自然科学性特征(如果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的话)。这一认识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也无法在翻译效应的研究中仅仅以知性方式来领会、把握翻译行为与翻译效应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二者的关系做出简单的程式化理解。这是因为,翻译行为自身所具有的人文性以及翻译效应的产生、其作用的发挥往往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这又为二者关系的理解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虽然就翻译自身固有的人文性特征而言,后现代译论的诸多方面并非不无道理,但却冲淡了翻译实践的终极目的:有效的跨文化交流。若使交流顺利进行,翻译活动中所牵涉到的原文本与译文本在各自读者人群中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效应便成为不可或缺的翻译论题。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首先是理解的主体。一般认为,对原文本的把握主要来自于译者从语言与内容或形式与意义的结合。形式与意义的完美结合往往被译者看作是达到了对原文本理解的充分性,因而忽略了原文本在原语社会中所发挥的文化、历史效应。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译者无视译本对译语读者群体的效应预期。
关于“文本理解”,当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通过对“理解”的历史性论证,将其纳入到历史语境中,并提升到人类生存的存在论高度。他认为,理解只能依托理解者的历史认知背景而发生。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知性思维逻辑对文本意义和各种相关语境条件所做的人为疏离[7]。翻译效应学在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作为理解者不仅要把握原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还要深入理解原文本在当时代以及未来时代已经引发的和可能引发的社会历史效应。这样的理解显然已超出了原文本自身的范畴,为译文的效应预期做好了充分准备。
译者作为触发翻译效应的能动主体,其翻译行为过程本身不断受到效应预期的牵制。但译本一旦完成,并传递到译语读者的手中,译者便失去了效应预期的牵制,从而使他无法继续左右其译事行为对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甚或整个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带来的或显或隐、或强或弱、或短暂或长久、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第三,译语文本作为译语读者人群所直接面对的效应载体,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说它是客观的是因为译语读者不懂原语文本或无法看到原语文本,只能把它当作母本;说它是主观的是因为它是译者经过创造性劳动或一定程度的二度创作完成的。换言之,经过“三千里路云和月”的艰难跋涉和行进,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原语文本,而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或变异。这既是客观的命定和无奈又是主观的自由能动和创造契机。最终结果是原语文本的幸运抑或灾难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效应。
第四,译语读者作为翻译效应的受众群体,他是被动的、消极的又是主动的、积极的
说他是被动的、消极的是因为他在很多情况下是别无选择,无论是不懂外语,搞不到原语文本,还是只有一种译语文本;说他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因为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结合自己前有知识或已有历史传统文化知识,加上当下的阅读体验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变化、情感起伏和审美体验,并最终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价值观。
翻译效应学主要研究原语文本通过复杂的语言转换将异质文化传播到译语国度后的翻译效应或接受效应。而评判此种效应的优劣程度主要看这种异质文化在译语国度的“文化适应性”(cultural compatibility)。[8]“文化适应性”是文化翻译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指准确的文化意义把握,良好的读者接受和适境的审美判断。所谓
“文化适应”既不意味着让源语文化去适应译语文化,也不意味着相反,而是文化信息的表现应该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现实和发展所需,最终通过文化翻译使目的语从各方面接触外域文化,吸收其精华,上升为一种更具生命力、更适应新的历史生态条件的新文化。文化适应性问题应该是我们衡量作品质量的价值标准之一。在翻译批评研究中文化适应性应该成为翻译价值观论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这正是翻译效应学孜孜以求的起点和和归宿,也是这一翻译新论的终极价值。
六、结语
从译学研究的本体论角度看,翻译效应学旨在追问和研究异质文化在译语国度传播的全过程,尤其是其传播效应和接受效应,或曰文化适应性。从认识论意义而言,翻译效应学可从中西传统和现当代译学以及哲学思想中获得丰富的滋养和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致谢: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海平教授对此文的宝贵意见及贡献。
[1]刘瑞强.翻译效应视野下的《玩偶之家》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影响[J].昌吉学院学报,2010,(6):73-76.
[2][3]刘瑞强.翻译效应学初探[J].昌吉师专学报,2001,(1):84-88.
[4]刘瑞强.翻译效应学的范畴[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22-225.
[5]http://www.hudong.com/wiki/本体论?hf=youdaocitiao&pf=youdaocitiao
[6]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7]李海平.论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哲学解释学模式[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2):9-12.
[8]文化适应性——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