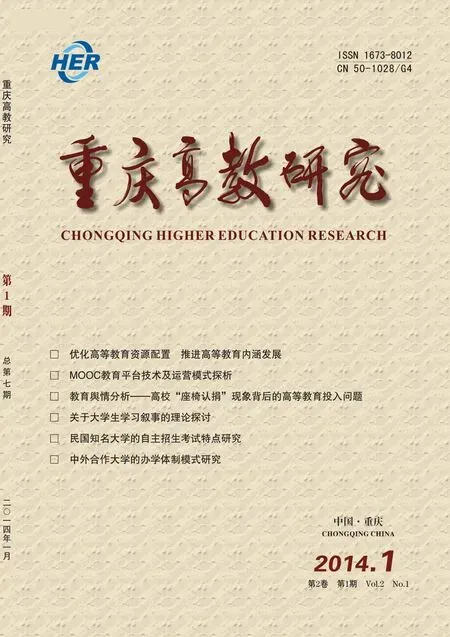民国知名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特点研究
党亭军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大学的招生考试,是大学培养人才的逻辑前提。如果说我们的大学没有能够培养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型人才,那么在诸多的原因之中,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换言之,我们没有能够把握好大学生的入围选拔关,是导致创新性人才难以有效培养的关键之一。而纵观民国时期大学的招生考试,尽管有如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在其最新著作《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中所说“从单独招考到统一招考”的制度改革的历史必然性[1],甚至于还有民国时人丁天骢所批驳的“大学入学考试内容过分偏重检测高中书本知识的记忆程度以及忽视高中三年成绩在录取之中的作用”等诸多弊病[2]。但客观而论,民国知名大学依据自身办学力量和社会需要而开展的招生考试制度探索为大学进行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后备人才保障。此外,考虑到当前国内一些重点大学正在进行自主招生考试改革的现实需要,积极地探索与梳理民国知名大学在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显得尤为迫切。为此,笔者在本文中着重就民国前期南开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学院、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东北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交通大学、岭南大学、广州大学等一些知名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基本特点进行深入的学理探究。
一、自主招考和外部监管的有机结合:促进大学招考制度的不断创新
尽管在民国后期教育部曾通令各大学统一招生,但从民国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各大学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招考权,譬如民国三十七年交通大学工学院举行院务会议决定:建议招生委员会把土木、机械、电机3系新生名额由原来的30名增加为50名[3]。这个例子说明了大学拥有自主决定招生名额的权力。再如,根据民国二十年的《南开大学周刊》记载:“本年招考简章已于4月16日由各院院长会同订定,文学院一年级入学试验中之政治学改为中国历史;理学院一年级之无机化学改为中等化学。”[4]而民国十八年厦门大学则经过评议会通过了关于加考解析几何初步来提高本科入学试验程度的提议。[5]这两个例子则显示了大学具有设置与变更招考科目的自主权。事实上,民国时期知名大学自行成立招生考试委员会来自主处理包括设立考点、招生类型、入学试验方式以及试题设置等诸多招生考试的具体事务问题。
尽管民国前期知名大学具有高度的自主招考权,但是也需要接受必要的备案与审查。而民国教育部的职责之一就恰恰在于此。不仅对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学生作出了基本资格的要求,即“凡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而品行端正者”,而且对大学招考结果还负有查验备案职责,这首先包括对被录取者各种证件的审查与备案,对符合大学录取标准者进行备案,反之,则令取消该生学籍。为此,各大学需要把录取新生名单、新生履历表、高中毕业证书等证件呈交教育部。而教育部则委托学生所在地的教育厅针对性地查验这些毕业证书的真伪。譬如,民国二十三年,私立中国学院发布了教育部对本院学生录取新生资格的审查结果:“二十一年度英文系学生孙惠方所就读中学并未立案,因此该生入学一事‘碍难准予备案’,故而做退学处理;而商学系学生李叔成系私立春晖中学初中部毕业生,证书内所填高级中学之‘高’”字系由‘初’字擦改而成,着即开除学籍,以儆效尤。”[6]此外,民国教育部还需要对大学招考之中的招考简章、入学试题、评阅试卷等进行收缴和审查。民国时期大学与教育部在招生考试方面的这种权限划分,使得民国教育部在负责大学招考总体方针的制定与政策的及时调整以及必要的备案监管的同时,也保障了大学拥有较高程度上的招考自主权力,而这些权力的真实存在使得知名大学在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上具备了必要的逻辑基础。
二、“承认中学”的择优推荐和夏令馆活动的举办:有效地拓展大学优质生源
民国时期知名大学为了拓展优质生源,往往采取主动和中学沟通的策略,具体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举措:一方面是把一些教学质量高的中学作为享有推荐免试生的“承认中学”。譬如,民国十九年,燕京大学把南开大学中学部作为“承认中学”,提出“凡毕业成绩总平均在B等(80分以上),国文、英语、史地、自然科学成绩平均在B(85分以上)者,得由学校保荐升学,凡保荐升学之学生,仅受国文、英文及智力测验三项试验,而该项试验可在本校行之。”[7]这样一来,“承认中学”的不断开辟就成为知名大学解决优质生源拓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民国时期知名大学对于推荐免试生的录取以及“承认中学”的监管也制定了必要的制度。譬如,张亚群教授在研究了厦门大学对各“承认中学”学生申请免试的具体规定后认为:“需要先行选习过厦门大学规定的本科或预科的入学考试科目,并且各科成绩均需要高出该校及格分10分以上,否则需要补考该门课程。然后经过厦门大学中等学校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而对于免试学生进入厦门大学1年后成绩不佳者,则由中等学校审查委员会通知该校,而其保送学生的成绩依旧无起色时,则直接去掉其入学免试的权力。”[8]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大学还往往采用举办夏令馆活动的方式来吸引中学毕业生的注意,以便挑选符合本校录取标准甚至于更为优秀的学生,这样也就成为拓展优质生源的有效途径之一。譬如,民国十年春季岭南大学发布招生规则,其中提出:“有心投考各生,以先入本校夏令馆修业一月为宜,既得一月之练习,考试合格,九月开学时优先收录。”[9]
当然,为了拓展优质生源,民国时期知名大学还积极主动地和各中学进行沟通与交流,这就为开辟“承认中学”或吸引学生参加夏令馆活动做了必要的前期宣传工作。譬如,根据民国十九年的《南开大学周刊》记载:“燕京大学注册部主任梅贻宝先生,于上星期一日来校讲演‘升学问题及燕京大学近况’,听讲者约40余人。闻此外尚有数大学拟不日派人来校讲演,藉资宣传云。”[7]这个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知名大学主动深入各中学进行宣传和拓展优质生源的客观事实。
三、春秋两季招生和多处设点招考:便于招生与人才培养预案的及时调节
民国私立大学往往在年度内的春秋两季都进行招生活动,譬如私立岭南大学在民国二十五年的校历中具体规定:“廿五年的九月七日至九日(星期一至三)为秋季入学试验;廿六年的一月廿八日至卅日(星期四至六)为春季入学试验。”[10]民国时期知名大学春秋两季招生的最大益处在于能够及时地调节招生与人才培养的预案,即按照自身办学力量以及社会现实需求和不断发生的变化来及时地预测和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譬如,民国十九年厦门大学发布招生消息时称:“本学期学生人数特别增多,宿舍余额仅有二三十人之缺。本期结束后,连毕业生毕业及转学他校之缺在内,至多仅有六十名左右缺额。兹闻入学审查委员会议决本学期招高中一二年级及大学插班生约六十名。”[11]鉴于此种情况的严重性,民国二十年厦门大学第三十六次行政会议决定大学部春季入学考试明年暂行停止[12]。此外,春秋两季招生不仅可以缩短中学毕业生的报考时限,而且还可以为一些特别生转为正式生赢得宝贵的时间,譬如,民国二十四年厦门大学文学院特别生提出改为正式生的要求,经过校行政会议议决,提出参加二十四年春季入学试验及格者即可转为正式生的规定[13]。当然,春秋两季招生还可以使得大学在适应社会方面具有更多的自主调节空间,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在于可以促进专业与课程的适时设置或调整。
此外,民国时期知名大学为了方便考生报名与考试,而在各地设立招考点。譬如,民国二十年,广西大学在梧州、柳州、南宁、桂林等地设立报考点[14]。如果说广西大学还只是把报考点设置在本省范围内的话,那么还有一些知名大学为了扩大本校在各地的影响,提出了在全国各地增设考点的招考思路,譬如朱君毅在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本校以设备与人才论,实为全国学府之一,应以教育天下英才为目的,但根据以前报告,本校学生多属福建子弟,充其量,本校之影响,现时只及于长江流域及其南部各省。故本校亟宜设法增加学生名额,使黄河流域之学生,亦不远千里而来,以期教育效力之普遍[15]。为此,厦门大学不仅在本地或本省设立报考点,而且还特意在全国甚至于国外设立多处报考点。譬如在1930年在常设的厦门、上海、福州、新加坡四处报考点外,还增加汕头教育局、小吕宋马尼拉华侨教育会两处报考点。并且在1935年又开辟了广州中山大学作为报考点。不过,为了节约考试成本,厦门大学提出每一考点在不满30人的情况下不作为考点而请报名者改往他处参加入学试验的对策。譬如,在1926年,福州报名处人数不足30人,即不举行入学试验。至于各处是否达到30人而举行考试的条件,学校在考试之前半月统一发函通知各考生[16]。诚然,增设招考点还可以适度增强学生的地域归属感。譬如根据民国十七年的《南开大学周刊》有关增设报考地点的报道:“自今夏起,学校当局拟于华中增设一招考处,以免华中各省学子有向隅之憾。地点定位汉口,想暑假后吾校同学来自湘、鄂、川、滇者,不愁无伴矣。”[17]
四、坚守质量底线和招生类型多样的统一:实现精英教育和尊重学习权力并重的办学理念
民国时期,由于各地中学学年设置、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程度不同而给予大学招考标准所带来的难以统一的难题,使得各大学在录取标准上宽泛不一。同时也因为一些“野鸡大学”的存在,使得大学招考标准问题一再成为时人抨击的热点问题之一。譬如民国二十九年,《东北大学周刊》发布招生消息称:“据可靠消息,下季招生自不成问题。唯以国内学制复杂,程度不齐。此次为慎重起见,严限资格。现在学校当局,正磋商进行计划。大概重量不重质的恶评,此后或可少灭也。”[18]事实上,一些知名大学往往主动恪守精英教育的理念。譬如民国十二年《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蒋梦麟先生的开学词:“今年新生投考的几及三千,学校只取了160余人,外面因为我们取得太少,有许多误会和责难。其实我们取新生,标准为重,不甚拘守定额。不想近年各地中学毕业生能合我们标准的,竟一年少似一年,这是现在教育界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拟以表册报告各地中学,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学生有几分之几不及格,所欠缺的是哪些功课,请他们注意改良。”[19]再如民国三十七年,交通大学在报考的7 479人之中录取了正取生507人和备取生85人,其总共录取率为7.9%[20]。事实上,不但国立大学如此,即便是私立知名大学也往往恪守重质不重量的招考原则。譬如,根据民国二十二年的《厦大周刊》刊载,厦门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从民国十九年秋季到二十二年春季,期间招考6次,共有报考学生884人,最终录取者为546人,其录取比例为61.8%[21]。事实上,民国时期变动不已的时局已经给大学招生带来了生源上的困境,但即便如此,这些知名大学还是选择宁愿多次招生甚至于招录不到足够的学生也不愿降低招录标准。譬如,民国二十五年的私立岭南大学于第一次报考120余人之中仅仅录取64人,其录取率为53.3%。为了录取足够的符合招考标准的学生,私立岭南大学在本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22]。而民国二十一年光华大学分别在7月27日至28日、8月21日至22日、9月7日至8日举行了三次招生考试[23]。当然,对于考试日期,各大学之间也尽可能避免时间上的相互冲突。譬如,1926年南开大学公布暑假后入学考试日期,原定7月19至21三日,但考虑到和南洋大学的考期冲突,故改为7月26至28日[24]。
此外,民国时期知名大学具有招生类型多样化的特点,即不仅招收本科一年级的正式生以及本科二三年级借读生等,而且还考虑到自主招生可能给予一生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从而导致大学难于保障录取名额的问题的客观存在,故而在录取学生名额上,往往采取同时录取正取生和一定名额备取生的应对策略,其中备取生只是在正取生不到校入学报到而导致录取名额不足时才依次递补。此外,民国时期知名大学还招收预科正式生与补习生、本科补习生、旁听生、试读生、借读生、编级生或插班生、特别生、特科生、选修生以及选科生等来尊重与落实学生自主学习的选择权。其中本科或预科补习生是指没有达到入学试验录取标准,但该生总体成绩还可以,只是需要进行某门功课的补习或补考就能够达到录取标准的学生。譬如,民国十六年厦门大学通过两次招考,录取本科补习生黄振英、吴崐仑、黄式厚、王升题、刘渠、钟世宗6人,此6人均需要补习或补考数学。同时录取预科正式生50名,预科补习生13名。并且第一次录取的预科补习生黄培德经过补考数学及格后已经改为正科生[25]。至于编级生是对于从其他大学转学而来的学生需要进行学力甄别以定其去留或所编入年级学生的统称。譬如在民国十八年,东北大学理工学院于春季开学两周后,对于转学而来的学生举行编级试验,最终录取5名[26]。其中特科生是指:“凡有志之士限于职业,不能依常例受课者”,因此,特科生不仅不住宿学校,而且还不需要进行修业课程的考绩,只是其修业课程需要由学校检定。而选科生是指:“高中毕业,或旧制师范毕业或有同等程度者,而志在专攻一种学科或数种相类之学科者。”选科生名单由各院长呈报校行政会议审查核准,其所修业课程须至少在6绩点以上。选科生不住校,并且也不得加入本校学生会[27]。特别生是指在录取的本科与预科正式生中,拟特别选习数科的学生。这需要经过所选习各科主任的特别许可。同时,本校教职员经过该科主任许可,也可以作为特别生。如果特别生要作为正式生,那么必须参加入学试验,譬如1934年12月25日召开第98次行政会议,提出:“各学院特别生请改为正式生,应参与廿四年春季入学试验。”[28]
对于上述所招生的旁听生、试读生以及特别生等诸多“非正式”类型的学生,民国时期知名大学也往往为了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提出学业成绩优秀即可转为正式生的措施。譬如,尽管在民国二十年十月,广西大学教务会议有“旁听生不得改为正式生”的决议[29],但却在同年的十二月,经过教务会议提出:“本期所收特别生,如期考及格,准予改作正式生。”[30]民国二十一年,广西大学又规定:“旁听生成绩优等者可提升为正式生。”[31]再如民国二十六年,私立广州大学在《学生入学规则》第四节提出凡华侨学生具备资格经过本校认可后为特别生,其于第一学年内补受入学试验及格者改为正式生[32]。总之,民国时期知名大学在招生质量底线的坚守和尊重学生学习权力上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和协调,这就为当代知名大学在进行精英教育的同时也尊重学生的学习选择权并重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对于学生自主学习的选择权的忽视一直就是导致当代大学转专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源之一。
五、考试科目设置不同:体现多样化的大学招考特色
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大学在招考之中也尽可能地凸显了各自不同的招考特色,即在考试科目的必考与选考上进行了各自实践探索。譬如,民国八年的北京大学招考简章规定,考试分为两场,第一场试验国文、外国语、数学;第二场试验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理化、博物。并且提出了第一场不及格者不得参加第二场试验的硬性规定[33]。显然国立北京大学意在强调基础学科的重要性。而民国十六年南开大学招考简章中提出考试科目的设置办法为:“文商科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世界历史、政治学、算学二以及选考科目(普通化学、中等物理、普通生物学三科中任选一科);理科的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无机化学、中等物理、算学四。”[34]由此可见,南开大学于该年招考中在文商科中进行了科目选报的探索。对于考试科目设置以及选考自由度较大的当属厦门大学。譬如,厦门大学则在民国十五年实施普通科目的必考与自然科学专业科目的选考制度相结合的试验方案,这就为院系专业自主招考权的落实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探索。因此,厦门大学在民国十九年实施了学校和院系两级试验来综合录取学生的招考方案,即通过学校层面上的必考科目和院系层面上的专业科目的两级试验。规定试验科目为普通必考科目和特别试验科目,即学校层面上进行党义、国文、外国语(英文、法文、德文选一)的普通科目试验,而院系层面上进行各学院的专业科目试验,譬如文学院的特别试验科目为史地、国学常识、算学、自然科学(4选考2);教育学院为史地、教育学概要、心理学大意、自然科学(4选考2);理学院为算学与自然科学。其中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三科,拟入理学院者在上述三科中选考二科,而入其他学院者则仅需要三选一即可[35]。事实上,民国教育部曾以第四二六九号训令发布了《二十三年度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办法》,指出本着以“国家需要”和“教学效率”的精神,“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收新生均须以学系为单位,招考时由学生自行认定之。”[36]笔者认为,这既是对大学录取新生时应当考虑文法商教与理工农医专业的平衡问题,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大学各院系在招考新生时的自主权的实现问题。笔者认为,充分发挥院系在招考新生中的作用是大学自主招考制度改革中的关键。
综上所述,民国知名大学在招生考试制度的实践上进行了诸多改革,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大学的招生考试自主权的实际运用进行了宝贵的历史探索,其中“承认中学”的举措、夏令馆活动、春秋两季招生、招生质量底线的坚守、招生类型多样化、招考科目的特色探索等必有值得当代大学学习与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 张亚群.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2-47.
[2] 丁天骢.论大学入学试[J].广大学生,1947(3):10-11.
[3] 匿名.工学院举行院务会议[J].交大周刊,1948(30):1.
[4] 匿名.招考简章付印[J].南开大学周刊,1931(103):42.
[5] 匿名.评议会记事[J].厦大周刊,1929(203):9.
[6] 匿名.本学院揭示第三十三号[J].中大周刊,1934(47):2.
[7] 匿名.升学佳音[J].南开大学周刊,1930(85):44.
[8] 张亚群.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235.
[9] 匿名.岭南大学简章[J],岭南季刊,1921(1):25.
[10] 匿名.廿五年度校历更正[J],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6(2):18.
[11] 匿名.本学期招生消息[J].厦大周刊,1930(245):9.
[12] 匿名.行政会议第三十六次会议记录[J].厦大周刊,1931(275,276):11.
[13] 匿名.第九十八次行政会议[J].厦大周刊,1934(358):28.
[14] 匿名.校长布告(三)[J].广西大学周刊,1931(4):9.
[15] 朱君毅.本校九周纪念大会演说辞[J],厦大周刊,1930(230):14.
[16] 匿名.招生简章[J].厦大周刊,1926(151):1.
[17] 匿名.报考地点又增一处[J].南开大学周刊,1928(56):23.
[18] 匿名.招生消息[J].东北大学周刊,1930(93):31.
[19] 蒋梦麟.蒋梦麟先生开学词[J].北京大学日刊,1923(1288):2.
[20] 匿名.招生的三个阶段[J].交大周刊,1948(31):4.
[21] 匿名.本年度及三年来报考学生录取学生数[J].厦大周刊,1933(312):58.
[22] 匿名.大学新生人数突增[J].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6(1):3.
[23] 匿名.学校日记[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2(1):26.
[24] 匿名.入学考试改期[J].南大周刊,1926(32):40.
[25] 匿名.本届录取新生一览[J].厦大周刊,1927(171):8.
[26] 匿名.理工学院取定编级生[J].东北大学周刊,1929(68):50.
[27] 匿名.重订选科生规程[J].厦大周刊,1930(234):18.
[28] 匿名.第98次行政会议[J].厦大周刊,1934(358):28.
[29] 匿名.十月三十一日教务会议纪要[J].广西大学周刊,1931(4):9.
[30] 匿名.二次教务会议记[J].广西大学周刊,1931(10):12.
[31] 匿名.本学期旁听生提升正式生[J].广西大学周刊,1932(1):14.
[32] 匿名.学生入学规则[M].私立广州大学概览.私立广州大学印行,1937:93.
[33] 匿名.北京大学招考简章[J].北京大学日刊,1919(360):3.
[34] 匿名.本校招考新生简章[J].南开大学周刊,1928(60):106.
[35] 匿名.厦门大学招生简章[J].厦大周刊,1930(234):22.
[36] 匿名.公牍(教育部第四二六九号训令)[J].国立北平大学校刊,1934(92):2.